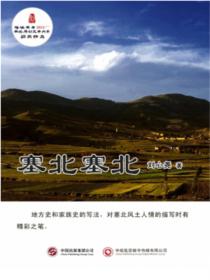32.
卫荞麦老实了几天,就坐不住了。谷三小赶着牲口很少回家,他和他爹吃住基本都在饲养院的饲养房。夜里怕狼叼了羊,就把过去卫大毛砸破的郑家的那口破锅挂到了饲养房门外,有动静的时候就敲那口锅,吓唬狼。
谷三小答应过卫荞麦上山找羊蹄蹄,她还没有忘。可好几天见不到谷三小,她就跑到饲养院去找,谷三小早就赶牲口上山了,还不到晌午,卫荞麦没事干就在饲养院外面溜达。营子里有的人说卫荞麦喜欢三牛倌,没事天天往饲养院跑。有的人不以为然,打死都不信卫荞麦能看上三牛倌。可无论人们信还是不信,反正那天卫荞麦在饲养院外面转悠的一直等到三牛倌赶着牲口回来。
天都擦黑了,卫荞麦等的心焦不耐烦的,所以三牛倌刚把牲口们圈进饲养院,她就问他咋才回来。三牛倌说:“早回来了,我得饮牲口啊。”说话间他爹谷大愣也赶着羊群回来了,羊群里的葛丁紧追着一只绵羊不放,还往它身上趴。卫荞麦不知道咋回事,就说葛丁欺负那只绵羊了。谷三小告诉她说:“羊跑羔呢。”可卫荞麦不懂,就追着那葛丁打,不让它欺负那绵羊。谷大愣说:“荞麦,你别追葛丁,小心它碰倒你。”还没等他的话音落下,卫荞麦已经被葛丁碰倒了,
被葛丁碰倒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躺在地上甭起来,卫荞麦不懂,刚起来就又被碰倒了。葛丁长着粗大的犄角,又肥又壮的,顶一下半天缓不过气来。谷三小紧喊:“荞麦,甭起,甭起。”可她不听,一起又被重重的碰倒了。谷大愣急忙抓住葛丁的犄角,费了半天的劲儿才把它拉走。卫荞麦被碰的灰楚楚的,起来后不顾肚子疼,再次冲进了羊群,要找葛丁算帐。可那葛丁正趴在一只绵羊的背上耷拉着两颗大羊蛋抖屁股呢,卫荞麦上去就是一脚,正好踹到了葛丁的屁股上,可那葛丁屁股抖的更欢了。卫荞麦抬腿又准备踹第二脚,被谷大愣拦住了,“荞麦,快走吧,女孩子家家的,羊跑羔有甚看的。”没想到卫荞麦却抓住了葛丁的蛋,可把谷大愣吓坏了,那要是揪坏了,满群就一头葛丁,正是羊跑羔的时候,去那里找葛丁,等找到葛丁怕羊早跑过羔了,冬天连一个羊羔也甭下了。
卫荞麦揪着葛丁蛋不放,非要把它从母羊身上揪下来。葛丁正在兴头上,趴在母羊屁股上匆匆地抖动着大屁股,卫荞麦就是不让它抖。谷大愣真和它急了,“荞麦,你快撒手,再揪真揪坏了,揪坏了连羊羔也下不了了。”卫荞麦不明白,好奇地问:“为甚下不了了?”谷大愣说:“没有你爹能有你么,你这孩子。”说着要往开掰卫荞麦的手,正赶上葛丁**了。**后马上就从母羊的背上下来了,谷大愣没提防,卫荞麦是不懂,结果弄了两人一人一手,粘糊糊的。
卫荞麦以为是母羊尿了,一惊一乍地叫:“尿了,它尿了。”谷三小笑了,说:“甚尿了,你快擦手吧。”说着让她在羊身上擦手。卫荞麦这才感到了恶心,皱着眉头屏着呼吸把胳膊伸的大老远说:“死羊,死羊。”谷三小说:“谁让你揪葛丁蛋。”“它欺负母羊。”谷三小坏坏地笑,“不欺负咋有羊羔。”卫荞麦不相信他,“那非得欺负啊。”
谷大愣开始催卫荞麦了,“荞麦,你快回吧,天黑了。”说话间葛丁又去追另外一只母羊了,追的满群的跑,一边追还一边叫,还不住地仰起头翻卷着上嘴唇闻来闻去。虽然天已经擦黑了,可卫荞麦还是能看见那只羊群里捣乱的葛丁的。她非让谷三小把它赶出去,拴住,不让它捣乱。谷三小告给她说:“拴住了谁种羊啊。”可卫荞麦就是不明白,“种羊,种羊做甚。”谷大愣火了,“三小,你快别和荞麦瞎咧咧了,赶紧让她回吧。”谷三小把手一摆说:“快回吧,快回吧。”谷大愣开始烧火准备贴锅饼子,火已经生着了。为了方便冬天饮牲口,卫大毛在饲养院南面打了一口井。生着火的谷大愣让儿子去提一斗子水烧开了准备活莜面。
谷三小提着水斗子前脚出了饲养房,后脚卫荞麦就蹦了出去,“我也去,我也去。”说着就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跟着谷三小去提水了。拉风匣烧火的谷大愣却长长地哀叹了一声。
当年的娥子如果和荞麦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她也许就不会被她爹远嫁到后草地了。虽然营子人都说荞麦喜欢谷三小,可谷大愣却明白的很,荞麦永远不会喜欢谷三小。她每天找他耍不过是觉得好玩,因为营子里也只有谷三小能和她耍到一可块去,地主家的闺女别人只有看看的份,而谷三小不过是因为特殊的关系,卫荞麦才愿意接近他和他一起耍的。
在谷大愣的眼里荞麦那孩子太冒失,风风火火的,谷三小的性格一点都没跟了他娘,完全跟了谷大愣,虽然长的人高马大的,却一脚踹不出一个响屁来。甭说荞麦不会相中三小了,就算相中了,将来也和他一样,三小他娘郑三花说了算,他连半点主都做不了。可三小却喜欢荞麦,一举一动看的清清楚楚的,可他再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他还是白的,香头烤火一头热。儿子的眼里只有荞麦,可荞麦的眼里却没有他。
那次荞麦把马缰绳缠到儿子的脖子上,明明知道儿子已经昏过去了,却还在不住地赶着马跑,仿佛他的死活他根本就不在意。那天荞麦掉进小庙庙错一点淹死,儿子却心疼的不知所措的。
水提来的时候,锅底剩的那点水已经开了,谷大愣停了风匣又填了两舀子水。卫荞麦撅着屁股一火铲一火铲地往灶火里填马粪。谷大愣一边往灶火坑坐一边说:“荞麦,你少填点,填多了倒不过嚼。”荞麦非要替谷大愣烧火,不让烧都不行,“大爷,你起开,你起开。”说着拉着谷大愣的胳膊让他起来。谷大愣说:“你这孩子,饲养房灰麻糊楚的,快回家吧,一会你爹又该哇哇的叫你了。”卫荞麦就是不听话,坐在灶火坑的小板凳上“哗嗒哗嗒”地拉着风匣说:“大爷我也想吃贴锅饼。”谷大愣“嘿嘿”地笑,“你这孩子,锅饼子有甚吃头,油没油肉没肉的。”
水还没烧开,卫荞麦就没了耐性,说风匣太沉了,她的胳膊都拉酸了。谷大愣赶紧让谷三小接着烧,莜面他已经瓦好了,就等着水开了。卫荞麦问:“为甚不能用凉水和。”谷大愣说:“凉水和就蒸不熟了。”谷三小硬硬的顶了几风匣,水就开了。谷大愣踩面的时候,卫荞麦担心地叫:“大爷,烫,烫。”可谷大愣却像不怕烫似的,所以卫荞麦也要踩,谷大愣说:“烫啊。”卫荞麦却说:“不怕。”没想到刚踩了一下一块莜面就粘在了手背,那可是滚烫的水和的,所以一下就烫红了。
卫荞麦捂着手背,泪都出来了,谷三小心疼地抓起她的手不住地吹着气,可无论咋吹卫荞麦都感到火辣辣的疼。谷大愣说:“细皮嫩肉的,你看我这老手呢。”卫荞麦就眼泪汪汪地怪他,“大爷,你真坏。”谷大愣“嘿嘿”地笑,“我说烫烫,可你不听。”谷三小埋怨他爹,“爹,你看看把荞麦烫的。”谷大愣反问儿子,“咋,你心疼了。”卫荞麦听出了谷大愣话里带着话,就把嘴一撅道:“大爷,你尽瞎说。”
看着儿子谷三小心疼的那个劲,谷大愣真想给他泼凉水,告给儿子心疼也白心疼,可他不能当着荞麦的面说,所以只好叹息一声说:“没事,明儿就不疼了。”
卫荞麦还没等吃上谷大愣的贴锅饼,她爹卫大毛就在饲养院外面“哇哇”地叫她了,“荞麦,荞麦,赶紧回家,也不怕狼叼了你兔子。”谷大愣听到卫大毛的声音,巴着饲养房的小窗户喊:“大毛,吃了没有,进来吃点吧,贴锅饼。”“吃了大哥,你快吃吧,让荞麦赶紧回家。”谷大愣就开始催卫荞麦,“荞麦快跟你爹一起回吧,一会还得三小送你。”
谷大愣不想人们说闲话,更不想卫大毛说他的闲话,说他想让儿子娶荞麦当老婆,整天把他俩往一块捏,就如当年他和娥子一样,她和他之间是有距离的。如今三小明目张胆的喜欢荞麦,荞麦明明不喜欢他,却要和他耍。可无论三小咋喜欢荞麦,他都是一个放牛的,在荞麦的眼里他就是三牛倌,他放的那些牲口里,没有一头或者一匹是他家的,就如他放的那群羊一样,没有一只羊是他谷大愣的,那都是卫大毛的,是卫大毛的,就是卫荞麦的,因为卫大毛是卫荞麦的爹。就如当年卫大毛的爹卫万一样,无论他谷大愣为卫家做出多少贡献,卫万死的时候都没有给他一亩地。
当年的卫大毛在营子人眼里甚都不会,不会种地,不会锄地,不会割地,不会碾场,可他有个好爹,他爹死后给他留下了那些土地,然后他把它们都租了出去,几年的时间就置了那么多的房,还把两个儿子卫富和卫贵送进了城,跟着先生学习知识。在谷大愣的眼里,卫大毛比他爹能干,不但守住了那几百亩土地,而且还买了那么多的牛马羊。
卫荞麦不走,非要吃了锅饼子走,谷大愣只好说:“大毛,你先回吧,一会让三小送荞麦吧。”谷大愣不明白荞麦为甚吃的那么香,就锅底熘了两个山药片片,擦了点萝卜丝,搁了把大青盐,连个油点点都没有,蒸熟了拌一起倒股蒸饭水。谷大愣和儿子谷三小给卫大毛放牲口,好歹吃喝不愁,还有兄弟二愣,孩子四五个,地是种了不少,可一遇到灾年吃饭都成了问题,虽然卫大毛二哥二嫂的叫,可租子该交还是要交的。
那天卫荞麦又回的晚了,她回家的时候她爹卫大毛正抽旱烟呢。谷三小把她送到门口就回饲养院了,走在路上的时候,谷三小一句话都没说,她也没说。路上她走的快,谷三小就走的快,她走的慢谷三小就走的慢,就不远不近地跟在她身后。
卫荞麦想学骑马,因为营子里谷三小的马骑的最好,可她爹说了以后不许她再骑马,再骑就打断她的腿,所以她想谷三小更不敢教她骑马了。
爹决定从城里搬回卫家营子的时候,她哭过闹过,可她拗不过爹。爹把卫富和卫贵留在了城里,却惟独把她带回了卫家营子,爹怕他被土匪祸害了。城里那么多的女孩子白天连门都不敢出,出去就把脸都抹成花的,可她却不怕那些土匪,不但不怕,反而很羡慕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举着刀端着枪。可卫荞麦不知道那些端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土匪实际都是逃兵,从战场上逃回来的士兵,仗着手里的武器到处杀人放火祸害女女。
那些逃兵都穿脏兮兮的旧军装,可在少女卫荞麦的眼里,他们却是那样的威风,骑着马城西跑到城东,城东跑到城西。当然她爹不知道她为甚不想回卫家营子,为甚不想离开城里。多少乡下有亲戚的女女都躲到乡下了,惟恐躲的慢了被祸害了,卫荞麦却不怕,甚至潜意识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被那些土匪抢了,可至于抢了做甚她也说不清楚。回到卫家营子后,她对那些骑着马的穿着旧军装的逃兵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她不顾爹的反对追着谷三小让他教她骑马,可他却不教他,不但不教她还捣乱。最后她掉进了小庙庙,错一点淹死。可她还是想学骑马,她想有一天回到城里,她要骑在马背上和那些土匪比试比试。
卫荞麦一进门,爹就问她,“喜欢三小甚?”把卫荞麦都问愣怔了,所以她出口就道:“谁喜欢三小了。”“不喜欢咋整天往饲养房钻,臭哄哄的。”爹叹息了一声说:“你要是喜欢三小,爹不反对你。”卫大毛想起了妹妹娥子,爹非要她嫁给大愣,可大愣不娶她,因为她怀了二愣的孩子,可爹又不让她嫁给二愣,最后爹把大着肚子的娥子远嫁到了后草地。那年秋天的时候,他去赶牲口路过一卜树的时候,特意进了营子打听娥子,人们告诉他娥子在爹和大愣离开的第二天就上吊死了,和她一起死的,还有她肚子里即将临产的孩子。
回来后谷大愣问过他,他说娥子死了,血涌了,至于他为甚没说实话,他也说不清楚。娥子是他最亲的人了,爹活着的时候没少和他提起过娥子,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娥子,抓着他的手让他有机会一定去找娥子,可那时娥子已经死了。他不想荞麦也像她姑姑娥子那样,被人说闲话,哪怕她喜欢讨吃的,他也不反对。三小其实挺好的,为人实在。
虽然营子不少人都说三小是他的小子,可卫大毛最清楚,自从他娶了荞麦娘后就再没有去找过三小娘郑三花,所以三小不会是他的种。就是从长相上也看的很清楚,他跟了他爹谷大愣,脚大手大个子大。小宝和小爱虽然和他是一个爹的种,可他总感觉和他们亲不起来,他们和他也很寡,反而他们和谷大愣和谷二愣却很亲。无所谓了,爱亲不亲,想象他这个做哥哥的也够一份了,小宝和小爱他都把他们弄到了城里,有了安定的生活,也算对的起他死去的爹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没能帮爹找到娥子,因为娥子早早的死了。
卫大毛有时候感觉自个活的很累,无论在卫家营子还是在城里,独自守着偌大的家业。虽然在卫家营子有谷大愣和谷二愣,可他们却没有拿他当亲兄弟。
荞麦整天往饲养房钻,小老婆早提醒过他,让他说说荞麦,别没事总往饲养房跑,三小再好就是个放牛的,荞麦迟早是要回城里的,所以她和三小就不是一路上的人。开始卫大毛也没往心里去,可那次荞麦掉小庙庙,三小抱着她哭的那个伤心,他才知道三小是喜欢荞麦的。至于小老婆说回城,他想都没想,其实他就不明白城里有甚好的,兵荒马乱的。
荞麦却告诉他说,她才不会喜欢三小呢,愣头愣脑的。卫大毛就告给荞麦说:“不喜欢就少往饲养房钻。”“为甚?”荞麦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学他爷爷的样子嘴一咧说:“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那么大孩子了,甚都不懂。”
33.
塞北的连阴雨是人们最盼望的,祭神求雨后的日子里,人们就开始盼了,正值小麦坐胎的时节,雨水格外显得重要。
历年祭雨求神都会格外的隆重,女人们大早起来蒸了供献,然后男人们把早已备好的猪头羊头用红漆炕桌抬了,从营子出发了。出发的路上是节奏不紧不慢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一声半声的咳嗽声。那样的场面女人们是不许参加的,女人们只能在家里等自家的男人。四个男人每人抓着一个桌角,穿过芨芨滩,淌过小庙庙龙王庙就到了。依然是那间破旧的小土坯房,依然是那尊丢失了脑袋的泥塑,依然是灰楚楚的泥台。可男人们依然默不作声地依次跪下,烧香磕头,然后是一声紧似一声的呼唤:“龙王爷,给下点雨吧。龙王爷,给下点雨吧。”
多少年了,呼唤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呼唤的意思却从来没有改变过,永远是“给下点雨吧。”似乎已经干旱的很严重了,似乎不敢奢求龙王爷下太多的雨,朴实而充满渴求的声音里多了虔诚多了知足。从不求龙王爷下太多的雨,只求下一点。在那声声的呼唤里透着庄户人的无奈和憨厚。
雨还是在人们的等待中来了。先是薄薄的云遮挡了日头,然后云层渐渐的厚了,日头便彻底的隐没在了云层后。没有了日头的天空在庄户人的眼里是湿的是润的,是承载着希望的。果然零星的雨开始滴答了。大人孩子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道:“下雨了。”
是啊,下雨了。在庄户人看来,命有多重要,雨就有多重要。因为有雨才会长庄稼,长了庄稼才会有粮食,有了粮食才不会饿死。
雨沥沥拉拉地下着,云层翻滚着,在远山的顶端。芨芨滩完全笼罩在了那灰蒙蒙的雾气里,时大时小的雨把塞北的天塞北的地,塞北的庄稼塞北的芨芨彻底的洗涤干净了,却泥泞了牛羊路,泥泞了饲养院,也泥泞了家家户户的院子。
夏天牲口们吃的都是青草,所以屙的都是稀屎,尤其是牛们,冲屁股的稀屎屙的那里都是,然后牲口们一踩过不来过不去的。最臭气熏天的要数猪圈了,猪屎猪尿加上雨水,再垫上土,猪都没个猪样儿了,滚的。
牲口们整天就在芨芨草滩里滚着吃草,雨天也不需要饮,谷大愣就钻在饲养房抽烟,隔段时间披条破麻袋出去看看羊群的动静,谷三小待着没事就滩里搬蘑菇。数伏天赶上连阴雨,正是起蘑菇的时候。谷三小披着一条烂口袋,芨芨棍儿上串了好几串蘑菇。雨下的拉拉的,怕打湿了裤腿子,他挽的很高。
卫荞麦已经好几天没出街门了,院子里泥的过不来过不去的,一不留神就会摔一身泥,所以她不想出去。已经憋好几天了,无聊透顶了,所以就想起谷三小了。她挪到炕沿的时候,她爹卫大毛问她,“去哪啊?”她却说:“这雨下上没完没了了。”“不下雨你吃甚?”卫大毛反问了她一声,她没回答就出了院子。卫大毛的小老婆隔着里屋的门喊:“你披上麻袋,荞麦,你披上麻袋。”开始她以为荞麦是去茅厕,可没想到披着麻袋的荞麦却淌着泥水出了街门。
她前脚出街门,后脚她爹就唉声叹气地道:“又去饲养房了。”小老婆说:“你管她呢,想去就去吧。”
卫荞麦走进饲养房的时候,谷大愣还在抽烟,看到荞麦顶着麻袋进来,他愣怔了一下,愣怔间被烟呛的咳嗽了两声,然后才问:“荞麦,大雨天你来做甚?”“找三小。”卫荞麦大大咧咧地回答。谷大愣告给她三小不在,可她感到特别的纳闷,“不在,大下雨的跑哪儿了?”谷大愣不紧不慢地说:“芨芨滩,搬蘑菇。”卫荞麦唧唧喳喳地问:“在哪儿在哪儿,我也去,我也去。”谷大愣说:“水淋扒拉的去做甚。”“搬蘑菇。”
天灰蒙蒙的,谷大愣瞅了半天才在芨芨滩里瞅见儿子,拿手指给卫荞麦看。卫荞麦好不容易才在密密麻麻的雨丝中看到三小的身影。其实她只能看见一个顶着麻袋在芨芨滩里晃动的人影,根本就看不清楚他的面孔,尤其是风伴着雨,更看不清楚。谷大愣也是凭感觉,感觉那里有个人影就判断是他儿子谷三小。
卫荞麦显得十分的兴奋,就顺着芨芨滩的方向大一步小一步地赶了过去。谷大愣在后面喊:“荞麦,你慢点,小心滑倒。”
没等走到谷三小跟前,卫荞麦就喊上了,“三小,三小。”开始谷三小没听见,只顾着低头找蘑菇了,等他听见的时候,卫荞麦都快到他跟前了。谷三小和他爹谷大愣一样样儿的话,“大下雨的你不在家待着,跑滩里做甚。”卫荞麦似乎并不关心谷三小说甚,她只关心她手里提溜的那两串蘑菇,“哇,你从哪儿找到的,搬这么多。”谷三小不关心他手里提溜的蘑菇,他只关心卫荞麦的裤腿子,急忙把蘑菇放在芨芨草丛里,给卫荞麦往起挽裤腿儿。卫荞麦不知道他要做甚,就往后退,“干甚,你要干甚?”谷三小说:“不挽裤腿儿一会就湿完了。”卫荞麦这才乖乖地让谷三小把两条腿的裤腿儿都挽了起来。
挽起裤腿后,谷三小头一低又开始在草丛中找蘑菇了,卫荞麦跟在他身后,也像模像样地找,找着找着突然激动地冲着前面的谷三小叫:“蘑菇!蘑菇!”谷三小被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笑了,“狗尿苔。”卫荞麦不懂他的意思,就问:“狗尿苔咋了?”“咋了,不能吃。”“咋不能吃?”卫荞麦一脸的茫然。谷三小就说:“狗尿苔是狗尿后长出来的,咋能吃。”卫荞麦似乎懂了似乎又没懂。
谷三小又找到一个蘑菇,指给卫荞麦看。卫荞麦嚷嚷着要她搬,结果搬了个稀巴烂。谷三小埋怨她说:“你真笨,你抓住根根。”卫荞麦就吐了一下舌头。很快卫荞麦就学会咋搬一个完整的蘑菇了,然后还会把蘑菇小心翼翼地串到芨芨草上。雨虽然不大,可天阴沉沉的,而且雨忽大忽小的,风也乱刮,一会东一会西的,虽然卫荞麦披着麻袋,可还是把衣裳湿了。
湿了衣裳的卫荞麦就感觉到了冷,嘴唇就青了,说话都不利索了,哆哆嗦嗦地道:“三小,好冷,快回吧。”可谷三小不明白卫荞麦的意思,就说:“再搬会儿着甚急。”“我衣裳都湿了。”谷三小这才说:“回吧,回吧,你也不知道来做甚。”
俩人并排往饲养院走,营子里不少人走到营子跟前才看清楚芨芨滩搬蘑菇的两个人一个是谷三小,一个是卫荞麦,于是就有人说:“荞麦一个女子家家的,大下雨的搬蘑菇。”其实人们议论来议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卫荞麦跟着谷三小一起搬蘑菇,一个女孩子家家啊,裤腿子挽那么高像甚话。可人们说人们的,卫荞麦才不会在乎。人们爱说甚说甚,想说甚说甚。
进了饲养房卫荞麦鞋都不脱就上了炕,谷大愣问她,“荞麦,搬了多少蘑菇?”卫荞麦冻的直打颤,“搬了两串。”说完又“嘿嘿”一笑道:“都是三小搬的。”
虽然是大夏天,可谷大愣和谷三小爷儿俩得做饭烧火,所以炕特别的热乎,一会的工夫就不冷了,可湿潮的衣裳一遇热,粘在身上更不舒服了。卫荞麦不住地扭动着身体说:“三小,我想把衣裳脱了,难受死了。”谷大愣急了,“三小,快把荞麦送回家换衣服去。”可卫荞麦就是不回去,说烤干了衣裳再回去。谷大愣拦也拦不住,无奈他只好叹息一声躲出了饲养房。
雨下的拉拉的没地方去,只好拐回了家。谷大愣好久都没有回家了,郑三花都觉得新鲜,就问他,“大雨天的咋回来了?”谷大愣无奈地叹息一声说:“荞麦去饲养房了。”“大雨天去做甚?”郑三花纳闷道。谷大愣叹息一声道:“做甚,找三小,做甚。”郑三花就乐了,“你说荞麦是不是真相中咱家三小了?”谷大愣头一歪,眼一翻就把上次在庄稼地荞麦把马缰绳缠在三小脖子上,故意赶马错一点把三小拖死的事告给了郑三花。郑三花叹息一声道:“荞麦这孩子心真毒。”“可不是,小小的孩子。”郑三花开始替儿子担心了,“傻小子,就喜欢荞麦。”谷大愣更担心,担心儿子谷三小迟早被荞麦耍了,所以就对老婆说:“你没事说说三小,让他离荞麦远点,别总和她在一起耍。”
郑三花提议给儿子三小说个媳妇,谷大愣把营子里的女女想了一遍,觉得郑三花四爹家的外甥女改芹不错。郑三花说改芹还小,才十四。谷大愣说:“你去说说,看看人家甚意思。”
就在郑三花和谷大愣替儿子谷三小担心的时候,雨一直在下,丝毫没有晴起来的意思。郑三花问男人,“这回下到了吧?”“下到了,夜来格儿我去滩里瞭羊,拿铲子挖了挖,没挖出干土。”“这回牲口们能吃饱了。”
谷大愣问老婆郑三花,“你说改芹家能要多少彩礼?”郑三花说:“少不了。”谷大愣就说:“多少咱也答应,我慢慢给他,把我新缝的那件白茬皮袄给她爹吧。”“你还没穿呢,那可是大毛用了五张大羊皮给你做的。”谷大愣说:“那有甚办法,娶个媳妇不容易啊。”郑三花说:“那你还喜欢小子。”谷大愣给了她一句,“谁不喜欢小子,没小子咋传宗接代啊。”郑三花顶了他一句,“女子还不用掏彩礼呢。”谷大愣说:“掏,人们也愿意生小子。”
郑三花说等雨停了就去问,谷大愣说等雨停了早了,催她赶紧去,一会都且不得的样子,“快去吧,荞麦还在饲养房呢。”郑三花这才觉得着急了,顶着雨一路小跑就到了姐姐家。姐姐正在纳鞋底儿,见郑三花推门进来特别稀罕地问:“三花,你咋来了?”郑三花说:“没甚事,串个门子。”说着瞟了一眼炕上绣鞋垫的改芹问:“哟,改芹给对象绣鞋垫儿呢。”改芹的脸腾就红了,“大姨,你瞎说甚。”她娘就说:“改芹还小,还没对象呢。”郑三花却说:“也不小了。”说着又问改芹,“改芹,今年十五了十六了?”改芹娘急忙说:“那有啊,孩子才十四了。”郑三花一惊一乍地道:“一点点都不像,高高大大的就像十五六似的。”说完又试探地对改芹说:“大姨给你说个对象吧。”
改芹头都没抬就难为情地道:“大姨,人家还小。”她娘也说:“就是,孩子还小,过几年再说吧。”郑三花却急了,“过几年就晚了,好后生都被说走了。”显然改芹的娘被她说动了心,跟着叹息一声道:“你说也是,现在的人都不知道急甚。小小的懂个甚,就给孩子找人家。”“是啊,一年比一年小,咱们那几年十八九就够小的了,可现在十四五就早早的给孩子找人家了,你不找,等你找的时候就没好人家了。”说着郑三花就提起了她家的三小,“前几年我就张罗着想给三小找个对象,可谷大愣非说不急,现在急了,同年般辈的都嫁人了。”改芹娘拍着郑三花的腿说:“三小有荞麦,你急甚。”
郑三花惆怅地叹息一声道:“快甭提荞麦了,荞麦能看上咱家三小?”说着又叹息一声,“人家可是金凤凰,咱家没那梧桐枝。”改芹娘又拍了一下郑三花的腿说:“我看荞麦对三小挺上心的,走站的跟着,都快好成一个人了。”郑三花啧啧地道:“快甭说了,都快愁死我了,你说说墙上的画儿似的,娶的家里能做甚。”
姐妹俩可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改芹娘也说:“就是,娶媳妇还是娶实实在在过日子的,纸糊的是栓正,可中看不中用。”于是郑三花就抓住时机道:“我看改芹就不错,将来一定是个会过日子的孩子。”改芹娘不经夸,一夸就来劲儿了,“别的不敢说,我家改芹绝对是过日子的孩子,可不像荞麦一朵花似的。”然后改芹娘就问郑三花,“你说荞麦跟了谁?”郑三花就说:“跟了谁,跟了她娘,她娘那时候就瘦马精神儿的,麻杆儿一样,风大了都能把腰吹断了。”
两个女人说了半天,改芹娘才想起来问郑三花准备给改芹说谁家的小子。郑三花就实话实说告给她想把改芹说给她的儿子三小。然后还一本正经地说:“虽然三小他爹这几年给卫大毛放羊吧,可娶媳妇的彩礼早准备好了,改芹过门后保证不会让她受制,三小那孩子,你也是看着他长大的,没心眼,保证疼老婆。”改芹娘半天没支声。郑三花就开始做她的思想工作了,“你放心,定亲后改芹甚都不会缺的,我供养的起。”
其实改芹娘也知道全营子里除了卫大毛家,现在就数谷大愣家日子过的宽裕了,爷儿俩一人放一群牛马,一人放一群羊。虽然谷大愣给卫大毛放羊从没给过他一文工钱,可卫大毛却从没有亏待过他,还有三小,一年光粮食卫大毛给他好几口袋。改芹若是嫁给了三小,一定饿不着也冻不着。
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三小有荞麦,所以改芹娘叹息一声道:“估计我家改芹也没那福分,三小眼里只有荞麦,营子人谁不知道,刚刚雨下的拉拉的俩人还在滩里搬蘑菇。”郑三花急了,说:“荞麦甚都新鲜,甚都没见过,所以才追着三小搬蘑菇的。”
就在郑三花积极的给儿子谷三小说对象的时候,荞麦已经把衣裳脱光了,捂着盖窝让谷三小给她往干了烤衣服,可饲养房铺的是牛毛毡子,谷三小只能把毡子卷起来,把土炕扫干净,才把荞麦的湿衣裳展豁豁地铺在了炕头。铺好后,为了让荞麦的衣裳快点干,谷三小就坐在灶火坑里拉着风匣烧火。卫荞麦已经催他几次了,“别烧了,快上炕吧。”可他就是不听,烧上没完没了了。卫荞麦急了,“甭烧了,你行不行。”谷三小这才住了风匣戳在炕沿底还不上炕。卫荞麦就问他,“你的衣裳没湿了啊?”“湿了。”“湿了还不脱下来烤。”
在卫荞麦的催促下,谷三小把身上湿透的衣裳也脱了下来,然后挨着卫荞麦的衣裳铺在了炕头。卫荞麦说:“赶紧钻被窝吧,戳着干甚。”谷三小就听话地钻进了卫荞麦的被窝。卫荞麦说:“我身上可凉了,你摸捞摸捞。”
谷三小就听话地摸捞了卫荞麦,然后说:“是很凉。”
卫荞麦莫名其妙地问谷三小,“母羊为甚乖乖的让葛丁欺负。”谷三小说:“舒服。”“咋欺负的,还舒服。”
那之后,谷三小就扮演葛丁一步步地欺负了卫荞麦,事后卫荞麦说:“三小,你胡说,一点都不舒服,疼。”
34.
改芹娘答应了这门亲事,改芹始终低着头没吭声,算是默许了。
郑三花出了姐姐家的门觉得特别的高兴,没留神错一点跌了一跤。一进自个家门就对炕上躺着的谷大愣说:“准备彩礼吧。”谷大愣腾地就从炕上起来了,“咋,答应了?”“答应了,改芹娘说了,择个日子先把亲订了,等改芹大大再过门。”谷大愣惆怅地道:“那还得再供养几年,一年到头吃啊穿啊少不了。”郑三花却说:“怕甚,你放着一群羊怕甚。”谷大愣说:“一群羊又不是你的。”“那也不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之后谷大愣让郑三花猜测下改芹家会要多少彩礼。郑三花说:“王宝家的孙女刚订婚,彩礼是两口袋小麦,两块牛毛毡。”谷大愣说:“这几年一垄地都没种,咱吃的还将够,去那淘换两口袋小麦。”郑三花却一点也不愁,“找三小他二爹先借两口袋。”谷大愣眉头一皱,“你说的轻巧,好几年了干的都不下雨,他那有小麦,今年的子种还是大毛借给他的。”郑三花撇撇嘴,“你咋知道没有,那几年年成好没少打粮,咋能都吃完呢。”谷大愣火了,“没吃完,还和大毛借啊!”
郑三花觉得谷大愣太愣,而且她保证二愣家绝对有粮食,如果不信,让他去碰碰。谷大愣坚持说:“碰也白碰,三四个孩子都等着吃呢,去那儿有那么多粮食。”谷大愣还说:“开春我还看见他二娘挖野菜吃呢,有粮她还挖甚野菜。”郑三花恼了,“你不去老娘去。”说着跳下炕要去谷二愣家。谷大愣无奈地道:“就算有,他家的小子也该娶媳妇了,他不跟你借就不赖了。”郑三花这才突然想起,二愣家的大小子比她的儿子三小还大一岁多了,可不也到了找媳妇的年龄。一个营子里住着,没听说订了谁家的女子。
郑三花犯了难,“那咋办?”谷大愣说:“不行我先跟大毛借两口袋,就顶半年的工钱。”卫大毛让谷大愣给他放羊从来没给过他工钱,可每年剪羊毛的时候多给他留肚底毛和腿毛。而且这几年家里的烧柴就没缺过,冬夏无常烧着大块的羊砖子。一只羊剪个一两多毛,一百多只也剪个十几斤,擀一块炕毡绰绰有余了。可郑三花死活不让他和卫大毛张嘴,“你少给我和他张嘴借,老娘就是讨吃也不和他借。”
有时候郑三花想不明白谷大愣和谷二愣兄弟俩,他们的女人都被卫大毛透过,他们应该恨他才对,应该杀了他才对,可他们却和没事人似的。郑三花对卫大毛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他是个薄情的男人,娶了荞麦娘后就连个照面都不打了。她承认她没有荞麦娘栓正,没有荞麦娘年轻,可毕竟他从几岁就开始摸捞她了,十几岁他就透了她。所以郑三花的心里,她是恨卫大毛的。她从那么小就给他摸捞,可到最后他却碰都不再碰她一下。
郑三花不知道小莲是咋想的,卫大毛把小莲带回来,自打进家们就脱光了她的衣裳,白天黑夜地想听曲就听曲,想摸捞就摸捞,想透就透,可说不要一会都不且,冷冬寒天地撵的小莲没处去,最后是她和大愣说服了二愣才收留了她。所以郑三花觉得小莲也应该是恨卫大毛的。
营子里不少人私下议论说三小是卫大毛的种,郑三花真想把嚼舌的人嘴撕了,眼瞎了,明明三小长的和他爹谷大愣一模一样。上了年岁的郑三花有事没事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想卫大毛在他家羊圈里脱她的裤子,她乖乖的就让他脱了,想着想着她的脸就开始热了。更多的郑三花想刚和谷大愣成家的时候,入洞房那夜,她没出血,谷大愣猩红着眼问他血呢血呢,她竟然理直气壮地说:“谷大愣,是老娘娶的你,不是你娶的老娘,你管老娘血呢。”那一刻郑三花觉得是那么的骄傲和自豪,她的血给了卫大毛。
刚成家那几年她咋看谷大愣都没有卫大毛顺眼,咋看谷大愣都觉得自个委屈。她爷爷为了他们郑家的香火能续上,把谷大愣招进她家做了她的上门女婿,可他爷爷有那么多的孙女,为甚偏偏是她。刚成家那几年,她和谷大愣三天两头的打架,白天不给他做饭,夜里不让他碰,熬煎的他也不轻。那几年谷大愣脸上的伤基本上就没好过,每天都被她挠。
可自从卫大毛娶了荞麦娘后,郑三花就变了个人,赌气似的对谷大愣好。好着好着就觉得谷大愣才是她的男人,无论卫大毛曾经对她多好过,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可郑三花最反对他有甚没甚都爱和卫大毛借,觉得他没有骨气。所以谷大愣提出和卫大毛借小麦,郑三花又火了,“我小子打光棍,我也不和他借。”
最后郑三花望着窗户缝外面的雨说:“我给改芹娘说说,小麦咱秋后给,先把毡子给她。”谷大愣只好说:“那你看行不行。”“咋不行,迟早欠不下她的。”
就在三小娘和三小爹为他的亲事犯愁的时候,三小又欺负了荞麦一次。第一次后俩人搂着在被窝里热乎乎的直冒汗。搂着搂着三小就说:“荞麦,我还想欺负你。”荞麦说:“疼,不让你欺负。”三小就亲了荞麦一下说:“你看人家母羊多听话,等着让葛丁欺负。”荞麦就抓了三小的手说:“那你欺负吧。”
虽然隐隐的有一丝疼,可比起第一次却不那么疼了,不但不疼了还有一种让荞麦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所以之后荞麦抱着三小说:“愿不母养让公羊欺负呢。”“舒服吧。”“舒服。”
俩人又继续躺着,可躺着躺着荞麦就说:“三小,你再欺负我一次吧。”然后她就像母羊一样乖乖地等着三小趴在她身上欺负她,于是三小就又欺负了荞麦一次。之后三小又亲了荞麦一下说:“荞麦,做我媳妇吧。”荞麦想了想却摇头了。三小急了问:“为甚,荞麦,为甚?”荞麦淡淡地道:“不为甚。”谷三小更急了,“荞麦,你都给我欺负了。”“欺负了又能咋。”卫荞麦还是不紧不慢地道。谷三小急的直揪自个的头发,“荞麦,你咋这样,你咋这样。”荞麦打了个哈欠,“三小,我想睡觉。”
谷大愣回到饲养房的时候,卫荞麦和谷三小还搂抱在一起睡的正香,或许是炕热的缘故,两人都没盖被子,荞麦光溜溜地躺着,谷大愣急忙闭眼还是甚都看清了,臊的谷大愣大气都没敢出就退出了饲养房,然后轻轻的把门带上,出了饲养院才大口大口喘气。谷大愣愁的都不知道该咋办了,这要是让改芹知道了,这门亲事就算完了。不能让改芹知道更不能让营子里任何一个人知道,知道了就会传出去。思前想后,谷大愣把头顶上的麻袋往墙上一搭站在饲养院的墙外扯开嗓门喊:“三小,三小,牲口都跑庄稼地了,你也不去撵。”
谷三小听到爹喊他,说牲口都跑庄稼地里了,光着屁股就跳下了地,牙着饲养房的门朝外看。谷大愣假装甚都没看见,惊讶地问儿子,“大白天,你脱甚衣裳,还不赶紧穿,牲口都跑庄稼地里了。”谷三小这才急忙上炕,让荞麦赶紧穿衣裳,说他爹回来了。荞麦一点都不着急。“我还想睡。”谷三小就说:“回家睡吧,一会我爹进来了。”荞麦说:“进来吧,怕甚。”好半天谷三小才哄着荞麦穿好衣裳。
等谷大愣进去的时候,他假装甚都没发生问荞麦,“荞麦,你咋还没回家,雨下的啦啦的。”荞麦却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大爷,我的衣裳才烤干。”说着又打了个哈欠。
谷三小已经去撵牲口了,谷大愣赶紧说:“荞麦,快回吧,披上麻袋。”荞麦这才慢悠悠地披上麻袋走了。可她前脚走后脚谷三小就顶着雨跑回来了,一进饲养房就埋怨他爹道:“爹,你尽瞎说,牲口那跑庄稼地了。”谷大愣明知故问,“啊,没跑吗?我站饲养院里瞭,还以为跑庄稼地了。”说完又说:“以后别和荞麦耍了,你娘给你说改芹了。”“我不要!”谷三小想都没想就说。谷大愣愣怔了一下,“为甚不要?”“我要荞麦。”谷三小说的特别的坚决。谷大愣却笑了,“你要荞麦,那荞麦要你吗?”谷三小回答不上来,吭哧了半天说:“她都让我欺负了。”谷大愣叹息一声,说了一句和荞麦一样的话,“欺负了又能咋。”
荞麦走后,谷大愣瞅了一眼儿子和荞麦刚刚睡过的褥子,就明白了,荞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儿子谷三小却不懂。就如当年他和他娘圆房时一样,他娘没见红。他娘把第一次甚至无数次给了卫大毛,他娘跟他的时候,已经成了个烂货。
谷大愣进郑家门的当天,他娘塞给他一块白布,告给他夜里睡觉时铺到媳妇郑三花的屁股下面。谷大愣不懂问娘为甚,娘说:“傻小子,三花要是黄花大闺女会见红的。”谷大愣从来不知道黄花大闺女第一次会见红,但他知道甚是黄花大闺女。所以他只一眼就明白,荞麦已经不是黄花大闺女了,所以他才对儿子说:“欺负了又能咋。”
谷大愣那时没有办法,他喜欢娥子,可二愣也喜欢娥子,并且二愣和娥子好了,还把肚子好大了。所以娥子爹卫万让他娶娥子,他说甚都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娘怕他打了光棍,让他给郑家做了上门女婿,他才娶了烂货郑三花。可如今他的儿子谷三小娶个老婆容易的很,所以他是不会同意儿子再娶个烂货回家的。谷大愣觉得,只要儿子离荞麦远远的,营子里的女女拿鞭子赶都赶不完,他放着一群羊,一年剪十几斤羊毛,儿子放着一群牛马,从不愁吃粮。
儿子谷三小有股愣劲儿,所以谷大愣不敢和他来硬的,就往他娘郑三花那里推,“你和你娘去说吧。”三小最怕他娘郑三花了,所以他爹让他去找他娘去说,他就没脾气了,只好和他爹嘟囔说:“反正我不要改芹。”他爹叹息一声道:“爹是没意见,只要你娘同意就好,她已经给你说下了。”谷三小犯难了,问都不问用,他都知道他娘是不会同意的。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嗡嗡他爹,“爹,你和我娘说说,我要荞麦。”谷大愣反问儿子,“你觉得你娘会听你爹的吗?”谷三小茫然地摇摇头道:“反正我就是不要改芹。”“跟你娘说去啊,跟老子说管球用。”谷大愣火了,“荞麦有甚好的。”“改芹有甚好的?”谷三小反问他爹。
谷大愣还真想不出改芹和荞麦比起来有甚好的,想来想去就觉得改芹是黄花大闺女,荞麦已经烂了,可他又不能和儿子说,就直戳戳地道:“反正改芹就是比荞麦好。”
让谷大愣感到庆幸的是,荞麦给儿子谷三小在饲养房里欺负了的事营子里只有他知道。不然的话改芹娘是绝对不会再答应这门亲事的。老婆郑三花还在为儿子和改芹的亲事犯愁,愁去那里弄两口袋小麦去,可儿子在饲养房却把荞麦给欺负了。谷大愣不知道这事如果让荞麦的爹卫大毛知道了会咋样,会不会逼三小娶了荞麦。到那时就怕他不答应也得答应,谁让三小欺负了人家荞麦呢。如果他不答应,那么卫大毛一定会不让他再放羊了,也不让三小放牲口了,这样改芹给不给三小就难说了。
谷大愣惆怅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时又没准主意,只好顶着雨急匆匆地赶回了家。郑三花正为彩礼犯愁呢,见谷大愣又回来了,就问他,“你咋又回来了?”谷大愣急的直冒火,“你那王八蛋儿子不要改芹。”“你跟他说了?”“说了。”“那要谁?”郑三花纳了闷了。谷大愣叹息道:“王八蛋中邪了,非要荞麦。”郑三花“啪啪”地拍着炕沿,“不行,不行,你把那王八蛋给我叫回来。”谷大愣嘟囔了一句,“不回来。”郑三花风风火火地要去饲养房找儿子,被谷大愣拦住了,“荞麦让三小欺负了。”“荞麦喜欢三小了?”郑三花疑惑地问。谷大愣叹息道:“谁知道,可荞麦不是闺女了。”“你咋知道?”郑三花瞪着他问。谷大愣只好说:“我看他们睡过的褥子了。”
郑三花立刻来了情绪,说甚也不能让儿子找个烂货。或许郑三花忘记了自个那时也是个烂货,或许她不但没有忘记,反而记得很牢,总之她是铁了心不让儿子娶荞麦那个烂货的。郑三花在家里吵吵成一团了,非要去找饲养房找儿子。谷大愣拦都拦不住,只好吓唬她说:“你吵吵吧,吵吵的全营子人都知道了,看改芹还给三小不。”郑三花耷拉着脸吼,“你去,你去给我把那王八蛋叫回来。”
谷大愣没有想到老婆知道荞麦不是闺女后反应会这么强烈,她给他的时候也不是闺女了,却没有这样反应强烈过,反儿理直气壮的告给他。可如今轮到儿子了,她却坚决不让儿子要荞麦。谷大愣说:“你赶天黑了再去找他吧。”
郑三花没事很少到饲养房去,所以谷大愣让她天黑了再去,以免人们看见起疑心。本来彩礼的事她就够麻烦的了,三小又把荞麦欺负了,更麻烦了。郑三花提心吊胆地问:“大毛知道不?”谷大愣摇摇头说:“不知道。”“要是让大毛知道了会咋?”谷大愣反问老婆,“要是你闺女被欺负了,你会咋?”郑三花说:“我没闺女。”谷大愣得去滩里赶羊了,临走又安顿郑三花天黑透了再去饲养房,郑三花已经焦头烂额了,不耐烦地道:“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你!”
谷大愣赶回羊群的时候,谷三小也把牲口们都赶回饲养院了。雨还在拉拉的下,顶着麻袋的谷三小问谷大愣,“爹,羊够不够?”谷大愣说:“够了。”爷俩这才把羊往圈里赶,一边赶谷大愣一边和儿子嘟囔道:“夜来格儿黑夜有动静。”“狼进营子了?”谷三小吃惊地问他爹。谷大愣说:“这几天夜里得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