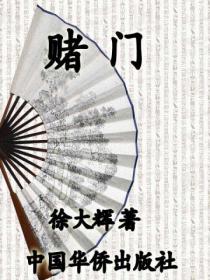昨夜,独坐在山洞前的童志林想一个人——和天上的月亮一样的物体,遥远的夜晚,第一次见到她,浑身哆嗦。
“你怎么啦?冷吗?”
“不是冷的,是激动……”
山里最炎热季节,他的表现打哆嗦并不是冷的。童志林不是没见过女人,那块石头跟他一起生活多年,女人**的事冷漠俨然是一块石头。前妻到死也没主动一次,像是这种事见不得人,极其隐秘地做。
皮肤很白的女人书一样打开在面前。
“你不是没见过女人吧?”
童志林何止见过女人,跟已故妻子有了儿子。但是,一本合着和打开的书不一样,而且是它自己打开,往下只剩下愉快阅读,对他来说又是激动地阅读。
读书在山间的小屋里,太吸引人的缘故,他差不多彻夜苦读……窗玻璃发红,阅读才告一段落。
“你行!”女人评价道。
男人欢迎这个评价。他用跟昨天不一样的眼神望着她,说:“见了你,我都要疯啦。”
“唔,驼疯。”
公骆驼**称驼疯,一向温顺的动物,至少在人的面前是这样,它谁都不认,如果你妨碍它恋爱,将撕碎你。
“谁见了你……”
“不,没谁,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她纠正道。
童志林不相信,她的表现怎么都像过来人,他说:“你看上去很懂,懂。”
“是啊,懂得早,十几岁就懂。”白娘子承认懂,却没说详细怎么懂,长长叹息一声,难以启齿的事她永远不会说。耳濡目染这种事是在她少女时代,目睹的是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他们并非完全因为**,一室的房子无法背着,她和两个成熟动物之间隔一块毛布(造纸毛布,又称造纸毛毯。造纸机上使用的毛毯。按照在造纸机上的部位可分为湿毯、上毯和干毯。湿毯在造纸机上带水运转,作用是压榨纸坯使之脱水和纸面平滑。),它只挡视线并不隔音。有了这块遮羞布,他们尽情地放肆。
十二岁的女孩上床便睡,每晚隔壁操作的事情她不知道。落雨的夜晚,急骤的雨点敲打窗户将她惊醒,隔壁的像下雨的事情,乌云一样向一起堆积,一场大雨将要降临。
“上来吧,都让你弄湿……”女人渴望的声音。
“等一会儿,她没睡实。”
“你真坑人啊!”女人埋怨道。
女孩什么也没听懂,但是没立即睡,是雨点喧哗不让她睡。
“你上来,停下你的爪子!”女人愤怒的声音。
“开尅!”男人的声音。本地人把开战、开弄什么的称为开尅,有时也当开始讲。
女孩朝毛巾被子里缩缩,她搞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不是打架吧?继母走到这个家,他们有时吵架,继母总是先喝口水,润嗓子使声音洪亮,而后敲搪瓷缸子,抑扬顿挫地骂……今晚会不会敲缸子骂人啊?
平常她“哧溜”吸缸子里的水,喝翻开(沸腾)的茶水避免烫,嘴唇到缸沿拉开距离,将水吸到口中称为吹,故有吹茶水一说。生活中这么个细节足以使一个少女哆嗦。继母吹的过后是一场交恶,骂人的语言听来叫人脸红,只一个字(字典上以前没有这个字,现在收录了,字头字母是B)。少女还是听懂这个字的。
“哧溜”始终未出现,声音还是有,发出的声音跟水有关系,搅水、激水……像踩在稀泥中的声音。继母像似生病,发出的声音很难受。少女以后的日子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慢慢搞懂是她十五六岁……她说的懂指此。
“十几岁?够早的。”童志林喟然道。
“什么?”
“你懂……”
白娘子委屈了,觉得遭到误解。童志林是她第一个男人这可以肯定,但不是处女地的第一个犁者。锋利的犁铧恰恰是她自己。在此涉及一个女人的隐私,不便公开。她说:“你看看床单。”
童志林见到花朵在浅黄色的织物上绽放。
“我是你的,永远是你的。”她说,声音像清晨阳光一样柔和,“你需要一盏灯。”
“白炽灯。”养蛙人没在林蛙身上学到任何东西,恋爱季节的蛙表现很出色,求偶需要歌唱。古人韩愈诗: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莫道盆池作不成,藕稍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水盆子里养青蛙在三江孩子是很普遍的经历。童志林饲养的严格意义上说属于蛙类,并不是常见的青蛙。天上掉下来一只青蛙,皮肤颜色另类一些,白娘子在那个夏天成为童志林的一只蛙、一盏灯。
几百万元的蛙场一夜间易主,就剩下一只——她,不久也跳走,跟众蛙不同的是她没偷偷,明确说“走啦”才走的。
七年没灯照亮他的生命很黑暗,比他蜗居的山洞黑暗,壳似的山洞一天之中还有太阳照射进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几乎是黑屏七年。最初的日子更是黑暗,他整日不见人,跟岩石说话,夏天有自然界的其他生灵来访,到底是探访神秘的山洞,还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几十万只林蛙离开自己,生命顿然失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行走壳儿,再没其他内容。
下山去进城,他选择的时间多在没人注意到他的时刻,到的地方以前几乎没有到过,看到了所有陌生的面孔他心才安定。遇到白娘子——以前的一盏灯,他绝没想到灯还是主动照射,他接受了灯光,黑暗中有了一缕光明,像似从某个极其窄的缝儿挤进来的那种。饥不择食,黑不择明吧,他渴望这种光亮。灯突然问到他住在哪里,这一问,他如一只动物看到猎人的枪口,仓然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