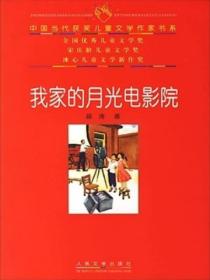第十七章 打开天窗(一)
单单与鸟蛋
小烟出现以前,单单就指望有一天她能从天窗飞出去。但单单是一枚躺在鸟窝里的鸟蛋,飞翔的梦被坚硬的蛋壳包裹着,这个蛋壳就是轮椅。
单单用拇指和食指量过了,天窗的尺寸足够她通过的。对于那个窗子,她不过是一片单薄的叶子。后来,小烟带着她飞出去时果然非常顺利。单单是个痩女孩。
单单家的红顶小楼是一座孤单的小楼,年纪比爷爷和奶奶还老,他们走了以后它归爸爸妈妈和她。后来妈妈也走了,它就只属于她和爸爸了。
妈妈走了以后它一下子变大了,空****的大。单单平时是不常出去的,也很长时间没去芍药居地铁站了。前几天单单发现一个秘密,是这样的:地铁站旁边挂着一个特别大的广告牌。那是个奇怪的牌子,上面画着一条通往林间的小路,不管单单站在哪个角度,路口都是朝向自己的。这是单单的独家发现。单单想过,要是真的走进去,它一定是可以走通的。单单亲眼看见一只灰色的麻雀从路口飞进去,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却飞出两只,多了一只黑色的。黑雀可能被城市的声响吓坏了,直接飞向天空。灰雀跟上去,安慰她的新朋友去了。
“去地铁站看看。”单单对爸爸说。爸爸没反对,就推着轮椅向芍药居走去。爸爸知道女儿喜欢那里的广告牌,却不明白为什么喜欢。那个牌子很普通啊,一个公益广告而已:建设森林家园。
走出院子,身后传来一声鸟叫。单单回头,却没有看见鸟,那个鸟窝安静地挂在屋檐下面,鸟在楼脊的另一侧呢。“不去啦,就等等鸟吧。”单单不想去地铁站了,反正那条小路不会走失的,也不必担心第二个人能发现它的秘密。
借这个片刻,爸爸给女友打电话了。女友在桃花苑邮局工作。他一直想约她来看看这幢红顶小楼,还有红顶小楼里的女儿。他早就想娶她了,她却一直犹豫,现在总算愿意嫁给他了,却又担心单单的态度。女友的电话占线,爸爸马上放弃了约她来的念头。单单还不能接受妈妈以外的女人,这是一定的。
……这就是单单的生活,一枚草窝里的鸟蛋。秋天来了,阳光洒在窗外的草坪上,草坪一天天枯黄了,单单就想那是阳光烤的吧;一转眼春天来了,阳光洒在草坪上,草坪却一天比一天绿了起来……单单的心放了下来;不久,来了两只蝴蝶,在草坪上舞上舞下。单单又不安心了:它们的双翅又薄又轻,阳光把它们晒成两团火焰怎么办?整整一天过去,两只蝴蝶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什么事也没发生。
伙伴们
壁虎比小烟早来一步。
壁虎出现时,单单吓得全身发抖。单单担心这个鬼东西会为难她。他浑身没毛,很像外星来的家伙。他要是顺着轮椅的架子爬上来,她只有捂着脸惨叫了,没有别的可做。
壁虎没有为难单单。他也注意到单单了。他抬头盯了单单一眼,伸出前爪挠了挠脸。他的脸有点痒,早上起来还没洗脸呢。壁虎挠脸的动作把单单逗乐了。单单一笑,便轮到壁虎紧张了。他哧溜朝墙角跑去,一转眼不见了。第一次,壁虎在单单的视线里只存在了这么几秒钟。就这样,单单多了一个不好看的伙伴,他住在一个潮湿的角落里,时常经过单单的卧室去别的地方办事。也从未邀请单单去他家做客。壁虎那边想,我的小地方容不下那个贵客的。单单这边想,的确如此啊。
后来的某一天,壁虎从单单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也没跟单单打招呼。单单想起他时,只剩下他那副谨慎敏感的样子。
红顶小楼里一直是寂静的。小蜘蛛攀着细丝从天而降、蚊子从这窗飞到那窗、棉布娃的笑、壁虎的奔跑……都没有声息的。有一天,单单决定开口说话,跟她的伙伴们说话。单单一开口说话,却成了一个唠叨的女孩。这个健谈的小女孩在轮椅上不能有大动作,她不动声色地问伙伴们的身世和来历。
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但都沉默着。说了也听不懂嘛!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比如那把老胳膊老腿的老木椅,从前是一棵树,来自北方一片森林。他和无数同伴站在一道山岭上,像标本一样静立。轻易不说什么,有风经过的时候,彼此相连的伙伴才抖动枝叶相互摩挲,把一些话传向伙伴。相互不挨着的想通话便需要使者了——在林子里散步,不是可以看见鸟吗?本来在一根细枝上蹲着,好好的,也没有谁去招惹他,蹲着蹲着便飞走了,飞到别的枝上去了。莫名其妙吧?其实,这只鸟多半是给这树与那树传递问候呢!
有一天伐木者来了,他们从森林的边缘干起。老木椅战战兢兢地等待他们向自己推进。
这一天果然来到了,他被一副电锯割断,叶子震落下来,纷纷落在身边伙伴的身上。他被加工成了木板。他赶紧关闭所有知觉,不声不响,亲眼看着自己被拼成一把椅子。从一根笔直的树,变成这么一个驼背的古怪东西,他郁闷了很长时间。后来(其实是许多年前)单单的爷爷把他买进了这座红顶小楼,成了一件家具……又过了很久,单单出生了……
老木椅平时蹲在房子东南一角,好些年没人坐他了。有一年半时间,他上面放了一摞书。后来那摞书去了别处,那摞书悻悻地嘟囔着,总算离开这鬼地方了。老木椅其实恋恋不舍的。那段时间,他与那摞书之间互相解闷,老木椅时常不屑一顾地问一难道一本书的价值非要用厚度体现吗?这句话老木椅重复了无数遍。沉甸甸的家伙走了,数不清的灰尘接二连三地光顾这里,让老木椅觉得自己还有点用途。
老木椅的经历他自己一清二楚,单单无法知道。老木椅最痛苦的事情是从一天晚上开始的。他的某个部位生了蛀虫,这小家伙的尖牙在那地方蛀了个洞。更过分的是,这小家伙打算在这里修建新居。
老木椅彻夜难眠,就因为小家伙弄痒他了。老木椅并不知道,生了蛀虫,有比痒还麻烦的事情。
天窗。小伞兵发现天窗,是小蜘蛛帮忙。
假如生了一对翅膀,小蜘蛛能当天使吧。这个假设成立了一他攀着一根细丝从天而降。细丝通常是看不见的,只见他什么都不借助就落下来,像一个莽撞的伞兵,离舱时忘了背上降落伞。
小蜘蛛在天窗上结网来着,不小心从天窗上掉下来的,幸亏有安全带。安全带飞速地从肚子里抽出来,弄得肚皮很痒很痒。小蜘蛛紧张地下降,几秒钟后终于停下来。
小蜘蛛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双惊奇的眼睛,眼睛绝对的够大。而这双大眼睛看见的是一个不带伞的小伞兵,单单和小蜘蛛就认识了。
这是一些好玩事情的开端。
单单和小蜘蛛认识的时候互相没打招呼。两人都呆了,人一呆就忘记礼貌了。有点趟她的是小蜘蛛,他贸然闯入这个陌生的房间十分不适应。还有,他面前这双眼睛大得有点夸张。小蜘蛛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回去。然后憋了一口气,攀住细丝飞快地往回爬。他爬得太用力了,轻飘的身子在半空中悠**起来。单单怕鼻尖碰着小伞兵,往后闪了闪,目光却追随他向上移去。
小伞兵回到天窗前就消失了。他毕竟太小了,空气轻易就吞没了他的小身子。
小伞兵不见了,天窗出现了。看见天窗,单单的身子不由得往上挺了一下。假如她的双腿有知觉她一定要跳起来的。
天窗平时是不开的,这么多年他只开过一次。那时,爸爸还是个小孩子,单单还没有出生,爸爸玩火柴,不小心点燃了被子。火势不大,奶奶用一盆水扑灭了,但烟迟迟不散,爸爸仰着一张黑脸看着奶奶,不知该怎么办,爸爸正经历一个比天大的灾难。奶奶把爷爷喊回来,请他爬上天窗,打开它,烟从那个小窗口飘出去。爸爸也是第一次发现头顶有个天窗,他的功能是把烟放出去,此外他还能干什么,爸爸就不知道了。
妈妈
单单再一次开口说话,她对所有的伙伴说:“我有个发现!”可是所有的伙伴都没把单单的发现当回事。老木椅是红顶小楼里的老居民了,他跟这天窗有几十年的交情了。棉布娃呢,只要她躺在**,对面就是这个天窗。
单单还不知道应该管那个四个角的“小房子”叫什么。爸爸告诉女儿,这个东西叫天窗,用来通气透光的,许多年前打开过一回,用它排掉房间里的烟……爸爸一边做晚饭,一边讲了他小时候干的那件光彩事情。讲着讲着话题与天窗越来越远,可单单那时只对天窗有兴趣。
熄灯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整个红顶小楼都淹没在黑夜里。天窗收集了许多遥远的星光,就像一盏灯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它的光芒是均匀散开的,均匀散开的光芒不刺眼,照在脸上能想起妈妈温和的抚摩。
单单出神地望着如灯的天窗。
天窗是有变化的。有一会儿,它是一扇屏幕,在上面是空矿深远的蓝色星空。蓝色星空也是流动的,不久,成了一条起伏不定、草木茂盛的山谷……单单着迷了,小心地喘息着,怕多余的声音吓坏楼顶那个胆小的放映员。某个地方坐着一个放映员,瘦瘦的,是个男孩,不太干净,不干净吧却也不讨厌。单单就这样在心里认定了这样的事实。
另一个景象让单单完全屏住了呼吸一妈妈在屏幕上出现了!
妈妈的样子有点模糊,忧心忡忡地想跟单单说什么。可是屏幕就定在这里,不肯让妈妈动一下,妈妈的话最终也没有说出来。单单想起来了,这是妈妈临走时的表情啊!妈妈究竟想跟自己说什么呢?这期间单单已经设想了一千句话,可是没有得到妈妈本人的确认啊。
眼泪悄悄地流下来。眼泪流经的地方痒痒的,单单都不敢用手挠一下。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打断屏幕上的画面啊。
单单流泪,棉布娃看得一清二楚。她不明白身边的女孩为什么又流泪。棉布娃告诉老木椅,单单又不高兴了。本来,今天她发现了天窗,挺高兴的。现在究竟为什么呢?棉布娃想跟大家议论一下。
老木椅的话有点道理:“我们冷落她了。”棉布娃说:“那可怎么办啊,我现在对她好点吧。现在对她好点不算晚吧?”
棉布娃这样打算着,一边向单单身边靠了靠,想挨她近些。她努力了却没办到,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天窗,心里不停地想着:对她好点,对她好点吧我这个无情的小东西!
“妈妈”是单单眨眼的瞬间消失的。眼睛太累了,忍不住了。单单特别后悔眨了眼睛。
仍旧是原来的天窗,一盏不太明亮的温和的灯。不,只是相当于一盏灯,它不过是一扇普通的天窗。
“妈妈,您还是走了……”单单侧过脸去,眼泪渗在枕巾里面。
棉布娃对老木椅说:“假如我是她妈妈多好啊!”老木椅说话就是不客气:“你太小啦!她肯定嫌你小。你太不切实际了。”
棉布娃轻轻叹了口气。她不明白,太小怎么就不能当妈妈,难道妈妈一定要比女儿大?
老木椅说:“叹气有什么用。你一个小孩子,别像我们大人,动不动就叹气!”
棉布娃不想再跟老木椅对话了。这个老头子有时候喜欢教训人。反正,自己已经决定给单单当妈妈了。老木椅又不是爸爸,他顶多是一个邻居,自己家的事用不着他同意。
空白的天窗
天窗上的景象没再出现。
单单试过无数次,每次都特别虔诚。她小心翼翼,并努力培养那天的心境,可是一次次都失败了。天窗就是天窗,连那个冒冒失失的小伞兵也没再来过。是不是小伞兵不肯再来的缘故呢?是小伞兵先出现,然后才是妈妈,小伞兵不出现妈妈就不肯出现吗?就是这么回事。单单便期盼小伞兵再次从天而降。可爱的小伞兵,快来吧,把妈妈带来……单单爱上了那只小蜘蛛。
夜里盯住天窗看,白天打瞌睡。窗外,一群孩子由老师领着,坐在草坪上玩丢手帕的游戏。单单知道,那是芍药居学前班的孩子们。几个月前,爸爸把单单送到那里。那是一个童话城堡一样的院子,孩子们在那里为正式上学做准备。爸爸推着单单穿过城堡,还有“卫兵”跟她打招呼呢,单单一下就喜欢上了那地方。三天后单单却不肯去了,老师也表示为难。三天里,单单坐在轮椅里一句话也不肯说。原因非常简单,单单发现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他们跑来跑去的,而她只有傻坐在角落的份儿。结果是单单远离了其他伙伴,其他伙伴也远离了单单,就像互相不太喜欢似的。既然彼此不喜欢最好不在一起,单单主动选择了走开。一个人走开总比更多人走开方便些嘛。
爸爸知道单单的坚决,没有勉强女儿。第四天单单又回到了小楼。
单单失眠,爸爸也失眠。
单单把爸爸喊到自己的房间。今天晚上她想跟爸爸谈谈。单单说:“妈妈要是知道会怎么样呢?我都八岁了,还没去学前班呢,我着急了。”
爸爸说:“爸爸要让你自己走着去上学。你能站起来。”单单叹了口气:“那天我看见妈妈了,她在那里。”单单指了指天窗。
爸爸心里痛了一下:“我也梦见过她。”
“不是做梦,她真的来过。”单单刚要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说给爸爸听,可是爸爸不想听了。没办法,爸爸是个固执的男人,对固执的男人,也不能太较真儿。不说也罢,这个天窗不过是一个单调的洞,像从前一样。单单都不愿意再看到它了。
本来多好的一件事啊封闭的红顶小楼上,突然发现头顶多了一盏灯,照亮了房间;它还是一个屏幕,放映了新鲜的东西,有最想念的人……好好的,都要指望它生活了,它偏偏又告诉你那些都是假的、虚幻的。
单单轻易不肯再抬头了。她尽量避免这个动作。这样,老木椅啦,桌子啦,棉布娃啦又回到她的视野里。
老木椅说:“欢迎你回来,年轻人。记住,天上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实实在在的。”
棉布娃问:“天上都有什么事情?”棉布娃反倒对天上的事情十分有兴趣。
老木椅不耐烦地告诉这个孩子:“天上的事情多了,让我从哪说起?说云彩吗,他飘来飘去的,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有时候是一匹马,老老实实待在那儿,过一会儿成了一只鸟,飞了。哎,天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您就是见多识广,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知道正常,你原来不是在商店里吗?我呢,从一片大森林里来的,非常大的地方。这就是我与你的区别。”
棉布娃不说话了,又有点想念商店里的伙伴们了。不知他们还在不在了,是不是都被人买走了。与他们分开很长时间了。
老木椅也没有了说话的兴趣,原因是他的身体又开始发痒。那个蛀虫又开始工作了。他已经把老木椅的腿蛀了一个不大的洞,他的目标是把这里搞得宽敞些,在这里住下来。他一边艰难地前进,一边用后腿把木屑推出去。雪白的木屑从老木椅的腿上飘落下来,撒在地板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老木椅不知道他的身体正在下雪,只是觉得痒极了。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变成别人的别墅。他知道很多事情,却忽略了这件最重要的事情。
天太小啦
小烟的出现是一个意外。之前小烟在什么地方,单单并不知道。星期天,爸爸去郊区拜访一位老中医,为治单单的病探探路子,留单单一个人在家。爸爸带女儿去过不少医院看过不少医生,往往是白白让单单挨累,他们多半是让单单和爸爸等待奇迹,这个诊断爸爸也很满足。这次他是想知道奇迹究竟要多久才可能发生。他答应单单的妈妈了,既然女儿活了下来,就要让女儿幸福地活着。
单单老老实实坐在轮椅里,打算就这样睡过去打发这一天。有一阵她想到了广告牌上的林间小路,想到它的方向一直朝着她。是在暗示她什么吗?那么它究竟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单单一下子兴奋起来,努力把轮椅摇到了第一道门槛。单单试了几次后放弃了,又回到出发前的位置。老木椅对棉布娃说:“乖乖回来是明智的。”棉布娃拖着长长的声音说:“我,希望她成功……我听见外面有一种声音,特别好听。”
老木椅说:“没见识。那是鸟的鸣叫,从前在我的老家听得多了。天底下至少有125种鸟叫,知道吗?”
棉布娃有点害羞:“我什么都知道。我喜欢听鸟叫。他们要是经常叫就好了。”
“你知道刚才他说的是什么?”
棉布娃当然说不知道。这个回答老木椅早就料到了,但他要亲耳听见她说不知道。棉布娃怕老木椅扫兴,就说她非常想知道。其实他就是喜欢那声音的本身,让人的耳朵特别舒服,至于是什么意思一点都不重要。老木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清清嗓子,告诉她鸟叫的含义。原来,他们说的话一点都不复杂,其中一个说天好小啊,另一个也说天好小啊。反复说而已。单单也听见了鸟鸣。
老木椅说:“他们说的话也是单单心里要说的话。”棉布娃同意老木椅的推断。
有一会儿,鸟鸣来到了头顶,他们大概是落在了天窗上面。单单抬头看着天窗,呆呆地望着听着,入迷了。老木椅叹了口气:“是啊,天太小啦。”棉布娃小声问:“天究竟有多小呢?我还没见过天呢!”老木椅说:“你没见过的东西多啦。以后我慢慢告诉你,现在听他们说,他们说天太小了。”
他的脏脸
红顶小楼里所有的居民都痴迷鸟鸣的时候,天窗上面突然安静下来。鸟的叫声远了,很快便断了声息。
单单过了片刻才清醒过来:是什么惊动了鸟,让他们飞走的呢?
单单看着天窗,琢磨着鸟飞走的缘故。她喜欢上他们了。为什么她喜欢的东西都转眼即逝,留不下来呢?
天窗上传来另一种声音:哧哧,哧“一哧。这声音不好听,单单没有兴趣,她留恋刚才的鸟鸣。单单低下头来,才感觉脖子都酸了,是该换一个姿势了。可是天窗上面的声音却响个没完了。单单有点不耐烦了,连老木椅和棉布娃也有点受不住了。老木椅甚至还联想到铁锯的来回拉动,所以都不寒而栗了。许多年前,他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给加工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单单终于忍受不了了。单单喊道:“谁在那儿?走开!”马上,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从上面落下来:“我还没完呢。”老木椅小声告诉棉布娃,来了一个淘气包。棉布娃不明白“淘气包”是什么东西。老木椅就敷衍说:“一种常见的男孩子。”棉布娃对老木椅的解释很满意,然后等着听这个“常见的男孩子”还要说什么。
“你在那里干什么,没人叫你来。”“我不用请,半个月来一回,这回赶在白天了。我见过你睡觉的样子,像趴在六号楼顶上睡觉的猫。”
单单嘿嘿笑出了声,因为天窗上面的那个男孩子的比喻。被他比喻成猫,她愿意接受。
男孩子也嘿嘿笑着,停止了工作。“哎,你在上面究竟干什么呢?”“我有名字,叫我小烟吧。”“嘻,小烟,你怎么上去的?”
“别提了,你家的天窗落了鸟粪,我刷洗上面的鸟粪呢。这群家伙到处给我添麻烦。”
天窗上面又开始哧哧响了起来。“他们哪去啦?”单单捂住耳朵。
“不知道,见我飞来了他俩就飞走了。他们飞得真快,不然我饶不了他们。”
自称小烟的男孩说到这里,老木椅跟棉布娃议论上了。老木椅说话时无所顾忌,他和棉布娃的交谈是发不出声音的,别人听不见。
老木椅说:“听见没有,这孩子说的什么话?飞来的,他怎么飞?我用力帮他想办法都想不出。”
棉布娃还小,应和着:“对啊,他怎么飞……难道这可能吗?”
老木椅说:“怎么可能!”天窗上面的响声马上停止了。“嘿,你这根老木头,你一辈子坐在一个地方,怎么能看见我飞。你爬到楼顶来,让你亲眼看我是怎么飞的!听好了,我不是你说的‘常见的男孩子’。”小烟不高兴了。他的意思是,他会飞,谁要是怀疑这件事他要生气的。
老木椅没话说了,他没打算惹这个男孩子不高兴。红顶小楼他爬不上去,只能先沉默着。棉布娃替老木椅难堪:“你怎么办呢……”
单单感到很奇怪:“小烟,你跟谁说话呢?是我爸爸回来了?”
小烟说:“跟你家的老木椅说话呢,他有点轻视我。你相信我是飞来的吧?”
单单现在对老木椅更有兴趣,就一边说相信相信,一边转过头去盯着老木椅。
“就是一把椅子啊,听说跟我家的小楼年纪差不多。”单单看着天窗,对小烟说。
“你忽略这老头啦。他是个讲故事的老手,把你的棉布娃讲得整夜整夜失眠。”
老木椅得意地说:“这评价还算公道。”棉布娃却觉得这说法有点夸张,说:“故事确实好听,可我睡得也很好啊。”
小烟说:“你明明是睁开眼睛的,我看得一清二楚。”
棉布娃说:“我要是坐着睡觉,眼睛闭不上的。我一定是坐着睡的。”
单单觉得受到冷落:“小烟!你在跟我说话吗?你说的我不懂!”
小烟告诉单单,又有一个棉布娃加入进来了。单单看了看棉布娃,她在**老老实实坐着,看上去一言不发的样子。单单觉得非常奇妙,一下子感受到了小楼里的活跃气息。她一直是搂着这个小东西睡的。“我听不见他们的话。”单单告诉小烟,她想加入他们的交谈,大家一起谈更有意思。老木椅和棉布娃也有同样的心愿。
小烟说:“我能帮忙。除了会刷天窗,别的事我也擅长呢。”小烟掀开天窗,把头伸进来。人们看到的是一张不太干净的脸和两只格外明亮的眼睛。小烟知道自己的脸对不起“观众”,解释说,脸色跟工作有关系,他整天给人家洗刷天窗,脸色应该这样。单单还真不讨厌那张脸,反倒觉得有点可爱呢。单单说:“一定帮我们啊,你能行,对不对?”小烟说:“那还用怀疑吗?”小烟沉默了片刻,又说:“让我试试……”听口气信心不大,说完小烟把头缩回去,天窗上面没有了动静。单单、棉布娃、老木椅互相呆呆地看着,也不交流,只等着小烟来帮忙。单单期待着一个好结果,以后她就不必一个人闷在小楼里了,她和他们就要能通话了。
小烟的手段
过了一会儿,上面还是没动静。
棉布娃有点急了,问老木椅:“他去了哪里呢?”老木椅不客气地说:“他这是在吹牛吧?胡吹一气,牛跑了他也跑了。我还怀疑他会不会飞,他不像个诚实的孩子。”
这时小烟偏偏回来了,现在赶回来对他的声誉来说很重要。天窗上面一有动静,老木椅马上闭嘴了,只等着看他的手段。与老木椅不同,单单和棉布娃对小烟还是有点信心。天窗打开,一束光线射进来,接着进来的是小烟的脑袋。“有办法啦!”小烟很得意。
“快说,我该怎么办?”单单把身体从轮椅上欠起来。“那你说说看。”老木椅对小烟保留着怀疑。棉布娃瞪太眼睛看着小烟,她开始准备跟单单说的第一句话了。”
“各位,平静一下,别让心里太乱,一定要做到。”单单、棉布娃表示做到了。老木椅也只好乖乖地做。得给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嘛。
“好了,把一只手放在胸口,真诚地想着对方。一定照我说的做。”
单单马上按照小烟说的做了。
老木椅却扑哧一下笑了,“我没有手,也没有胸口。怎么办?”
棉布娃小声说:“我有手,也有胸口,可是我动不了。”小烟看了看下面的情形,支吾着:“我姨姥可没说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对了,你俩就想象吧,想象着把手放在胸口。”老木椅决定陪这个咋咋呼呼的男孩子练下去,然后想象着枝条被森林里的风吹动,然后抚在树干上面。很快,一股湿热的暖意开始在枯干的躯体里流动。这样的感觉很久没体验了,很好。棉布娃一刻也没耽搁,想象着僵硬的胳膊弯曲过来,双手放在胸口……
小烟说:“做得很好。现在说一句话试试,应该行的。”棉布娃马上把预备好的话对单单说了:“单单,我想做你的妈妈,你要是同意就管我叫妈妈。”
老木椅提醒棉布娃:“喂,小东西,这想法可不成熟啊。”单单居然听懂了他俩的话,非常兴奋,不过单单尴尬极了:“你太小了,我做你的妈妈还差不多。”
小烟看见下面已经开始交谈,心里说:“姨姥,您真伟大。”然后缩回头去继续刷这扇天窗。他要干完的时候,下面的交谈还在进行呢,主要是单单与棉布娃之间。
“假如你做我的妈妈,我可以对你好点吗?”这是棉布娃说给单单听的。
“当然可以。”单单回答。单单和棉布娃不但忘记了小烟的存在,连老木椅都被忽略了。单单轻轻握着棉布娃的手。刚刚能够交流,她反而不习惯抱着她了。
“那你做我的临时妈妈吧,我做你的临时女儿。我就是想对你好点,你太寂寞了。”
棉布娃面对单单,双眼亮晶晶的。单单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棉布娃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临时妈妈!嘻嘻!”“我的小心肝!”―做了临时妈妈,棉布娃做了临时女儿,两人都非常满意。老木椅向她俩祝贺,祝贺她俩交流成功,祝贺她俩成了“亲人”。棉布娃赶紧把老木椅介绍给单单。大家在一起相处很久了,现在却像新朋友见面似的,互相问候了一番。单单问老木椅,平时爸爸总是把一大堆衣服放在他上面,他是不是特别不舒服。老木椅说这样的事情早已经习惯了。应该感谢一下小烟了。老木椅朝天窗说:“你确实有点手段。”天窗上面是安静的。不知什么时候,小烟已经离开了。老木椅相信,他是飞走的,飞走的。
新生活
没有及时道谢,小烟是生气才离开的。单单和棉布娃这样估计,所以特别愧疚。老木椅却说那男孩子不像小心眼的家伙。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当面致谢呢?他好像说过可能要半个月才来一次。想到这儿,单单和棉布娃一人叹了一口气,半个月太漫长啦。老木椅却说:“急什么,该来的时候自然就来了。从现在开始,忘掉他。”
从现在开始,忘掉他,是个好办法。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情呢。单单觉得她的新生活开始了,老木椅和棉布娃也这样认为的。接着,单单的轮椅在客厅里转来转去,很快,她找齐了花布头、剪刀、针和线。她要给自己的女儿缝制一套新衣服。整个中午,单单都在忙这件事,还要不时地问这样女儿喜欢不、那样女儿喜欢不。棉布娃不客气地说出自己的爱好。
最后,棉布娃高兴地接受了临时妈妈的礼物。单单帮助女儿穿上新衣服,还照镜子给她看。
“里面的人是我?”棉布娃第一次面对镜子,有点不知所措。
“不是你是谁呢?”单单把镜子挪近了些。棉布娃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样子,激动地说:“我太漂亮啦!”
本来老木椅一直沉默着,他对过家家一类的事情没有兴趣。现在忍不住说话了:“你就别臭美了。这样的赞美最好出自别人。”
棉布娃赶紧闭上了嘴巴。
三个人一齐笑起来。单单第一次笑得这样开心。爸爸的脚步在院子里响起的时候,热烈的交谈仍在进行。单单打算在三个人的世界里把爸爸加进来,用小烟的手段。棉布娃不反对,但是老木椅坚决不同意。原来,他一点也不喜欢单单的爸爸,这个男主人总是习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他身上;还有,这个男主人小时候是个淘气的家伙,经常在他身上又蹦又跳,弄得他腰酸背痛。老主人生前可从来不这么干,老主人真正把他当做伙伴,轻轻地坐,还轻轻地为他按摩,隔一两天时间女主人还为他清洁身上的灰尘。
“我反对!”老木椅的态度非常坚决。“要是我妈妈在,她可以加人吗?”单单想到了妈妈。“那还用说!自从她不在了,我身上的灰尘从来没人给认真打扫过,她和你奶奶一样好。可惜她们都不在了。”老木椅叹了口气。
红顶小楼里的气氛一下子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棉布娃都不适应了,不时地眨着眼睛。爸爸进来时单单正在打扫老木椅身上的灰尘。爸爸说:“甭管他了,过几天我们买新的吧。”老木椅大声说:“都听见了吧,他是这样对待我的!”单单拍拍他,轻轻说:“没事,我不会让他得逞的。”爸爸问:“你在跟谁说话?跟我吗?”单单转向爸爸:“买新的我不同意!我就要这把老木椅,他是爷爷买的,留个纪念吧。”
爸爸想了想,不做声了。老木椅向单单致谢,棉布娃也跟着高兴,她也不想少了这个老伙伴啊。
奇迹是一个名词
夜里,单单突然小声问了老木椅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名词解释”的问题。当时棉布娃蜷在单单的胸口睡着了,梦话里不时叫着“妈妈”。单单把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搂得紧紧的,直到她完全睡踏实才跟老木椅打招呼。
“嘿,睡了吗?”单单故作随便地打着招呼。其实单单在心里已经把他当做爷爷了,就因为他是爷爷买来的,又跟爷爷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她还打算让爸爸也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他呢。
“哪里睡得着啊。身上有个地方特别痒,我猜是一个牙齿尖利的坏家伙干的好事。”老木椅说着轻轻呻吟了一下。
“明天我帮您看看。只能等明天了,行吗?”单单现在真的无能为力。
“你大概帮不上我。我还在森林里的时候好像听邻居说起过,可能是蛀虫,一种特别小的东西,成不了气候,不必在乎它。明天你帮我挠挠就行了,”老木椅接着说,“呀,现在好多了,它不敢动我了。可见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
见老木椅没事,单单问:“那我想问问,奇迹是什么意思?”老木椅想都没想,回答说:“奇迹是一个名词,是指不经常发生的事情。别相信奇迹。我离开森林以后,一直指望发生奇迹再回到森林里当一棵树,可我一直是一把椅子。这两年,我都快要忘记森林的样子啦!”
老木椅的口气起初像一位教师,后来变得悲观起来。之后,听不见单单的反应。老木椅问是不是他的解释有不对的地方。单单开始抽泣:“不,您解释得对极了。也就是说,我差不多得在轮椅上坐到老了,坐到像您一样老!”老木椅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后悔极了。“这个这个……我解释的也不一定对,我没有文化,就是你爷爷读书时我顺便跟着学了点东西。你能站起来,一定能。对啦,我可完全记起来了,奇迹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我老了记忆力不行了。”
单单问:“这回不能再错了?”
老木椅赶紧说:“错不了,我敢打保票的。”
单单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棉布娃又说梦话了:“妈妈,您在哪儿?”
单单马上说:“妈妈在这呢。”
老木椅说:“她提到的是另一个人啊,别忘了,她管你叫临时妈妈。”
老木椅的话不见得好听,但说的往往是实情。单单也承认,棉布娃梦里提到的是另外一个人。
老木椅告诉单单,棉布娃一直想见到自己的妈妈。单单便抱紧了这个小家伙。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