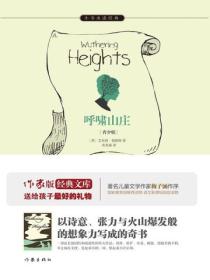第三十二章 几个月后
一八○二年。这年九月,一位北方的朋友邀我去他们那儿的原野旅行。在我去他住地的旅途中,不期来到了离吉默屯不到十五英里的地方。在一家路边客店里,一个店伙计正提着一桶水来给我喂马,这时,一辆满载刚收割的碧绿燕麦的马车从旁边驶过,那店伙计说:
“你是从吉默屯来的吧。嘿!他们那儿总是比别处迟三个星期才开始收割。”
“吉默屯?”我重复了一声,我对自己在那儿的居留,记忆中已经变得模糊,如同梦幻了,“哦,那地方我知道!离这儿有多远?”
“翻过这些小山,大约还有十四英里吧,路可不好走啊。”他回答说。
我突然产生了要去画眉田庄的想法。这时还不到中午,我想,我可以到我自己租的房子里去过夜,反正这跟住客店也差不多。而且,我还可以很方便地腾出一天时间,跟我那位房东把事情了结掉,省得以后麻烦,又要去打扰这位邻居。
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吩咐仆人去问清了到那个村子的走法。这段路我们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把我们的牲口都累坏了。
我让仆人留在吉默屯,独自一人沿山谷走去。灰色的教堂看上去更加灰暗了,那凄凉的教堂墓地也显得更加凄凉。
我在日落前到达了画眉田庄,敲门要求进去。可是我从厨房烟囱里袅袅升起的一缕青烟判断,这家人都到后院去了,所以没能听到我的敲门声。
我骑马进了院子。门廊下面坐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正在编织。一个老妇人靠在台阶上,悠闲地抽着烟斗。
“丁恩太太在里面吗?”我问那老妇。
“丁恩太太?不在!”她回答说,“她不住在这儿,她住到山庄去啦。”
“这么说,你是管家了?”我又问。
“对,我管这个家。”她答道。
“好吧,我是洛克伍德先生,这宅子的房客。不知道这儿有没有房间可以给我住。我想今晚在这儿过一夜。”
“房客!”她惊叫起来,“哟,谁想到你会来呀?你该先捎句话来啊!这儿没一块地方是干净的,什么也没有啊!”
她扔下烟斗就往屋里奔,那小姑娘跟着她,我也进了屋。我立刻就看到她说的是事实,而且,我这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的到来,都把她给急得昏了头了。
我叫她不用慌张——我打算先出去走一走。在这段时间里,她得在起居室里收拾出一个角落来,好让我吃晚饭,另外再整理出一间卧室,供我睡觉。用不着扫地掸灰,只要生一炉旺火,铺上干净的床单就行了。
她看来很乐意尽力去办,尽管她还是错把炉帚当成火钳捅进了炉栅,还用错了其他几样工具。我顾自走了出来,相信她一定能为我收拾好一个休息的地方,等我回来。
呼啸山庄是我外出的目的地。
我没有翻越院门,也不用敲门——门一推就开了。这真是一大改进!我心里想。借助鼻子的帮助,我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事:从那片普通的果树林中,飘来了一阵紫罗兰和桂竹香的芬芳。
门和窗都敞开着,不过正像煤区人家常见的那样,壁炉的炉火烧得通红,一眼看去就给人一种舒适感,那过多的热量也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呼啸山庄的正屋很大,屋里的人有足够的空间来躲避这种热量的影响,因此他们一个个都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占了位置。还没进屋门,我就看到了他们,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于是我就这样看着,听着,这完全是受好奇心和妒忌心的驱使,而且当我待在那儿时,这种混合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强烈。
“相——反!”一个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说,“这已经是第三遍了,你这个蠢货!我可不想再教你了——记住,要不我要扯你头发了!”
“好吧,相反,”另一个声音回答说,低沉而柔和,“现在,该亲我一下了,瞧我学得多好。”
“不行,先得把这正确的念一遍,一个错误也不许有。”
那个说话的男人开始念起来。他是个年轻人,穿着体面,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本书。他那俊美的脸庞高兴得容光焕发,他的目光老是不安分地从书页溜到搁在他肩头那只白皙的小手上,可是小手的主人一发现他不专心,就在他脸上轻拍一下来提醒他。
小手的主人就站在他身后,当她俯身指点他学习时,她那轻柔闪亮的鬈发,有时就跟他那棕色的头发缠在一起了。而她那张脸——幸好他看不见她的脸,要不,他就绝不可能这样安心学习了——我能看到。我不由自主地咬住了嘴唇,后悔自己丢掉了本该拥有的机会,现在只落得站在一旁,对这个迷人的美人干瞪眼了。
课业完成了,并不是没有出错,可是学生还是要求奖励,结果至少获得了五个吻。当然,他也慷慨地用吻作了回报。后来,他们来到了门口。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他们打算出去,到原野上去散步。我心里想,要是这会儿我这个不幸的人出现在哈里顿·恩肖的面前,他哪怕嘴里不说,心里也会诅咒我下到地狱最底下一层的!我觉得自己非常自卑而且不祥,于是便想绕道溜进厨房避一避。
那里也是门户大开,进出无阻。我的老朋友内莉·丁恩正坐在门口做针线,嘴里还唱着歌。
丁恩太太正想再唱起来,这时我来到了她跟前。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跳起身来喊道:
“哦,老天保佑你,洛克伍德先生!你怎么会想到回这儿来的?画眉田庄的东西全都收起来了,你应该给我们通知一声的啊!”
“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暂时住一下,”我回答说,“明天我又要走了。你怎么搬到这儿来住了,丁恩太太?告诉我。”
“你去伦敦不久,齐拉就走了,希思克利夫先生希望我先来这儿住,直到你回来。哎,请进来呀!你今晚是从吉默屯来吗?”
“从田庄来,”我回答,“趁他们在那边给我收拾房间,我来跟你家主人把事情了结一下,因为我想我以后不会再有机会抽时间来了。”
“什么事情呀,先生?”内莉说,把我引进正屋,“这会儿他出去了,一时恐怕不会回来呢。”
“关于房租的事。”我回答说。
“哦!那你得跟希思克利夫太太谈,”她说,“要不就跟我谈吧。她还没学会怎样处理她的事务呢。我先代她办着,没有别的人。”
我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哦!我看你还没有听说希思克利夫的死讯吧!”她接着说。
“希思克利夫死了?”我大为吃惊,叫了起来,“多久了?”
“三个月了。还是先坐下吧,把帽子给我,我会告诉你一切的。等一等,你还没吃过东西吧,吃了吗?”
“我什么也不要,我已经吩咐田庄给我准备晚饭了。你也坐下来吧。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死啊!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吧。你说他们一时不会回来——是说那两个年轻人吗?”
“可不——他们闲逛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我每天晚上都不得不责备他们,可他们对我的责备毫不在乎。你至少得喝一杯我们家的陈年麦芽酒吧。这酒会对你有好处的。你看来有点累了。”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她就忙着去取酒了。这时我听到约瑟夫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勾引野男人,这还不是件很不要脸的丑事吗?还到主人的地窖里拿酒!人家坐着看看都觉得害臊呢。”
她没有停下来应嘴,不一会儿又进来了,端来满满一银杯酒,我对那酒着实大大夸奖了一番。随后,她就继续给我讲了希思克利夫后来的事。如她所说的那样,他的结局还真有点“离奇”呢。
你离开我们后还不到两星期,我就被招来呼啸山庄。为了凯茜,我满心喜欢地服从了。
我一眼看到她时,我真是既震惊又难过!自从我们分手以后,她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希思克利夫先生并没有解释他改变主意召我来这儿的原因,他只对我说他需要我来,他一看到凯茜就心烦,我得把那间小客厅当作我的起居室,让她跟我在一起。哪怕他每天不得不见她一两次,他也都觉得够多了。
她似乎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很高兴,我又逐渐地偷偷搬来一大批书,以及她在田庄时喜欢的其他一些东西。我自以为往后我们总可以较为舒坦地过日子了。
我倒不在乎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拌嘴,可是当主人要独自一人待在正屋里时,哈里顿也就只好跑到厨房里来了。虽然开始时她一见他来就离开,或者是一声不响地帮我做家务,既不跟他说话,也不议论他——他呢,也总是绷着脸,尽可能默不作声——可是过不多久,她的态度就有了改变,变得让他不得安宁了。她对着他大发议论,批评他笨拙懒惰;还说她觉得奇怪,他怎么能忍受自己过的这种生活——怎么能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死盯着炉火,或者是打瞌睡。
“我知道我在厨房里时,哈里顿为什么总不说话。”有一次她大声说道,“他是怕我笑话他。艾伦,你看是不是?有一回他开始自学读书,我笑了他,他就把自己的书给烧了,再也不学了。他还不是个傻瓜吗?”
“也是不是你太淘气了?”我说,“回答我。”
“也许是吧,”她接着说,“不过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蠢。哈里顿,要是我现在给你一本书,你会要吗?我来试试!”
她把她正在看的一本书放到他手上,可是他把它扔到一旁,嘴里还咕哝说,要是她再来纠缠他,他就要拧断她的脖子。
“好吧,那我就放在这儿,”她说,“放在桌子的抽屉里。我要去睡了。”
然后她悄声叫我看着,看他来不来碰那本书,说完就走了。可是他根本就没挨近它,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时,她大为失望。我看出,她为他的郁郁寡欢和懒散无为感到难过。她的良心受到了责备,不该把他吓得不想改变自己了。她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
不过她设法运用她的机灵来弥补这一创伤。在我熨衣服,或者做其他一些不便在小客厅里做的活儿时,她就带一些有趣的书来大声念给我听。遇到有哈里顿在场,她常常念到精彩处就停了下来,让书摊在那儿,走开了。她一次又一次地这么做,可是他固执得像头骡子,不但不上她的钩,而且碰上下雨天,他就跟约瑟夫在一起抽烟,像自动玩具似的坐着,壁炉前一旁一个。好在年纪大的一个耳聋,听不见他所说的她的胡说八道;年纪小的一个则竭力装出不屑一听的样子。晚上每当遇上好天气,他就出去打猎。凯茜唉声叹气,老来逗我跟她说话,可是我一开口,她又顾自跑到院子里或者花园里去了。她的最后一招就是哭诉,说什么她都活腻了,她活着毫无意义。
希思克利夫先生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跟人来往了,他几乎已经不许哈里顿进他的房间。由于三月初发生的一个意外事故,这小伙子有好些天成了厨房里的一件摆设。他独自在山上时,枪走了火,一块弹片伤了他的胳臂,回到家里时已流了很多血。结果他不得不在火炉边静养,直到康复。
有他在,凯茜倒觉得很自在。不管怎么说,这一来她更不喜欢她楼上的那个房间了,她老是逼着我在楼下找活干,她好陪着我。
到了复活节那个星期的星期一,约瑟夫赶着几头牲口去吉默屯赶集了。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忙着整理床单。哈里顿坐在壁炉的一角,像往常那样沉着脸,我的小女主人则在窗玻璃上画画,以此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她有时则变换花样,忽然哼上几句歌,轻声叫喊一两声,或者朝她那个老是抽烟和望着炉栅发呆的表哥投去烦恼和不耐烦的目光。
我对她说,她挡住了我的亮光,我都没法做事了,她就挪到壁炉那边去了。我也就没有去注意她干些什么,可是没过多久,我听到她说:
“我发现,哈里顿,要是你对我脾气不这样坏,不这样粗暴,我是要——很高兴要——很愿意要你做我的表哥的。”
哈里顿没有回答。
“哈里顿!哈里顿!哈里顿!你听见没有?”她继续说。
“去你的吧!”他吼了一声,一副毫不妥协的样子。
“让我来拿掉这烟斗。”她说着,小心翼翼地伸手从他嘴里拔出了烟斗。
他还没来得及夺回来,烟斗已被折断,丢进了火里。他对她恶声咒骂着,顺手又抓起了另一只。
“等等,”她喊道,“你得先听我说几句话。这些烟雾直往我脸上飘,我没法说话。”
“你给我见鬼去吧!”他气势汹汹地嚷道,“别来管我!”
“不行!”她坚持说,“我偏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跟我说话,而你又下决心不肯理解我的意思。我说你蠢,绝没有别的用意,绝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好了,你该理我了,哈里顿,你是我的表哥,你应该认我呀。”
“我对你和你的臭架子,还有你那套捉弄人的鬼把戏,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说,“我宁可肉体和灵魂都下地狱,也不愿再瞟你一眼!滚出去,现在就滚!”
凯茜皱起了眉头,退回到靠窗的座位上,咬着嘴唇,哼起了怪调子,极力想以这来掩饰住自己即将哭泣。
“你应该跟你的表妹和好嘛,哈里顿先生,”我插嘴说,“既然她已为她的无礼感到后悔了!这对你会有很大好处的,有她给你做伴,会使你变成另一个人的。”
“做伴?”他叫了起来,“她讨厌我,认为我给她擦皮鞋都不配呢。不,就是让我当上国王,我都再也不愿为讨她的好受到取笑了。”
“不是我讨厌你,是你讨厌我呀!”凯茜哭着说,再也掩饰不住心头的痛苦了,“你跟希思克利夫先生一样讨厌我,而且更讨厌。”
“你这个该死的撒谎的人!”哈里顿开口说,“照你这么说,那我干吗为了向着你,惹得他上百次生气呀?可是你却取笑我,看不起我,而且还——继续来烦扰我,我马上到那边去,说你把我赶出了厨房!”
“我不知道你向着我啊,”她回答说,一边擦干眼泪,“那时候我心里难受,对谁都有气。现在,我谢谢你,求你原谅我,可除此之外,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她又回到壁炉边,坦率地朝他伸出手。
他脸色阴沉,怒气冲冲,如同雷电交加的乌云,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眼睛直盯着地面。
凯茜本能地意识到,他的这种固执的举止,完全是出于倔强,而不是因为厌恶。她犹豫了一会儿后,突然俯身在他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
这小淘气以为我没看见,接着便退回到窗边,坐到原先的座位上,装出一副非常正经的样子。
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于是她脸红了,悄声说:
“哦!那我该怎么办呢,艾伦?他不肯跟我握手,也不愿瞧我一眼,我总得设法向他表示我喜欢他——我想跟他做朋友呀。”
是不是这一吻打动了哈里顿,我说不准。有那么几分钟,他小心翼翼地不让人看到他的脸;等到他抬起头来时,他显得心慌意乱,两眼不知该朝哪边看才好。
凯茜忙着用一张白纸整整齐齐地包好一本漂亮的书,又用一条缎带扎好。然后写上送交“哈里顿·恩肖先生”,要我作为她的特使,把这份礼物送交给指定的收礼人手中。
“告诉他,要是他接受这一礼物的话,我就来好好教他读书识字,”她说,“要是不接受,我就上楼去,从今以后再也不打扰他了。”
我在我的委托人的焦急注视下,把书送了过去,并且转达了要我带的口信。哈里顿不肯张开手指,于是我就把书放在他的膝盖上。他也没有把书扔掉,我仍回来干自己的活了。凯茜把头和两臂都靠在桌子上,等到听见撕开包装纸的轻微声音,她就悄悄走过去,默不作声地坐到她表哥的身边。他浑身战抖,满脸通红——他的所有粗鲁,所有固执,都已弃他而去——面对她那询问的目光,还有她那低声的恳求,他都鼓不起勇气来说一个字了。
“说你原谅我了,哈里顿,说呀!你只要说这几个字,我就会感到无比幸福!”
他咕哝了一句什么,没能听清。
“那么你愿意跟我做朋友了?”凯茜疑惑地问道。
“不!你今后一辈子每天都会为我感到羞耻的,”他回答说,“你越了解我,你就会越觉得羞耻。这我受不了。”
“这么说,你不愿跟我做朋友了?”
她问道,笑得像蜜一样甜,又朝他靠近了一些。
以下再谈些什么,我就听不清了,但是等我再抬起头时,我看到俯在那本已被接受的书上的两张脸,是如此地容光焕发。毫无疑问,和约已经签订,两个敌人,从此结成了盟友。
他们俩共同阅读的那本书里,满是精美考究的插图;这些插图,还有他们的位置,都很有吸引力,以致直到约瑟夫回家,他们都没挪动一下。他,这个可怜的老头,看到凯茜和哈里顿坐在同一张凳子上,她还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完全给吓呆了。他所宠爱的人居然容忍她来亲近,他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对他刺激太深了,使得他那天晚上对这件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他郑重地在桌子上打开他那部大《圣经》,又从口袋里掏出白天交易所得的脏兮兮的钞票,放在经书上,这才深深地叹了几口气,流露出他的心情。最后,他把哈里顿从座位上叫了过去。
“把这些拿去给主人,孩子,”他说,“就待在那儿。我也回我的屋子去了。这屋子对咱们不大合适,咱们得出去另找一个地方。”
“过来,凯茜,”我说,“我们也得‘出去’了。我已经熨好衣服,你准备走了吗?”
“还没到八点呢!”她回答说,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哈里顿,这本书我就放在炉架上了,明天我再多拿几本书来。”
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而且迅速地发展着,虽然这中间也遇到过暂时的挫折。哈里顿并不是凭一个愿望就能变得有教养的人,我家小姐也不是个哲学家,不是个能忍耐的模范。可是两人的心都向着同一个目标——一个是爱着,想着尊重对方;另一个也是爱着,想着对方尊重——双方都尽心尽力,要求最后达到这个目标。
你瞧,洛克伍德先生,要赢得希思克利夫太太的芳心是很容易的啊。不过现在嘛,我很高兴你没有做这种尝试。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他们两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