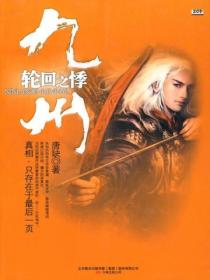云湛到达海边的时候,条件好一点的客船都已经停运了,好在这一页风并不大,海面尚算平稳,云湛诱之以金铢,好歹说动了一艘渔船点上灯把他载过去。毕竟除去了礁石的航道并无天险,对岸近在咫尺,不然他也只好等到天亮再说了。
云湛在南淮城定居之前,到过不少地方,雷州也曾去过一次。但当时他是坐着舒服的大客船,去往雷州最大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毕钵罗,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为了赶时间,他不断换马,连续奔驰了三天两夜,才在夜色阑珊时来到宛州最西南端的港口城市衡玉。此时他已经四肢僵、浑身疼痛,似乎一碰就会化为无数的碎片散落在地上。但他仍然不能休息,还得拖着疲惫的躯体去找船。云望海峡并不宽阔,如果是一个气力悠长的羽人,甚至能直接飞过去,然而云湛不幸地只能感受到暗月,在这样明月当空的时候无计可施,只能乘船。
云望海峡在历史上让人们头疼无比,因为它是如此狭窄,似乎西陆与东陆只有一线之隔,偏偏海峡内暗礁密布,完全无法通航。古人云望洋兴叹,海峡两边的人们却可以望岸而兴叹——但就是过不去。商人们只能从和镇或者淮安绕道,在海上兜好大一个圈子,才能进入雷州。
几百年前,当九州终于迎来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时期后,东陆商人开始频繁前往西陆寻找商机,垂涎着那些尚未被开发的广大土地,希望在其中找到丰富的矿藏和动植物资源,而交通又一次成为巨大的障碍。此时火药已经被发明并且逐步推广利用,人们本着成固欣然、败亦无害的心态,用火药一点点爆破礁石,最终开辟出了几条虽不太宽却也安全的跨海航道。但炸完后才发现,此地水深不够,载货量过大的商船还是过不去。所以这些航道并不能为宛州的大商家们所用,倒是许多散客行商在此登船渡海,寻求着微薄的利润。
云湛靠在甲板的船舷上,鼻端闻着臭烘烘的鱼腥味,不知怎么的,越是困累,越是睡不着,全身的肌肉都在酸疼或许是原因之一。他侧过头,看着船舷外黑乎乎的水天一线,以及星光在远处的海面上洒下的跳跃的亮点。夜色之中,对岸的山与树的轮廓隐约可见,远处的灯塔则多少有些光线暗淡。云湛问船主,船主一边掌舵一边回答:“那边几乎没有什么礁石——都被炸掉啦,登岸很方便,而且夜间很少有在海峡两边来往的船只。不过也只能横渡海峡,不能顺水北上,再由直通大海的运河,结果造成了海水倒灌,引发巨大的灾难,导致九州分成了三块。云望海峡就是那次灾难的见证。”
“倒是很有意思的传说,”云湛笑了起来,“可见在一切的民间说法里,皇帝从来不干好事。”
“也未见得啊,皇帝有时候也是干好事的,”船主说,“比如三十年前皇帝打魔教,就打得好啊,不打的话,没准我老子就死在那时候了,我也生不下来啦。”
渔民常年在海上奔波,风吹日晒,看起来显老,这位船主皮肤被晒成古铜色,看来有三十多岁,但实际上也许就比自己大几岁,还不到三十。云湛来了兴趣:“讲讲呗,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嗐,还能有什么,家家户户都差不多,魔教害人呗!非要人拜什么魔王,不拜的又是打又是罚钱,要是伤了他们的人更是得赔命,比官府还厉害,而官府已经被他们买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管。我老子那时候年轻,一冲动就纠集了一帮人想要和他们拼,哪儿拼得过?反而自己被抓起来,魔教说要选个吉日公开行刑,杀鸡给猴看。幸好就在行刑前两天,皇帝的军队开始到处杀魔教,他们慌了神,丢下犯人就跑了,我老子他们在地牢里差点闷死,最后拼死撞破了牢门,才捡回条命。之后他才娶了我娘,生了我,哈哈……”
“那后来,那些魔教徒都被杀光了?”云湛问。
“大概是吧,不过听说,最后死的活的加在一起,数目并不多,很可能逃了不少,”船主不以为意地说,“鬼知道逃到哪儿去了,反正后来皇帝和诸侯们还在追捕他们,应该跑不掉吧。”
应该跑不掉?云湛眉头一皱,想到了点什么。从船主的叙述中可以判断出,在皇帝发兵之前,净魔宗就已经判断出了形势,并且开始有意识地提前撤退。可在这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上,还能往哪里逃跑?往内陆上的话,宛南平原的地势决定了没有什么藏身之处,也无险可守,迟早会撞上皇帝的大军死得很难看,所以只剩下唯一一条逃生之路了。
那就是渡过浅浅窄窄的云望海峡,逃往地广人稀的雷州。雷州气候多变、地形复杂,要供净魔宗的残部躲藏并不难。他本来想让这支部队常驻雷州防御,但一来雷州的气候让宛州人难以适应,二来净魔宗在总坛被攻破后再无任何声息。所以不久之后,随着石之衡的病故,继任的国主石之远召回了驻军,再也无人关心雷州是否有净魔宗藏匿的事实了。
一定有!云湛握紧了拳头。他们不但存在,而且一定就在神秘莫测的云望废城里藏身。云湛甚至怀疑,所谓云望废城对闯入者的死亡诅咒,也许就是净魔宗搞的鬼。他们把这一区域涂上恐怖诡奇的色彩,以吓唬外来的人,以保护自己不被发现。三十年来,他们就这样藏身于雷州的阴暗角落里,悄悄积蓄着力量,等待着重新在世上现身的那一刻。一旦这一天到来,对于整个九州而言,恐怕又是一场大灾难。
他这下是真的睡意全无了,但当船在雷州靠岸、付过船资走上海岸后,他还是发现不休息一下根本不可能。连续几天不惜命地纵马狂奔,身体已经在提抗议。他跟随云灭修习多年,只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吐纳运功两三个对时,就能比睡上半天觉还管用,不过他一向贪恋躺在**睡觉的乐趣,轻易不会丢掉睡觉的机会。但眼下时间紧迫,还是牺牲一点睡眠时间的好。
静坐吐纳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所以还是得找间客栈。云湛拖着快要断掉的双腿,在码头附近找到一家鱼腥味几乎与渔船上无异的小客栈。这是方圆几里内唯一通宵营业的客栈。他也顾不得那么多,向半睡不醒的伙计要了个房间,在**盘膝坐下,开始按照云灭传授的方法调整呼吸、驱除杂念。
在头脑慢慢进入空明之前,他的眼前依次闪过六张面孔,那是半年前到此处的石雨萱一行人。他并没有见过这些人的真容,所以那些面孔并不真切,看来模模糊糊,就像水中的倒影。在极度疲倦的边缘,他的头脑反而激发出了一些异样的灵感,这种灵感最终指向了六张面孔中的一张:伍肆玖。伍肆玖的脸跳跃着,叫喊着,旋转着,好像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要提醒云湛。
这个滑稽伶人会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呢?来不及多想,练功的惯性已经让他停止了多余的思虑。他的身心开始进入了近乎一片空白的休眠状态,精神完全松弛下来。
睁开眼睛时,刚刚天亮不久,窗外海风劲吹,码头上已经渐渐热闹起来,渔民们已经开始出海,客船与商船也开始启程。云湛伸个懒腰,觉得神清气爽,走到客栈的大堂里吃了点东西,招呼伙计过来问话。
“能帮我找一个向导,替我带路去云望废城吗?”云湛往桌上放下一枚亮晶晶的银毫。
伙计并没有伸手去拿银毫,而是面有疑惑之色:“您是什么意思?是要到云望废城外面的山上观光一下,还是想要到废城里面去看看。”
“当然是到里面看看了,”云湛说,“在外面有什么好看的?”
伙计咽了口唾沫,遗憾地看着那枚银毫:“这银毫……您还是自己留着吧,这里向导多了去了,你想要去看看螃蟹岛,看看枯木林,看看绮罗山,看看古战场遗迹都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就能带您去。废城……那可是要命的地方,没人敢去的。”
“一个人都找不到?”云湛斜眼望他,“不大可能吧。我相信会有不少人愿意出高价找向导带他们进废城去看看的。”
“过去是有不少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伙计叹了口气,“可是三十年前……忽然之间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命案,三户家里有人做向导的人家,一夜之间全部都死了,而且不见尸体。老人们说,那是亡灵忍无可忍的警告,从此之后,再没有当地人敢干这活了。”
“也就是说,外地人还是有人敢去带路的,”云湛把从桑白露的纸片上得到的人名报了出来,“卫柯莟,看名字像是个女人吧?”
伙计听他报出了“卫柯莟”三个字,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云湛:“您要找她?开玩笑吧?”
云湛莫名其妙:“找她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奇怪,不奇怪……”伙计这次不客气地把桌子上的银毫抓在手心,“我这就告诉您她在哪儿,离这儿不远,就不必我带您去了。”
他说完,一溜烟跑掉了。云湛满腹狐疑,却也没法再把他抓过来问,只好起身自己走出去。卫柯莟的地址确实离这间客栈不算太远,因为就在码头里边,用伙计的话说,“您到码头里一问,没有不知道她的”。
云湛走进码头,向他碰到的第一个人询问卫柯莟的下落,对方果然毫不迟疑地就告诉了他,只是看他的眼神又很奇怪。云湛沿着他指点的路径来到海边,找到了一艘正在装货的船。他一眼就认出了卫柯莟是谁。虽然并没有其他人告诉他,但他确定,那就是卫柯莟,因为只有这个人才有资格让伙计听到名字就发颤,才有资格让整个码头的人“没有不知道她的”,才有资格让被问路的人都显得有些慌张。
卫柯莟这昂在往船上装货。其他人用尽全力才能两人拖动一个木箱,她却能毫不费力地一手提起两个,健步如飞地把木箱运到甲板上,挽起袖子的胳膊上肌肉饱满鼓涨,就像一块坚固的岩石。她并没有去踩搭在船边的木板,一来是用不着,她只要站直了伸出手就能够到甲板;二来是没法踩,这样的木板,让她去踩,必然会一脚下去就断成两截。
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常人三倍身高的身躯巨大的女夸父。在她的身边,那些在码头上忙忙碌碌的人类劳工显得那么的瘦小而脆弱。后来这位有着一个蛮好听的东陆名字的女夸父告诉云湛,她的名字是请一位人类的私塾先生起的,根据真名音译而来。她的夸父语名字叫做维克图汉。
请一个夸父吃饭是桩很让人挠心的灾难,尤其当你遇上的夸父每天都在干着重体力活、胃口上佳的时候。但云湛是这样的人,没钱的时候会玩命想办法赚钱,赚到了钱之后却绝不吝惜花销。他的人生哲学是,人的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能够随意掌握、随意放弃的东西少之又少,如果连钱都舍不得花,活着作甚?
再说了,反正身上的钱是从席峻锋那里讹来的公款,不花更是有违天理。
所以在饭铺外面席地而坐的维克图汉吃得很满意,云湛看她兴起,又要了五斤牛肉做点心,这让她更加心情愉快。夸父生性爽直淳朴,喜欢结交豪迈大方的人,一顿饭之后,两人的交情已经很不错了,而这个女夸父给云湛的印象也还好。夸父一向给外族以肌肉纠结的巨大怪物的可怕联想,但实际上,女夸父的脸比起粗豪的男夸父线条要更加柔和一些,维克图汉假如身量小上三分之二,再去掉过分强健的肌肉,也可以算一个中上之姿的宛州女人了。
云湛也借此问清了维克图汉的底细。她原本是毕钵罗到处找饭吃的夸父力夫,因为被克扣工钱,不小心轻轻一推就把工头推到了墙上,头破血流而亡,于是只好逃命。她躲在这个东南半岛的小镇上,为了活命什么都干,曾经跟随者一支寻宝的探险队进入过云望废城,并且或者出来了——而队里的其他人都遇上了意外的灾难死掉了。
“一块岩石滚下来,除了我,别人都砸死了,”维克图汉说得轻描淡写,“镇上的人都说那是亡魂们在作祟,我不信,以后遇到这种活还去,他们给钱多。”
“你们夸父不信鬼神?”
“我们信盘古天神,信部落的神兽,也相信神秘事物的存在,”维克图汉说,“但我们敬天神,敬神兽,却不会害怕其他各部落所谓的鬼魅。因为即便有什么亡灵阴魂,我们的精神力也足以克服它们,天神与我们同在。”
“你们真强,”云湛由衷的说,“难怪这么大个镇子只有你敢带路。”
“听说在过去的时候,本来还有另外几个胆子稍微大点的人的,身上带着护身符——其实就是在骗自己——也做这个行当,毕竟愿意去云望废城的人,都很舍得掏钱,做向导养家糊口很容易,”维克图汉的说法和刚才那个伙计一模一样,“后来有一天,一个向导连同他的全家人都莫名其妙地在家里死掉了,也找不到死因,尸体的手里就紧捏着那种护身符。没过两天,同样的事情连续发生,这里的人都吓坏了,说这又是废城的恶灵什么的追杀出来杀害敢于对他们不敬的人,这回才货真价实没别人敢带路了。”
“恰好在三十年前,一下气冒出那么多吓唬人的凶案,”云湛若有所思,“这时间还真是巧啊,看来那些鬼魂的确不希望外人闯进云望废城。”
这座无名的海岸渔镇距离废城并不太远,大约半天的路程。为了节省体力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云湛雇了辆驴车坐在上面,维克图汉却跟在车后大步流星,吓得拉车的驴子腿脚都变快了一点。云湛装作无意地问起维克图汉,过去曾经带过些什么有意思的人去废城,维克图汉一点一点回忆着,但说起的几帮人都不合云湛的胃口,她不由有点生疑:“你是不是想打听什么人?”
云湛正想打个哈哈蒙混过去,转念想想夸父的性格,千万莫要弄巧成拙,于是改变了主意:“你说得对,我们是朋友,我应该对你说实话。我这一趟来雷州,主要就是为了寻找几个人过往的踪迹。”
他把石雨萱等六人的形貌大致描述了一下,当然这些人他一个都没见过,全是转述亲王府侍卫总管洪英的形容。维克图汉对云湛的坦诚相当满意,差点就伸出巨掌拍拍他的肩膀,幸好最后悬崖勒马,不然云湛只怕要当场废掉。
“有这么一拨人,七个来月之前来的吧,”维克图汉说,“我带着他们去了废城,最后他们一个没死都回来了,也算不容易。”
“就这些?没点其他细节?”
“没有。那六个人中间有一半会武功,而且相当不错,基本用不着我去照顾。”维克图汉的神情有点不悦,令云湛敏锐地捕捉到一点什么,“他们是不是得罪你了?”
“还好,不算得罪我,”维克图汉的语气里有些不屑,“就是除了那个傻头傻脑的河络,其余四个人一路上围着那个小姑娘转,看起来很……看起来很……”
她努力在记忆力搜罗着东陆语的词汇,最后蹦出来一个字:“贱。”
云湛哑然,想想也觉得不奇怪。石雨萱贵为郡主,其他人当然得以她为尊,这种尊卑观念大概很难让崇拜力量的夸父理解。而他也可以想象,“那六个人”肯定是紧紧抱成团,比较疏远带路的夸父,也难怪维克图汉想起这些人就不高兴。因此她在整个行程中并没有和这些人过多接触,几乎是闷头带路,对这六个人的具体情况也说不出太多,这让云湛略有些失望。
“那就麻烦你带我到他们去过的地方吧。”云湛说。看来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寻找答案了,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