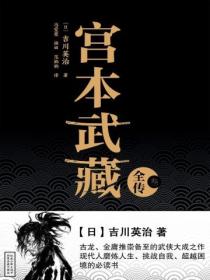大事
一
不知是有眼疾还是老花眼,这名茭白僧人找东西时似乎总是摸摸索索的。
他吹尺八并不是泽庵要求的,吹出的曲调就像一个外行人在消遣一样。
不过泽庵从中感受到一种自然流露的诗意与真情。曲调生涩,却是用心在吹的。
要说这位年迈的遁世者到底在通过笛声表达什么,仿佛尽是忏悔之意。
泽庵也在笛声中大致了解到了这位茭白僧人的人生。不管是伟大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人的内心旅程大致是一样的,都心怀着过往烦恼。
“咦,好像在哪里见过?”
泽庵嘀咕道。茭白僧人眨眨眼。
“这样一说,我也感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您的声音。莫非您就是但马的宗彭泽庵?曾在美作吉野乡的七宝寺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话听到一半,泽庵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挑了挑角落里的灯芯,凝视着这位斑白胡须、瘦削脸庞的茭白僧人。
“啊……这不是青木丹左卫门吗?”
“嗯,果然是泽庵先生。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如今这般样子,太惭愧了。宗彭先生,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青木丹左卫门了。”
“真是意外,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七宝寺一别已经十年了。”
“说起来,真是如冰雹砸心一般难受啊。我现在已经等同于一具行尸走肉了,整日徘徊在黑暗之中,只是一味地思念我那儿子。”
“你的儿子?你的儿子现在身在何处,在做什么?”
“我当年曾追赶武藏——后来的宫本武藏到赞甘的山上,并将他绑在千年杉上受苦。而今听说,我的儿子成了他的弟子,还来到了关东。”
“什么,武藏的弟子?”
“听到这些后,我非常惭愧——无地自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再去面对那个人,于是索性试图让自己忘了儿子,避免与武藏相见。就这样,在不安中度过了很多时光……如今掐指一算,城太郎该有十八岁了,真想看看他长大成人的样子。于是,也顾不得羞耻,找到关东来了。”
二
“那城太郎是你的儿子?”
泽庵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跟武藏如此熟识,却从未听阿通或武藏谈起过城太郎的身世。
茭白僧人青木丹左卫门默默点头。看他现在枯槁的样子,完全想象不出当年他也曾留着络腮胡子,一副武士大将风范。泽庵只是怅然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语。对于一个洗尽人间纤尘,来到萧条旷野的暮年之人,一切安慰之语似乎都显多余。
只是实在不忍看皮包骨头的他一味活在对往昔的忏悔中,迷失了未来的方向。这个人从自己的社会地位上跌落后,一蹶不振,完全忘了还有佛陀的救赎、法悦之境界。虽然有权有势时,滥施权力、为所欲为,而今下台后,却也能良心发现,甚至想扼杀自己的残生来赎罪,可见也不是无可救药之人。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便是能在有生之年——见一见武藏,说上一句道歉的话,看看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样子,知道孩子会有安稳美好的未来——然后便在那片杂树林中,再无挂念地自缢而死。
泽庵想,在这个男人见他的孩子之前,得先引导他见见佛陀。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只要放下屠刀潜心向佛,佛也会拯救他的。至于和武藏的见面,也是放在后面比较好,对这个男人来讲是一个悟佛后的忏悔机会,对武藏来讲也是件舒畅的事。
想到这儿,泽庵告诉青木丹左卫门,城内有一个禅寺,只要报上自己的名字,住几天都可以。等自己这边倒出时间,再过去详聊。至于他儿子城太郎,也不是完全没线索,必当竭尽全力安排他们父子相见。不要太过闷闷不乐了,五六十岁后也该有自己的人生乐土,有很多要做的事。在自己去找他前,让他先在禅寺与和尚们聊聊人生,聊聊自己的想法。
这样劝完后,便让青木丹左卫门赶紧动身了。青木丹左卫门似乎猜到了泽庵的良苦用心一般,不断道谢,然后背上茭白和尺八,靠竹杖探路离开了。
这一片是个小山丘,青木丹左卫门因怕下坡路滑,向树林的方向走去。从杉树林的羊肠小道到杂木林的羊肠小道,青木丹左卫门按照大自然的指引一路走下去。
“……?”
青木丹左卫门的竹杖碰到了什么东西。他并非完全失明,感到异常后,他俯身望去。刚开始什么都没有看见,让眼睛适应了一会儿环境后,借着枝叶间泻下的一点点蓝色星光,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在这被露水濡湿的大地上躺着的是两个人。
三
青木丹左卫门想了想照原路返回,向依旧亮着灯的草庵内看了一眼。
“泽庵先生……我是刚刚打扰您的青木丹左卫门,在前面那片林子中,有两个人从树上掉下来失去了知觉。”
听到这话,泽庵起身走向草庵外。青木丹左卫门继续说道:“不巧我这儿也没带什么药,眼睛也不大管用,连口水都不能给他们找来。不知他们是附近乡亲们的儿子,还是来野外游玩的武家兄弟。您救救他们吧!”
泽庵赶紧穿上草履,向丘下茅草屋内大声叫着谁。
有人影从茅草屋内闪出,向丘上草庵走来。那里住的是一位老爷爷。泽庵拜托这位老爷爷准备松明和一竹筒的水。
当老爷爷举着松明上来时,泽庵给青木丹左卫门指了下路——这次青木丹左卫门顺着坡道下行了,刚好与上坡的老爷爷在坡道中央擦身而过。
若是青木丹左卫门走刚刚那条路,必定能随举松明的老爷爷认出城太郎,可是阴差阳错,他又跟泽庵打听了一下去江户的路,直接下坡走了。
可是焉知不幸还是侥幸,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当时的事是意味着缘浅还是缘深,幸运还是不幸。
带着水和松明赶来的老爷爷是这两天帮忙修葺草庵的村民,他不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一脸不解地跟在泽庵后面进入树林。
松明照亮了青木丹左卫门所说的地方——可是状况和刚才有些不同了,青木丹左卫门发现时,城太郎和伊织重叠地倒在一起,而这会儿城太郎已经苏醒了,正呆呆地坐着。他的一只手搭在伊织的身体上,正在犹豫是看护到伊织苏醒,问他想问的问题,还是赶紧逃走。
突然感觉到松明的亮光和人的脚步声,城太郎像夜间的野兽一般,迅速机敏起来,摆好了随时都可以出击的姿势。
“……哎呀!”
泽庵停住了脚步,举着冒着烟雾、荧荧燃烧的松明的老爷爷也随泽庵停了下来。城太郎感觉来者不像有恶意,放下心来,只是望着来者。
泽庵的那句“哎呀”是因为他听说两个人都失去意识了,如今到来发现一个人坐起来了。可是双方都盯着互相打量起来,这句“哎呀”像是变成了表达双方相见无比惊愕的心情的语言。
泽庵看到的城太郎已经长高许多了,相貌、身姿都多少有些变化,而城太郎则应该一眼就认出了泽庵。
四
“这不是城太郎吗?”
泽庵瞪大了眼睛。
在泽庵愣神惊讶的当儿,城太郎已经双手扶地,深深地一拜。
“是的……是我。”
再次抬头看泽庵时,又是以前那副流鼻涕小孩儿的表情,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哦,不知不觉间你已经长大了,变成如此机敏的年轻人了。”
泽庵惊异于见到城太郎和他的变化,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救助伊织是最要紧的。
泽庵抱起伊织,感觉他体温并无异常,给他灌了点竹筒内的水,伊织很快恢复了意识。伊织醒来后张望一下四周,“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很疼吗?哪里疼?”
听泽庵这么一问,伊织摇了摇头,边哭边说自己哪里都不疼,只是师傅不在身边了,师傅被带去秩父的牢房了,好害怕。
他这么边哭边说,又事出突然,泽庵一时没有听明白怎么回事,又仔细一问,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由得也忧心忡忡。
也在旁边听伊织哭诉的城太郎,则不禁冒出一身冷汗,愕然地颤抖着小声说道:“泽庵先生,我有话想说。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
伊织止住了哭泣,狐疑地看着城太郎窃窃私语,也贴近泽庵的耳朵指着城太郎说道:“那家伙,是盗贼。他说的话肯定都是谎话。泽庵先生要小心啊!”
同时伊织用随时准备作战的犀利目光回视城太郎的目光。
“两个人都别吵。你们原本应该是兄弟弟子的。你们信我的话,跟我来。”
泽庵将他们带到草庵前,命他们在草庵前燃起篝火。村民老爷爷见没自己什么事了,便返回坡下茅草屋了。泽庵在火旁坐下,让他们也和睦地坐于篝火旁。可是伊织却迟迟不肯过去,一副不愿与盗贼城太郎称兄道弟地坐在一起的样子。
远远看了会儿泽庵和城太郎亲热地谈从前的事,伊织不由得有些嫉妒,终于也靠了过去。
只见城太郎像个在佛前忏悔的女人一样,低眉垂泪,默然一会儿,主动说起了自己成为盗贼的经历。
“……嗯,是啊。离开师傅已经整整四年了。这期间我被奈良井的大藏大人抚养,聆听他的教导,听他讲他的远大志向和处世之道,我决心誓死为他效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大藏大人——没想到今天被人称作盗贼。我也是武藏师傅的弟子,离开他身边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忘记师傅的教诲。”
五
城太郎继续说道:“——我和大藏大人在神灵面前起过誓,不能向别人泄露我们的目的,所以恕我也不能对泽庵先生您说了。师傅武藏因宝藏库一事而含冤入狱,我不会不管的。我打算明天就去秩父自首,为师傅洗脱冤屈。”
泽庵默默地点头听城太郎讲,听到这儿抬头问道:“那么,盗宝藏库一事,是你和大藏干的了?”
“是的。”
城太郎一副无愧于天地的语气答道。
泽庵严肃地盯着城太郎的眼睛。城太郎低下了头。
“那你不就是盗贼吗?”
“不……不是,我们不同于一般的盗贼。”
“你们还分三六九等吗?”
“我们不是为了私欲而偷盗的。是为了百姓挪动了公家财产而已。”
“不明白啊。”
泽庵抛出一句表示不理解的话。
“这么说来,你们是义贼吗?中国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形象,剑侠、侠盗什么的。你们是这样的吗?”
“若我再说下去,肯定会泄露大藏大人的秘密。”
“哈哈哈哈。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会中我的圈套吗?”
“不管怎么说,我会去自首救出师傅的。拜托高僧您随后跟我师傅好好解释关于我的事情。”
“我不会替你说这些的。武藏本身就是被冤枉的,即使你不去,最终也应该会没事的。你还不如拜拜佛,拿出你的真心,向佛祖自首。”
“佛?”
城太郎似听到了什么新鲜事一般。
“是的。”
泽庵像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
“听你的口吻,你似乎是在为天下众生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你照顾好了没有,你周围就没有不幸的人了吗?”
“只为一己之私,办不成大事。”
“黄口小儿。”
泽庵大喝一声,扇了城太郎一巴掌。城太郎捂住自己的脸,被这突如其来的巴掌吓到了,有些不知所措。
“没有你自己,何来天下,你自己是根本。连自己都不考虑的人,能为别人做什么?”
“不,我只是说不考虑自己的欲望。”
“住嘴,你不知道你还是一个青涩未成熟的人吗?一个未经世事的人居然摆出一副对天下了然于心的姿态,还自认为在为什么了不起的宏愿做着贡献,你再这样下去,真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来。
城太郎,你和大藏做的那些事情,我大体了解了。不用再说什么了,真是个小笨蛋,身子虽然长大了,心智上没有一点儿长进。你哭什么,委屈你了吗,好好擤擤你的鼻涕。”
六
因为泽庵以命令的口吻让城太郎先去睡觉,城太郎只好先盖着草席躺下了。
泽庵和伊织也都睡了。
可是城太郎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想起了还在牢狱之中的师傅武藏,内心不断涌起深深的歉意。
仰面朝上,泪水顺着眼角流进了耳朵中。侧过身去,又想起了阿通如今怎样了。即使是阿通在,他也没脸面对她了。泽庵的这一巴掌打得很疼,若是阿通的话,恐怕会捂着胸口伤心地哭泣,责备他吧。
对于向大藏起誓不泄露的秘密,城太郎选择了守口如瓶。想到天亮后恐怕还要受泽庵的责备,城太郎决定趁现在悄悄走掉。
……
城太郎轻轻起身。刚好这草庵没有四壁和天花板,最适合逃走了。
他走到户外,仰望星空,如果不抓紧的话,恐怕天就放亮了。
“你,站住。”
刚要迈步,城太郎被后面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泽庵如同他的影子般站在了他的后面。见他停住了,走上前来将手搭在他的肩上。
“怎么了,想去自首吗?”
“……”
城太郎默默点头。泽庵怜爱地说:“就这么想白白送死吗?真是个简单的家伙。”
“白白送死?”
“对,你觉得自己一自报是盗贼,就能救武藏了吗?没那么简单的事。到了衙门,你以为那些差人能轻易让你隐瞒掉你想隐瞒的事情吗?
武藏还会依旧被关在狱中,而你注定这一两年要活活接受拷问。这是必然的!”
“……”
“你认为这还不算白白送死吗?你若想洗清师傅的冤屈,就必须先洗清你自己。你觉得是在衙门接受拷问的好,还是坦诚面对我的好?”
“……”
“我泽庵是佛陀的弟子,你的事并不是由我来裁决。我只是引导你向佛罢了。”
“……”
“要是你仍心有不愿的话,有一个方法。我昨天在这儿意外地碰见你父亲青木丹左卫门了。有赖上天眷顾,接着我又遇见你。……你父亲青木丹左卫门去了江户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寺院,你若还是非去送死不可的话,我先带你见一见你父亲怎么样?再跟你父亲商量一下,看我说得对不对?”
“……”
“城太郎。你面前有三条路,你自己选吧!”
泽庵扔下话后,便又回到了草庵内。城太郎想起了昨天和伊织在树上打斗时,听到的远方传来的尺八声。如今才知道那原来是父亲,通过笛声,他已对父亲现在的状况、徘徊于世的心情大体了然于心。
“等等,泽庵先生,我说!我说!虽然我曾起誓于大藏,不对旁人泄露,可是……我愿意对佛祖坦白一切。”
城太郎跑上前去,拉着泽庵的衣袖,向林中走去。
七
城太郎坦白了一切。就像在暗暗黑夜中冗长地自言自语一般,城太郎吐露了一切。
泽庵不曾打断城太郎,静静地从头听到尾。
“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见城太郎不再作声,泽庵才开口问道:“就这些吗?”
“是的,就这些。”
“好了。”
泽庵不再说什么。在一片静默中,杉树林的枝头已悄悄染上了拂晓的淡蓝色。
乌鸦成群地聒噪着,四周滴露闪烁。泽庵似乎是累了,坐在了杉树的树根上。城太郎等着接受泽庵的责骂般,低头靠着一棵半身高的树站着。
“……这伙人可真不简单啊。连天下大势都观望不清楚,还说什么为了天下苍生,真是愚蠢至极。还好,现在还没起事。”
说这话时,泽庵已经心有打算了。他出其不意地从怀中掏出两枚黄金交给城太郎,让他赶紧远走。
“若不快些离开的话,你父亲、师傅都难逃一难。走得越远越好。
要避开甲州路到木曾路路段,因为从今天下午开始,要严设关卡了。”
“我师傅该怎么办?我就这样扔下他不管,远走他乡吗?”
“这个你就交给我泽庵吧。等过个两三年这件事平息后,你再回来向你师傅武藏道歉,怎么样?到时泽庵会陪你走过这一关的。”
“那么……”
“等等。”
“是。”
“走之前到下江户。你父亲昨晚去麻布村的正受庵了。”
“是。”
“这是大德寺的印可。从正受庵领取一下斗笠和袈裟,然后你和你父亲扮成僧人,抓紧时间一起上路。”
“为什么必须扮成僧人?”
“傻孩子。你不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狙击德川家的新将军,趁乱袭击大御所所在的骏府,让关东陷入一片混乱。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鲁莽之辈,你还自认为很光荣地加入他们。往大了说,你们这是造反,是要被处以绞刑的。”
“……”
“快去吧,趁着太阳还没完全升起。”
“泽庵先生,我再问您一个问题:为什么想扳倒德川家的人成了造反之徒,而扳倒丰臣家夺取天下的人就不是造反之徒呢?”
“不知道……”
谁能说明白这些。泽庵不是找不出说服城太郎的话,只是他没有找到一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理由。这个社会在一天天变化,谁意图对德川家不轨,谁就是造反,这已经成这个社会公认的事实了。逆潮流的人,肯定会被时代的巨轮甩出在外,落得身败名裂,凄惨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