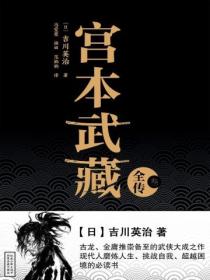空心麻线球
一
什么人?
武藏完全不清楚那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不过武藏心中做好了随时对抗威胁生命的敌人的准备。
杀伐无序这种乱世的遗风现在依然存在。在曾经的充盈着阴谋与间谍的乱世中生存的人们被社会环境磨炼得是那样疑神疑鬼,甚至连枕边的妻子都不相信,骨肉亲情也**然无存。如今,这种歪风依然存在。
难道——
至今为止,被武藏手刃的人,还有因为他在社会上败北的人不计其数。再加上那些败者的亲属,数量甚是庞大。
不管是不是正当比试,不管武藏是不是占着理,总有败者将武藏视作仇敌。比如说又八的母亲便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志于这条路的人随时都可能遭遇到生命危险。危险和敌人是挥之不去的,就算去修行,危险的地位也稳如磐石,敌人也会层出不穷。
将睡梦时的危险视作一种磨炼,将不断威胁自己生命的敌人视作老师,当剑之道最终能够帮助你永久地安身立命、保家卫国、拥有菩提一般的心境时,你便可以尝到永恒的喜悦。可是在此之前有一段艰辛无比的道路要走,还要承受时不时袭来的疲惫、虚无、无为等种种束缚。突然发现弯着身子的敌人的身影向这边走来了。
矢作桥的桥身处——
武藏原本屈身静观,一瞬间感觉自己平日里的怠惰、迷惘全都顺毛孔蒸发出去了。
是一种**裸地暴露在危险前的凛然感使然。
“……咦?”
武藏想靠近敌人,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是谁。那边的影子见没有找到想象中的武藏的尸体,开始向能藏身的暗处张望过来。
望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武藏的心中依旧感到疑惑。那行动非常敏捷,一身黑衣打扮,佩带腰刀、鞋袜轻便利落的浮游之徒并不像是普通的民间武士。
这一带的藩士有冈崎的本多家、名古屋的德川家,从这方面看,应该不存在什么危险因素。真是奇怪,可能是认错人了。
不,如果说认错人了的话,那时常在露地口和竹林中窥看的到底是谁呢,就连隔壁的夫妻二人都感觉到了他们的目光。看来他们应该是知道自己就是武藏的,之前只不过是在寻找时机而已。
“哈哈……桥的那边还有同伴。”
武藏望过去,躲在那边暗处的三个人,在那里重新装好火绳,向河的对岸挥舞起火绳来。
二
那边竟然也有装备整齐的同伙,看来这些敌人还真是准备周全。
他们一定是摩拳擦掌,决心就在今晚干掉他。
武藏往返于八帖寺要经常通过这座桥,这些敌人定是掌握了这一点,充分了解了桥这里的地形特点,准备好了武器。
武藏依旧静静躲在桥身处。
他知道,若是贸然跳出去,子弹定会飞过来。撇开敌人跑上桥,也跑不出子弹带来的危险。可是,一直蹲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那对岸的同伙也在用火绳向这边的敌人发送着信号,事态早晚会对他不利。
就在这危急时刻,武藏想出了应对方法。不依赖兵法,所有的理论系统只成立于平时,到了真正的关键时刻,瞬间的决断通常是最起作用的,一板一眼的理论往往会掣肘,“直觉”最重要。
不可否认,平常的理论为“直觉”提供了纤维,可是当事态紧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理性思考,延误了时机,等待的就只有失败。
虽然“直觉”无知的动物也有,可是我们不要把这种“直觉”同无知的天然感官反射混淆在一起。只有经过了智能等各方面训练的人,才能超越理论,达到研习理论的终极目的,在瞬间爆发出正确的直觉判断。
特别是在剑术上。
在武藏现在所处的这种情景下。
武藏屈身向敌方大声喊道:“你们即使潜伏起来,我也能看见火绳。没有用的。若是找我武藏有事的话,请过来吧。我武藏在这里。”
川风猛烈地刮着,让人怀疑声音是否能够顺利传到,不多时,第二声枪响和飞奔而来的子弹验证了他们确实听到了。
武藏在喊完话后便换了个地方。沿桥身移动了九尺左右,在与子弹擦肩而过的同时,他向敌人隐藏的地方跃去。
那三个敌人还没来得及上第二发子弹,用火绳点燃弹药,便见武藏挥舞着刀,跳了起来,他们非常惊慌。
“呀——”
“啊——”
这三个人若是及时反击的话应该还来得及,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合作好。
武藏朝这三个人劈来,大刀正中中间迎着刀锋的人。紧接着武藏用左手上的腰刀向左侧的人一个横砍。
另外一个人扭头就跑,由于太惊慌了,他像瞎子一样撞到了桥栏杆上,就像要将桥吃掉一样,然后正一正方向,继续向前没命地跑。
三
武藏沿着栏杆用平常的步子前行,没再感觉到有什么动静。
走了几步,武藏像是在等该来的敌人一般停住了脚步,依旧没有再发生什么。
回到家后,武藏便睡下了。
第二天,他又作为无可先生坐在小桌前领着一群孩子习字。
“有人在吗——”
来了两个侍卫,站在廊檐处向里面张望。因为狭窄的房门口处堆满了孩子的鞋子,所以他们绕过房门口,来到后窗处。
“无可先生在吗?在下是本多家的家臣,奉命来到这里。”
武藏在孩子中间抬起了头:“我是无可。”
“无可是您的假名吧,尊公本名是不是叫宫本武藏?”
“嗯——”
“原来您确实隐居在此处。”
“我是武藏没错。不知有何事?”
“您知道藩内的近侍首领亘志摩吗?”
“这个,不是太清楚。”
“您应该知道的。您曾去参加过两三次俳谐会。”
“我是受人邀请去参加俳谐会的。无可这个名字并不是我的假名,是我在俳谐会上偶然想出的俳名。”
“啊。是俳名啊。不管怎样,亘志摩大人也很喜欢俳谐,家中经常聚集很多吟友。他说想和您聊上一晚,在下特来邀请您。”
“要是聊俳谐的话,还有很多比我更适合的风流之士吧。我虽受人邀请,一时兴起去参加过俳谐会,可是我根本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土人。”
“啊,不是。不是想和您切磋俳谐。亘志摩大人听说过您的一些事情,所以想见见您。想来应该是想聊聊武艺之类的事。”
习字的孩子们都停下了笔,很担心地望着先生和站在庭院中的两名侍卫。
武藏不再说什么,只是望着檐下的两名受差遣的侍卫,看起来是在做着决定。
“好吧。那我就承蒙邀请,前去拜访亘志摩大人。时间呢?”
“若是您没有什么不便的话,就今晚。”
“亘志摩大人的宅邸在哪里?”
“在下到时会来接您。”
“那我就恭候了。”
“那——”两名侍卫互相交换了下目光。
“就不打扰您了。武藏先生,打扰您上课,真是失礼了。我们到时再来接您。”
说罢两人转身离去了。
制笔工匠的太太在隔壁的厨房不安地向这边张望。
武藏见客人回去了,边望着小手、小脸满是墨迹的孩子们,笑着说:“喂喂。不要随意分神停下手来。好了,快点学习,先生和你们一起来。别人的讲话声、蝉声,此时都不应该进耳。小的时候你们若是容易懈怠的话,长大后就得像先生一样,还得习字。”
四
黄昏——
武藏准备了一下。
穿上了一条和服裙裤。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了,找个理由拒绝了吧……”
隔壁的太太前来阻止,差点儿没哭出来。
可是,没过多久,前来迎接的轿子便到了露地口。并不是像畚箕一样的町轿,而是类似于神舆一般的华丽轿子。早晨来的那两名侍卫和一名小随从跟在一旁。
怎么回事?附近的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轿子的周围站满了人。见武藏被侍卫们迎着进入轿内,有人煞有介事地对周围人说,看来这位私塾先生出人头地了。
一些孩子叫来其他的孩子。
“先生可了不起了!”
“能坐上那种轿子的人,特别厉害。”
“去哪儿呢?”
“不再回来了吧?”
放下轿帘后,侍卫在前开道道:“喂,让一让,让一让。”
并命令抬轿的人:“快点儿。”
天空在晚霞的辉映下,红彤彤的十分美丽。人们议论纷纷。在人群散去后,隔壁的那位太太出门倒了趟混着瓜子、饭粒的脏水。
这时,有一位带着年轻弟子的和尚走了过来。看僧衣可以知道他便是禅家的云水和尚。只见他秋蝉一般的黝黑皮肤,眼睛深深凹陷在高高的眉骨下,眸子闪亮。年纪四五十岁,这种禅家人的年纪一般很难凭凡胎肉眼猜测得出。
身材瘦小,没有赘肉。可是声音却很洪亮。
“喂,喂——”
他扭过头去望着身边长得像越瓜一般的弟子。
“又八吧。又八和尚!”
“是,是。”
沿街迷茫地边张望边行走的又八和尚慌忙来到秋蝉一般面孔的云水和尚面前,低下了头。
“还不清楚在哪儿吗?”
“在找。”
“你没来过这里吗?”
“是,通常是他来山上找我。”
“在这附近打听一下吧!”
“是。打听一下吧!”
又八向前走了几步又马上返了回来。
“愚堂大师。愚堂大师。”
“嗯——”
“知道了。”
“知道了吗?”
“就在前面的那个露地口上有一块看板。上面写着启蒙学堂,无可什么的。”
“哦,是在那里呀?”
“我去看看吧。愚堂大师,您在这里稍候。”
“算了。我也去吧。”
前天夜里和武藏说了那些话的又八心里一直没放下自己说的话,不过今天却有惊喜降临了。
两个人望眼欲穿等待的愚堂和尚终于从旅途中归来,来到了八帖寺。
又八赶紧将武藏的事情讲给愚堂和尚,愚堂和尚还记得武藏。
“见见面吧,把他叫来吧。不,他已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子汉了,我去找他吧。”
就这样,愚堂和尚只在八帖寺稍事休息,便在又八的带领下来到了町内。
五
武藏知道亘志摩在冈崎本多家的家臣中属重臣之列,可他对这个人本身却了解甚少。
到底为什么叫自己过去呢?
武藏百思不得其解。莫非是与昨晚在矢作桥附近受袭有关?自己当场砍了两个黑衣打扮、貌似家臣的胆小鬼,难道那两人是他的家臣,现在他要拿这个来说事?
另外,他也想到,是不是平日里总是盯着自己的那些人觉得自己不太好对付,于是最终决定亮出幕后黑牌亘志摩,打算跟自己正面交锋。
不管怎么说,不像是有好事,武藏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到底打算怎样应对呢?
若是有人这样问的话,他只有一句话。
随机应变。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关键时刻纸上谈兵是万万使不得的,只有随机应变才是上上策。
这变到底是在途中发生呢,还是在自己要去的地点发生呢?
一切还是未知数。
在轿子中,感觉就像在海上随波摇晃一般,外面一片漆黑,只听得到松风的声音。从冈崎城的北郭到外郭一带松树很多。现在要通过松林了吧——
……
武藏看起来就像完全没什么警惕之心一样,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样子。
“吱”的一声响起开门的声音。
抬轿人的脚步放慢了,微微传来家臣们的说话声,还有能感受到柔弱的灯火。
“到了吧!”
武藏下轿望去。有殷勤的侍从默默迎来,将他引入宽敞的客厅。这间客厅的卷帘都是卷起的,四面通达。带着涛声般声音的松风源源不断,让人感觉清凉无比,忘记夏日,烛火明灭。
“在下亘志摩。”
主人见客人来了,赶紧接应道。
看起来他五十岁左右,很刚健,典型的三河武士。
“在下武藏。”
武藏以礼相回。
“请不要拘礼。”
亘志摩点头致意,很亲和的样子。
“听说前天您在矢作桥附近斩杀了两名年轻的家臣。……这是事实吗?”
他单刀直入地说道。
不容过多的思虑,武藏也没有包着藏着的意思。
“是的。”
接下来会怎样呢?武藏凝视着亘志摩的眼眸。烛火的光影在两个人的脸上匆匆变幻。
“关于这件事。”亘志摩慎重地开口了,“我必须向您道歉。武藏先生请您原谅。”
他低下了头。
可是武藏还没有真的接受这份歉意。
六
据亘志摩说,他是今天才听说这件事的。
“当时有消息传到藩内说是死了两名家臣,是在矢作桥附近被斩杀的。经调查,他们是与您进行的打斗。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但是之前我并不知道您就住在城下。”
看起来亘志摩并不像说谎,武藏也姑且信之。
“关于他们为什么会在暗处偷袭您,我也进行了仔细调查。原来我这里的客人中有一位东军流的兵法家,叫三宅军兵卫,是他的门人和藩内的四五名人员一起谋划了此事。”
“……哈哈?”
武藏还是一副不解的样子。
随着亘志摩接下来的话,武藏渐渐明白了。
三宅军兵卫的直系弟子中,有以前在京都的吉冈家做过事的人,本多家的弟子中也有几十人是吉冈门流的人。
这些人互相传言:最近在城下有一个化名无可的流浪武士,据说他就是在京都的莲台寺野、三十三间堂、一乘寺等地相继杀害吉冈一族,让吉冈家绝了后的宫本武藏。
他们对武藏的深深的怨恨于是又被勾了出来。
真是碍眼。
去收拾收拾他。
最终这些人决定:杀了他。
他们精心地策划,不想前夜却失败了。
吉冈刀法之名,威震各地,现在仍引来不少人的羡慕之心。可以想象得到,在它全盛时期,各地有多少门徒。
光本多家学习过吉冈刀法的就有几十人。武藏相信此言不虚,也理解那些恨自己的人的心情。可是这些情感只是单纯的人类情感,他们并未站在武门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对于他们的鲁莽而卑劣的行径,我今天在城内已经斥责过他们了。由于客人三宅军兵卫先生的门人也混在其中,三宅军兵卫先生也感到非常不安,想见见您,道个歉。……怎么样,若是可以的话,我把他叫过来,介绍你们认识吧!”
“三宅军兵卫先生若是不知道就算了吧。作为一名兵法者,前夜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不,不管怎么说还是见一见吧!”
“道歉什么的就算了。若是谈论武士道的事情的话,我倒是挺想见一见久闻大名的三宅军兵卫先生的。”
“您跟三宅军兵卫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那我快去请他吧!”
亘志摩赶紧让家臣去传达意思。
三宅军兵卫先生看起来是先等在附近别的房间了,不多时就带了四五名弟子进来了。这些弟子都是堂堂的本多家家臣。
七
应该是没什么危机了。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亘志摩将三宅军兵卫和其他几个人一一介绍给武藏。
“前天夜里的事情,请不要放在心上。”
三宅军兵卫为自己门人犯下的错事道歉道。而后大家在席上毫无嫌隙地聊起了武术及世事。
武藏问道:“在世间很难找到与东军流同流的流派,这个流派是先生创始的吧?”
“不,并不是我创始的。”
三宅军兵卫说道。
“我的老师是越前的人,叫川崎钥之助,传书上记载他在上州白云山上闭关研习,开创了一代流派,其实他应该是向天台僧东军和尚学习的东军流技艺。”
说罢,三宅军兵卫又重新审视了一下武藏。
“以前听你的名字感觉你应该是更年长的,没想到这么年轻。以此为机缘,想请你指教一下。”
他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武藏轻轻带过:“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并带着辞行的意思向亘志摩说道:“路我还不太熟。”
三宅军兵卫赶紧挽留道:“天还早呢,回去时派人将你送到町口吧!”
然后三宅军兵卫接着说:“当我听说有两个门人在矢作桥被你斩杀了时,我赶过去看了尸体,感觉两具尸体的位置和身上的刀痕并不相称,有些奇怪。……问了那个逃回来的门人,他说他也没看清,只知道你是双手同时持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可真是世上少有的招数,可以称之为双刀流吧?”
武藏笑着说,自己并没有下意识地去使用两把刀。总是一体一刀,还不能自称为双刀流。
可是三宅军兵卫他们依然不依不饶地说:“太谦虚了。”
三宅军兵卫针对两刀的技法没头没脑地问了各种近似于幼稚的问题,到底是怎样练习的,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同时将两把刀运用自如,等等。
武藏已经不想多留了,怎奈这些人抓住他问个不停,一时脱不开身。突然他发现在壁龛处立着两把枪,便向主人亘志摩征求能否借一下这两把枪。
八
得到主人的许可后,武藏从壁龛处取下这两把枪,来到在座各位的中间。
“……咦?”
大家疑惑地望着武藏,不知他要干什么。莫非是想通过两把枪来回答关于双刀的问题?
武藏左右两手持枪,单膝跪地。
“双刀是一刀。一刀亦是双刀。左右手为一体。所有的一切,道理都是一样,理之极致,无流派之分。——献丑了。”
说着持枪展示起来。
“请别见笑!”
话音刚落,随着“呀”的一声呐喊,只见两把枪“呼呼”地被挥舞起来。
在座的都感觉到了枪起枪落带起的风声,两把枪在武藏的肘间旋成了空心麻线球。
……
震惊四座。
武藏收手,使枪回到原位,微笑道:“失礼了。”
说完便向各位辞行,转身出门了。
在座的依旧愕然于刚刚的表演,还没有缓过神来,原本说回去有人送武藏,可武藏已经出门了,却没有人跟出来。
回首望向门内——
在飒飒的松风、墨色的夜幕中,客厅的灯依旧意犹未尽地微微闪烁。
……
武藏松了一口气,终于从刀光剑影的威胁中脱身了,这道门如虎口一般。在这些摸不清底细的对手面前,武藏是毫无防备之策的。
既然真实身份已经暴露了,也酿成了不可挽回的事件,武藏觉得冈崎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该趁今晚速速离开了。
“和又八的约定怎么办?”
武藏在思虑中前行。就在看到冈崎人家的灯火时,意外地从路旁的小佛堂处传来又八欣喜的声音。
“哦,武藏兄。——是又八,担心死我了,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
见武藏平安归来,又八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怎么在这儿?”
武藏疑惑不解。
这时,他发现在小佛堂的房檐下还坐着一个人,顾不上听又八细细道来,武藏向那个人走去。
“这不是禅师吗?”
武藏赶紧叩拜。
愚堂和尚望着武藏的背,片刻说道:“好久不见!”
武藏也抬头道:“好久不见!”
短短的一句话中汇集了万千感慨。
对于武藏来说,能将自己从无为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人非泽庵或愚堂和尚莫属。日也盼夜也盼,终于盼到了愚堂和尚。武藏仿若仰望月空中的明月一般,仰望着愚堂和尚。
九
又八和愚堂和尚都为武藏今晚是否能够平安归来颇为担心。都怕武藏被困在亘志摩府中无法脱身。为了了解状况,他们决定去亘志摩府邸处一探,正好走到此处。
又八和愚堂和尚在武藏刚刚起身离开后,找到了他的住处,听隔壁的太太说起经常有人在附近盯着武藏,今天看到有侍卫来找武藏。他们担心不已,决定去找找武藏,若发现有什么不妥,看看有无应对之策。——通过一旁的又八,武藏了解了这些。
“劳烦二位费心了,真是过意不去啊!”
武藏表示深深的谢意,依旧跪在愚堂和尚的面前,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终于,他盯着愚堂和尚的眼眸大呼一声。
“大师——”
“怎么了?”
就像母亲能读懂孩子的眼神一般,愚堂和尚感受到了武藏的无助。
“怎么了?”
愚堂和尚又问了一遍。
武藏握住愚堂和尚的双手。
“距在妙心寺参禅第一次见到您,已经过去十年时间了。”
“是啊!”
“虽然过去了十年时间,可是我到底前进了多少,如今内心充满困惑。”
“怎么还说这样幼稚的话。应该相信自己。”
“真是遗憾。”
“什么?”
“修行上总是有达不到的境界。”
“整天都将修行挂在嘴上的人怎能达到什么境界?”
“那么,我要是放弃呢?”
“那就前功尽弃了。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懂的无知者。”
“放弃的话,会一落到底,攀登的话,却总也攀登不尽,有种悬在峭壁上的感觉。我现在有些手足无措。——不管是对于剑道还是我自身,都是一片茫然。”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大师——我期盼与您见面的这一天已久了。我该怎么办?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摆脱现在的这种迷惘与无为的状态。”
“这个我也帮不上忙,只有靠你自己。”
“请让我和又八在您的膝下聆听教诲吧。或者,请您给我当头棒喝,将我从虚无中唤醒吧。……大师,拜托了!”
武藏伏地恳切地请求道。脸几乎都粘到了尘土,虽未流泪,声音哽咽,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苦闷。
可是,愚堂和尚却不为所动的样子,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小佛堂的房檐处,只唤了一声:“又八,走吧!”
说完他便先行一步了。
十
“大师——”
武藏起身追赶过去。拉住愚堂和尚的衣袂,祈求答案。
愚堂和尚默不作声,只回头望着武藏。见武藏并不罢休,愚堂和尚说道:“空无一物。”
稍顿了顿,他又道:“还有什么?你祈求得到什么施与——只有一喝。”
愚堂和尚举起了拳头。
仿佛真要打过来。
……
武藏松开愚堂和尚的衣袂,还想说些什么,愚堂和尚却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
武藏茫然地望着愚堂和尚的背影,又八上前急急地安慰武藏:“禅师好像不喜欢太啰唆。我在寺里看见他时,跟他将你的事情,还有自己的想法,希望拜他为师的意愿都说了,他都没有仔细听,他当时只说‘是吗,那么先给我系下草鞋’。……所以你也别说太多了,跟过来就是了。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再多请教他吧!”
这时,远处愚堂和尚停下了脚步,又唤了又八一句。
又八应了一声,又对武藏说道:“好吧,就这样吧!”
说罢,又八匆匆朝愚堂和尚追了上去。
看来愚堂和尚对又八比较满意。武藏很羡慕被愚堂和尚收为弟子的又八,也反省自己缺少又八那份单纯与坦率。
“是啊。再怎么多说也无用!”
武藏感觉到体内有喷薄欲出的火焰在燃烧。哪怕是刚刚那一拳真的打来,武藏也是甘心接受。若是未能在此处得到提点,就这样分别了的话,还要何时才能再见面呢?在这不知存在了几万年的悠悠天地之中,短短几十年的人生转瞬即逝,能见到难以见到的人,是多么难得啊。
“这难得的机缘。”
武藏热泪盈眶,定定地望着愚堂和尚远去的背影。
我要失去这宝贵的机缘吗?
不行!
我一定要祈求到我所要的答案。
武藏赶紧向愚堂和尚的方向追了上去。
不知道愚堂和尚知不知道武藏跟在后面。
他没有回八帖寺,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再回去,他已经过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出了东海道,向京都的方向走去。
愚堂和尚若是住在带米自炊的小客栈的话,武藏便睡在小客栈的檐下。
每当早晨看到又八为师傅系草鞋,武藏就为友人而感到高兴。而愚堂和尚即使看到武藏也并不打招呼。
武藏并未因此而感到委屈,还怕惹愚堂和尚烦,只远远地恭敬地跟着。——从那天夜里起,武藏将留在冈崎陋巷的避风居所、那里的一桌一椅,竹筒插花,还有隔壁太太、街坊里姑娘们的倾慕目光,与藩内人的恩怨纠葛都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