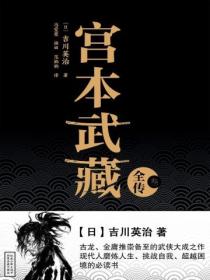鹫
一
拜托别人推荐自己,却因忠利公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临时反悔。
“算了,没关系。”角兵卫想。
“爱护后辈是应该的,可是也不该一味纵容他的错误。”同时角兵卫也自省。
不过他还是非常喜欢小次郎这样的人。他认为小次郎绝不是凡人。
因此,即使现在他被夹在中间很尴尬,也只是一时气恼,过几天就会好的。
“唉,也许这正是小次郎的不凡之处。平常人的话,一听说能面见主君,定会高兴得不知所以。”角兵卫又开始善意地揣测,可能有这种气概的年轻人才更靠谱,小次郎值得拥有这种气概。
这段时间,角兵卫一直值夜,心情、气色也有些不好,所以也就没再见小次郎。第四天早晨,角兵卫来到小次郎这里。
“佐佐木小次郎先生——昨天我从藩邸回来的时候,忠利公又在催促你的事情。怎么样,少主说想在练箭场见你,可能也想见识下你的弓法吧。就轻松些,过去拜访一趟吧!”
小次郎窃笑,没出声。
于是角兵卫又说:“要想做官的话,事前拜见主君是惯例,并没有辱没你的意思。”
“但是,大人。”
“嗯——”
“若是不合他的心意,拒绝了我,那我小次郎以后还怎么见人。我还没到把自己当作商品去供别人挑选的地步。”
“可能是我表达的有问题。少主并没有这个意思。”
“那大人是怎么回复忠利公的?”
“——这个,我还没有说什么。不管怎么说,少主应该是一直都在等着见你呢!”
“哈哈哈哈。让恩公为难,真是抱歉啊!”
“今天我也值夜。少主可能又会问我这件事。那就不要让我再为难了,到藩邸去一趟吧!”
“好的。”
小次郎卖人情般地点点头。
“那我就去一趟。”
角兵卫听到这句话,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非常高兴。
“今天怎么样?”
“可以,就今天吧?”
“那再好不过了。”
“时间呢?”
“少主虽说什么时候都行,但我想若是下午的话,他定能抽出时间去练箭场,气氛也不会太拘束。”
“明白了。”
“那我们就定下来了。”
角兵卫又确认了一下,便出门去藩邸了。
之后,小次郎开始悠然地进行行装准备。虽然小次郎经常表现得像个豪杰一样,说从不在乎装扮,其实他是一个很爱打扮,很注重形象的人。
他让仆人给准备了新的轻罗上衣、舶来裙裤、草鞋、斗笠,又向仆役长问:“是否有马?”
因为听说大人将换乘白马寄放在了坡下花店内——小次郎来到了花店,今天老大爷也不在。
这时,向寺庙那边望去,花店的老大爷、僧侣、附近的人们都聚集在那儿,一阵骚乱。
二
怎么了——小次郎也赶了过去,原来地上有一具盖着粗草席的尸体。大伙此时正围在一起商量如何处理。
不清楚死者的身份。
年纪很轻。
据说是名武士。
肩头被深深地砍了一刀,涌出的大量血迹已经干涸为黑色。身上好像没带任何物品。
“我见过这名武士。在四天前的傍晚。”花店的老大爷说。
“哦?”
僧侣和附近的人们都将视线移到老大爷身上。
老大爷还想再说点什么时,感觉自己的肩膀被人敲了敲,不由得扭过头来,正看见小次郎。
“岩间大人的白马寄放在你的店里了,我要用用。”
小次郎说。
“哦,是的。”
老大爷赶紧行了个礼。
“您这边请。”
说罢,引着小次郎走回花店。
小次郎抚摩着被从小屋里牵出来的**青马说:“是匹好马。”
“是的,真是匹好马啊!”
“我走了。”
老大爷望着骑在鞍上的小次郎,赞叹道:“与您真是很配呀!”
小次郎从荷包中取出一些金子,给老大爷说:“老大爷,麻烦买些香火、鲜花供上吧!”
“嗯?供给哪位?”
“刚刚见到的那个死人。”
小次郎说罢,绕过坡下的寺门前,向高轮街道骑去了。
呸,他在马上吐了口唾沫。看到不吉利的东西后的生理反应——四天前的那个月夜,他用刚磨好的“晒衣竿”杀的这个人,此时仿佛就跟在马后。
“没有理由怨恨我。”
小次郎在心中为自己辩解着。
在炎热的阳光下,小次郎骑着白马招摇而过。町里的百姓、旅行的人、正在行走的武士都躲闪着他的马,扭头望向骑马人。
他那在马上的矫健身姿,即使走在江户街头,也是引人注目的——人们都很好奇地想知道他是哪家的武士。
在正午时分,小次郎到达了细川家的藩邸。安置好马匹,一进邸内,就见岩间角兵卫远远迎来。
“你来得正好。”
角兵卫欣喜地迎接,就像在忙自己的事情一样。
“来擦擦汗,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刚刚已经有人去通报少主。”
角兵卫忙不迭地准备上麦茶、冷水、烟草。
“请您去练箭场吧!”不一会儿,一名侍卫前来引路。
小次郎按规定将“晒衣竿”交给这里的家臣保管,自己只带了小刀过去。
细川忠利正在练习弓箭。说是要在夏天每天连续百射,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很多近侍围着忠利,帮忠利取箭、拭汗倒水。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屏息观射。
“毛巾,毛巾。”
忠利立起了弓。
汗水流进眼睛,看起来已是颇为疲倦了。
角兵卫伺机跪下禀报。
“少主。”
“什么事?”
“佐佐木小次郎已经来了,在等待拜谒。”
“佐佐木小次郎,是吗?”
忠利依旧像没什么事发生一样,顺手拿起一支箭搭在弦上,叉开脚,将弓箭举到头顶。
三
不仅仅是忠利,家臣们谁都没有看小次郎一眼。
终于,百射结束了。
“水,水。”
忠利长出一口气说道。
家臣们赶紧提来井水,倒进大脸盆中。
忠利赤膊拭汗、洗脚。旁边的侍从则忙着为他提袖、换水,丝毫不敢怠慢。可是纵然他有前呼后拥的侍卫,此刻看起来也绝不像一名大名,倒像是一个野人。
身在故乡的老太爷三斋公是一位讲究喝茶的人。上代主人幽斋公更是一位风雅的诗人。因此小次郎认为,在这样的家风下,第三代忠利公也一定是一位高雅倜傥的公卿贵人。今日一见,大吃一惊。
洗过以后,几乎没怎么擦,忠利就把脚伸进了草鞋,“啪嗒啪嗒”
地回到了练箭场。一看到仍在那里不安地等候的岩间角兵卫,忠利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
“角兵卫,我们见见他吧!”
忠利吩咐侍从在帷幕的背阴处放上坐具,背对着九曜星的家徽坐下了。
看到角兵卫招手示意,小次郎来到忠利的面前跪下了。在这个爱才惜才的年代,觐见的人还是需要遵守礼仪的,忠利赶紧说:“请坐。”
坐下的话便是客了。小次郎站起来,点头行礼道:“恕在下无礼。”
小次郎说着面对着忠利坐下了。
“我已经从角兵卫那里了解了你的一些情况,故乡是岩国吗?”
“是的,正如您所说。”
“岩国的吉川家很有名。你的祖辈是吉川家的侍卫吗?”
“很早以前,近江的佐佐木自成一族,室町幕府灭亡后,母方隐居乡里,并没有食吉川家的俸禄。”
就这样,谈了些有关家族、亲缘的事情后,忠利又说:“以前曾出任官职吗?”
“我还没有过主家。”
“听角兵卫说你想来这里任职,你觉得这个藩哪点比较合你的心意呢?”
“我认为贵藩是一个值得以死奉命的地方。”
“嗯——”
忠利看起来挺中意的样子。
“武道是……”
“严流。”
“严流?”
“是我自创的兵法。”
“有何渊源呢?”
“我曾学习过富田五郎左卫门的富田流,也曾师从故乡岩国的隐士片山伯耆守久安学习片山的神速拔剑法,加上在岩国川河畔斩燕练剑时,悟得的一些东西,自创了这个流派。”
“哈哈,严流——是根据岩国川命名的吧?”
“您明察秋毫。”
“真想见识见识啊!”
忠利一一看过周围的家臣。
“有谁和佐佐木小次郎比试一下吗?”
四
这个男人就是最近经常听说的小次郎啊。
比想象中的年轻啊!
大家从刚才开始便一直在打量小次郎,一片赞叹。此刻忠利突然问:“谁和佐佐木小次郎比试比试?”
大家面面相觑。
小次郎却无半分介意,脸上泛着红晕,一副正等着这一刻的样子。
看大家没主动上前的,忠利指名道:“冈谷五郎次。”
“在。”
“在关于矛与刀的争论中,你不是力主矛更好的吗?”
“是的。”
“正好是个好机会,试试吧!”
冈谷五郎次接到指令后,上前一步道:“不才,在下向您讨教了!”
小次郎很有气势地点了点头。
“请。”
双方虽然也殷切地行了礼,但是让人感觉有股寒意。
在帷幕内打扫的人、整理弓箭的人,此刻也都聚集到忠利的身后,等待观战。
即便是一天到晚把武学放在嘴上、用刀或弓就像用筷子般熟练的人,也很少有机会能有场真正的比试。
反倒是说起这样的话:“在战场上作战和平日里的比试,哪个更让人有压力呢?”
多数武士都会很实在地说:“是比试。”
战争是集团性的行为,而比试是单打独斗。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从头到脚都要提起万分的精神来战斗——在比试中,不会有人替你挡枪挡刀,不会有喘息的机会。
——此刻气氛紧张,冈谷五郎次的朋友都挺替他担心的。但是见五郎次还是蛮镇定的,也就稍稍安心了,觉得他应该不会输。
细川藩并没有矛术专家。幽斋公、三斋公都是历经战场,步兵中倒是很多人善用矛。而矛术并不是奉公人的必备技能,所以藩内没有请相关的指导教师。
在这里面,冈谷五郎次相对来说,要算是善用矛者了。他不仅有实战经验,平时也勤于练习,算是用矛老手了。
“请稍候。”
五郎次和忠利、对手打过招呼后,静退到一旁。他要进行一些准备。
这些早晨笑脸出门,晚上就可能横尸而归的奉公武士,他们习惯每天都换上干净衣物。此刻退下备战的五郎次,心里泛上一丝凉意。
五
完全放开,随时准备迎接挑战的小次郎,已经选好了作战地点,等在了那里。
小次郎提着借来的三尺长的木剑,连和服底襟都没有撩起,很是英姿飒爽。即使你带着怨恨的眼光看他,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雄姿。
像雕一般勇猛、美丽的身姿和表情,让你感觉是那么的自然,丝毫没有异状。
会怎么样呢?
看到小次郎的异彩,其他侍从都对冈谷五郎次燃起了关切之情,不安地向五郎次的方向望去。
五郎次这边已经沉着冷静地做好了准备。他将矛头用湿布做了番包裹。
小次郎看到后说:“五郎次大人。你那是什么准备啊?要是怕不小心伤到我,大可不必这样大费周章。”
话虽是用很平常的口气说的,听起来却很傲慢。五郎次用湿布包裹的这个矛是曾在战场上助他一臂之力的短刀形菊池矛。柄长九尺有余,从手握处到前端,涂有贝壳色的泥金画,矛头菖蒲式的,有七八寸长。
“用真矛就行。”
五郎次知道小次郎在嘲笑他多此一举。
“行吗?”
五郎次望着小次郎说道。
主君忠利和周围的朋友都暗暗地给五郎次加油。
(对,就是这样!)
(加油——)
(杀了他!)
小次郎就像催促他快点开始一样,也凝视着五郎次,强硬地说道:“是的!”
“要是这样的话……”
五郎次解开了湿布,握住长矛的中间,走上前来。
“悉听尊便。不过既然我用真家伙,你就用真剑吧!”
“不,这个就行!”
“不行。”
“算了。”
小次郎高过他的声音说道:“藩外的人怎能在他家主君面前拿真剑,这样做就显得我太不成体统了。”
“那么……”
五郎次依旧不能释怀的样子,紧咬嘴唇。忠利见他这个样子,替他捏了把汗。
“冈谷五郎次。不要有什么顾虑。别管他怎么说,做好自己的。”
明显,忠利的声音也有些激动。
“那么……”
两个人互行了注目礼,都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突然,小次郎迅速后退。
小次郎就像被粘在竹竿上的小鸟一样,顺着矛柄下方,向五郎次的身体刺去。
五郎次还来不及用矛,一转身体,矛尖从小次郎的颈后划过。
——“啪啪!”矛尖被弹开。小次郎的木剑又趁势呼啸着刺向五郎次的肋骨。
“唰,唰,唰!”
五郎次后退着,紧接着向旁边一跳。
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小次郎又是一剑过来,五郎次不得不再次躲闪。
——就这样,五郎次就像被雕追赶的隼一样,疲于躲闪,最终矛也“咔嚓”一声断了。瞬间,五郎次的魂儿也像被从肉体中硬拽出来了一样,一声呻吟。看来,胜负已定了。
六
回到伊皿子的“月之岬”的家中,小次郎问岩间角兵卫。
“我是不是有些做过了——今天在主君那里?”
“哪里,非常棒!”
“我回来之后,忠利公没说什么吗?”
“没说什么。”
“应该说些什么吧?”
“确实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嗯……”
小次郎显然并不满意角兵卫的回答。
“不管怎么说,最近应该会有通知的吧?”
见角兵卫这么一说,小次郎道:“能不能出仕无所谓……只是觉得忠利公名不虚传,是位明君。希望能够投靠他——虽说如此,这也是要靠机缘的。”
角兵卫也逐渐感觉到了小次郎的锋芒毕露,昨天看到他那桀骜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了一些反感。一直以来当作晚辈来爱护的他,如今看来,已经成为羽翼丰满的空中之雕了。
昨天,忠利本来想找四五个人来试试小次郎,看到他和冈谷五郎次比试时,招招凶狠,忠利发话:“了解了,行了!”
结束了这场比试。
五郎次虽然随后苏醒过来了,但是脚跛了,左大腿和腰部的骨头被打断了。小次郎暗自得意,让他们见识了自己的本领就行,即使不被录用也没什么遗憾的。
可是,小次郎静下心来考虑自己前程的时候,还是不免有些不安。
将来的托身之所,除了伊达、黑田、岛津、毛利,就要数细川家了。大阪城还有遗留问题,将来难免风云变幻,若是投错了藩,将来怕是会沦落为穷浪人或是逃亡者。谋求主君时,必须得看得长远些,否则可能会因半年的俸禄,搭上一生的俸禄。
小次郎思量再三,只要三斋公在领地屹立不倒,细川家的地位就会稳如泰山。考虑到将来的前程,还是登上这艘大船比较稳妥,更能确保自己高枕无忧。
(可是,门第越高,越不容易进。)小次郎不由得又有些心焦。
过了几天,小次郎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看看冈谷五郎次。”
说罢便出门了。
这天,他是徒步而行。
五郎次的家在常盘桥附近。面对小次郎的殷勤探望,五郎次微笑着说:“比试见高下,我恨自己技不如人,你还特意……”
说着,眼里露出泪花。
“谢谢你的关心!”
小次郎回去后,五郎次对枕边的友人说道:“真是位不错的武士。
原本以为他太傲慢了,没想到他还挺讲情谊,挺注重礼节的。”
小次郎则是料准了他会这么说。
结果五郎次果真对后来的探病客人说了这番赞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