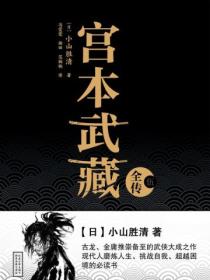鸣动
一
二月,城中梅花齐放。武藏门人为数越来越多,仅此已够武藏忙碌。不过,晚上,武藏仍常闭居一室画画,当然是画花。
大渊和尚把武藏面对的女性譬喻为花,真是深得个中三昧。武藏将所画的花比作阿通,比作悠姬,比作由利公主,而拿起画笔。
和尚认为武藏似乎为女性,尤其为由利公主而烦恼,这也一言中的。不过,这并不是说武藏恋慕公主。
武藏已排斥恋慕之情,甚至说已完全加以克服,也不为过。他虽然没有恋慕之情,却尽力想拥有宽宏之心,以便坦然体悟女人寄情于他的心思。
不论对阿通或悠姬,武藏似乎都没有感受到她们的爱情,因而,他虽已达万里一空之境,但那是冰寒无人无爱亦无情的世界。
他还没有穷究这世界,就想下凡,与人共同思考、共同行走。如果无心接受他斥之为修行之敌、愚昧之思的人情与爱欲,武藏第二人生的建设,即大渊所说的“回向”,终究难有所成。
可是,这对武藏却是一大难事。武藏还未完全从无人之境下到凡间。甚至只能说下凡,但身上仍佩带以前斩断情丝的刀剑,小心翼翼注视天空的彼方。就是这刀剑、这眼睛阻碍了喻之为花的情。
武藏摊开纸,握着画笔,却闭上了眼睛,眼帘上浮现出由利公主的姿容,真像高贵的白百合。武藏想一口气把浮现眼帘的白百合画在纸上。
突然,“轰!”传来了天地鸣动的声音,武藏吃了一惊,望着窗外。
一道闪光从黑漆的天空像枪尖般朝武藏脸上刺来。
“哦!”武藏躲过,不禁握住身边的大刀,拔刀出鞘刺之。武藏额上已沁出汗珠。
“啊!天上之敌!”武藏怒吼。当然,这是武藏的幻觉,而其根源则存在武藏心底。他提着大刀跃下庭院。
“来吧!”武藏睨视天空。
二
不久,武藏也发觉这是幻觉,但心已为天空的世界所吸引,不禁认为眼不能见的敌人已盘踞天空彼岸,正欲捕捉自己。
“是这家伙,这家伙才是我的敌人!”武藏狂喊。
心已凝结为争斗之气势,像冰一样冷明,既无爱花之情,亦无悯人的慈悲。所有的人都已从武藏心眼中消失。
“这家伙,是谁?”武藏又高叫一声。是神,是佛,还是魔?无论如何,总之,不是人间世界的人,是统治人,给人生老病死之苦,剥夺人类自由的东西。
“喂。”武藏把大刀刺向天空,前后上下挥动,眼不能见的火箭接连射来。
“老,老爷!”仆人和助从石灯笼的背后,以战栗的声音唤道。
“谁?”武藏注视天空,反问。
“是和助。”
“下去!没事!”
“不,老爷!”
“你这家伙。”武藏扑过来,往石灯笼砍去,但刹那间突然清醒过来,收住了刀。
“哦,是和助吗?有什么事?”
和助顿然跌坐在地,说道:“老,老爷,城,城里有使者来。”
“什么,使者?是谁?”
“阿部先生。”
“哦。”武藏收刀走入客厅,老内侍阿部弥一右卫门正在等候,年轻武士冈部在招呼。
“阿部先生,辛苦了。有什么事?”武藏心情烦躁,就座后即问。
“主上从傍晚时分起,觉得身体不舒服,提早就寝,但突然觉得很痛苦……”
“什么?”
“立刻延请典医1,痛苦稍减。主上下令召见武藏,所以深夜打扰,敬请上朝。”
“好,马上就去。”武藏即时更换衣服,与阿部一起徒步离开城中府邸,这时,又传来如雷鸣般的“轰隆”声……“先生!是阿苏山喷火,已经是第二次了。”
“原来如此。”武藏仰视黑暗的天空,不祥的预感逐渐压上心头。
1 典医: 即藩主御医。
三
武藏蹑足走进忠利寝室,枕边坐着长冈佐渡。两人互望一眼,表情忧郁。
“主上,武藏来了。”佐渡轻声传达。
忠利静静张开眼睛说:“到这边来。”
武藏膝行靠近。
凝注着武藏诊断般的目光,忠利脸色苍白,表情并不痛苦。
“我是武藏。”
忠利把脸转向武藏,说:“哦,夜半让你受累了。我想见见你。”说完后,莞尔一笑。
“真叫我大吃一惊,但看到尊颜就安心了。”
“以前也曾有过,突然呼吸困难,胸部像被勒住般疼痛。现在好多了,这样躺着休息,实在很轻松。”
“不过,别太勉强。”
“是啊,这是我的毛病,已经很熟悉,不会勉强,幸好不在江户。”
“主上,请休息。武藏在此守候。”
“没事的。”
“是……”
“武藏,你不后悔出仕为官吗?”
“哪里的话!”
“最近,大渊来,谈到你的事。大渊说武藏想画花哪!”
忠利停了一下,又说:“武藏,我也想要你的画,能画吗?”
武藏起初表情有点惶恐,旋即泪水潸潸而下。
“主上!我画画看。”
“真的,我等你的画呵。”忠利望着武藏微笑,旋即闭上眼睛。武藏也噤口不言。
宫邸内悄然无声。不久,忠利发出沉稳的呼吸睡意了。
之后,过了四个半时辰,佐渡向武藏示意,要他退下。武藏摇摇头,用眼睛说:“爵爷先退!”
佐渡以目为礼,再注视一下忠利的睡脸,走出去。
武藏纹丝不动地端坐着。
过一会儿,第三次阿苏火山的鸣动声又传来了。忠利动动身体,并没醒过来。武藏手按匕首柄端,赫然而怒,似欲维护忠利,以防死神潜进……
烛台灯光下的武藏,有如生根地底的磐石一般,凝重不动。
四
阿苏火山已经很久没有冒烟,爆发后开了新的火山口,开始积极活动。火山的鸣动,连熊本也听得见,天晴的日子可以看到火山口的冒烟。
忠利的病势从第二天起日有起色,看来可保无虑。但藩里的人都惴惴不安,仿佛阿苏山的爆发是不祥的预兆。忠利是很有人情味的名君,所以家臣为忠利的病体都深感痛心。父亲三斋还健在,世子光尚已成年,继承人大可无虑,但暗中为藩之前途而忧的气氛却弥漫着:“如果主上发生万一之事……”
武藏见忠利逐渐好转,第三天就回府邸,但他依然不放心。他未对门人说一句话,只对慢一步回来的求马助说:“病势不轻,若坚持不住,变故难防。”
“师傅,今天不是说想起床看看吗?”
求马助吓得变了脸色。
武藏摇摇头,说:“大意不得!”
“这么说,很危险啦?师傅!”
求马助端坐,说道:“刚才还召见我说,你还未行冠礼1 吧,我替你取名字2,你外祖叫藤兵卫,是位相当豪勇的武士,你可取名藤兵卫信行,以武藏为干爹3 加冠。主上比平时更亲切慈祥……”说着泪水滂沱。
“真的?”武藏也连眨眼睛,交代道,“求马助,明天就举行加冠礼吧。当然,我做你的干爹,快回去告诉父母详情。”
“是,向师傅叩别。”求马助急忙起身离去。
之后,武藏闲居室中端坐,微闭双眼冥思,旋即起身走向大门。
“先生,要出去?”年轻武士冈部急忙赶过来。
“嗯,到岛崎去。”
“腰间的东西呢?”
“不用。”武藏只带短刀,不带大刀,悠然走出大门。
五
天快黑的时候,武藏到了白梅庵。
由利公主觉得很意外,把武藏引到客厅,即问道:“听说忠利先生身体违和,病况如何?”
“一度相当痛苦,现在看来相当舒畅了。”
武藏一如往常,以谨严的姿态回答,接着,现出和蔼的笑容,说:“由利小姐,今天我是来问问你的心意。”
公主惊讶地反问:“我的心意?”
“最近,由于你的诘询,我也接连试着去探查我的心。不错,不只对女人,就是对男人,我也实在太过任性。而且以兵法修行为借口……”
1 冠礼:江户时代十二岁到十六岁的男子即成人,成人仪式主要为剃前发,缩短衣袖。
2 取名字:行冠礼时,去乳名取正名。
3 干爹:江户时代,成人仪式时,都以实力者为孩子的父亲,替孩子加冠帽,当时称为“乌帽子亲”,此处姑且译为“干爹”。——译者注公主还不懂武藏的意思,也不随声附和。武藏毫不计较,继续说下去。
“但是,今沐忠利侯温情,知人情之美,愈发反省自己的任性。”
公主终于懂得武藏的内里含义,却冷冷地微笑说:“武藏先生,只此而已?”
“不,不是。”武藏激烈地回答。
“那请问,你觉得悠小姐的事如何?”
“以今思之,当以悠公主为妻。为此,必须斩杀对公主抱有邪念的主水。”武藏坦诚回答。
“通小姐呢?”
“跟阿通别离,以当时的心境而言,乃事非得已,但应更亲切地体谅她的心。我同情心不足。”
“我懂了。”公主深受感动,俯下了头。现在该轮到自己的事了。
武藏击膝说:“由利小姐。总之,对阿通和悠姬,我都没有由衷尝试去了解她们的爱情。真抱歉,你的情形也一样。虽然为时已迟,但我愿仔细体贴你的心意,然后才知道该怎么做。由利小姐,请莫矜持,坦诚说出你的心中话,好吗?”说着,他凝眸注视公主。
六
由利公主的脸赫然燃烧起来。但立刻变得僵冷到苍白。接着开口说:“武藏先生,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到如今,还说什么假话?”
“好,那我说。”公主直视武藏的脸。“一眼看见你以后,再没有第二个人是我的梦,我内心的火,我片刻难忘。领养孤儿,与天主教徒战斗,向权势挑战,这些都是为了要把内心高燃的火焰转移罢了!武藏先生,懂了没有?”
武藏点点头。“我非不知。我对你怀着敬意,也怀着骨肉般的情爱。”
“武藏先生,你的冰冷就是这样!对悠小姐的态度亦然……”
“说的不错,不过,现在不同了。”
“请你坦诚地由衷接受好吗?”
“可以。以前,你没有告诉我。”
“我的勇气不足。好,现在我告诉你,请你迎我为妻。”
武藏蜡样白皙的脸上立时泛起血色。
“主上痊愈后,即来接你。”
“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放下刀剑。这不是要你停下探求的战斗。而是希望你放下杀人的刀。”
武藏猛吸一口气,眼中漾着决然之色。
“好!主上痊愈之后,我要和你一起到田野耕种。”
“今天,立刻就放下刀?”公主追问。
“由利小姐,现在,我正跟潜近主上的死神战斗。用这剑……”
武藏拍拍短刀。“所以今天不带大刀。”
“武藏先生。”公主的脸又燃烧起来,眼睛闪亮地冒着热气。
“武藏先生。”公主膝行贴近武藏。武藏全身热烘烘,眼前逐渐朦胧,但他清楚看见一朵牡丹花漂向眼前。
“由利小姐,你好美!”武藏喘着说,手却不敢抚摩。
“由利小姐,主上痊愈后,我一定来接!一定来接!”他说着长身而起。
七
当晚,阿松到白梅庵来访。
阿光端出茶水和点心,退下后,由利公主脸上洋溢着平时所无的喜气,说:“松小姐,我跟武藏先生订婚了。”
“哇。”阿松吓得退了一步。公主微笑说:“很意外吧?今天傍晚,武藏先生突然来访,要听听我的心中话。所以我下决心把一切说出来了。”
阿松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其实,在先生带阿光母子到这里来的归途上,我也曾下决心痛责他对女人的冷酷。他似乎也很烦恼,说要好好想想由利公主的事。想不到……”说着她又瞪大了眼睛。
“不错,松小姐,武藏先生近来已到了这样的心境,但我认为他绝不会接受我的爱情。总之,依我看来,剑便是武藏先生的妻子,是他终生爱恋的妻子。他为什么能跟这妻子别离,而跟我结合呢?”
阿松点头说:“是啊。对大多数武士来说,剑只是护身卫妻的工具,先生却相反,为剑而宁舍女人的情爱,无疑地,剑已替代了妻子。”
公主加重语气说:“所以啊,松小姐,我讨厌刀,进而想从这世上消灭刀。”
阿松似有未解,却点头说:“由利小姐,以后呢?”
“我正面向武藏先生表明心迹,这还是第一次。但我想,毕竟仍是徒劳,所以谈过许多话以后,我无礼地迫他迎我为妻。于是……”
公上热切地说:“武藏先生意外地答应娶我。我还不满足,要他放下刀。武藏即时答应放下刀。”
“哇!连刀也不要啦!”阿松愈发不解。即认为武藏的剑已代替了妻子,放下刀的武藏!阿松简直无法想象。
这时,公主的脸上突然展现了悲愁,接着露出寂寞的微笑,悄声说道:“不过,松小姐,武藏先生的允诺附有一个条件,一切待忠利先生病体痊愈哪!”
八
次晨,武藏上朝奉职时,忠利倚坐棉被上,靠着小茶几。
“哦,主上,气色好像很不错……”
“嗯,从昨天起,好多了。叫你挂心啦。”忠利说着微微一笑。
“千万别勉强。”
“怎么会勉强?又不是第一次生病,一切都很熟悉。幸好有佐渡这些能干的老臣可以倚靠,行政方面的事务不必烦心。”
“不错。请耐心疗养。”
“嗯。武藏,花画得怎么样啦?”忠利说着又微微一笑。
“会画啦……已经可以清楚把握花姿了。”
“武藏,真的?”
“主上,痊愈后,一定送一张给主上观览。”
“真的?”
“主上,武藏也决心像一般人一样娶妻了。”
忠利表情滑稽,说道:“武藏,让我猜猜新娘是谁,好吗?”
“哦?”
“是由利!”
“惶恐,惶恐。”武藏满不在乎地回答。
“由利是杰出的女性,与你实在是天作之合。以前曾跟佐渡谈过这件事,准备做你们的媒人。但生病了,很遗憾,只好请佐渡代理了。”
武藏有点惊慌。
“主上,我想等主上痊愈后再做最后决定。所以,媒人还是主上。”
“什么,我痊愈之后?武藏,不必这样斟酌。我想早日看见你们在一起。尽快择吉日迎娶好了。”
武藏严肃地俯伏道:“此事可暂缓。”
“是吗?”忠利表情寂寞。
武藏凝视忠利,道:“主上,武藏还没有这种余裕。”
“没有余裕?”
“武藏正在拼命。”
忠利侧首沉思。武藏挺直上身,重新坐好。
“我正跟烦扰主上的病魔拼命战斗,无分秒的余裕。”
“什么?”忠利吃了一惊,又望武藏,眼中却潸潸流下泪珠。
“武藏,我知道了,不管多苦,我都觉得你正在我背后,跟病魔不停地作战。”忠利感动地说。
九
武藏接着说:“今天就依主上的意思举行求马助的加冠礼。”
说完,他向忠利施礼,旋即从花畑馆退下,往寺尾新太郎府邸走去。
寺尾府邸,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以武藏为干爹,遵古礼,顺利完成加冠。
然后,以武藏为中心,邀请亲友,举行庆祝酒宴。
武藏先向剃掉前发、青年模样的求马助——藤兵卫信行敬酒,并向在座诸人,以干爹身份致意:“我要顺便说一下,武藏今天决定由信行继承本流派。今后愿各位多加提携。”
武藏以前曾将这事向忠利透露,新太郎也察觉到。但今天却突然在众人面前宣布出来,来宾的惊讶自不待言,连新太郎也吃了一惊。
新太郎慌忙开口说:“师傅,这,这太……还是未成熟的年轻人。”
武藏明朗地微笑,反问道:“新太郎!你认为信行还未成熟吗?”
“是……无论如何,今年只不过十七岁。”
“哈,哈,哈……新太郎,你试他一手看看?”
武藏回答,并环视一座,开口说道:“我走遍六十余州,因对方要求而加指导的已超过万人。但能继承本流派的始终没有发现。有而且只有这个信行,今已九州无敌,虽年少却天赋异禀。于今即使不经我指导训练,亦能自臻名人之境。”
这简直是异乎寻常的礼赞,在座诸人听来深觉扫兴。
但信行本人却不动声色,脸露笑容,泰然自若。
武藏拿起酒杯,放在左边架上,说:“信行,砍砍看!”
武藏的手仍伸着。
“是!”
信行手按短刀,说声“抱歉!”随即扭腰,“咻!”刺目的锐光!分成两半的酒杯!短刀早已回鞘。
武藏静静把手收回。
坐在末座的阿松,泪水横溢。
十
忠利的病势眼看日趋好转,但到二月底,又再度恶化。
三月是上江户朝觐的时期,忠利已经无法赴江户。于是他向幕府阁老1 陈述病情,请求延期赴江户。
三月上旬过后,病势日渐严重,藩士们的忧愁也越来越深切;虽然无人出口做不祥的预测,但暗中朝拜神佛、祈其平安愈痊者,与日俱增。
八代老君侯也遣使探病,自己则到妙见社祈愿。
江户阁老当然接到了延期赴江户的请求。
阁下病情已达天听,敬请宽心。将遣典医以策兼程前赴贵处,切望慎加休养。
由阿部对马守、阿部丰后守及松平伊豆守署名发出慰问函,接着,名医以策也从京都赶赴熊本。
将军家光似乎相当痛心,特派曾我又左卫门为上使,西下慰问。
武藏大部分时间都守候在忠利寝室,端坐一隅,如岩石般耸立不动。他正与潜近的死神战斗。
1 阁老:当时幕府由四位老中组成内阁,故称阁老。
“武藏……”忠利病痛时,时唤武藏名字。
“武藏在此守候,切请宽心。”武藏即时回答。忠利便放心地沉入梦乡。
忠利的肌肉日渐凹陷,同样地,武藏的双颊也慢慢消瘦。
在这期间,身体比较舒服时,忠利便把武藏唤到枕边,微笑着说:“武藏,病愈赴江户时,你也一齐去!”
三月十五日晚,忠利已完全进入危笃状况,重臣与近侍相继奔赴花畑馆。武藏仍顽强地继续端坐寝室一隅。
深夜,佐渡把武藏唤到另室,重臣皆列席。
“爵爷,何事?”
佐渡有点口吃地说:“武藏,深为哀痛,主上的天命已尽。”
武藏庄肃问道:“谁说的?”
“典医都这么说。而且已束手无策,说只有静祈冥福……”
“……”
“此外,受托祈祷病愈的释迦院常观也说,若继续违抗天命,只有增加痛苦。”
“那各位重臣的看法呢?”武藏亮着眼睛反问。
十一
佐渡垂下眼睛,泪水潸潸而下。其他重臣也都俯首,一会儿,佐渡抬起头,沉声说:“武藏,大家都万分希望主上不要跟我们诀离,但是,看主上日夜痛苦的情状,只好希望早日仙去,以免再受痛苦……”
武藏表情紧张严肃。
“再问一次,典医、大渊和尚、常观阿阇梨都说天命已尽吗?”
“是的。大渊和尚甚至希望主上平静归去……武藏,很抱歉,想请你暂且离开主上身侧。”
“什么?”武藏赫然瞪目以视。
佐渡额现汗珠,说:“常观说,主上安谧的病况因有妄执的恶魔盘踞身侧,致有所执着而忧闷痛苦……呵,不,武藏,我们都知道你的忠诚。不会认为你是恶魔。”
武藏脸上泛起血丝,冰冷苍白,猛然垂下头。紧握的拳头不断颤动。
佐渡等重臣屏息守望着武藏。
过一会儿,武藏抬起了头。“知道了。”
“武藏,抱歉。”重臣一齐低头致歉。
武藏回到忠利寝室坐下,肃容端坐,俯伏道:“主上,我已尽力战斗到今日。武藏,就此告假。并请采纳诸臣意愿,平安归去。再见,主上……”声音低沉得难以听见,泪水频频滴落到榻榻米上。
佐渡慌忙说:“武藏,你还要继续为主上……”
“不,是告辞……”武藏抬起脸,静静地起身而立。
武藏走向大门的时候,守候在各房间的家臣,以各不相同的心情目送着武藏。
听到常观阿阇梨视武藏为恶魔而加排斥的话语,有的人认为想必如此,有的人却生气地说:“混账!常观才是缩短主上生命的妖僧。”
武藏不坐轿车舆,走回城里的府邸。看他那沮丧的样子,年轻仆人吓了一跳,问道:“老爷,主上的病情——?”
“呵,没有变化。”武藏只回答一声,便进入居室端坐。
不久,久已不响的阿苏火山又“轰隆”鸣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