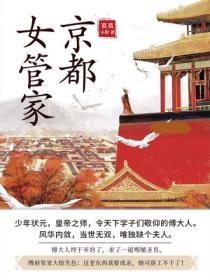花以香难得连面汤都喝完了,她饱饱的放下碗,嗯了一声,“对呀,怎么了?”
“香香,你知道这是哪吗?是京城啊。”钱白果痛心疾首,“你就算受了打击,也不能堕落的当个菜农吧,你想以后旁人怎么喊你,卖菜女?!”
花以香不解,“卖菜女怎么了,我不偷不抢,我自己种菜得菜,种瓜得瓜。”
“……”钱白果没词反驳了。
*
宿疾难熬,傅时第一次希望时间能停顿下来。
可这段时日重又接管内阁,首辅头衔摆在那,无论新入阁的两位还是之前他的老同僚倒是服帖的很,至少明面上,无人敢违背他的命令。
本就是京中受人追捧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说大白于天下,却真是逃不出有心人之眼。
“首辅大人,近来可好?”
随着傅小灰领进来的男子,一身便服,行走间两袖摇摆,身形矮小,满面笑容。
傅时抽空抬头看了一眼,眉头微挑,“李大人?”
“呵呵,多年不见,大人还是如斯俊秀……而冷淡呢。”
礼部侍郎李正宁,为官多年,据朝中人评价,精于算计,多好古玩,处事作风问题一向是监察御史们钉牢不放的话题,两人之前并无太大的交际,因为李正宁的顶头上司才是礼部之首,位列六部之一常在傅时跟前。
傅时仍是在桌前疾笔,垂下头去没有看见对方眼里一闪而逝的精光。
“小灰,去沏茶……”
“不用,属下冒然前来拜访,实为一桩私事。”
李正宁掩唇轻咳起来,面色微变。
许是傅时的大名,太过有震慑力了,不然以他户部侍郎的身份,也不用如此做小俯低到不敢失仪咳嗽。
“嗯?”轻哼了声,傅时明显不愉,却按耐着继续批注。实乃他头疼,不愿与人打机锋,若为正事,李正宁越级来他这儿本就不合情理,这样一个在官场八面玲珑的人,不会犯傻,而所谓私事,傅时没有多少耐心听他们说。
李正宁往前靠了靠,并未言语,那厢傅小灰会意,便无奈的放下刚要为傅时研磨的动作,往外头走。
直到门被掩上,李正宁才开口。
“我手里有几根草药,不知大人有没有兴趣?”他顿了顿,又笑着补充,“月半,明石……还有,昙现。”
“嘀嗒……”墨水滴在宣纸上,瞬间染黑了一小片。
傅时手里的笔被他搁置,他抬眼望过去,眯了眯眼,似乎第一次认识这个人一样。月半明时,花正开时……这句话是他父亲傅维祯绝笔手信上的一句话,至今他都未曾参透,原来是代指草药名?那么它们分别对应什么药材呢?
李正宁只是笑,三角眼本就比常人稍显难看,笑成一条缝之后,更是渗人。
“条件。”
傅时冷冷的吐了两个字。
却引来对方更加恭维讨好的笑,李正宁身子往前又是凑近了,神情敛着,眼神里却掩不住的得意,“这两年未见,大人似乎更为爽直。”
傅时不置一词。
李正宁见好就收,收敛了下神色,点头间,忽而从手里拿出一竹简,“您先拿着,药材稍后我便遣人奉上。”
傅时并没有接,好似在思量。
后者却不急,很有耐性的举着手,眼睛至始至终都在傅时的脸上,却没有窥到一丝异样,除了那滴墨。
“时间可不等人,大人,若是不放心,我还有个大礼一并送上。”李正宁不等傅时搭话,他将手中竹简,放在桌上,未了手指还轻点了几下,笑容微敛,“这是一份名单。”
傅时垂眼扫了一眼,而李正宁收回手,又作揖,态度一直很卑微。
“当年京中闹匪贼,大人曾悬赏数百纹银捉拿……却是无果。咳咳,有没有想过,贼子不在外,而在内呢?”
外贼易擒,内鬼难捉。两年前他离京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有人盗走了他父亲留给他的亲笔遗书,为了那封信他亲自追拿许久,最后却是石沉大海,再无踪迹。
傅时终于拧了眉,而满意的看他神情变换的李正宁,噙着意味深长的笑,往后退开。
“恭候首辅大人佳音。”
一会儿大人的套近乎,一会儿首辅大人的客套恭敬,真不愧是连御史台几个老狐狸都撬不动的能臣。
身为礼部侍郎,上有礼部尚书压着,下有礼部员外郎顶着,他居于中位,却游刃有余,这些年下来,不仅使得礼部一跃成为六部之首,还能让皇上赞誉有加。
之前倒是未曾注意这样的一号人才。
“大人……”
李正宁走后,傅小灰见他神色不好,忙端了热茶奉上。他刚才虽然没有听见两人的谈话,但是能揣度些事情,这几日来府里投诚的官员确属不少,大多是往年不曾来靠拢的,而往年积极奉承的反倒来的少了,这便是怪异之处。
在傅小灰眼里,傅时可是个撼不动的大树,在朝内顶梁,在家自然也是房柱。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些个墙头草的官员说变了脸色?
就在傅小灰疑惑不解时,傅时揉了揉额角,按压下胸中翻涌的恶感,他这几日时常觉得乏力,这种无力感同以往宿疾发作并不同。
而李正宁的到来无疑是坐实了他的猜测,他不是宿疾又犯,而是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发现,自己被人下过药。他不由得想起猝发急病的父亲,同比旁人,父子二人感情深厚,小时候就比对母亲更对父亲多一份尊敬。父亲的溘然长逝,如同一座在他身后的大山突然就倒了,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想不明白,人生在世的意义。
“那边还没有消息么?”
沉默了很久,傅时依旧没有去动那份竹简,他自任首辅多年,本以为事情已经平息,没想到愈演愈烈。
“回大人,没有,这两年那边一直在追查……”傅小灰想起傅维祯去世之后,傅时心中一直梗着一根刺,心绪跟着沉重起来。
傅时此刻脑海里烦乱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傅小灰和许多人都不知道的内情,当年他能荣登首辅之位,以最年轻的资历擢升内阁,实则是傅维祯的安排。
他现在都还记得一向宽容温和的父亲突然间严厉起来,对他的言行举止诸多挑剔,之后没多久就生了病,临终前将他叫到榻前,叙说了许多为官之道,也娓娓道来当年他是如何在内阁立足,从小做大……或许是积攒的太多的过来人的经验想要一股脑儿倾倒给他,又或许是太急切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他从未有过的脆弱和无奈,甚至是对生的眷恋全都暴露出来,被傅时看在眼里,终生不能忘怀。
等他说的再也说不动了,才开始沉默,细细碎碎的喘气,将最后的话,说的断断续续,傅时努力克制着情绪,将他的一字一句拼凑起来,又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
傅家曾一度衰微,直到傅维祯进士及第,才又有了些起色,然而要带动整个家族的兴盛,太难了,靠一个人更是难上加难,可家族的使命落在他头上,他只能挑着,也曾外放离京,说什么为民为国,不过是无奈之举。等他磨炼回朝,先帝年盛,处于权利顶峰,而今上,就是当初的太子逐渐成长,身边少不了挤了一堆拥护者。
权利,永恒的争夺点。
太子是嫡皇子,却不是长皇子。宫闱之争,哪朝哪国没有?分派结党,阴谋算计……傅维祯选择了辅佐储君,筹谋划策,为了目的设局构陷,借刀杀人……又何尝能随心?
新帝登基,他位列百官之首……世人只看见那无上的荣耀,谁会关心那背后的血泪心酸。
“阿时,我只愿你当年为国为民读的圣贤书,能用之正途,万事莫不过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傅时抬手揉了揉额角,驱散纷乱的思绪回到眼前的宣纸上。
“大人,你两日状态实在不好……这……”
下面的话勉强咽回去,因为傅时终于拆开了那竹简。
*
“不用再劝了,我是不会参加的。”花以香不知道第几回说这句话了。
钱白果也不知道自己第几回劝了,“香香,我错了,不会让你去假唱假演的,可你想想等你菜种出来,西北风都凉了。我们三个人得吃得穿,良玉也不小了也要送去学堂,我打听过了,京城里的私塾不是光有束脩就能进的,还得送礼,你自己算算看这一样样……”
花以香长叹了口气,她脑袋都快被钱白果说大了,“好了,好了,你说这些也没用,我参加也不是就真的能得第一,那么多人呢!”
钱白果却笑了,“香香,你说这话的,从小到大有哪样事情,你但凡愿意去做了,没有成功的?”
花以香沉默了,当然有,她在傅时面前,笑也无用,哭也无用,人家根本没多看她一眼。
在屋内看书看不下去的良玉,蹦蹦跶跶的过来了,他也不知道听了多久了,小脑袋晃了晃,在两人间坐下了,小短腿在凳沿蹭了蹭。
“今年这红人赛要想夺魁,基本是不大可能了。”他说着,一本正经的叹了口气,“你们是不知道长公主府的封彤郡主,太后最宠爱的外孙女参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