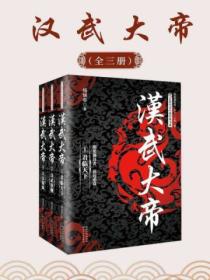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七章 连环案毁两重臣 兴国计出双英杰
丞相府现在的人员十分充实,仅长史就设了三位。
这可不是三位平庸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曾做过主爵都尉的朱买臣、做过右内史的王朝和做过济南王相的边通。
从表面上看,派遣巡察使的谏言是庄青翟提出来的,而其实都是出自这三位幕僚的主意。
他们的本意是要借丞相的政绩压一压张汤等人的气焰,以泄各自在任上饱受欺凌的恶气。却不料这事反而被张汤接了过去,又一次成了向皇上邀功的机会,并且还白白搭进了右内史和大农令两条人命。
自严异以“腹诽罪”判处弃市以来,塾门往往是“一鹞入林,鸦雀无声”,只要远远看见张汤过来,朝臣们就都封了口,一个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生怕因为嘴唇动了几下惹来“腹诽”大祸。
可人总是“终日而思”的精灵,封得了口,封不了心。
这会儿,丞相署中三位长史还是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愤,议论起近一年来发生的是是非非。
说到义纵,大家心知肚明,他不是死在拘捕杨可下属这件事情上,而是在不治京畿之道,太怠于职事了。
至于严异就不免太冤枉了,这么一个忠于职守、勤政廉直的人却遭此下场,实在是太悲惨了。
朱买臣在火盆边暖着手,看着窗外的春雪,纷纷扬扬地飘过官署回廊,在墙根落了薄薄的一层。他触景生情地长叹一声道:“雪里埋尸,终不得久啊!”
正在起草公文的王朝停下手中的笔道:“听阁下的语气,这是话里有话啊!”
朱买臣伸了伸脖子,神秘地问道:“想听吗?”
边通就在一旁打趣道:“你就别卖关子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买臣掩上门,说话的声音低得只有两位同僚听得见。
“知道么?御史大夫当年办的李文一案近来有了新证。当年李文被牵扯进巫蛊案,就是张汤用钱买通小吏鲁谒居做的假证。事隔多年,有人看见张汤不惜屈御史大夫之尊,亲自为他按摩病足,怀疑其有把柄握在鲁谒居手中。鲁谒居死后,他的弟弟犯了事,想通过张汤帮忙,孰料他竟然佯装不知,这下便惹恼了鲁谒居的弟弟。他一纸文书,将当年张汤与鲁谒居合谋诬陷李文的事告到了廷尉府。”
朱买臣说到这里,眨了眨眼睛道:“据说,接到这文书的是廷尉府的一位中丞,名叫减宣。此人与张汤有隙,于是便私下里把案情查得清清楚楚,但却慑于张汤今日的权位而没敢上奏圣听。”
边通思索道:“阁下的意思是,这事若是让皇上知道了……”
“呵呵……”
“呵呵……”
三人相视而笑,那意思都在不言中。
王朝做了一个握拳的姿势:“到时候,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信扳不倒这个奸佞。”
门外响起踩雪的脚步声,三人急忙打住话头,回到自己的案几前,一本正经地批阅文书。
进来的是丞相庄青翟,他一屁股坐下,气喘吁吁地骂道:“小人!十足的小人!”
朱买臣一听这语气,就知道丞相一定与御史大夫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一边整理案头文书,一边劝解道:“大人何必和这个奸诈阴险之徒生气呢?”
庄青翟长叹一声道:“能不招他倒也罢了。皇上竟要张汤追究老夫的失察之罪呢?”
朱买臣“哦”了一声,他是知道这事的原委的。
自大司马霍去病去世后,皇上一直精神不振,早朝的时间比过去短多了。已过了四十岁的皇上也越来越听不进逆耳的话。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孝文皇帝寝园瘗钱被盗的案子。
这瘗钱是埋在地下专供亡灵用度的,先帝的瘗钱被盗,这是继李蔡盗卖景帝寝园堧地之后又一重大的案件。庄青翟不敢怠慢,立即找到张汤,相约在朝会上面奏皇上。
“先是李蔡盗卖堧地,现今又有人盗掘瘗钱,人心不古如此,我朝这是怎么了?”
张汤道:“此案干系重大,下官亦不敢妄断,还是奏明皇上为妥。”
“本相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依本相看来,此案像是乡野无赖所为。”
张汤道:“这很难说,李蔡不就是一个例证么?”
“御史大夫精通我朝律令,既是如此,你我就如此奏明皇上了。”
“好!一切就依丞相。”
谁知到了朝堂,张汤却一改宫门前的承诺,声言他不知陵园瘗钱被盗之事,倒认为丞相奉诏祭祀,经常出入于陵园,有失察之责。
刘彻大怒,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严责丞相,诏命张汤会同廷尉府严查此案。
面对朝夕相处的几位幕僚,庄青翟伤心地说道:“李蔡死后,老夫在这个位置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想竟遭此诬陷,也该老夫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
庄青翟返朝不久,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身受张汤诬陷之苦,别的不说,就他身边的三位,哪一个不曾受过他的排斥呢?
王朝在庄青翟对面坐下,轻描淡写道:“此乃预料中事。李蔡之后,他原以为丞相非他莫属,孰料皇上却选了大人,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边通却恨恨道:“姑息养奸,必有后患,平时丞相总是劝我等息事宁人,现在他却将手伸向大人了。”
元光年间入朝的朱买臣毕竟年长些,他走到三人面前说道:“我们现在与丞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不能让小人得志,奸佞横行。”
“那依阁下之见呢?”
朱买臣让一个曹掾在门外守着,才压低声音对众人道:“如此这般……”
庄青翟有些惊恐:“这行么?”
“只要有了人证,他即便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买臣冷笑道。
第三天一大早,雪还没有住,天气很冷,可张汤却早早地出了门。他伸手抓了一下飘在空中的雪花,踌躇满志地笑了。
一个“失察”罪名加在庄青翟头上,他这回死定了。他在心底很鄙夷这个书呆子,他以为大汉的丞相是那么容易做的么?
哼!我可以将李蔡击倒,你庄青翟就更不在话下。
庄青翟一死,朝廷将没有谁能比他有资格更适合做丞相了。他虽觉得这雪来得晚了些,但却预示着这个已拉开序幕的春天该属于自己了。
从身后传来的赶车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张汤回头看去,庄青翟的车驾换了两匹红马,竟以飞快的速度从他的身旁冲了过去。
车轮扬起的雪尘,落到张汤脸上,十分冰冷。
庄青翟板着面孔,目不斜视,似乎张汤是素不相识的路人。
走完司马道,进了塾门,庄青翟一边跺着脚尖的雪,一边谦恭地向各位同僚打着招呼。他看见张汤进来,故意高声说道:“等天晴之后,本相请大家到咸阳原上一游,以解朝事之累。”
看见刚刚康复的卫青,庄青翟越过其他同僚,迎了上去,关切地问道:“大司马近来可好?”
卫青微笑着点了点头。
庄青翟又大声道:“只要大司马出现在塾门,大家的心里都是亮堂的。”
朝臣们都十分吃惊,懦弱的丞相大人怎么一下子又刚强自信起来了。
张汤进来得晚,只看到最后的一幕。他心里不免觉得好笑:都快要死的人了,还乐个什么?
辰时二刻,刘彻出现在朝会上。他一眼就看见卫青出现在大臣中,那种久违的愉悦一下子就涌上了眉头。霍去病走后,他就是中朝唯一的中心了。
刘彻知道他的这种欣慰已通过脸上的笑传给了卫青,因此,在微微点头之后,他就把议题直接转到瘗钱被盗额度案件上来。
“张爱卿!先帝陵寝瘗钱被盗案可有眉目?”
张汤回道:“臣正与廷尉一起加紧侦查,不日便有结果。”
张汤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庄青翟接着道:“皇上,瘗钱一案已真相大白。”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就像晴天响了一声炸雷,不仅张汤,连刘彻也很吃惊。
前日朝会,这个庄青翟还语焉不详,时隔二天,竟然像换了一个人。大家纷纷睁大眼睛,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
庄青翟今天反应分外敏捷,不等张汤回过神来,就在皇上和朝臣面前爆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皇上!臣奉诏四时祭祀于陵园,失盗之事自有臣责,因此臣连夜搜查,现已查明,此案是御史大夫张汤与商贾合谋。”
庄青翟这话一出口,他并不着急详说细节,而是冷静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果然,朝臣中一阵**。
“堂堂御史大夫,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真乃我朝奇耻。”
“平日里标榜清廉,清风两袖,今日……”
这样的结果,是刘彻没有想到的。虽说张汤为人刻薄,善于逢迎,心里不那么坦**,觊觎相位也由来已久,这些他都了解。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李蔡犯案后,他思之再三,最终选择了庄青翟继任丞相。可要说他与别人合谋盗取先帝寝园瘗钱,这让他难以置信。
张汤来到庄青翟面前,冰冷地质问道:“无凭无据,丞相竟信口雌黄,诬陷下官,就不怕皇上治罪么?皇上!此乃丞相诬陷之词,请皇上明察!”
事关外朝重臣,刘彻不得不谨慎。
“庄青翟!你看着朕说话,此事果真与张汤有关么?”
“臣身居宰辅之位,对汉律了然在心,岂能随意诬陷他人?”
“可有证据?”
“这是臣审理张大人旧友、商贾田信的口供,请皇上圣览。”庄青翟说着,就从袖间拿出一卷绢帛,递给包桑。
刘彻大体浏览一遍,上面不但有作案的时间、地点、经过,还有嫌犯的画押。
田信在口供中说,他在盗掘陵寝瘗钱时,不料被张汤发现,于是,他便与张汤商议,将所盗之钱藏起来,等将来事情平息,再与张汤平分。
刘彻放下口供便问道:“朝廷之事,商贾是如何知道的?是否有人勾结商贾呢?”
张汤道:“也许有吧?”
“那请御史大夫告诉朕,此人是谁呢?”
张汤知道,此时说错一句话,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选择了沉默。
“好个张汤!”刘彻阴沉着脸道,“你乃当朝御史大夫,位居三公,竟然如此下作,蔑视先帝,盗取瘗钱,该当何罪?”
张汤一时无措,只有跪在地上。
刘彻又问道:“盗贼何在?”
庄青翟道:“现正在长史王朝府中看押。”
“张汤!”刘彻愤懑地将口供掷向张汤,厉声道,“证据在此,你有何话可说?”
张汤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以“见事风生”而自信的他竟无法将许多细节串成一个完整的情节。他无法相信这些事情与自己有关,可事实摆在面前,连他都无法推翻。可他就是想不通,这些证据是怎样造出来的。
他绝望地跪倒在刘彻面前道:“皇上圣明,臣区区小吏之子,能有今日,全赖陛下。臣虽位居三公,却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岂可有此污行?丞相所言,乃是诬陷,请皇上明察。”
毕竟张汤曾以执法严峻,给刘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他曾以办事干练,赢得了刘彻的青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彻真希望廷议能有助于廓清案情真相。
“众位爱卿!”刘彻扫视了一圈殿内的群臣,“朕将此案交与廷议,众卿有何看法,不妨一一奏来。”
皇上的话一出口,张汤就颓然跌坐在地,知道自己完了。这些年得罪了多少人,陷害过多少人,排斥了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正因为如此,后来有案件他都尽量不在朝堂议论,而习惯于事后单独奏禀皇上。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时候,一个听起来很平静的声音却让他感觉到大殿在摇晃。
这是卫青的声音,他从怀中掏出一札上书,呈送给刘彻道:“此臣前日到太医坊诊病,路过北阙,恰逢廷尉中丞减宣,他说经多年查访,当年李文一案为张汤与鲁谒居合谋所为。他慑于张汤权位,要微臣转呈皇上,请陛下明察。”
张汤只觉得大殿的横梁塌了,直朝着自己的胸口压过来,他顿时昏厥了……
张汤的入狱,一扫大臣万马齐喑的局面,无论是朝堂上还是各署中,笑声多了,同僚之间走动多了。
但作为外朝宰辅的庄青翟却没有丝毫轻松。
皇上已几次在朝会上就盐铁和币制的变革进展太慢而斥责外朝,他也清楚在瘗钱被盗案中靠刑讯逼出来的狱词也很虚弱,一旦皇上知道了真相,他的头随时都会挂在长安东市的高杆上。
他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做几件实在的事情,提高朝野对新政的信心。
可早年倾心于黄老,后来改学儒家的庄青翟对农商关市之道根本不懂。他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为什么严异宵衣旰食,却在新政上毫无建树?一天,他在和长史们外出踏春时,把这个问题提到朱买臣面前。
朱买臣呷了一口茶道:“丞相应该知道,不是勤政廉直就能推动新政的。用非其人,越勤政,说不定离目的越远。”
庄青翟想了想,觉得这话是有些道理,于是便问道:“你说说眼下该怎么做?”
“依下官看来,新政要继续往前,须倚重两个人。”
“可是孔瑾和桑弘羊?”
“对!不是下官夸海口,一个孔瑾或桑弘羊,足以当一百个严异。”
“好!”庄青翟的眉头顿时展开了,他来回踱着步子道,“再过两天就是春分,你约他们两位到城外踏青,老夫要向皇上举荐他们。”
“好!”看着日色已近中午,朱买臣起身准备回府,脚刚刚迈出丞相公署,却被庄青翟拉住道:“若是能就新政拿出一些新举措,老夫在皇上面前说话就更踏实了。”
朱买臣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道:还用你啰嗦,就干练这一点说,你比张汤差远了。
清明节后的第五天,刘彻在庄青翟的陪同下,到渭渠巡视漕运了。
行前,他口谕给孔瑾和桑弘羊随行。
当包桑传完皇上的旨意离去时,孔瑾和桑弘羊无言相视许久,两人有种预感,他们的机遇来了。
春雪融后,渭河的水涨了不少,站在水监公署的楼台上举目远眺,虽没有汹涌波涛,却也浩浩****。漕运船只在渭渠口入渠转向东南,傍南山而去。撼天动地的号子随风在渠河之间回响。
白日当头照呀!
嗨呀!嗨呀!
渭水滔滔流呀!
嗨呀!嗨呀!
脚下步步稳呀!
嗨呀!嗨呀!
两眼朝前瞅呀!
嗨呀!嗨呀!
……
这情景和歌声,让刘彻想起前任的大农令来,他由衷地感慨道:“朕自推行新政以来,大农令中有所建树者,惟韩安国与郑当时耳。当年郑爱卿对朕承诺三年通水,结果还提前开了漕运。”
庄青翟听得出皇上是借着追怀故人,曲折批评当朝的臣僚们怠于政事,不思进取。他忙在一旁说道:“郑大人一世英名,实为臣等楷模。”
不料刘彻接下来的话却让庄青翟无论如何也不敢回应了。
“虽说张汤盗先帝陵寝瘗钱,罪该万死。然朕每每想起他的勤于政事、严于自律来,还是难以释怀。”
从水监署的楼上下来,刘彻和一干大臣沿着渭渠岸柳行间缓缓前行。
柳叶很瘦,透过树隙,可以看见因为无雨,麦子显得十分低矮,刘彻的眉毛又“锁”了起来。他在心里埋怨死去的严异,就觉得庄青翟此时推荐大农令很及时。
刘彻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孔瑾和桑弘羊道:“丞相举荐你们的奏章和你们的上书朕都看过了,今天要你们随朕出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陈奏。”
孔瑾上前一步道:“郡国之所以感到盐铁官营不便,不在新政本体,而在转输遥远,资费甚高。臣近来思虑,朝廷若能在盐铁产地设均输官,以京都实价就地收买,屯于官署,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既可以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利,又可以供给百姓之需求。如此,则盐铁官营名则符实,利在朝廷。”
刘彻又向桑弘羊问道:“爱卿也是这样看么?”
桑弘羊回道:“孔大人所言,亦臣之所见。只是臣以为,我朝元狩年间所铸白金,因郡国铸钱未能有效禁止,致使真假混淆,不仅使钱币失控,造成物价上涨,而且使朝廷失信于民。因此臣建议将铸钱回收,以利新币推行。”
此刻,庄青翟也在旁边建议道:“皇上还可诏令天下,非上林三官钱不能行于天下。”
徘徊了许久的盐铁官营和币制变法,终于在元鼎二年的春天有了新的思路,这让刘彻因为瘗金盗窃案而带来的阴影渐渐淡去了。
刘彻停下脚步,等孔瑾和桑弘羊拱手站在面前时,双手就分别按在他们的肩头:“明日早朝,朕就诏命孔瑾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望二卿勿负朕望。”
孔瑾和桑弘羊纳头便拜:“谢皇上隆恩,臣等当为社稷鞠躬尽瘁,肝脑涂地。”
其实,从皇上的决定中最受鼓舞的还是庄青翟。他希望皇上能因为新政的顺利推进而淡化对瘗钱盗窃案的印象。当晚,他兴冲冲地回到相府,就要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一起饮宴,庆贺风波的平息。
可朱买臣却不那么乐观,他知道皇上不是那么容易健忘的,而且这朝廷也不是平湖秋月,水波不兴,说不定在哪儿就会翻船。
夜阑席散,众人起身向丞相告辞时,朱买臣留下了一句让大家酒醒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诸位大人多加小心吧!”
但是,当日子平静的一天天走向春天深处,走向夏天的时候,仿佛一切真的过去了。
谷雨刚过,就从上林苑三官处传来喜讯:三官钱的流行杜绝了假币的流行。仅从京畿各县的情况来看,三官钱型范精准,成色足,尤其是铸造手段高妙,很难仿造。
孔瑾主抓的均输官也相继离京赴任。
让刘彻欣喜的是,孔瑾不仅深谙他的用人喜好,所选人才都是少壮精锐之士,而且都是商贾世家出身,熟悉贸易之道。大农府报来的奏章说,朝廷的财政状况近几个月也大有好转。
“哈哈哈!这个孔瑾,还真是个人才!”
刘彻每天阅读这些奏报,心情就像暮春的风一样,温暖中渐渐融入了夏日的热流。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再次出使西域的张骞也回来了。
社稷依旧,河山历新。
庞大的大汉使团和数十人的乌孙国使团走下咸阳原时,张骞一直在追忆着第一次回归时的感觉。然而,那辛酸和寂寞早已随大汉疆域的延伸和国力的强大而渺无踪影了。且不说他们此次一路西去,畅通无阻;就是所到之处,百姓更是倾城迎送。现在横桥对面迎接乌孙国使团的阵列,也让他找到了作为大汉使节的尊严。
张骞暗地打量了一眼身边的乌孙国使节昆窳,在心里暗笑乌孙国王昆莫的目光短浅,他竟然因为对大汉的孤陋寡闻,而对皇上联手破匈奴的诚意漠然置之。
偏安一隅就可以享国长久么?笑话!张骞目光中掠过短暂的鄙夷,旋即恢复了平时的热情。他指着前方道:“使君请看,前面就是皇上派来迎接使君的大行李息、右内史苏纵和典属国。”
昆窳“哦”了一声,口张得老大。他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长安的壮观,汉官的威仪,让他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
李息已经老了,却仍不失将军的气度和老臣的稳健,当张骞介绍昆窳时,他雍容大度地上前,以汉朝的礼节表示了对远道而来客人的欢迎。
“请使君到驿馆歇息,明日皇上将在未央宫前殿接见使君。”
李息邀张骞同乘一辆车驾,引导着使团朝长安城内走去。
途中,张骞对李息道:“此次没能说服乌孙国内附,下官甚觉愧对天恩,无颜见长安父老。”
李息抚着张骞的肩膀道:“使君两次出使西域,迢迢万里,风餐露宿,彰显大汉国威,何愧之有呢!”
当李息问他是否找到纳吉玛母子时,张骞伤感地摇了摇头:“当初离开时,下官特意在那里用石头垒了标志的,可这次去,大漠茫茫,那里早已被沙海掩埋。”
李息沉默了一会儿道:“闻听使君即将归来,我已向皇上辞归,并举荐你为大行令。”
他告诉张骞,在他离开长安的这些年里,朝廷发生了许多事情。李蔡死后,现任丞相是庄青翟,而御史大夫张汤因为涉嫌盗卖先帝陵寝瘗金而入狱。而经过这些事情,皇上也日见消瘦了。
一听到这些,张骞的心就一下子沉重了,他恨不得立即就去拜见皇上,他有许多话要对皇上说。
第二天,刘彻在未央宫前殿召见了乌孙国使者昆窳。昆窳转达了昆莫国王对他的问候,并献上了乌孙器物、果蔬和战马的清单。刘彻口谕,典属国会同少府寺,挑选大汉布帛、银器等,待昆窳返国时,一并回赠。他特别叮嘱庄青翟,在乌孙国使节逗留长安之际,一定要带他到各处看,让他多了解一些大汉的风土人情。
“睦邻方可邦兴,远交才可结友,互通才能开眼,此乃朕凿空西域之根本也。”
送走乌孙国使节,刘彻单独留下张骞。
一进宣室殿门,张骞就跪下了。
“未能说服乌孙国东归内附,臣有负于皇上重托,臣罪该万死!”
刘彻让包桑阻挡一切大臣来见,自己则拉着张骞相向而坐,一脸宽容地看着他,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
“国之邦交,在自愿互利,非一厢情愿可致。然朕相信,爱卿此次所获绝不亚于上回,快快与朕奏来。”
张骞隔着案几,向皇上做了一揖:“臣在乌孙国逗留经年,发现乌孙国君臣皆惧匈奴,毫无东归意愿。臣觉着与其徒留此地,耗费时日,倒不如多道出访,广结西域诸国。臣遂将随行三百余人,分为数拨,持我大汉符节,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臣东归时,这些使节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不久,将会有书报告于朝廷。”
张骞说着,便从随身带来的行囊中拿出新绘的西域各国图,一个个指给刘彻看。
“依臣观之,西域诸国,地广人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其地东接玉门、阳关,西则以葱岭为界。臣所遣副使,循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循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些国家,长期被匈奴奴役,臣要副使以大汉资财,厚贿其国,欲图使其臣服我国。臣启程回国时,赴安息副使差人捎来书信,言说我汉使达到安息时,安息有二万人出城出迎,盛况空前。安息百姓如今才知道,在万里之外,有大汉这个地域广大的国家,有皇上这样伟大的君主。”
刘彻的眼神随着张骞的介绍在西域各国盘桓走游,他嘴上连道:“此次出使,虽然费时不足五年,然爱卿对西域各国情势之熟稔,远远超过元朔三年。”
尤其让刘彻兴奋的是,当年他欲出蜀郡,从滇国通身毒道的设想,终于在此次出使西域时得以实现。
“身毒乃我朝西南之大国,其道一通,则商贾货流纷纷南下,源源不断,外可远播大汉文明,内可给富于民,充实府库。爱卿啊!你此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张骞忙道:“赖陛下神威,臣才得以西行。倘若皇上有意,臣愿再赴西域!”
刘彻看了一眼张骞,哈哈大笑道:“看看!爱卿的两鬓都白了,可壮志依旧。这倒让朕想起荀子的一句话,涂之人可以为禹也!朕与爱卿都不再年轻了,这些年来,朕看着建元以来的老臣走的走,去的去,人越来越少了,朕不免有些寂寥,这次爱卿回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朕已准了李息的辞呈,不日将任命你为大行令,早晚就在朕身边说说话。”
皇上话里的伤感,说得张骞心里酸酸的,忙道:“臣谨遵皇上旨意。臣……”
刘彻见张骞欲言又止,问道:“爱卿还有何事么?”
“臣听说李老将军去了,臣想到郎中令府上祭祀一下。”
刘彻背过身去,没让张骞看见他复杂的表情:“李敢他也去了。”
张骞十分吃惊,正要问皇上缘由,不料包桑这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皇上!出事了,出事了!”
刘彻立时一脸的不高兴道:“何事如此慌张?”
“廷尉来报,张汤在狱中自杀了。”
“什么时候?”
“今日凌晨。”
刘彻近乎发怒地喊道:“快传廷尉来见!”
……
三月初的明月悬挂在春寒料峭的夜空。
张汤终于醒了过来——他是被几只觅食的老鼠吵醒的,他环顾周围,黑漆漆一片,从墙角散发出的霉味告诉他,这是让许多人畏惧的廷尉诏狱。
这里曾关过大行王恢。
这里曾关过丞相窦婴。
他曾在这里把御史中丞李文送上了断头台。
现如今,终于轮到他了。
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墙角摸过来,用尖利的牙齿撕扯着他的鞋子,“吱吱”的叫声立刻招来鼠群,他用力甩开脚镣,砸死了咬开他鞋尖的那只老鼠,其他的老鼠才四散而逃。
这真是报应,当年他因为厨房丢肉,演绎了一出审鼠的闹剧,并且从此与汉律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制定的严刑峻法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多少有点作茧自缚的意味,并且现在连老鼠都不怕他了。
身陷囹圄的时候,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就是追忆往事,张汤也不例外。这几天,他回顾了从长安小吏到御史大夫的经历,发现自己的仕途生涯与别人截然不同。
他从步入官场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唯一目标。
他喜欢一切按自己意志旋转的那种感觉。
他喜欢看着别人俯首帖耳的样子。
他喜欢听到政敌被打趴下时的哀鸣,那是让他亢奋的最美音乐。
这些让他一方面不容许别人高居于自己之上,另一方面,他也从不贪恋金钱女色。
他这种性格常常让他的对手感到棘手。
他凭执法严苛,扫除了仕途上一个个障碍,甚至圆滑过人的李蔡至死都没有弄清是谁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至于庄青翟,他原本就没放在眼里,可自己偏偏就败在了他手上,这难道不是天意么?
他根本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老朽,竟然照搬了他诬陷人的本领,如法炮制了伪证,把他与瘗金盗窃案扯在一起,并运用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致他明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却无法为自己辩解。
而卫青的举证,加速了皇上的定案。
这个中朝首辅的每一句话,不仅皇上相信,就是大臣们也没有人怀疑。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更因为他的为人连张汤也挑不出任何瑕疵。
张汤明白,他多年来一直守着一个底线,就是绝不轻易把卫青当成政敌。所以,他与卫青之间没有过节。
望着窗外投进来的淡淡月光,追忆着当时皇上的眉目,却是十分地模糊,隐隐约约只记得几个字:怀诈面欺。
他了解皇上的性格,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臣下蒙骗,皇上用了最严厉的措辞,这预示着被枭首弃市的结局在等着他了。
白天,赵禹列举了八条罪状前来对簿。其实赵禹也清楚,所谓对簿不过是个程序而已。
行前,他命人备了些酒菜,与张汤在狱中席地对饮,当谈及皇上发怒,赵禹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人有今日,心里应该清楚。如今大家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皇上很重视这件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不然为什么还要多次对簿呢?”
赵禹走了,可张汤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万念俱灰,与其遭受酷刑,倒不如自裁,一死了之。
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不甘心。下午,趁着仅有的光亮,他向皇上上了最后一道谢罪书。
“罪臣屡受皇恩,死无憾矣,然臣与瘗金被盗案毫无干系,陷害臣者,乃丞相与三长史也。请皇上明察,还臣清白之身。”
他痴呆呆地看着几行因心绪烦乱而写得十分潦草的笔迹,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后半夜,窗外飘起了稀稀疏疏的雨丝,从谯楼上传来更鼓苍凉的声音,张汤最后望了一眼窗外,心里呼唤道:“皇上,臣走了,皇上保重!”
“咚……”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新一天的更鼓敲响了。
……
望着张汤的遗书,刘彻刚才与张骞畅谈时明朗的心境又沉重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他相信,一个垂死之人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他一遍又一遍地推敲着上书中的每个句子,追溯此案前前后后的细节,越想就越觉得蹊跷。
刘彻向赵禹问道:“爱卿曾到狱中与张汤对簿,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赵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陈述了当时的一件事:“那天廷尉府到王朝家中抓人时,嫌犯已悬梁自尽了,这不能不说是此案的一大疑点。”
刘彻从牙齿缝中发出冷叹:“莫非此案真……”
赵禹进一步上前道:“这是廷尉府审理此案的奏章。”
廷尉司马安在他的奏章中说,张汤死后,他奉诏去查看张汤府邸,他全部的家产不过五百金,甚至办理丧事都很艰难。灵柩摆在厅堂,用幔帐隔着,棺木十分平常,与普通百姓无异,而且还是有棺无椁。
因为张汤获罪的原因,还可能是他生前伤人太甚,以致没有人来吊唁。
张母面对廷尉府的询问,竟然没有泪水,话语中透着女人的刚烈。
“别的不敢说,可我儿这清廉,却是青山为证!妾身绝不相信他会伙同巷闾小人,盗掘先帝陵寝瘗金!”
司马安发现,张母把张汤的尸体运回府上时,竟是用的牛车。这让他很费解,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惜刑讯逼供、诬陷政敌的张汤,与一个洁身自好、家无积蓄的张汤是怎样重叠在一起的呢?那些无奸不贪、枉法必贪赃的议论为何就被张汤打破了呢?
刘彻看着奏章,手抚腮帮沉思许久,终于决计对瘗金一案重审,诏命将庄青翟、朱买臣和王朝等下狱。
消息很快传到丞相府,当晚,王朝和边通,一个在府中饮鸩,一个在郊外林子里悬梁。
朱买臣没有走,他一直陪着庄青翟等着廷尉府的拘捕。他对参与构建伪证的行为没有后悔,因为他当时的目的就很明确,他要为严助报仇。
尽管他知道严助所犯罪行绝不容赦,但他还是不能容忍张汤杀了他。
他之所以面对张汤一次次的欺凌而忍耐,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
司马安带人进入丞相府时,朱买臣正和庄青翟在书房里喝酒,他推开冲上来的士卒,亲自给庄青翟弹了弹肩上的灰尘,才伸出了双手。
在庭审公堂,庄青翟对自己的行为毫不讳言。监审的赵禹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大汉丞相要造伪证陷害他人。
庄青翟淡然一笑道:“大人素与张汤交好,那就请大人问问张汤,他为何要编造假证陷害他人呢?”
赵禹又问道:“那当年赵绾之死,与你可有关系?”
庄青翟仰头看了一眼廷尉府的屋顶说道:“无须多问,当年盗走赵绾奏章的代女就是在下派往赵府的。”
审理竟然这样顺利,赵禹和司马安都没有想到。
第二天早朝后,当刘彻在宣室殿看到庄青翟的狱词时,一时心绪十分复杂,他无法评价这场瘗金盗窃案中各人的是是非非,更无法在心底给这两个重臣一个精确的描述。
人!实在是太复杂了。
庄青翟紧步张汤的后尘,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他没有留下任何话语。
司马安在派人为他收尸时想,也许这就是罪有应得。
张汤与庄青翟的死,给朝廷蒙上了瑟瑟的氤氲。
朝野围绕新一任外朝人选私下议论了多日,而处在两难之中的便是刘彻。
这些天,他将元朔以来的朝臣一个个从眼前过了几遍,忽然,他吃惊地发现,一向自诩儒学昌盛的大汉朝,竟然找不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丞相和一个既刚正廉直,又精于朝政的御史大夫。
那一天,刘彻传卫青到宣室殿,要他效仿周亚夫,以军职兼任丞相。
卫青思之再三,还是坦诚地辞谢了。
“不是臣有意推辞,而是臣现已官居大司马,常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生怕朝臣议论。若再兼任丞相,真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到时候,不仅丞相做不好,恐怕连兵务也废弛了。”
“可朕反复考虑,却无合适人选。”刘彻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一副无奈的样子。
卫青道:“微臣举荐一人,不知皇上看合不合适?”
“谁?”
“太傅赵周如何?”
刘彻想了想,摆摆手说道:“恐怕很难胜任。他是荫庇祖先的功绩走进朝廷的,少有建树,讲讲学倒还可以,要做丞相,恐怕难以服众。”
卫青道:“人无完人。微臣当年不也是骑奴么?请皇上考虑先任用一下。赵大人宽厚有德,是眼下最好的人选。”
“那就这样吧!御史大夫人选,朕意就让石庆来做,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赵周是在博望苑中接到皇上的圣旨的,前任庄青翟的命运,让他在接到诏书时,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
赵周是没有野心、也没有多少欲望的人。
父辈的遭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景帝中元元年,他的父亲因为拒绝跟随楚王刘戊反叛而被杀,先帝为了追念功臣而封他为高陵侯。
而他入朝以来将心思都用在研习儒家典籍上,当初皇上命他接替庄青翟为太子太傅,他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很安于每日在博望苑里讲习儒家经典,这不仅符合他的性格,而且也使他避免了与朝臣之间的龃龉。
可谁知道先帝陵寝瘗金被盗的一场大案,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赵周回到府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在心里历数建元以来朝廷人事的变动,竟有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发现——除公孙弘终老任上之外,从窦婴到田蚡,从薛泽到李蔡,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而随着皇上年岁的渐长,这种转换的频率也越来越短。公孙弘四年,李蔡和庄青翟仅仅在位不过三年。
这个朝廷怎么了?他不禁在心里疑惑。
不仅如此,御史大夫也一样更换频繁,今日还在署中处理政事,明日说不准就有什么罪名落在头上。
他在这个时候接任丞相,心里能轻松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