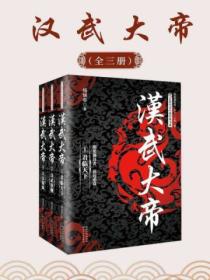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八章 秋风辞载悲凉意 酎金案拷忠义心
卫青刚刚进入甘泉山二里地时,就望见宫苑周围烟云缭绕,隐约有火光闪闪。宫内传来祭祀的乐音,围着翠峰旋转,许久才渐渐散去。
他望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李晔道:“速去禀告丞相,就说本官有紧急军情奏明皇上。”
“诺!”
李晔去了不一会儿,赵周就跟着来了。
彼此见过礼,卫青便问道:“皇上这会儿在殿里么?”
赵周长叹一声道:“皇上昨夜几乎未眠,坐在祠坛旁祭祀太一神,坛中烈火彻夜熊熊,炊具、皇榻都搬到了坛旁。”
卫青让李晔带着卫队在外边守着,他跟随赵周进了宫。
这甘泉宫本是在秦朝林光宫的基础上扩建的皇家避暑之地,从景帝时起,每到六月,皇上就携带着皇后来此居住,直到中秋之后才回返。自元朔以来,刘彻又笃信方士,在这宫中建了专供祭祀的台、观、坛。宫苑从莽林的边缘一直绵延到山脚下。
赵周说:“皇上从陇西巡视回来后,就直接进了甘泉宫。”
卫青沉默无言。皇上刚刚才五十,为何就变成这样子了呢?
在祠坛外守候的包桑瞧见卫青和赵周,忙上前迎候。
卫青问道:“公公,皇上在哪呢?”
包桑指了指寒露观,没有说话。
从观内传出刘彻浑厚的吟诵声,断断续续,起起伏伏的: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赵周闻此道:“这是皇上在河西汾阴为后土祠写的。”
他至今仍不能忘记,在离开汾阴县时,登上楼船,望着滔滔东去的汾水,刘彻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听得出来,皇上的心境是复杂的。眼前初冬的阴冷,满树的黄叶,南归的大雁,都引起皇上太多的联想。
他感叹着青春不再,老去的凄凉。
他难以忘怀卫青、霍去病带给他的快意,也难以忘怀张汤、庄青翟带给他的创伤。
赵周听得潸然泪下,欷歔不止。这惊扰了坛内的刘彻,他问道:“是丞相在外面么?”
赵周忙道:“启奏陛下,大司马从京城来,有紧要军情奏报。”
“哦!大司马到了,让他到紫殿等候。”
……
从寒露观出来,刘彻立时就判若两人,由缥缈的虚空中回到现实,忍不住发泄对河西战后边事松弛的不满。
“上个月(元鼎五年十月)朕登崆峒山后,巡狩陇西,太守竟毫无准备,以致朕与随行从官无法就食。朕随后北上萧关,率数万骑勒兵新秦中,竟然发现千里边塞无亭障。边关如此懈怠,还能保匈奴不会卷土重来么?朕一怒之下,斩了北地太守以下数十人。而你身为大司马,总领朝廷军务,可不能浑浑噩噩!”
卫青十分惶恐和不安,忙道:“此臣治军不严,自当自省。皇上指斥,让臣振聋发聩。”
刘彻挥了挥手道:“此事也不能全都怪你,自韩安国、李广之后,霍去病又早早离朕而去,文官乏才,武官乏将。朕欲命中书令拟一道诏书,发往郡国,令两千石以上官员举荐人才。”
“皇上圣明,臣回京后即刻去办。”
接着,卫青把文书呈送给刘彻道:“臣今日来,就是为这个事情。种种迹象表明,南越国欲图谋反。”
刘彻大体浏览了一下文书,抬起头问道:“去年,南越王太后请求内属,朕念赵婴齐在世时,忠于汉室,故诏准。并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内比诸侯。到现在时间不过一年,他们就要谋反,真是岂有此理?”
卫青解释道:“皇上有所不知,此次反叛的主谋正是吕嘉!”
“哦?”
“据从南越国传来的消息说,吕嘉连续担任三代南越王的丞相,宗族为大吏者达七十余人。他的几个儿子都娶了南越王室的公主为妻,他的几个女儿又都嫁给南越王室,在国内盘根错节,势力庞大。早在南越王太后上书请求内属时,他就多次阻止,后又称病不见朝廷使者。眼见南越王太后内附意决,遂发动政变,杀了幼主和王太后,气焰甚是嚣张。”
“大汉天下,岂容逆贼作乱!”刘彻抽出宝剑,“刷”的一剑下去,面前的白玉案几碎为两截,“传朕旨意,朕要讨逆伐罪,震慑诸藩。”
刘彻目光射人,卫青仿佛又看到了当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皇上。
卫青明白了,既对生命充满了眷恋,又把江山紧紧地拥在怀中,这就是皇上的性格。一向对方士不屑一顾的他,心底生出期待:倘若上苍有眼,真赐皇上永寿,那该是大汉的福祉……
议完大事,卫青骤然就有了一种紧迫感,他跨上战马,如腾云一般朝京都驰去。
李晔见此很吃惊,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大司马如此意气飞扬了。他不敢懈怠,招呼身后的卫队,紧紧地追了上去。
可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它的背后是国家人力、物力的较量。
等刘彻回到长安,要真正打一场彰显国威的战争时,国力早已不像当年那样应付自如了。
首先面临的现实是,自元鼎三年以来的连续灾害,使朝廷不得不拿出大量物资赈济灾民,又免除了一些郡国的赋税。
其次,皇上近年来热衷方士求神之事,在京都和离宫广建神坛,用度十分庞大。
另外,这次战争的战场远在南方,主要靠水战,需要大量战船,这样不只费用巨大,而且也十分费时。
朝会已就此廷议了几次,孔瑾几度呈送的关于财物筹集的奏章,都因为过于拘谨而被刘彻否定。
朝廷不得不将进军的时间一延再延,最后才确定在秋季发起讨伐,好留出时间筹备军需。
这也是刘彻最烦躁的一段日子,他每天不断对前来奏事的少府、大农令和大司马幕府的官员发脾气,严令他们尽力筹集财力,最迟也得八月进兵。
一天,刘彻正在批阅奏章,忽然从一道清秀的奏稿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卜式。
他的奏章每个字都散发着男儿志在战场的豪情,彰显了士者忧国的情怀:“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
刘彻被感动了,他立即找来赵周,询问卜式的情况,可赵周却不甚了解。
他又找来卫青,问道:“朕怎么觉得,这个卜式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现在就在齐国任相。”接着,卫青又与刘彻一起回顾了几年前河西大战时,卜式慷慨捐出二十万钱资助朝廷迁徙贫民的壮举。
刘彻“哦”了一声,身体向后仰着道:“朕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不愿意做官,而愿意放羊的卜式啊!真是时艰见忠贞,我朝像卜式这样的臣子多一些,何愁江山不兴,社稷不固呢?朕要赏赐卜式,令天下臣民效仿,为国尽心出力!”
接着,刘彻坐了起来,从案头拿起朱笔,洋洋洒洒地写道:
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畜悉,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刘彻聚精会神地写着,卫青也在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在他的印象中,这大概是皇上自建元六年以来唯一的一道亲笔诏书。这让他对征讨南越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又多了一层理解。卫青不懂行文的起承转合,他更多的是透过文字感受皇上的胸怀,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从宣室殿出来,卫青没有回大司马府,而是直接奔了左内史児宽的官署。
児宽此刻正召集辖内的县令,商议为朝廷筹集军备的事宜。他闻听大司马到了,遂急忙出府迎接。
进了客厅,席地坐定,児宽便问道:“大司马此来必有要事,下官当不遗余力。”
卫青道:“本官今日前来,是要给阁下看一样东西。”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中书令抄写的诏书副本,児宽仔细地读了一遍,不禁为卜式的忧国情怀而动容,连道:“此举乃社稷之望!吏民之望!自下官上任以来,在辖内奖掖农耕,轻徭薄赋,虽不敢称物阜民丰,然则辖内各县官民丰润却是实情,听说朝廷要南下平叛,下官正召集各县县令商议筹集财物。大司马若能屈尊一见,定可鼓舞人心,凝聚众志,共赴时艰。”
卫青忙道:“本官乃一介武夫,谈不上屈尊。既然来了,就不妨把卜式的义举告知诸县令,也好高标风范,蔚成风气。”
两人相携到了前堂,各县县令平日对卫青七战匈奴、横扫大漠的传奇多有耳闻,今日一见,不仅相貌奇伟,而且举止儒雅,又多了几分钦敬。及至听了卜式的介绍和皇上褒扬的诏书,大家更是士气大涨,纷纷表示回去后,要加紧筹集财物辎重,以报效朝廷。
接下来的几天里,卫青又走访了当年跟随他征战的公孙贺、公孙敖、李息等将军,大家纷纷拿出积蓄的家财,以应朝廷急需。每一次分手揖别,走出属下府邸时,他总是心怀歉疚,觉得给他们的太少,有了事,却总是先想到让他们付出……
几天后的朝会上,刘彻又以児宽为垂范,严厉地斥责列侯们尸位素餐,只知向朝廷求赏,而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他尤其点了新任太常、太后的兄长、盖侯王信的名:“你何功于汉,竟然身居高位,宅甲京都,膏地连属?今天下不幸,你竟然装聋作哑,熟视无睹,百年之后,你有何颜面去见太后?”
遭到亲外甥的斥责,王信觉得很没有面子,可他也只能垂首恭听……
七月,刘彻敕令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浩浩****地开往番禺。
诏令颁布第二天,太子刘据破例不待召见就前来觐见父皇。
刘彻很诧异,放下手中的奏章和朱笔问道:“你不在博望苑中习书,为何到宫中来了?”
“父皇,孩儿请求担任此次讨伐南越的监军。”
刘彻又吃了一惊,道:“你?小小年纪,为何想领兵出战?”
刘据撩了撩袍袖,近前一步说道:“孩儿已经十九岁了,骠骑将军当年出兵漠南不也是这岁数么?”
刘彻笑道:“你和他不一样,你是太子,当学治国御臣之术,要心无旁骛。”刘据有些着急,出口便道:“父皇当年睢阳破案时,不也是太子么?”
刘彻仔细打量面前的太子,心中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温暖。这些年,他整天忙于打理国政,运筹战事,不经意间太子已经变成一个翩翩青年了,看那眉眼、那体魄,听那说话的声音,都深深嵌着自己的影子。
他的心瞬间便有了触动,恩准他的话就在舌尖上滚动,可他还是将话收了回去,究竟为什么?他一时也说不清。
刘彻给了儿子一副很严肃的表情:“朝事眼下还不需你分心,下去吧!”
他重新埋头批阅奏章,不再理会刘据。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时,看见刘据还站在那里,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高声对包桑说道:“送太子回博望苑。”
刘据极不情愿地离开宣室殿,很长时间,他的呼唤似乎还在刘彻的耳边回响。
“一样的父爱,两样的心境,朕这是怎么了……”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臂膀,茫然地问着自己。
这事在处理朝政之余,总在刘彻心头盘桓,直到出征前一天,卫青到宣室殿奏事时,刘彻才将自己的思虑说出。
“前几日,太子进宫要朕允准他担任此次平叛监军,被朕回绝了。”
卫青“哦”了一声,道:“皇上不准自有道理,只是太子已不小了,历练历练,对日后执掌朝政也有好处。”
刘彻捋了捋胡须道:“朕是如此想的。朕主政时,汉家诸事草创,加之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遵循,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都如朕所为,则重蹈亡秦之覆辙也。”
卫青道:“陛下所虑圣明,不过臣……”
刘彻挥手截住卫青的话头说道:“朕知道爱卿想说什么,朕只是觉得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朕是要他做一个守成之主啊!朕知道,太子因为朕不恩准他出征有些怨气,皇后也不理解,故请爱卿以朕意晓之。”
卫青领旨谢恩。
走出宣室殿,卫青还在想皇上为什么在这个日子里和他谈起这番话。
也许是出于一腔爱子之情吧!他在心里默默地这样想。
路博德出征那天,卫青、赵周率众官员到灞城门外相送。
路博德一脸严肃地来到赵周面前,抱拳作揖道:“宫中卫戍,下官已做周密安排。皇上安危,系于天下,下官走后,还请丞相早晚照应。”
他转过身来,对卫青行了军礼,言语中就多了许多的追念。
“末将有幸跟随骠骑将军北征匈奴,得以封侯,此情没齿不忘。末将离京期间,倘逢祭祀之日,还请大司马遣人代末将向骠骑将军敬酒。”
说罢,他跃身上马,正要号令出发,却听见耳边传来呼唤声。
众人回头看去,原来是皇上刚刚诏封关内侯的卜式。他后面跟着几位年轻人,个个生龙活虎地朝这边来了。
卜式来到卫青和赵周面前,躬身行礼道:“下官区区齐相,未有寸功于朝廷而得封侯,实乃皇恩浩**,终下官一生而难报万一。今将犬子四人交与将军,往死南越,卫我大汉社稷!”
卫青闻此对卜式说道:“阁下此举,义薄云天。我大汉数十万大军,不日即会于番禺,也不缺阁下几位虎子,阁下还是将其带回,日后定有报国机会。”
卜式却没有丝毫回转的意思,道:“所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当初下官上书朝廷要率子请战,绝非戏言,今日大司马若拒绝了下官的请战,岂非要陷下官于不义?”
话说到这个分上,无论是卫青还是赵周,都没有理由再阻挡卜式送子从军。
路博德更是感慨卜式父子的忠心,于是上前问道:“各位可以驾船么?”
卜式的长子急忙回道:“回将军,小人自小在海边长大,颇通水性,擅于撑船。”
路博德大喜道:“如此甚好,你就随本将左右,早晚教习水卒操船。”说罢,他朝身后的从事中郎和卫队高声喊道:“上马!”
大汉的旗帜伴随着“嘚嘚嘚”的马蹄声向东去了……
送走讨伐大军,刘彻觉得很疲倦。
那种“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悲凉又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他常常会在批阅完奏章后望着宣室殿内的一切发呆,偶尔会伴随着悠长的叹息:“上苍有知,当赐我彭祖之寿。”
从甘泉宫回来后,他要赵周寻访方士,求延缓衰老之法。
皇上寻求长寿之法已有些年头了,当年赵周在太常寺任博士的时候,就听说过皇上曾请方士李少君炼制丹药,引起了朝野的议论。
元狩四年,皇上又拜方士李少翁为文成将军,并于甘泉宫中筑高台,上画天、地、太一诸神,整日祭祀。后来,李少翁把自己书写的符语藏于牛腹,用来蛊惑皇上,后被识破。不久,宫中就传出消息说,李少翁因为吃了六月的马肝身亡。时间刚刚过去六年,皇上又开始寻找长生之法,倘若自己重蹈当年覆辙,岂不要城门起火,殃及池鱼?
可皇命如天,他只有硬着头皮四下奔波。他是个儒生,向来对方士之术是不屑一顾的,因此,他忙碌多日,却不得要领。
一天,赵周独自一人驾车郊游时,却不料碰见了乐成侯丁义。这丁义乃高皇帝功臣丁礼的重孙。在听了他的心思后说,他认识一位方士,叫栾大,与李少翁师出同门。声言能见神仙,寻到长生不老药。
赵周闻言,急忙将栾大带进宫引荐给皇上。
刘彻在听了栾大的一番陈词后,竟然相信栾大就是神仙的使者,在短短的几个月间,连续敕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刚刚进入四月,刘彻又一道诏书敕封栾大为乐通侯,而刚在不久前,皇上才把丈夫刚刚去世不久的卫长公主嫁给了栾大。
这一回,赵周真的害怕了。
卫长公主是皇后卫子夫的女儿,他最怕的就是卫青过问此事。
果然,在一天早朝后,卫青就在司马道上等他,见面之后,卫青直截了当地问道:“皇上将当朝长公主嫁给方士,丞相不怕落下欺君的罪名么?”
赵周顿时脸色通红,低下头只管走路,不敢看卫青。
卫青见他没有说话,警告道:“若是公主有个闪失,丞相休怪本官言之不预!”
过了好些日子,卫青的话还在耳边萦绕,这让赵周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定。他最大的期盼就是栾大尽快找到神仙,求到长生之药,使他摆脱尴尬。
在朝廷为平叛忙于筹集军资的日子里,栾大向皇上告辞,往东海寻神仙去了。
他一去数月,竟然杳无音信。
此时,赵周坐在塾门,全身就像针扎般的难受,他猜不透皇上宣他来干什么。
“皇上有旨,宣大人觐见!”包桑颠颠跑过来道。
“皇上心情可好?”
包桑摇了摇头:“大人见了皇上可要谨慎些。其他,咱家就不多言了。”
赵周小心翼翼地进殿,跪倒在刘彻面前道:“臣赵周参见陛下。”
刘彻抬眼看了看赵周问道:“栾大呢?”
“陛下!栾大往海中寻求神仙尚未归来。”
“他不是神仙使者么?难道与常人一样跋山涉水不成?”
“皇上圣明,臣也做如是想。”
“莫非又是一个李少翁不成?”
赵周能体会皇上等待的焦急,立即表示道:“臣下去后马上遣人往东海寻找,催他早日带延寿丹药回京。”
赵周正要告退,却见包桑满怀欣喜地进来道:“皇上,吉祥降临了!吉祥降临了!汾阴县的巫者发现了一只巨鼎,御史大夫石庆派精通金石的使者前去验看,确系真品,现正在塾门候旨。”
哦!刘彻心中暗道,这不正应了栾大的神仙征兆么?忙宣石庆觐见。
赵周这时候的心情才松了一些,忙上前道:“宝鼎出世,乃大汉社稷之福,臣贺喜皇上!”
石庆向皇上禀奏了发现和验看大鼎的过程。刘彻听了,自是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迎宝鼎于甘泉宫,并告知宗庙和上帝。
“知会各郡国,十月在甘泉宫朝觐上寿贺。”
安排完这一切,大家发现皇上累了,连忙告退。
出了宣室殿,石庆发现赵周布满皱褶的脸上汗水淋漓,脸颊也红彤彤的,像涂了朱粉,笑着说道:“大人一定热坏了吧?”
赵周指了指石庆的鼻尖,也憨憨地笑道:“彼此彼此!老夫每天战战兢兢,唯恐获罪于皇上。日子一久,只要听见传召就会冒汗。”
石庆虽然没有搭话,内心却有着同感。建元年间他曾在太皇太后身边做事,那时还觉得老太太难以捉摸;如今做了太子太傅和御史大夫,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伴君如伴虎。现在倒觉得那太皇太后和气多了……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月,在一年一度的雍城祀五畤前夕,刘彻忽然下了一道诏命,要列侯献金助祭。
朝臣们虽对出兵南越没有积极响应,但为祭祀天地献金却是毫不迟疑地。
少府寺依据皇上的诏命,对所有献金做了核查,结果发现不少黄金成色不够,显有欺君之嫌,少府寺卿不敢耽延,急忙到丞相府禀告。
赵周正为筹集献金之事的顺利而大喜,准备向皇上写奏章报喜,却不料少府寺的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兴奋的火焰。他大致浏览了一下献金清单,十分吃惊地问道:“献金成色不够者竟达一百〇六人?”
少府寺卿道:“丞相也知道,前几个月,南越王太后请求内附,引起臣下反叛,卜式上书请出兵,并献上资财助军。皇上封其为关内侯,要群臣响应他的做法,孰料应者寥寥,皇上十分生气,让他们献金也是对他们的惩戒。”
赵周苦着脸道:“可这样一来,是害了老夫啊!”
赵周再仔细一看,涉案名单中竟然有两个令他心悸的人物:卫不疑和卫登。
“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将他们也牵扯进去了?”
“唉!”少府寺卿叹了一口气道,“他年少不谙世故,又是大司马之子,列侯以为拉他进来,皇上就会网开一面。”
唉!赵周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列侯们的行为。在过去为太子讲书时,他不止一次列举古来忠贞义士为君主不惜剔骨割肉,不惜抛却生命的故事,可现在发生的一切,哪里还有国士的影子呢?
赵周不敢相信的是,这些位居列侯的大人们,为了向皇上讨赏,无所不用其极,可如今国家有事了,却冒着杀头的危险,以假充真,甚至连皇上都敢欺骗。这世事究竟怎么了?
一份报喜的奏章,就这样被“酎金案”变为了请罪疏。
消息很快就传到椒房殿,卫子夫的心情就不安起来。卫氏一门列侯甚多,她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侄子陷进去。
一大早,她就要人去传卫青过来说话。
卫子夫看着病后消瘦的卫青问道:“大司马近来忙些什么呢?”
“臣弟近半年来一直在处置南越之乱呢!”
“不是南越王太后自己提出要内附的么,怎么又乱了呢?”
卫青呷了一口茶水说道:“南越之乱生于臣下,不关王室。”
卫子夫闻言眉头就蹙到了一起,随即便问起震动朝野的酎金案。
“为何一下子牵涉进去那么多人呢?”
卫青娓娓道来:“其实此事也与卜式有关。此次平息叛乱,卜式父子率族人请缨于前阵,皇上闻言,下诏褒奖卜式,赐关内侯,昭告天下。然郡国、列侯竟漠然视之,致使皇上龙颜不悦,恰逢秋祀在即,皇上下令列侯献金助祭,并严加审核。这一审就出事了,他们竟用了成色不够的金子诓骗朝廷,皇上闻言大怒,听说已下诏削去了一百多位列侯爵位。”
“本宫也正为此事忧虑。”卫子夫朝前挪了挪道,“你一家四位列侯,可千万不要陷进去!”
“眼下尚无他们涉案的消息。”卫青说着,叹了一口气,“臣弟这几个儿子,唉……不立功倒也罢了,又喜滋事,不思进取,公主又多有怂恿。”
“你也不要总怪公主,常言道:养不教,父之过。你既为父亲,自当教子成才,不能总顾着朝廷之事。本来当初皇上就不该封襁褓之中的孩子为列侯,以你的家境,也不缺这个!依本宫之意,这空头爵位不要也罢,倒不如你自请于皇上,削了他们的爵位,也免得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打他们的主意。”
卫子夫喝了一口热茶,继续道:“本宫年龄大了,皇上不能总守着一个色衰的女人,一旦有变,要紧的是太子。因此,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太子近来可好?”
“人大了,心也大了。皇上要他学儒,他却结交一些古怪之人,为此被皇上多次申斥。”卫子夫忧虑道,“而且皇子也越来越多,李夫人去年又生下一个,本宫担心,他这样不知思过,会……”
卫青看着面容憔悴的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但忍受着皇上移情别爱的痛苦,还要为自己揪心牵挂,他纵然不能为姐姐排解一二,也不应给她徒添不必要的烦恼。想到这些,卫青道:“皇后所言极是,臣明日就进宫去,恳请皇上削了他们的爵位。”
“此事你还得说服公主才行。”
卫青点了点头,可他心里明白,要说服虚荣的妻子并非易事。他已在心底打定主意,绕过公主,径直面奏皇上。
看着天色不早,卫青起身告辞,这时春香急忙进来禀告:“长公主哭哭啼啼进宫来了!”
话音未落,刘嫣推开殿门,一下子扑到卫子夫的面前:“母后!孩儿……”
“究竟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卫子夫不悦道,“都是大人了,你怎么……”
刘嫣早已哭成了泪人儿,话都说得断断续续的:“母后!栾大他……”
“栾大怎么了?你好好说……”
“栾大他被父皇下狱了。”
卫子夫一下子惊坐在地上:“本宫早该想到这一天的。栾大每次在长安作法,吸引大臣与皇上一起观看,然后就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前往东海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可每次回来,都没有带给皇上多少惊喜,却总有许多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不!刚刚新婚不久,就……”
刘嫣又看了看卫青,喘着气道:“恳请舅父劝劝父皇,饶过栾大,刘嫣已没了曹襄,栾大再一死,刘嫣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人世……舅父……”
卫青本来就不静的心就更乱了。
唉!这真是个多事的岁初啊!怎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
……
当卫青回到大司马府时,却看见府上的车驾正停在门口,长公主正要上车。他急忙下马,上前问道:“你这是要去往何处?”
“进宫!”长公主愤愤地说着,“大司马整天忙得不着家,可你知不知道,不疑和登儿已被牵进酎金案了。”
“啊?”卫青心里“咯噔”一声,皇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可他现在担心的是,依长公主这性子,如果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惹恼了皇上,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雪上加霜。
眼见天色已晚,卫青说道:“此案十分复杂,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先歇息一晚,明日我进宫面君,恳请皇上开恩,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
长公主见卫青如此果断坚决,冷冷地盯了他一眼道:“好!本宫就听你这一回,看看你如何救自己的儿子?”说罢,她拂袖便进了府门。
当晚,卫青唤来儿子们到书房问话。
两个平日被母亲娇惯得无法无天的公子,这时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卫不疑小声说着原委:“皇上的诏命颁布后,就不断有人来找孩儿,说是冲着父亲的战功,冲着孩儿是皇家外甥、皇后侄儿的分上,就算皇上发现了献金成色不足,也会法外开恩的。”
卫青听到这里,再也无法遏制一肚子的怒火,上前就给了两人一个耳光,骂道:“蠢材!一对蠢材。别人是拿着你当挡箭牌,你们知道么?”
他们遭到父亲如此重责,捂着脸一个劲地喊着:“母亲救命!”
长公主冲进书房,杏眼圆睁,冲着卫青喊道:“你在外面还没有威风够么?回来还拿孩子撒气,算什么本事?”
“你可知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别人欺君罔上,拉着他们来垫背,蠢!”
“那又怎样?难道皇上还要杀了我儿不成?他要敢那样,本宫就死在他面前!”长公主骄横道。
“你……”卫青叹了一口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洁身自好,迟早是要出事的。若有朝一日,为父不在了,你们何去何从?”
这一夜,翡翠也是一夜不眠,她听着隔壁高一声、低一声的争论,从内心深处替大司马抱屈。
长期伺候长公主,她最清楚长公主是怎样借着皇家的威势,放纵自己儿子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她不但不自责,反而怨天尤人,这让大司马心里能好受么?
忽然,从隔壁传来卫青清晰的声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翡翠心里一惊,她猜不透大司马说这话的意思。她多希望看到他们琴瑟和鸣,一家和和气气。
更漏刚过了子时三刻,卫青就起床来到书房。
翡翠打来温水,为大司马洗漱。卫青擦了一把脸,抬头问道:“昨夜你都听到什么了?”
翡翠摇了摇头。
卫青道:“就算听见了,也只能烂在心里,绝不可传将出去。”
卯时一刻,卫青已乘车上朝了。一路上,他不断地整理着思路,思谋该怎样面对皇上的斥责,该怎样应对栾大一案。
走完司马道,就远远地听见塾门里人声嘈杂。一进门,大家的目光就集中到他身上。
“大司马到了!”官员们纷纷上前打招呼,卫青微笑着回应,眼睛却在人群中寻找丞相的影子。终于,他发现赵周低着头躲在一个角落。
“丞相,栾大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完了!一切都完了!”赵周抬起老泪纵横的脸望着卫青,“都是栾大害了老夫啊!”
他紧紧拉着卫青的手,目中满是求救的渴望:“请大司马看在老夫为太子授业的分上,恳请皇上饶恕老夫的失职之罪吧?”
那双冰凉的手使卫青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回绝的话。可因为儿子,他自己已是“酎金案”的当事人,命运都还未卜,哪谈得上去救别人呢?
辰时二刻,大臣们按照序列,整齐肃然地站在未央宫前殿,几乎每个人都感到了今天气氛的不寻常——殿门外多了许多卫士。
刘彻出现在大家面前,刚才还嘀嘀咕咕的臣僚们立即安静下来。
果然,刘彻今天没有让包桑代他宣布早朝的程序,而是很阴沉地问道:“赵周来了么?”
就这一句,让站在丹墀内的大臣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至于赵周,早已是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出列答道:“臣在!”
“你知罪否?”
“臣……微臣知罪。臣作为当朝宰辅,却对官员疏于管束,致使百余名列侯欺君罔上,卷入酎金案,臣罪该万死。”赵周说着就瘫着跪下了。
可刘彻却不理他了,转头要赵禹、廷尉周霸和少府寺卿当庭禀奏“酎金案”的审理结果。
今天,赵禹是所有大臣中最镇静的。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间拿出竹简,历数列侯所献酎金的缺斤短两、成色劣恶、欺瞒朝廷等罪状。
凡是在场的大臣,每读到一个人的名字,立即就被剥下朝服,拖了出去,塞进司马门外早已备好的囚车。
当场有十几名大臣获罪,一时间“皇上饶命”的喊声不绝于耳。
卫青发现公布的名单中没有卫不疑和卫登的名字,可他们确实也在削侯之列,这是皇上给他卫青留了面子啊!
赵周几次昏厥过去,等他再度醒来时,跌跌撞撞地爬到刘彻面前,额头在大殿的砖地上磕得咚咚直响,他哽咽着说道:“酎金一案,皆臣之罪,请皇上赐臣一死!”
刘彻从鼻翼间哼出冷笑道:“你就想死么?事情还没了呢!你说说栾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你骗了朕,还是他骗了朕?
赵周的精神彻底垮了,老迈的脸上泪流成河:“陛下,栾大乃乐成侯丁义所荐,他的斗旗术皇上也是亲眼见了的。”
“大胆!你不认罪,反倒诿过于朕。王温舒何在?将你跟踪所见告知于他。”
中尉王温舒应声出列——这个用屠刀和监狱让自己辖内的盗贼闻风丧胆的将军,用自己粗糙的语言描述了栾大的东海之行。
栾大一路上晓行夜宿,越是接近东海,就越心虚。
来到长安几个月,李少翁之死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更是他心头难以驱散的阴影。
他很清楚,事情一旦败露,他的下场将会比李少翁更惨。因此,当他一天天走近濒临东海的琅琊郡时,他甚至想从此隐居深山或乘船流浪到海中的孤岛上,销声匿迹。
可他终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丢不下五利将军的光环,更忘不了从卫长公主那里获得的快乐。
在琅琊郡最豪华的客栈住下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过于谨慎了。嘿嘿!千里之外的皇上怎么会知道自己见没见到神仙呢?
人一高兴,不免就忘乎所以,栾大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夜,有三位商贾模样的人敲开了他的房门。那领头的自称来自临淄,要到海边贩些海货。
他狡黠的眼睛围着栾大转了转,忽地就发出一声惊叫:“呀!先生乃神人也!”
栾大惊异地看着对方,眼里充满了迷惑:“客官何以见得?”
“不瞒先生,”那人眨了眨眼睛,“在下乃前朝徐福的后裔,名徐禄。今日一见先生,顿感先生周身紫云环绕,仙气弥漫,就自知遇到了仙家。”
他的话遭到两位同行者的嘲笑:“大哥这在诓谁呢?我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徐禄道:“你们不晓通神之法,如何能看得见?”
这话栾大不仅爱听,而且因为与他三人结识,一路上的恐惧和寂寞也渐渐远去了。
这一夜,他们围着鼎锅,吃着烤猪、蒸鱼,三位轮番向栾大敬酒。
夜阑席散之际,栾大已酩酊大醉了。
他举着酒杯,来到楼道的走廊,凭栏望月,临海听涛,醉语中就泄露了秘密。
“皇上!休怪栾大蒙蔽圣听,实在是黄金耀眼,公主勾魂啊!这世上哪有神仙?哪有不死药呢?连前人徐福都逃往海中,栾大岂能超脱凡尘?哈哈哈……不死药……神仙……哈哈哈!”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跃出海面,睡梦中的栾大和三位客商就被店家唤醒,言说海上有奇景出现。
四人奔出房间,居高远眺,果然岚霭蒸腾,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浮起一座都城,那里层楼叠翠,树影婆娑,人头攒动。
这情景让栾大盘算了一路的腹稿一瞬间臻于完善,他知道该怎样应对皇上了。
他回到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长安去。他觉得离开卫长公主太久了,他有点想她了。就在这时,三位客商进来了。
还是徐禄先问道:“先生这是要到哪里去?”
栾大回道:“回长安呀!”
徐禄问道:“不死药找到了么?”
“先生不是看见了么?神仙就在海中的瀛洲岛上,可他们今日聚会,岛上三五日,世上已百年,只有待明年再来了。”
“栾大!恐怕你没有明年了。”三位商贾立时亮出身份。栾大心里一哆嗦,又看见了七窍出血的李少翁。
……
“逆贼栾大现已羁押在廷尉诏狱!”王温舒最后道。
刘彻从案头拿起一叠文书道:“这是监视的司马一路快马密送的奏报,赵周,你还有何可说的?”
刘彻回到御座,就向身边的包桑摆了摆手。
包桑捧起早已拟定好的诏书,尖声念道——
制曰:查丞相赵周疏于职守,‘酎金案’迁延列侯百零六人,竟知情不奏;且荐人失察,致逆贼栾大欺君罔上,蛊惑众心,二罪并处,着即革去丞相职务,交廷尉府查办;乐成侯丁义,妄举方士,欺瞒圣听,着即削去侯爵,处以弃市;逆贼栾大,坐诬罔,腰斩。钦此!
在包桑宣诏的时候,赵周晕倒在殿堂上。他没有听到诏书所列的罪状,就被卫士拖了出去。在被塞进囚车的时候,他仍没有醒来,只有银须沾满了口中的白沫,将一腮美髯粘成一撮。
大臣们一个个面如死灰,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卫青的目光一直追着赵周,直到他老迈的身体从眼前消失,耳边似乎还回响着塾门求助的声音。
他几次欲挪动脚步,走到大臣面前恳请皇上对丞相从轻处罚。
可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皇上转向自己的目光,他很快就读懂了那目光中的意味,是一种冷酷的拒绝,一种断然的制止,一种隐约却是严厉的责备。
他于是选择退却而惭愧地低下了头。
是的!皇上毕竟看了皇后的面子,没有让赵禹点卫不疑和卫登的名字,但他知道,此事必然还要在宣室殿中延续。
此时,包桑又传下了皇上的另一道诏书——
制曰:御史大夫石庆,宽仁敦厚,着即任丞相,封牧丘侯;齐相卜式任御史大夫。钦此。
散朝了,大臣们各怀心思走出了未央宫前殿。
卫青没有同新丞相石庆说一句话,就加快脚步出了司马门,径直上了车驾。
驭手挥动马鞭,车驾早于其他臣僚离开了未央宫——他要告诉长公主,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要训诫儿子,让他们以对朝廷的忠诚来洗刷耻辱。
明天,他将进宫面见皇后,他想告诉姐姐,他的儿子们的爵位已被酎金案的狂风吹落尘埃,不复存在了……
石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李蔡自杀了,庄青翟自杀了,赵周下狱了……那下一个是不是就到自己了呢?
他不敢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依照惯例,在宣布了新的任命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留新任丞相到宣室殿谈话,可今天没有。
正午时分,天空渐渐阴了,灰色的云团很快覆盖了长安。
上车的时候,石庆抬头看了看天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阴雨天又来了。”
可不?车驾刚刚走动,密密匝匝的雨点就落到了宫墙外的柳树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