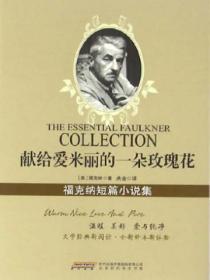§四
所以那天之后我们都认为她要自杀了,觉得那是特别好的事。我们都以为她会嫁给荷默·伯隆,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认为。后来又觉得:“他会被她说服的”。因为荷默在麋鹿俱乐部和年轻人喝酒的时候表示,他喜欢男人,他并不想成家。以后每个周日下午,他们都坐着那辆马车招摇过市:爱米丽小姐总是仰起头,荷默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握着马鞭,歪戴着帽子。每每此时,我们总是躲在百叶窗后感叹道:“可怜的爱米丽。”
随后,妇女们表示这件事令全镇人蒙羞,也会教坏了青少年。男人们不愿意管这事,妇女们却最终让牧师去找她谈谈,因为爱米丽小姐全家都属于圣公会。牧师虽然没有说出他们当天谈了什么,可却声称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于是,下个周末他们继续驾着马车在街上闲逛。牧师夫人只好将这件事写信告知了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人。
我们不清楚她还有亲人,便拭目以待。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果,接着,我们就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爱米丽小姐还去了首饰店,买了一套男人用的洗漱用品,每样东西还刻着“荷·伯”的字样。又过了两天,我们得知她买了全套的男人服装,包括睡衣,所以我们才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确实很高兴。不过比起爱米丽小姐,我们觉得两位堂姐妹的风度气质更像格里尔生家族的人。
小镇的街道铺路工作已经结束了很久,所以我们对荷默·伯隆的离开并不惊讶。我们只是觉得没有去送行有些遗憾,这少了许多热闹。当然,我们认为他是回去做准备——迎娶爱米丽小姐。我们甚至秘密地结成同盟,希望能帮助爱米丽小姐赶走那两个堂姐妹。结果,她们两个人一周以后就离开了小镇。
一位邻居看到荷默·伯隆重返城镇,就像我们对他的期待一样。某天傍晚的时候,那个黑人仆人打开厨房门让他走了进去。
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荷默·伯隆,也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爱米丽小姐。宅院的前门一直没有打开,只有黑人仆人提着篮子进出。我们虽然能偶尔看到窗口处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就像在她院子里撒石灰那次一样,可她却再也没有出门上街,足足六个月,她一直没有露面。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我们了解这是她父亲造成的,在那种恶毒暴力的性格教育下,她一波三折的人生很难消除他带来的阴影,这是毋庸置疑的。
爱米丽小姐再次出现的时候,她有些发胖,头发也变成了灰白的颜色。后来,她的头发越来越灰,那颜色像极了胡椒盐。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年,在她七十四岁的时候,她的头发始终像男人的一样,依旧是活跃的铁灰色。
在她四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她房屋的前门才打开了六七年左右。那时,她将楼下的一个房间布置成了画室,教小孩子瓷器彩绘课。那时,沙多里斯上校还在世,与他同年龄的人都让自己的女儿、孙女儿跟着她学画画。他们每个周末都带孩子们去那里,准时准点,态度认真,就像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教堂,还要给她们二角五分钱捐献一样。在那段时期,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她的一切税费。
几年以后,那些学画画的孩子们都长大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了以后,院子的前门这才关上了,而且始终没有再打开。那些学画的女人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来这里学画。年轻人掌控了城镇,他们推行免费邮递,可全镇人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人拒绝,她不允许自家房门上被钉上金属门牌和邮件箱。
时光流转,那黑人仆人也慢慢地老了,他的头发花白,也开始驼背,不过仍然拿着篮子来来回回。我们每年十二月都会把纳税通知单邮寄给她,可过了一周,邮局总会自动退还,因为每次都无人接收。她封了楼上,经常在楼下的窗口露出身影,像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庙宇里面的雕塑一样,用尊贵安静却又怪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使人难以接近,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她因病离世。在那个满是尘土、鬼影憧憧的房间里,只有那个年迈的黑人仆人照顾着她。我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得病了,也无法从黑人口中得知,因为他并不和人沟通,大概对她也是一样。他的嗓子因为许久不说话早已变得沙哑。
她死的时候,床帐垂挂在粗笨的胡桃木**,她的头发依旧是铁灰色,枕头因为许久晒不到太阳而变得发霉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