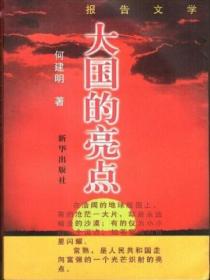说常熟,少不了说《沙家洪》。是常熟几十年前的革命烽火,才有了《沙家洪》这出戏。同样,有了《沙家洪》这出戏,才使许多过去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常熟的人知道了常熟。
说起(沙家洪),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那个八面玲珑、热情好客钓“春来茶馆”女老板阿庆嫂。常熟倒底有没有阿庆嫂?这是所有初次到常熟或对常熟感兴趣的人都会提出的同样间题。这也许正是河庆嫂的魅力所在。
我如实回答:常熟有阿庆嫂。常熟有很多很多的阿庆嫂。
我再透切一点地回答:阿庆嫂确实有其人。而且有名有姓。
(阿庆嫂其人其事)——这篇报道是11年前一位部队记者写下约,当时各种媒体曾纷纷转载过。这位部队记者便是11年前的我。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年正值“八一”前,我奉命到常熟,并在当地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常熟董洪镇一个叫雪沟村的小农庄,见到了年已古稀、但身板仍很结实、记忆也十分清晰的老人。有人告诉我,她就是戏中的“阿庆嫂”原型,她真名叫陈二妹。下面是我文章中有关与这位“阿庆嫂”的对话,原汁原味端过来给读者可能更好些吧——
……当记者同起她那段“阿庆嫂”经历时,陈二妹连连摆手道:“可千万别叫我阿庆嫂。但过去的事可以跟你说说。”
那是杭日战争时期, 日本鬼子和汉奸伪军在苏南一带为昨作歹,干尽了坏事。在茅山坚持游击战的陈毅将军派遗叶飞率新四军第六团组成“江南杭日义勇军”,东进苏南地区,发展敌后根据地。第一次东进的主力部队西撤后,1940年林俊(谭衷林)同志又率新四军第二次,十.进,与常熟地方杭日革命武装——常熟人民杭日自卫军一起,在常熟包括黄洪乡一带建立了不少地下交通站。老人说,那是我和丈夫陈关林在镇上开了个茶馆,交通站就设在茶馆内。当时的茶馆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涵芬阁至今仍保留完好,每日开张)。“涵芬阁”前面是街道,后面是一片芦苇塘,所以很适合作地下交通站工作。那时新四军和谭襄林等经常到“涵芬阁”来开会、碰头。他们一般总是夜里来,天一露白就走。我和丈夫负责接待和站岗放哨。当时在上海、苏州和常熟城里有许多青年为了寻找革命来到我们茶馆,我们就利用茶馆为他们安排住宿和联络接头。我不是地下党员,直到现在还是个普通群众。但当时我和丈夫都觉得鬼子太坏,给新四军做丰是应该的。我丈夫他是地下党员,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1939年至1941年是日本鬼子最疯狂的年月。有一天,我丈夫突然被鬼子抓走了。故人坏透了,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他喝下去。当我丈夫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我丈夫就是不屈服。后来他和另外62名新四军伤病员、地下党员一起,被敌人钾到苏州虎丘山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给刺死后又用银水灭尸于荒野之中……
“你丈夫死后,茶馆还开吗?”
“不行了,从那时起地下交通站也幕露了。”老人擦着眼泪对我说,“后来我也呆不住了。当时地下党负责人朱英同志让交通员带我到江北整整躲了3个月。从江北回老家后,常熟有名的民族杭日淤雄、游击队司令员任天石给过我200元钩喊让我傲小生意以妞东爵活。但生意不好做,后来我就带着两个小孩回乡下买了几亩地在一贡沟村安了家,一直到解放……”盼 ……享11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踏上常熟这块土地,想再一次见见住在雪沟村乡下的“阿庆嫂”时,人们告诉我她已在去年去世了。我听后异常心沉。
“阿庆嫂”终年83岁,她死之前一直是位普通的农家妇女。
常熟的同志说,陈二妹是当年数个“阿庆嫂”中的一个。还有像曹家洪地下联络站的那个徐巧英等等好几个“阿庆嫂”式的人物。她们也都救过新四军、作过地下交通员。我完全相信,因为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本来就是在众多生活原型基础上塑造出来的,何况当年常熟这块英雄的热土上出了岂止一个陈二妹!
然而阿庆嫂是常熟人的骄傲。而艺术中的阿庆嫂的形象,正是常熟广大妇女形象的典型体现。那种热情好客、周到待人、心灵手巧和勤劳大方等也正集中了常熟妇女的突出优点。常熟那句十分形象地勾划出当地市场经济特征与形式的名言,叫作“阿庆出门跑外勤,阿庆嫂在家开茶馆”。其实,今天常熟能有如此生机勃勃的市场和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千千万万个“阿庆嫂”。妇女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尤其是在农村市场经济大潮中,占有不可否认的主导位子。这种突出印象,在常熟尤为明显。
进入八十年代起,由于常熟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的男性公民或外出经商,或走上了企业管理岗位,而此时无论在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上,妇女的比例占了绝对多数。当现代化进程在常熟这样的先进地区先行一步后,那些稍有能耐的男性公民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第一代农民“白领阶层”。这一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那天起,就悄悄改变了的农村农民生产关系结构的过程,在发达的苏南地区已有二十年历史了。男女农民之间的这种变化,它既是社会向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又体现了中国广大农村进入全面市场经济后所出现的一个不可轻视的现象。这就是妇女对自身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认识。
常熟的“阿庆嫂”们不仅没有被历史进程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潮流所击垮,相反她们迅速调整自己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角色,摆脱了长期以来那种依赖男人做事的局面,大胆而又自信地担当起T市场经济战场的主角,并成为推动历史的坚固有力的车轮。她们以自己独有的聪慧天性和勤劳、坚韧作风,驾驶着每一辆属于自己的战车,并让它顺利地到达胜利的目的地。
不仅仅是我的感觉,也不仅仅是妇联干部们自己的感觉,常熟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同样地认为,常熟今天能出现如此繁荣和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景象,妇女不单单是一个参与的群体,而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主力队伍。
只要你走进这里的工厂车间,你看到那些埋头苦干的一定是“阿庆嫂”们;只要你走进喧闹的“服装城”,你看到那些叫得最欢最响亮的一定是“阿庆嫂”们;只要你往田野里一站,你看到那些依旧固守在耕地里农作的一定是“阿庆嫂”们;你再走进农户家门,那些挑灯夜战把织机操舞得彻夜长欢的准又是“阿庆嫂”们;你再静静等待那些胜利者酣睡后为他们料理喜悦、准备新战斗的准又是“阿庆嫂”们;而当哪,个失败者还在为流血的伤口大惊小呼时,默默守在一边为其擦血抚痛、安慰体贴、鼓励振作的准还是“阿庆嫂”们……
常熟的“阿庆嫂”们在为男人们烘托那一片夭时,更多奇多彩地编织出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人的那整个明朗的天。
市妇联主席张怀瑜把我领到了一位被百万常熟市民誉为“当代阿庆嫂”的女村干部、闻名全国的“梦兰集团”总经理面前。张主席说钱月宝是个真正的女人,一个爱做梦的女人,一个把梦变成现实的女人,但钱月宝不是那种爱掉眼泪的女人,就像上面讲述的那个丈夫被敌人残酷杀害后依然擦干血迹为革命奔忙的阿庆嫂原型陈
二妹一样。
钱月宝,普普通通的一位中年妇女。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
龄、论其相貌、论其谦逊而又朴实的神情,拿我们南方人习班而决不客套的话称呼一声“阿嫂”是最贴切的(十分巧合浅她是俄们何氏家族的媳妇)。我的这位新认识的阿嫂,她说她平常不爱开么记者报道员的采访,她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去想属于自己的事,她一生最不值得叫人看得起的就是她自己,她说这样说是因为她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没有照顾好、照顾住……她说到这里泪水已咽住了她的话语。
我这时才知道她的那位与她耳濡目染、相亲相爱了二十几年的丈夫去世不久。
她没能留住他,这是她最伤心和最悲枪的事。她说她的生命和事业里不能没有他。她跟元元(她一直这样亲昵地称呼他)在一个村,那时叫生产大队。她17岁时父亲死了,她与母亲便挑起了一个六七口之家的重任。从那时起他就像大哥哥似地融入了她的生命与生活中。他开始当大队会计,后来让给了她当。俩人都是队上的活跃分子,他天资聪明精细,她天资心灵手巧,1969年她跟他结成了百年之好,从此俩人驾驶着同一条生活帆船。她性格外向又愿闯事业,他性格内向把家又走路。
、老洪村是她和他的家乡,一个地处偏僻、基础簿弱的穷队。从小爱做梦的她对他说,好元元,你说为什么我们队上那么穷?为什么不能改变得像华西村那样富裕?元元告诉她,人家集体经济搞得好叹。哪我们就不能也搞得好些呀?行啊,你的绣花手艺不是很好么,如果把你们那个绣花厂搞搞好,说不定村上能改变面貌呢!他的话对她触动很大,这时村里也正好决定把全村唯一的企业——一个又破又烂的小作坊式绣花加工厂交给了技术顶好的她来挑头干。
钱月宝从此开始了她的“梦兰”生涯。
那创业的初始,爱做梦的她却没有可能去做她心中的梦。一切是那样的艰辛,她这个绣花厂原来干的活都是给苏州厂家搞外加工。十几个人、二十几双手拚命干一年,还挣不到3000块钱。入夜,月宝又问爱人,老给人家当下手,要干到何年何月才能让咱老洪村富起来呀?干脆我们自己干,好坏也是我们自己的,你看咋样?他想了想,又把她细细地看了个够。干啥老看人么,都跟你这么些年了,还没看够呀?她假装生气地操他一边去。他笑了,说我越看越觉得你标致了。去去去,没正经,人家着急你可倒好,拿人家寻开心。她真的生气了。他笑了,说你看你,我说你越来越“标志”是你现在干事比以前越来越有目标、有志向,难道不想也不要这个“标志”呀?她觉得自己又上这位“老大哥”当了。好你个坏!难道我就真的不标致呀?就只有干事体的“标——志,’?他连连投降,说你月宝在我心中啥都标致,人标致,工作也“标致”。别没正经,快说我的想法倒底行不行?她问。他说,还用问,我的月宝只要想干的事啥不成?这回她爱听了,说这可是你说的啊,成不成你我各半份。他说我永远是你的那一半。她抢过话亲昵说,我的全部可都是你的哩!
她照他说的去做了,把厂子原来为别人加工改成了直接做自己的活。她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可以叫办厂的做法。
然而,真正办厂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一个村办厂。这种厂在自己的村里可以叫厂,而一到外面它就不是厂了,谁认你一个村子办的厂?笑话,国家办的大厂现在都产品卖不出去,更不用说还有铺天盖地的乡镇企业,你一个小小破工棚里钻来钻去的土农民也想办厂?也叫啥厂长?哈哈哈,那咱们这个地球也不用叫球了,就叫厂吧,我们不是谁都可以办厂吗?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当厂长了,哈哈哈……有人这样笑话她,笑话她的厂。她感到委屈,委屈得直想掉泪,但她没有掉泪,她依然冲着笑话她的人微笑,心想总有那么一夭我会让你明白农民也能办厂,小村子也能办大厂,而且是真正的大厂。
她把心用在了厂上,把心用在了产品上。那一针针一线线她都亲自过问动手。她又把亲自绣出的一件件产品送到高水准的苏州绣除市场上让人看货订货。‘ 争 在苏州的一家涉外饭店里,‘主人手拿绣品,情不自禁地惊叹起!来:“这是你们自己的产品?太美太精细了!还有多少货?我们全1要!什么时候能再送货来?”一连串间号,一连串感叹号,使她喜出望外,信心百倍:“你们什么时候要货,我们就什么时候送货;你们要多少,我们就给送来多少!”她这样回答对方。
那天回到村子,她把喜讯第一个告诉了他。他好像早知道似的笑笑,说我已经给你定了个生产计划,你看看。她看后激动得又想掉泪,可她没时间。第二天天还未亮,她轻轻地给他盖好被子,自己穿起衣服就往厂子里跑……
她到厂好半天好半天了,怎么还不见她的工人上班来。一间,说都不来了。这为啥?市属、镇办企业这几天一直在招工,她们都到人家国营、大集体那儿去上班了。
她就差没晕倒。
“别急,会有办法的。”.入夜,他百般安慰,像哄小孩似的说道:“国营、大集体企业牌子硬,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嘛,这也算正常。只要你把厂办好办得像像样样,我看就啥都不怕了。”
她说:“人都没了,我怎么个把厂搞好?”
“会有办法的。”他一边安慰,一边沉思着。
“这夭,他比她起得早。
这天,他回得特别晚。
一进门,他满脸疲感,却满是欢欣。“告诉你一个喜讯:村里有8位妇女同意回厂子了,明夭她们就上班。”
她一听全明白了。她眼眶顿时发热,啥话没说,给他端上一盆热热的洗脸水。
一个如今年产数亿元、驰名中外的中国**用品名牌集团——“江苏梦兰集团公司”的最初雏形,就在他一家一户做工作、磨嘴皮子后开始重新起步了。
世上没有再有比他的这种支持帮助更有力量了。她与八位姐妹又从头开始编起了心中的梦。想起当年的情景,她自己都要笑出声。那是叫啥厂呀,我这个厂长就更甭提了。现在的工厂推销员出门都要讲点派头排场,那时我这个厂长出门就像北方赶集的大嫂,肩背手提的都是厂里几个姐妹绣出的台布、窗帘呀什么的。每次到城里,我都得大包小包这样扛着背着。那时出门进城还坐不起汽车,不是搭人家的拖拉机就是靠双腿跑。她说,有一次她到苏州绣品厂送货,搭的是人家一辆卖磨菇的拖拉机。谁知拖拉机半路出了毛病,她被扔在半道。当时已是下半夜,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因为身边有货,她只好去敲路边陌生人家的门。人家开始不开,后来听我是个女的,又是出门卖货的,就把门开了,让我跟他们的一个小固睡在一起。那夜,我一个女人家,就这样住在一户陌生人家的**,抱着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睡了一夜。我虽然人躺着,可根本就没合眼,我当时想得最多的是我自己家的孩子,想着他,还有就是我身边带的那些货……
钱月宝告诉我,还有一次,她到苏州送货,老黄牛式的拖拉机半夜才到城里。那时夜深人静,街道上不见一个人影。她是来送货的,可这当儿谁会接待她呢?照例她可以找个小旅店什么的住下,但那时厂子里每一分钱都是省着能不用就不用。就这样,她在苏州市的人民路上整整走了一夜。她笑说那夜她真的当了一夜“人民”。这样当整夜“人民”的历史,钱月宝有过几次。那年为了到上海买下几台“二手货”机器设备,由于别人告诉时把地址搞错了,结果她到上海后找了一个下午又转了一个傍晚也没找到。那天她手里还提了好几斤活螃蟹。无奈,她又在上海的大街上一直走到天亮。
等到她回家,才想起他给她讲的,家里的房子实在不行了,得重新动一下。等她想起此事,匆匆赶到他面前时,他一身灰一身泥地已经把两间房子给收拾利索了。他累得像瘫子似地坐在小木椅上,却反过头来关切地问:“生意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她赶忙把盈在眼眶里的热泪咽回去,点点头,说顺利顺利。
他笑了,说顺利就好。末后又说,两个孩子都睡了,刚才还问鸿啥辰光回来呢!你把桌上的饭菜吃了去踉孩子一起睡吧犷;他这操说着说着,自己倒先打起了呼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他为她托着一个家、两个孩子户还有一份份工厂的产品计划、生产报表。而她则在前线冲锋陷阵,攻克一个又一个坚固的堡垒和攀登着一个又一个商界高峰。终于有一天,她要实现自己生产好产品、生产大规模产品、生产名牌产品理想的时刻到了。小厂一天比一天大了。以往走出去求人推销的局面,变成了别人上门求她要货了。一个个由她亲自设计、亲自监制的产品,不断在市场上走俏。
“你说我该不该有自己的品牌了?”她依旧有什么事就先向他“请示汇报”。
一向凡事都要深思熟虑一番的他,这回反火急火急地说:“这事我早想跟你说,没有自己名字的产品就像没有奶吃的孩子,总归长不大。我查看了世界那些名牌纺织业生产大厂大企业,没有不注意自己品牌效应的……”
她有些生气了:“既然你早有想法干啥不早点告诉我?”
“哎,这几个月里我们家里连你的影子都见不着,别说你能静静坐在我面前几分钟听我跟你说点事呀?”
可不,总有那么好几十夭了吧?她歉意地笑了,说你不是不知道这阵忙叹。
忙是忙,那你也该回家看看孩子。
她说,咋不?我出差半夜在大街上遇步想的就是两个孩子,还有你。有时在车上旅店里打吨都在梦里想到你们……
他幸福地笑了。突然,他说:“有了!”
她一惊,有啥?
“你不是爱做梦吗?爱做能有一天让我们老饭村这个小厂也能大大气气跟人家一样在大市场上称雄称霸的梦,爱做有一天也能让我们老洪村农民家家户户过上富裕日子的梦。对,现在这个梦不是快来了吗?梦来——梦来,你做的又都是**用品,一枕美梦就来。对,就用‘梦兰’怎么样?”
“梦——兰,行,这个名字好听,又符合我们的产品内容。就用它!”
老板定了?
定了。她高兴地拍起手来,这个品牌一定要打响!
那——什么时候大老板给我颁发“专利奖金”呀?
她乐了,说现在就给。
“梦兰”——这个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响亮的**用品名牌就这样开始出现在国人的眼里。昔日那个连她在内由九名农家妇女组成的小厂,也一年一年地像滚雪球似的增大增结实了。
而就在同一个时候,她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都在长大,可她似乎并没有感觉,她甚至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也用起她的“舒而美”了?
——女儿说,妈你啥时正眼看一看我么,你看我红嘴唇好看不好看么?
而就在同一个时候,她的他越来越变得消瘦,变得“怎么没份量了”?
——他苦笑说,那是因为你现在越来越光彩照人。
她以为是他又在嘲笑她,娇柔地说了声“去你的”,就没有再去理会他……
真的没有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后,她觉得自己和“梦兰”产品都像被后面有人赶着似的飞奔在高速公路上,甚至连喘气的工夫都快没了。
1991年夏,她到上海“中百一店”探“亲”访友,见有家企业送来一批踏花被销售,便上前细瞧,发现那被面质地良好,印花美观鲜艳,包装也十分讲究。再用手一摸,手感极好,与平常百姓用的棉胎被,不知要高出几个档次和多出几倍舒服。
一定是个替代新产品!市场意识极强的她马上敏感到。
“如果我也生产这样的产品一,‘你们能帮着销吗?:她间“中百一咭”老板。
“你们‘梦兰’的产品过得硬。只要你拿来,我们保证全力促个。”末了,店主外加一句,“最好有成批销量来!” ‘粉
“‘哎!”她点点头。
回到村里,她和几个姐妹一商量,决定立即上马踏花被。
——于是,她们先把老厂一改新貌,在一片湿渡滚的菱白田里盗立起了一幢新厂房;
——于是,她们又花几十万元购进了几套新设备;
——于是,她们又兵分几路到各地既建市场又进原料……
这一连串的行动,事实上仅用了80来天。8月底,新生产线上马,日产1000条,“梦兰”正式从手工作坊式的落后生产形式,走向了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