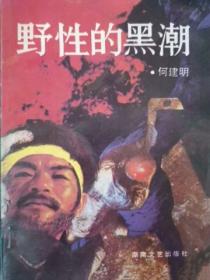乔斯,赫尔曼从赛场上退下无非是少得了一块奖牌。可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国家要从全球性的经济大赛中落伍,失去的就绝不仅仅是一块金牌,而是整个民族!
资源攸关着民族的存亡!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决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巨大躯体,需要依靠大量资源给予输血。谁想停止或者减少一点这种输血,便等于置国家与民族于死地。
中国的资源事业已被无情地悬挂在飞速向前的车轮上!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当中国面临资源危机的时刻,
一股叵大的野蛮的抢矿窃宝风,有如龙畚风一般地开始席卷神州大地。
圾初是那些岑星、边角的小矿,有人用锄头与铁铲,这儿刨一块,耶儿挖一勺,像轻风细雨,矿山无关痛痒;
后來是举足越过矿界线,有人开始肩驮担挑出现了买卖交易。矿山开始不安,在它的脚边和四周,已是噪杂的生意场。
再来,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开着汽车,打着显赫的招牌,漫山遍野地扑来,矿山陷入混乱和被动的退让,直至最后的失控。
开凿、采伐、抽吸!永无满足永无止境的开凿、采伐、抽吸!煤田、钨矿、铜山、汞窑……无数国家重点或非重点的矿产资源摧地,都在承受着空前的踩躺,处于存亡续绝的紧急关头!
于是,久负盛名的开滦惊呼:由于成百成千的小煤井与国营矿井争抢挖煤,大片有生煤田惨遭破坏,无法拾遗。
于是,号称世界锡都的个旧告急:十几个省的民采队进入国费区,矿山已呈无政府状态,每天竟有价值数十万元的精锡砂被窃;
于是,素有中国北极的漠河泣诉:当年慈禧派来的清兵和东洋鬼子都没有这么狠,用不了几年,富饶的金矿区将变成一堆废墟……
多少年来雄赳赳、气昂昂地鼎立在神州大地之上,支持着社会主义建设宏伟大厦,启动着共和国历史车轮前进的成百成千的国营矿山,似乎在一夜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崩溃。一份份停产的报告,告急的电文,如同雪片般的飞向地矿部、冶金部、煤炭部、石油部、民政部、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每一位珍惜人类资源、珍惜人类生存环境的有血性的炎黄子孙,当他了解中国矿山的现状时,都会拍案而起,忧心如焚!
据国家矿产管理部门统计:我国七千余座国哲矿山中,处在被劫、被抢、被占领而造成停产、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的达半数以上!其中,陷入水深火热的热点矿就有一百多个!
何谓热点?云南的兰坪铅锌矿便是典型一例。此矿国家耗资数千万勘察费,查明了1400万吨的储量。这一旗惊世界的铅锌大矿正处于筹建阶段,却被人乱采乱挖,在短短几年内,耗废了500余万吨高品位的富矿石,留下的是一片丙孔千疮而目全非的荒丘。
1989年7月,在塞外明珠一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资源学术讨论会上,一批老专家们用拐棍将地板捅得咚咚直响。他们疾呼道什么最重要?没有饭吃最重要。矿产资源就像我们吃的饭,上帝给得有限。可是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肆无忌惮的掠夺式开采,其结果是,明天的中国人将没有饭吃!
明天的中国人将没有饭吃!
难道这是耸人听闻的瞎说?不,当我们稍稍冷静下来看一眼处在无法无天中的中国矿山现状时,结论将自然而出。
希望明天的日子过得好些,就该多看一眼现实中的今天。我们应该学会这个。
啊,充满希望而又痛苦的民族,聪明而又愚昧的庶民!
由于对富有的追逐,常常使善良人变得贪得无厌,变得罪恶累累。
——魏斯曼
中国太穷。中国的山区更穷。
十一年前,那时我刚参军,部队就驻扎在湘西重镇怀化。我们的工作是整个湘西山区的普查与测绘。我随部队走了许多地方。那时的山民真纯。别说你是穿军装的解放军叔叔,就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地人,走到他家,他都会热情的接待你,尽家中所有往外拿。只是我发觉他们拿出的东西很可怜:一块黑得发亮的腊肉,据说是湖南的一大特产,可我怎么也吃不惯,吃不下。老乡们待我们太好了。后来我才明甶原因。一位大队党支书告诉我,他这村从他记事起,总共才来过两次解放军:一次是一九五〇年的剿匪时期,一次就是我们了。难怪!湘西剿匪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只是听人说,湘西是土匪大窝,土匪多得数不清。有人形容道:解放前的湘西,一家三代人,老子是土匪,儿子是土匪,孙子长大后还是土匪。我有点想不通:都当土匪,那么去抢谁呢?
怛湘西的土匪之多,是中外闻名的。原因只有一个字:穷!穷者则窃,窃者则为盗,盗者则为匪。自古以来,为匪者最可恶。湘西的土匪则分两种,一种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一种则颇本分、善良,不抢穷来不贪富,有了东西大家分,寨规很严,颇有点像早期的游击队。这些人原本是些安分守己的百姓,被3匪害苦了,才上山立寨,以求自保的。有的人甚至称他们为好土匪呢。
今天的湘西,又有人在当土匪呢!在长沙时,有位湖南籍朋友这样对我说。
现在还有当土匪的?我睁大了眼睛。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说得轻松,就像人们谈论今天广州和上海有妓女一样;开放了,别人都富起来了,现在湘西也通上了火车,一些老百姓家里也有了电视。他们懂得了人不该总贫困。城里人能住洋房,出国,玩女人,我们也是人,为啥不去住洋房、出国、玩女人?他们头脑在开化,观念在改变。他们是新一代的湘西人,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可他们没有帛开那块祖先留给他们的穷山辟壤,他们的血管里流眷父辈贪欲与野性的血液,他们就开始穷则思变。于是,便有良民变成了土匪有了八十年代的新土匪……
为了探究湘西的今天,我开始了冒险而又漫长的旅行。
祜井沟的阿里巴巴。
枯井沟村一一一个在我记忆里熟悉的村庄。这里是个滴水贵如油的穷山乡。方园十几里没有一条溪流,百姓喝的是老天下雨淤积的泥塘水。天一旱,乡亲们只得爬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担水。民国元年,村上有位出外当了洋学生的人回庄后,左看风水,右看地形,接一连二打了几口井,结果皆不见龙王爷出现。后来,又有几帮小伙子卖儿卖女,积攒了些钱在村边和山上掘了无数口井,可口口皆枯,枯井沟村因此而得名。没有水的村庄就象没有奶的婴儿,祜井沟永远是贫困村,打解放以来,年年吃国家救济。1979年,我一进这个村,奇怪地发现男男女女都穿着一色的劳动服。一打听,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国家的救援物资。枯井沟四面是山,到县城得走三天。小伙子找不到对象,姑娘宁可嫁给瞎子、聋子,为的就是飞出这山窝窝。我住的那家,儿子名叫墨西,是位二十来岁的壮小伙子,也不知是吃了什么东西,那大山一样结实的脊背充满着雄性的力量。据说他父亲生他下来没多长时间就死了。他的家离其他户宅远远的,孤单单地搭撑在两座大山相交的阴凹处。
他从不和村里人交往,不过他的房子挺宽敞,你们去试试看。生产队长听说我们要在他家住下,便说。
我们几个好奇地跑到他家敲了几声门。小伙子出来了,他仅穿一条黑裤子,上身赤着。石板一样的胸膊黑得:发亮,只有常年这样**的人才有这种颜色。见我们几个都是穿着军装的,小伙子那双仇视与暗淡的眼睛,顿时闪出热情的光。
哎,快出来给解放军同志倒点水。他这样招呼他的母亲。
为了帮助枯井沟的老乡解决千年之愁,我们部队决心在这一带为群众寻找地下水源。这里趋个岩溶干旱区,经过几位水文地质工程师的普查测探,我们得出结论:祜水沟一带是有地下水的,而且根据所攀握的地质资料证明9这儿的地下藏着龙王爷,只是人们过去一直没有发现而已。因为龙王爷一般隐藏于很深很深的地下老百姓靠简单的人工打井肯定难以见到他的尊颜。部队下了很大的力量,查了一个又一个千年古洞,也始终没有找到。最后,从地形上分析和老乡提供的资料,认为应该还有一个溶洞,结果发现这个溶洞的洞口就在墨西家后边。第二天,当我们正准备向最后一个洞穴探险进军时,没想到墨西死活不让我们进去。我见他怒气冲冲地站在洞口,手里还拿着一把劈柴的巨斧,仿佛要与我们拼命。
墨西,你这是怎么啦?我们连长问他。
墨西的双手在颤抖,胸膊起伏着,说我决不让你们进去。这是我祖先发现的洞,决不允许你们冲撞我祖先的神灵。
这真是怪透了!叫大队干部来劝说也没用。我们只好停止了行动。晚上发现,墨西把我们几个人的行装从他屋里全扔了出来。他是要赶我们走!
枯古洞的老乡含着眼泪送我们走,而我们则带着遗憾和惆怅离开了这个村。那时部队里有条纪律:工作中要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是啊,为了不触犯墨西的神灵,祜井沟的百姓还得过滴水贵如油的生活,还得永远穷下去。多么落后的山村,多么愚昧的山民!那时的湘西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
想不到在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接受地矿部委派,调查群众采矿风潮的第一个采访对象,竞然又是枯井沟!
去祜井沟,从古丈下火车后,还得走三天。在摇摇摆摆的手扶拖拉机上,我一边望着两边耸入云端的大山,一边想着进村后是否还是锣鼓喧天的欢迎解放军同志进村的热烈场面以及大队支书热情得发烫的贺词。当然,最想的还是墨西,他是否还那样壮实,还死守着那个神洞?
嘟嘟一一!拖拉机的急刹车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到了,下车吧!车把式对我说。果真,眼前就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山村!
交钱吧!
多少?
150块。
什么,才二十几里路就要150块?我对这位车老板如此黑的价大为惊讶!
车老板黑着脸,显然很不满意,蔑视地瞥了我一眼,说,看你没带什么家什,我开的还是便宜价呢?快拿钱吧!不然,就把你手里的皮箱留下也行。他看看我,露出一丝山民特有的狡黯的笑容。
我简直把肺都快气炸了!可想想要不给,叉有什么办法?礁对方那个虎视耽耽的神色和壮实得能同东北虎比高低的块头,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无奈,为了这倒霉的采访,为了这枯井沟的冤家。
给,把我这半个月的差旅费全给你!我气呼呼地打开皮包,把三张面值50元的新票扔给了他后,转身朝村里走去。
哟哟,同志,慢点走一!他又在后面叫住我。
怎么,还不够!我真火了,把皮箱往地上一放,意思是说:干脆你把这东西一起拿走算了。反疋里面除了一台旧相机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稿纸之外,没有什么值钱的同志,别误会,我,我不是这个意思。车老板一改方才那副生意人的面孔,笑着对我说你是记者吧?
我点点头,心想:怎么,记者就还可以多敲竹杠?
真对不起,对不起,这钱你收回吧!算我顺了你一段路。他把三张新票还给了我。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还以为您逛来收货的大老板呢!所以……
大老板?收货?我听不懂他的话。
您没听说?哈,咱枯井沟如今是发啦!山内山外,就是连省城的人都住咱这儿跑呢1车老板越说越来劲这开春季节还算是闲的呢!一到六、七月份,像你这样的外乡人,我每天大概要拉上三、四十个。
他们是什么人?来这儿干啥?我好奇地问。
车老板眼睁得溜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怎么,像你们这样的记者都不知道!他们呀,全是到这儿收货的大老板!收什么货?这儿真发现了金子?虽然在长沙时,省地矿局的同志对我介绍过枯井沟,可我夂直不相信这个滴水难找的穷山村怎么可能成为宝葫芦。
那还有假!车老板得意地说。
这么说,你和你们村全成万元户了?我禁不住高兴起来。
车老板眼睛眯着,直摇头万元户算个卵!
我一乐,想将他一军这么说,你是个十万元户啰他笑笑顿了一会,说这么讲吧,那些外地来收货的阔老爷们到咱这儿走一趟,一般都在这个数以上。山民自有山民的狡黠,他把我要得到的回答巧妙地搁到了一边。
五千!
他摇摇头,说乘十倍!
我伸了伸舌头。
你想,他们来一趟拣那么多,进山乘我一趟车,掏个三、四百元算个卵!
好小子,难怪他收我这么多路费还说少呢!他把我当成了走私黄金的大亨了。可惜他不知道那巧10元几乎是我一个月工资和奖金的总数呢!钱还在我手里。我想了想,说:虽然我不是大老板,但总归是搭了你的车,多少你得收点
得得得!留着你给老婆孩子买米买油吧,或者请什么情妇之类的小姐们吃一顿饭用吧!这小子还贼油。
喂,朋友,你给我好好说说村里的情况,还有墨西他还在吗?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枯井沟的今天和我以前所认识的
喔对不鸡,对不起,我可没那闲功夫,你们这些玩墨水的,一聊就没个完,而咱枯井沟这几年的事又非一两个小时能说完的!小伙子摊得干脆。他看我犯难,便说这样吧,到我家先歇歇脚,我老爷子在家,你跟他聊准行!反正,他整天歇在家里没事!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满怀信心地跟着他来到村头一栋新盖的木阁楼。这是典型的湘西山民建筑:伞形的木房,不用一块砖那儿也没有砖除了宅基是石头的外,全是用的木料。这个木房比我过去见的木房,除了结构没多大变化外,其面积,其用料,其装饰,简直是天壤之别。那崭新的木板漆着桐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衬着屋后的青山,远近看去,都显得高雅、别致。小伙子把我领进他的客堂。嗬,里而的陈设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木壁和顶板全都贴着高级墙布,地板上铺着大红地毯。我一摸,是正牌的内蒙货。一套组合式家具,虽样子有点土,但用料却是城里的组合柜绝对不能相比的。此外,什么电视机、冰箱、收录机、缝纫机……应有尽有。
怎么样,不比你们城里人差吧?
我自愧不如地点点头。他在向我端杯子的时候,我见他手上戴着两只少说有二十克的大戒指。纯的?我问。
他点点头,说:当然。我们可不像你们城里那些丫头骗子,戴的冒牌货。你想要吗?我可以给你搞个比城里便宜三成的戒指!
那得我挨半年饥肚!
他又摇摇头!得意地笑笑,那神态明摆着是嘲笑我们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城里人。
阿爹!您下来一下,这位北京来的记者想跟您老聊聊。他走出房门,朝阁楼上喊道。
半晌,上面才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管不了那么多,你看着办吧!
小伙子朝我摇摇头没法,打那年村里出现淘金发财热后,老爷子气得把党支书也辞了,一直呆在家里不出门。他看不惯大伙,也看不惯他的儿子。您瞧,我盖了这么好的房子让他住,他偏不,说是这资本主义温床他绝不睡。这不,一年四季在上头挨冻受热。唉,钻了牛角出不来哪!
你爹就是老支书?我忙叫小伙子带上楼,想听听当了三十年村支书的他是怎样看待枯井沟的今天的。
走上阁楼,只见老支书老多了,可他依然穿着我十一年前见过的那身装束:一身青布衫,一个旱烟袋,头上戴着一顶草绿色军帽一只是颜色已经变得发白我记得这帽是他跟我们连长特意要的他仰躺在**,裹着一条黑乎乎的被子。床头是一幅毛主席的正面画像,旁边贴着一纸红纸,上而写着艰苦奋斗,勤俭治国八个大字……
老支书,还记得那年有队解放军进村帮助打井的事儿?我上前问道。
老人抬了下眼皮,定神把我好好端详了一会儿,眼里顿时闪出一缕光泽,但即刻又阴沉下去。他是想起了十一牟前的事,也认出了我。
老支书,枯井沟比以前富多了,可我感到富得不太对劲呀!你能给我说说这几年的事吗?还有村西头的那个墨西,他还把着那个神洞不放吗?
老、一听我这话,似乎一下找到了知音,激动得哆嗦起来。你,你……是上面来的,今儿个,我们俩好好聊聊。枯井村的亊,我心里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年了,可……可就是没人听我的呀!呜呜……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那副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的肩膀剧烈地颤动着。那哭声,仿佛让我感到天怆地悲一般……
许久,他才抬起头,断断续续地对我说这枯井村的过去你是知道一点的,穷,穷得老鹰儿也不愿在树顶上歇一歇脚。都是因为老天爷断了我们的水源呀。打土改到1980年,我从二十八岁当大队干部一直当了30年,不知想了多少主意,可就是没法子让大伙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粮织布,也就只好年年吃国家救济。我是共产党员,一年四季白吃白穿政府给的,心里不忍呀,可又冒得法子。那年,也不知刮的什么风村甩的年轻人都背起铺盖往外跑,去广州、深圳的都有出去几个月,回来时不仅大包小包带着,而且带回来了满脑壳的钱钱钱。村上王贵的儿子小三,过去穿着老爷子的衣服,到深圳的香港老板那里干了一年,回来时两只手上都戴着金疙瘩。逢人就夸耀,多少钱多少钱一克。也不知咋的,向来不合伙的墨西一听这事格外起劲。他缠着小三带他到深圳去。墨西到深圳后一不找活干,二不与小三子合群,独自彡!一个人经常到外国人住的地方蹓跶。没儿天,墨西脸上像挂了彩似的回来了。大伙猜测他一定发了大财,可又不知道他用啥法发的。过了几天,他又走了,过几天他又回来了。半年里,他来回二、三十趟。也不知他搞的么子名堂。反正村里有几个后生说,他娘病死后,请的道士就有二三十个,念经七天七夜,那场面就连过去这一带有名的活扒皮王满大地主也办不起呀!这年是个大旱年,大伙过年时连一餐饱饭都吃不上,老老少少围着大队办公室,非要让我们同意把队里的三头黄牛给宰了填肚。这时辰,墨西来了。他打开一个布兜,对大伙儿说。拿去吧,过个好年大伙儿一看,天!全是一释择10元的新票子!大伙哄的一下抢开了,差不多每人都能得三、四张,那情景,就像外国有个么子电影里,对,叫阿里巴巴!咱墨西那时就像个阿里巴巴!墨西有钱这山里山外的人都知道。俗话,财大必招祸。那年疋月的十七还是十八,一群外乡人蒙着脸,带着家伙乘黑夜冲进了墨西的家。他们以为墨西在**睡觉,便举起大刀向**乱砍。后来发现遷西根本不在家里,这几个蒙面人便开始翻箱倒柜,结果啥都没有找到。正在这个时候,在外面放风的那个人见墨西从屋后的山
崖草丛里突然钻出米。放风的赶忙躲在一边。墨西不知他家里的每个角落里都有几双眼睛正叮着他。但是他楮明得很,当他点亮蜡烛瞅见屋里的东西跟以前摆的位置不一样了,便马上觉察有人。他鬼得很,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独自出了门,直往村外走。这屋里儿个人见墨西放在桌子上的东西闪闪发光,觉得好奇,上前划亮火柴一看,原来是几块金疙瘩!蒙面人一看这宝贝,大打出手。第二天,这事就在村里传开来,墨西的秘密也让外人知道了。后来,乡里的干部找到了墨西,问他金子是哪儿来的……
墨西是怎么说的?我问。
你还记得那年解放军帮我们找水,想进墨西后宅的那个山洞吗?老人反问道。
记得。
啥子神洞,原来是个宝窟。老人瞪大了眼睛继续说道那天,全村几百号人,跟在民兵后面,胆怯怯地往洞内走。洞内可奇了,你大叔我活了六十七岁,第一次见过那么中看的石头。那洞越往里走,越玄乎,洞中有洞,洞中套洞。穿过一个葫芦口,突然所到轰隆一一轰隆的响声,邠胆小的吓得直往后退。我和几个基干民兵亮着电简,举着枪,朝有响声的地方慢慢走去。这时,响声变成了一道大得吓人的白光。我双手捧着电筒,往发白光的那个方向瞧去。啊,你猜哪是么子东西?老人的脸上放射着我曾经见过的光彩。我摇摇头。
水!、就是你们要找的水!
什么?那个洞里真有水?我也不由惊呼起来。
是的,而且很大很大。
这下好了,枯井沟再不愁穷了!我高兴地说。
听了这话,老人刚刚露出的光彩又熄了下去。穷倒是不愁广,可后面的事让人更愁!
怎么讲?
就在我和几个老哥们为找到龙王爷高兴得快要昏过去的时候,一帮小年轻却在一边大打出手。你猜为么子,原来他们找到了墨西发财的宝窟1就在那条地下河的旁边,有一条很长很长的沙沟,从这条沙沟抓一把沙子就能捏出黄豆那么大的宝疙瘩来。穷得连娘儿们都睡不动的村里人,这下可闹翻了天,抢啊,打啊,折腾了整整一天!到太阳落山时,巳有四个人的胳膊、脚丫被打断砸伤,可受伤的人还在没命地同那些强壮有力的人拼抢。这枯井沟发现了金宝窟的消息不知是谁传出去的,第二天,墨西家的这个神洞内外足足聚了上千人。大伙儿简直个个像发了疯,连十几年不起床的八十多岁老爷子也拄着拐棍来挖金。也不知是触怒了地宝爷咋的,这天中午,洞内突然一声巨响,随后石头像雨点似的朝挖金人的脑袋砸来。人们不顾一切地往洞外跑,可洞口小,人多拥挤,那些跑得慢,或者还想多挖一些金疙瘩的全都埋在了石头底下……
听到这儿,我的心仿佛一下被针钩了起来。死了多少人?,
后来点了点,我们枯井沟死了6个,外村的5个,伤的就更多了……老人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照片,那上面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老人指着照片说我的大儿子是6个中的一个。他死后,媳妇带着我的小孙子改嫁到了隔县的石门那边。大儿子贪财命里注定,可我想孙儿呀……
我这时才明白方才老人为什么那样悲怆,他以前不坫这样的。那年我们进村,队里人都说,老支书的骨头跟大山一样硬。而如今……我不山同情地哽咽起来。
大叔,那个墨西现在在哪儿?
老人摇摇头那晚他遇到蒙面人出走后,再也没有回过枯井沟。后来有人说他在深圳走私黄金疙瘩时,被黑道上的人打断了一条腿,成了疯子。如今是死是活没人知道……十一年前,墨西这个人就烙在了我的记忆中。如今,这个中国阿里巴巴更让我发生兴趣。我非常想了解他从落后的山沟走向现代化城市过程中所经历的金钱梦。我费了好大劲,后来才在深圳公安部门主管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找到了他。可惜,只仅仅是一张他的病厉,一张写得特别简单的死亡记录:
墨西,性别男。约32岁。自称湖南湘西人。1984年因走私黄金被人用铁锤致残右腿,抢光身上所带大批钱财,故受精刺激患疯癞痴呆精神病。经三个多月住治,稍有好转。同年10月15日早,护罕人员发现患者卧地不起,原巳死亡三小时左右。患者鼻腔口腔内全部是堵满的泥土。经现场察看,为患者自身行为所致。死亡当日送火葬场火化呵,可怜的中国阿里巴巴!
湘西的每一座山,每一条路,越走越感到神秘。这+仪仅是怀旧和好奇。因为墨西的昨天和今天,使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思索与忧虑。我决定继续往前走……
龙山的黑道英雄们
不知是一出《乌龙山剿匪记》电视剧的缘故,还是龙山那儿的群山本身就具有**力,总之,我喜欢这儿。那山,那高入云霄的山,那苍绿遮着蓝夫的山,确实有股大都市的来客为之倾倒的魅力。但,龙山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怪石奇峰的峻、险、神、奇。一座山,足够组成一个迷宫,组成一个世界。
龙山的自然美,风光美。
美,常常与丑恶连在一起。不知是谁这样说过。
我踏入这块土地听到的第一个新闻是关于一个穷得潦倒的黑手帮主与富得毛孔里流油的被害者之间的纠葛。
事情发生在龙山某镇的一栋两层楼房的居民住室里。
住宅的男主人姓田,名二顺,女主人叫王玉秋。1984年夫妻俩退职,办起了一个马蹄锑厂,后来又租赁了一家精锑冶炼厂。一家两厂。日子无疑绝顶的红火,田二顺夫妇成了镇上屈指一数的人物。他们家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只知遒前年税务部门让其补税一次就补了38万余元。现在,田二赋和他的老板娘王玉秋,不仅有两爿厂,而且有一个运输队,五个产品销售员,完全是一条龙的生产方式,完全是正儿八―经的金属冶炼企业。
我很想结识一下这家以前曾是贫困户的山庄大富翁。碰巧,接待我的派出所长正在为田家的事忙碌着。咱这个派出所,一半的事与田家有关!所长唠叨说你感到奇怪吧?其实1没什么,这镇上他们一家的年收入相当于全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情况非常特殊。
这天早饭时辰,老板娘正在梳头打扮,17岁的女儿给她递上一封信。
这么早就有人送信了?王玉秋觉得奇怪。
不,是我从门口拾到的!女儿告诉她。
老板娘一听,心中顿起疑团。她急忙将信折开,仅扫了一眼,就吓得浑身发抖,黄豆大的汗滴直从额七冒出……
信很短,却句句如同炸弹:
田兄:
你好,久闻大名,无缘相会。今派人投书一封,有事相求:我刚成立乌龙山青天帮会,因缺费用,特请田兄帮忙,务于次日晚零点,将3万现金送到镇槐荫树下的坐石底盘处。我等虽生死无忧,但也讲究义气,望兄三思行事。如有违义之嫌,我会将在10曰之内诛灭你全家。拜托。
马龙山青天帮会主拜上。
田二顺一家虽对生意场上的种种明争喑斗,应付裕如,可对这类黑势力却无能为力。保镖是有,但怎能抵敌不长眼的黑枪?田氏夫妇只好求助公安派处所。经过三天突击侦破,便衣警察很快摸到线索,并一举全歼乌龙山一青天帮会成员一一可惜整个青天帮会连将带兵总共才一个人。
此人姓彭。第二天,当派出所公安干筲给其带上铁戒指,押向县城时,镇上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彭某是镇上有名的五好居民、老模范。一个年年当先进的老实人怎地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犯?人们摇头,叹气,又找不出答案。
后来,这个谜是从公安局的审讯记录中解开的。下面是彭的话:
……我同田二顺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在镇上工作。他和他老婆肚里装多少坏水,我都掂景得出。1958年时别人响应上面号召砸锅卖铁,他们却把公家仓库里的粮食往家里揹;1962年闹灾荒时别人饿得刨树皮挖野菜吃,他们却挑着白白净净的大米上街卖三块钱一斤。可就是这个田二顺前年竟然一下甩出20万元,给镇上盖了一崎后生念书的中学。为这,乡里县上不知多少次在会上、报上、广播上称他是致富不忘我龙山〃支援教育功千秋的大功臣。打那起,乡长放的屁不如田的香,县里干部恨不得唤他们做亲爹娘。我百思不解,最后想,大概是皇历变了,好人坏人要换个过。我思忖着,我是一贯老模范,老先进,这改革致富中也总不该变落后了。啥法?再靠带着红袖章义务扫街洗厕所也不会有人给我评先进和劳模了!我,我可怎么办呀?这个田二顺,他把我害得好苦!我可饶不了他。好日子你就一家过?香馍你就一个人吃?不行!我过不上好日子,你也别想过安乐口。于是,我就在半夜里爬起来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蒙蒙亮,就把信塞在了田家门缝内……
彭因诈骗、恐吓和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而被判了半年监外执行。田老板的锑厂无丝毫损失,反比以前更加红火。
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事,派出所的干替们已在忙着接待接二连三前来报案叫屈的群众……
听着一个又一个受害群众的诉说,我不由愤慨起来。可派出所的同志对此却很漠然。
唉,这类事太多了,几乎每周都有那么几起。我们这个三人编制的小派出所,如今已超编了一倍,就这样还忙不过来呢1所长摇头又叹气,道!再说,那些走黑道的人除了个别是天生的刺毛货,大多是些石卵子。
石卵子?
就是些被生活淘汰下来的人。执法者的语调里显然流露出同情感。这倒使我产生了想了解那些石卵子的兴趣。在正面接触那类靠抢矿窃宝发大财的大冨翁和暴发户的罪恶行径之前,能接触一下因穷困潦倒而参与偷矿抢矿,由良民变成土匪的人,无疑对我的采访有极大好处。
听说离镇三十里的深山里,这类人很多。于是,我把胆子吊在嗓门处,开始了一段不平常的闯**……
进山的路是条土公路。据说,山里有个新开的大矿,土公路是因此而修建的。公路两边是遮天盖月的大山,我抬腕看了下表,才下午四点多一点,可天色却已成暮。好在公路上有接二连三的马队和拖拉机、大解放、大挂斗等各种运输车辆,因而并不感到害怕。
我走着走着,慢慢发现公路上的车辆蓦地少了,偶尔出现一二辆大车,也开得特别快,并且上面都有持枪的人押着。这让我感到既紧张又兴奋,大概到了石卵子的她盘,或者是他们出山活动的时辰了。说实话,在这陌生的深山里,孤身只影,我的胆是颤着的。我一路走着,满脑子想着绿林小说里的那种主人公走进深山老林,突然从天上地上杀出一群土匪强盗,然后将他劫持到一个不知去向之处,或断骨碎尸于荒野的场面。过去自己曾经也写过这类的小说情节,没想到眼下倒是真个身临其境了。
生活比小说更奇特。拐过一个大弯,突然,前面的一个山坳里亮起了一团篝火。那篝火四周隐约可见不少人影,过一会,传来一阵参差不齐而又疯狂的歌声,细细听去,却是一有熟悉的歌: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哎!哎!哎!
别是山野酒巴?我不由提起梢神,大步走去。
喔!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见公路的两旁闪出几个黑影,动作极其神速地用什么东西将我双眼蒙住,然后连推带搡地将我推下公路。
双脚一高一低地被动地迈着,我感觉到是走在一条杂草丛生的山道上。
放开我,我抗议你们无故抓人!不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抓来一条旧毛巾蒙在我的眼上,我喘着气,直感恶心。
妈的,叫唤么子?老子让你抗议哟!有人恶狠狠地往我嘴里塞了块硬梆梆的东西。我的胃肠一下反倒到嗓门。这帮家伙大概拾了块擦脚布什么的塞在我嘴迅了。
六爷,抓来一个溜子!看样子是外地来的!
刮了?只听一个嗡里嗡气的声音问道,无疑他就是六爷。
没呢!
我感觉有人走到我的眼前,大概是在打量我。几秒钟之厂!,突然,六爷嗡里嗡气的命令道刮!
顿时,有无数只手在我的身上搜开了。
一个三路货,连抽的烟都是不带把的搜身停止了,那些似乎第一次这样带霉气的手,报复似地给了我几拳。把他的包打开!
我的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台照像机,就是二三百块旅差费。
么子油水?还不到半叠!这句话我懂,意思是说不到半千。
有入在扒弄照像机。佘不会是老公?
嗯?!我口中的布猛地被抽掉。说,你是什么人?盘问开始了。我思忖片刻,回答我是记者!
积善?哈哈,头回听说倒爷们还有这份善心!
瞎放妈个屁!那个六爷显然在生他那无知到极点的部下的气。后面的话却是对我所说既然是当记者的,不呆在城里吃东拿西的,来这儿干么子?
卜你们这儿不是也很好么,许多人靠山吃山,大发横财!我说。
说话别带弯,谁他妈的发横财了?你小子是不是觉得老子也楚两腿踩着国营矿山,双手尽往家里搬金银财宝的那号人?一把冰凉的刀搁在我的脖子上。
沉默。
六爷!山上的运输车下来了,动不动手?正在这时分,有人气喘喘地进来报告。
几辆车?六爷嗡里嗡气地问。
三辆车。
前后有没有跟帮的?
没有。
六爷,下令吧!他妈的!好儿天没得手了,弟兄们的裤腰带都松下来了。
对,三车矿石够我们吃一阵子的!下令吧!
好吧。不过,敢在这时候出山的车都有家伙,大伙得小心点!六爷终于开口了。他的话刚落,只听众人一边动作起来,一边说着不怕,我们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有武器。
六爷,这人怎么办?一个家伙搡着我问。
把他带到洞内,让老孙头看着。回头再处理。六爷说。
劫车的队伍喧喧哗哗地走了。两个人押着我七绕八绕地走了一段,然后进了一个黑乎乎臭哄哄的山洞。
老孙头,有个人,是外地的,六爷让你看着。我们去拿活了!两人说完便出了洞。
喔……咳咳咳……一串并不很响的咳嗽声,在洞内却如打雷一般地回**着。你把蒙眼的布摘了,怪闷的。咳咳……咳咳咳……这人大概就是老孙头吧?
我庆幸碰到了一个好人,因为我能自由了。不过,当我摘下眼上的黑布时,却发现自己多么天真,那个躺在一堆干草上的骨瘦如柴的人手里持着一支土枪,正虎视眈眈地盯笤我。
打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他说话有气无力,口气却象法官。
我没有回答他。心想,跟你们这些蛮不讲理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洞很大,只有几盏松子油灯在忽闪着,使人感觉阴森森的。地下有许多类似老孙头躺的干草床看样儿这是一个匪窝。
不会是哑巴聋子吧?或,或者咳咳……咳咳……几天没有吃饭?
我真不愿听这令人作呕的咳嗽。北京来,当记者的广我说。
啊一你,你是当记者的!不想老孙头那张死人一般毫无表情的脸蓦然露出一丝兴奋的光芒,随后颇埋怨地唉,老六他们搞么子名堂,不该咳咳……咳咳咳……不该抓你呀!你,你快走吧,他们要是拿不着的话,回来就要拿你出气的走,走吧!
半途遇难的我,万没想到匪窝后竟会是这个结局!老孙头越让我快走,我倒越不想走了。我感激而又关切地说:谢谢你了。我看你病得不轻,大概呼吸道有毛病,得上医院狞看,住在洞里又湿又潮,空气又不好,会加重病的!
老人收起土枪,苦笑着摇摇头山里人,有点病熬一熬就过去了。再说哪来那么多钱上大医院,
干你们这一行的不是很……活泛吗?
唉,一朝和尚一朝经,朝朝和尚都有难念的经。你不知道啊!
又一个没想到!都说强盗土匪拉出的屎都是金豆子,他们就这么可怜?既然这样,为什么不下山回家好好种地,或者搞点家庭副业,走正儿八经的致富路,干吗要当让人憎恨的土匪?
什么?你也骂我们是土匪?!看我咳咳……咳咳……老孙头重新拿起土枪,欲支撑起来与我拼命,可他怎么也没起得来。哎,土匪,土匪!可这是谁作的孽?!解放前那阵子,咱这儿十有八九的汉子出家成匪,我没去。没想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却……呜呜……
又一个没想到!!许久,我才问他:大爷,你刚才的话真让我不懂。为什么解放菔你都没有当土匪,可今天你却……?老人用干枯的双手象孩子似的抹着泪,说好后生,其实,我还不到你叫大爷的年龄呢。我满打满才55岁。可你瞅我这样足有七老八十了吧?唉,说句心理话,谁愿干这种造孽的事?可我们心理有气,有气呀!
看着他那样,我忙蹲下身给他后背垫上一件棉衣。你能给我说说吗?我该称呼你大伯才对吧?
说来话长,不过,讲给你们记者听听兴许有点用!他长叹了一声,说有几年光景了。上面号召大伙发家致富,咱这儿除了山还是山,种粮没水,有木材可运不出去,日子还是那样紧巴巴的。那年不知是哪个鬼孙想出个馊主意,说咱后山就是个聚宝盆,干啥不去呀!村上的人一听就来了瘾,一两天里,全村男男女女都往后山跑了。我就没去:
你为什么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