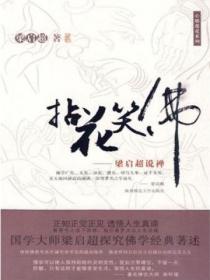叙论
爱有大物,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强取,发荣而滋长之,则可以包罗地球,鼓铸万物;摧残而压抑之,则忽焉萎缩,踪影俱绝。其为物也,时进时退,时荣时枯,时污时隆,不知其由天欤,由人欤?虽然,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不宁惟是,苟其有之,则濒死而必生,已亡而复存;苟其无之,则虽生而犹死,名存而实亡。斯物也,无以名之,名之曰“元气”。
今所称识时务之俊杰,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国也。欲进吾国使与泰西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诚当矣!虽然,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觉自任者,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不可不留意也。
游于上海、香港之间,见有目悬金圈之镜,手持淡巴之卷,昼乘四轮之马车,夕啖长桌之华宴,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陆有石室,川有铁桥,海有轮舟,竭国力以购军舰,胺民财以效洋操,如此者可谓之文明乎?决不可。何也?皆其形质也,非其精神也。求文明而从形质人,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他路可以别通,其势必不能达其目的,至尽弃其前功而后已;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
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自衣服、饮食、器械、宫室,乃至政治、法律,皆耳目之所得闻见者也,故皆谓之形质。而形质之中,亦有虚实之异焉,如政治、法律,虽耳可闻,目可见,然以手不可握之,以钱不可购之,故其得之也亦稍难。故衣食、器械者,可谓形质之形质,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则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致,非一人一家之所可成,非政府之力所能强逼,非宗门之教所能劝导。孟子曰:“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之谓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节节,模范其形质,终不能成。《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口气而已。故吾今者举国民元气十大端次第论之,冀我同胞赐省览而自兴起焉。
独立论
独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属,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嗟乎!独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易》曰:“君子以独立不惧。”孟子曰:“若夫豪杰之土,虽无文王犹兴,”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人苟不自居君子而自居细人。不自命豪杰而自命凡民,不自为丈夫而甘为妾妇,则亦已矣,苟其不然,则当自养独立之性始。
人有三等:一日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日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三日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夫世界之所以长不灭而日进化者,赖有造新风气之人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后,举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仅一二人。而举世目为狂悖,从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论、行事也,而在后则为同。在前则为独,同之与独,岂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则无所不同。而于同之前必有独之一界,此因果阶级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于同者则谓之独,古所称先知先觉者,皆终其身立于独之境界者也。惟先觉者出其所独以公诸天下,不数年而独者皆为同矣。使于十年前无此独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则十年以后之世界,犹前世界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
俗论动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世界上缺我一人不足惜,然使世界上人人皆如我,人人皆不自有其官体脑筋,而一以附从之于他人,是率全世界之人而为土木偶,是不啻全世界无复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木玄虚《海赋》曰:“水母目虾。”谓水母五目,以虾目为目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
阳明学之真髓曰“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等于不知。独立者实行之谓也。或者曰:我欲行之,惜无同我而助我者,行之无益也。吾以为此亦奴隶根性之言也。我望助于人,人亦望助于我,我以无助而不行,人亦以无助而不行,是天下事终无行之时也。西谚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于外者,则其精进之力必减,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责任既专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故曰天助白助者。孤军陷重围,人人处于必死,怯者犹能决一斗,而此必死之志,决斗之气,正乃最后之成功也。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当今之世,舍我其准?”独立之谓也,自助之谓也。
天下不能独立之人,其别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者,二曰仰入之庇者。望人之助者,盖凡民也,犹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隶也,不可言也。呜呼!吾一语及此,而不禁太息痛恨于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试一思之,吾中国四万万人,其不仰庇于他人者几何哉?人人皆有其所仰庇者,所仰庇之人,又有其所仰庇者,层积而上之至于不可纪极,而求其真能超然独立与世界直接者,殆几绝也!公法,凡国之仰庇于他国者,则其国应享之权利,尽归于所仰庇国之内,而世界上不啻无此国。然则人之仰庇于他人者,亦不啻世界上无此人明矣。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以全国之大?而至于无一人,天下可痛之事,孰过此也!
孟德斯鸠曰:“凡君主国之人民,每以斤斤之官爵名号为性命相依之事,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者。”孟氏言之,慨然有余痛焉,而不知我中国之状态,更有甚于此百倍者也。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颈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若夫以有灵觉之人类,以有血性之男子,而其实乃不免为畜犬、游妓之所为,举国如是,犹谓之有人焉,不可得也。吾今为此言,人必坐吾以刻薄之罪,吾亦固不忍言之。虽然,试观今日所谓士大夫者,其于求富贵利达之事,与彼畜犬、游妓之所异者能几何也?土大夫一国之代表也,而竟如是,谓国之有人,不可得也。夫彼求富贵利达者,必出于畜犬、游妓之行,何也?以有所仰庇也。此一种仰庇于人之心,习之成性,积数千年铭刻于脑筋而莫或以为怪,稍有倡异议者,不以为大逆不道,则以为丧心病狂也。彼其论殆谓人不可一日不受庇于人者,今日不受庇于甲,明日必当受庇于乙,如彼史家所论,谓不可一日无正统是也。又其人但能庇我,吾则仰之,不论其为何如人,如彼史家所纪载,今日方目之为盗贼,明日已称之为神圣文武太祖高皇帝是也。故数千年来受庇于大盗之刘邦、朱元璋,受庇于篡贼之曹丕、司马师、刘裕、赵匡胤,受庇于贱种之刘渊、石勒、耶律、完颜、成吉思,皆靦然不之怪,从其摆颈摇尾、涂指抹粉,以为分所宜然,但求无一日无庇我之人足矣。呜呼,吾不知我中国此种畜根奴性,何时始能划除之而化易之也!今来庇我者,又将易他人矣,不见乎入耶稣教、天主教者遍于行省乎?不见乎求人英籍、日本籍者,接踵而立乎?不见乎上海、香港之地皮涨价至百数十倍乎?何也?为求庇耳。有心者方欲以瓜分革命之惨祸致动众人,而不知彼畜根奴性之人,营狡兔之三窟,固已久矣。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
哀时客曰:今之论者,动曰西人将以我为牛马为奴隶。吾以为特患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而已;苟不尔,则必无人能牛马之奴隶之者。我国民盍兴乎来!
爱国论 (2 )
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耍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临之以势力,则贴耳相从;啖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骛。”盖彼之视我四万万人,如无一人焉。惟其然也,故日日议瓜分,逐逐思择肉,以我人民为其圉下之隶,以我财产为其囊中之物,以我土地为其版内之图,扬言之于议院,腾说之于报馆,视为固然,无所忌讳。询其何故,则曰支那人不知爱国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
哀时客又曰:呜呼,异哉!我同胞之民也,谓其知爱国耶,何以一败再败,一割再割,要害尽失,利权尽丧,全国命脉,朝不保夕,而我民犹且以酣以嬉,以歌以舞,以鼾以醉,晏然以为于己无与?谓其不知爱国耶,顾吾尝游海外,海外之民以千万计,类皆激昂奋发,忠肝热血,谈国耻,则动色哀叹,闻变法,则额手踊跃,睹政变,则扼腕流涕,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呜呼,等是国也,等是民也,而其情实之相反若此!
哀时客请正告全地球之人曰: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苟无外侮,则虽兄弟之爱,亦几几忘之矣。故对于他家,然后知爱吾家;对于他族,然后知爱吾族。游于他省者,遇其同省之人,乡谊殷殷,油然相爱之心生焉;若在本省,则举目皆同乡,泛泛视为行路人矣。惟国亦然,必对于他国,然后知爱吾国。欧人爱国之心,所以独盛者,彼其自希腊以来,即已诸国并立,此后虽小有变迁,而诸国之体无大殊,互相杂居,互相往来,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我中国则不然。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故吾曰: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谓其爱国之性质,隐而未发则可,谓其无爱国之性质则不可。
于何证之?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儿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哀时客粤人也,请言粤事。吾粤为东西交通第一孔道,澳门一区,自明时已开互市,香港隶英版后,白人足迹益繁,粤人习于此间,多能言外国之故,留心国事,颇有欧风;其贸迁于海外者,则爱国心尤盛。非海外之人优于内地之人也,蛰居内地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远游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故吾以为苟自知其为国,则未有不爱国者也。呜呼!我内地同胞之民,死徙不出乡井,目未睹凌虐之状,耳未闻失权之事,故习焉安焉,以为国之强弱,于己之荣辱无关,因视国事为不切身之务云尔。试游外国,观甲国民在乙国者,所享之权利何如,乙国民在丙国者,所得之保护何如,而我民在于彼国,其权利与保护何如,比较以观,当未有不痛心疾首,愤发蹈厉,而思一雪之者。彼英国之政体,最称大公者也。而其在香港,待我华民,束缚驰骤之端,不一而足,视其本国与他国旅居之民,若天渊矣。日本唇齿之邦,以扶植中国为心者也,然其内地杂居之例,华人不许与诸国均沾利益。其甚者如金山 (3 )、檀香山 (4 )之待华工,苛设厉禁,严为限制,驱逐迫逼,无如之何!又如古巴及南洋荷兰属地诸岛贩卖猪仔之风,至今未绝;适其地者,所受凌虐,甚于黑奴,殆若牛马,惨酷之形,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夫同是圆颅方趾冠带之族,而何以受侮若是?则岂非由国之不强之所致耶?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吾宁能怨人哉!但求诸己而已。国苟能强,则已失之权力固可复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复沾,彼日本是也。日本自昔无治外之权,自变法自强后,改正条约,而国权遂完全无缺也。故我民苟躬睹此状,而熟察其所由,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
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然国非能自强也,必民智开,然后能强焉,必民力萃,然后能强焉。故由爱国之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此联合之所以为要也;空言爱国,无救于国,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为要也。今海外人最知爱国者也,请先言海外。
各埠之有会馆也,联合之意也。横滨之有大同学校也,各埠之纷纷拟兴学校也,教育之意也。皆我海外同胞之民,发于爱国之真诚所有事也。新加坡一埠,当政变以前,议设学堂,集资已及二十余万金;檀香山一埠,通习西文谙图算之男女学生,已及六七百人;诸君子忧时之远识,治事之苦心,真不可及也。然吾犹有所欲言者,则于联合之中,更为大联合,于教育之中,更为大教育也。所谓大联合者何?商会是已。我中国人之善于经商,虽西人亦所深服,然利权所以远逊于人者,固由国家无保护之政策?亦由吾商民之气散而不聚,不能互相扶植、互相补救;故一及大局之商务。每不能与西人争也。即如海外各埠,吾民成聚之区,以百余计,而曾无一总汇互通声气者。甚且如旧金山一埠,三邑与四邑之人,互相讼阋,同室操戈,贻笑他人,于此而望其大振商业,收回利权,岂可得哉?殊不知全局之利害,与一人之利害,其相关之处,有至切至近者。互相提携,则互享其利;互相猜轧,则互受其害,其理甚繁,其事甚多,别篇详之。故远识大略者,知经营全局之事,正所以经营,一身一家之事。昔英人之拓印度,开广东,全藉商会之力,及其业已就,而全国之中商、小商,无一不沾其利焉,此其明证也。故今日为海外商民计,莫如设一大商会,合各埠之人,通为一气,共扶商务,共固国体;每一埠有分会,合诸埠有总会,公订其当办之事,互谋其相保之法,内之可以张大国权,外之可以扩充商利,此最大之业也。至其条理设施之法,当于别篇详之,今不及也。
所谓大教育者何?政学是已。香港有英人所设之大学堂,吾海外之民之治西学者,多从此出焉,外此各埠续设之学堂,亦多仿其制。虽然,英人所设之学堂,其意虽养成人才为其商务之用耳,非欲用养成人才为我国家之用也,故其所教偏优于语言文字,而于政学之大端盖略焉。故自香港学堂山者,虽非无奇特之才,然亦不过其人之天资学力别有所成,而非学堂之能成之也。且我同胞之民所学者何?学以救我中国也。凡每一国,必有其国体之沿革,存于历史,必有其国俗之习惯,存于人群,讲经国之务者,不可不熟察也。今香港之学堂,绝不教中国之学,甚至堂中生徒并汉文而不能通焉,此必不可以成就经国之才也。且西国学校,所教致用之学,如群学、国家学、行政学、资生学、财政学、哲学各事,凡有志于政治者,皆不可不从事焉,而香港学堂皆无之,是故不能得非常之才也。今如檀香山之生徒,其通西语解图算者,既以数百计,其人皆少年蹈厉,热血爱国,使更深之以汉学,进之以政治,则他日中国旋乾转坤之业,未始不恃此辈也。为今之计,宜各埠皆设学校,广编教科书,中西并习,政学兼进,则数年之后,中国维新之运既至,我海外之忠民,皆得以效力于国家,而国家亦无乏才之患矣!
哀时客曰:呜呼!国之存亡,种种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淳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莆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我民不以国为己之国,人人不自有其国,斯国亡矣!国亡而人权亡,而人道之苦,将不可问矣!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呜呼!我四万万之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爱国心乌乎起?孟子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惟国亦然,吾国则爱之,他人之国则不爱矣。是故人苟以国为他人之国,则爱之之心必灭;虽欲强饰而不能也;人苟以国为吾同;则爱?之心必牛:虽欲强制而亦不能也。愈隔膜则其爱愈减,愈亲切则其爱愈增,此实天下之公例也。譬之一家然,凡子弟未有不爱其家者,盖以为家者吾之家,家事者吾之事也;凡奴隶则罕有真爱其家者,盖以为家者主人之家,家事者主人之事也。故欲观其国民之有爱国心与否,必当于其民之自居子弟欤自居奴隶欤验之。
凡国之起,未有不起于家族者,故西人政治家之言曰:国字者,家族二字之大书也。其意谓国即大家族,家族即小国也。君者,家长、族长也;民者,其家族之子弟也。然则当人群之初立,则民未有不以子弟自居者。民之自居奴隶乌乎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已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后世之治国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议之,专断而行之,民不得与闻也;有议论朝政者,则指为莠民,有忧国者,则目为越职,否则笑其迂也,此无怪其然也。譬之奴隶而干预主人之家事,则主人必怒之,而旁观人必笑之也。然则虽欲爱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爱、不能爱,则惟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主人之荣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主人之中落也,则褰裳也去,此奴隶之恒性也。故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则不然,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
西史所称爱国之业,如昔者希腊以数千之农民,追百万游牧之蛮兵;法国距今四百年前,有一牧羊之田妇,独力一言以攘强敌,使法国脱外国之羁轭。皆彼中所啧啧传为美谈者也。虽然,吾中国昔者非无其例也。以《左氏春秋》所载,如齐鲁长勺之战,鲁曹刿忧国事,有所擘画,旁人笑之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而曹刿不顾非笑,卒谒其君而成其功。又如秦将袭郑,郑弦高以牛十二犏秦师,而报其谋于本国,卒使有备而退强敌。夫曹刿一布衣耳,弦高一商人耳,非有国家之责,受君相之命也,使其袖手,谁则尤之?然皆发于爱国之诚,以匹夫而关系大局。呜呼!此非古人独优于今人也,其所以致此者,盖有由也。古者视其国民如一家之人焉,征之左氏,如晋韩起求玉环于郑,郑子产告以本国与商人所立之约,曰:“尔无我诈,我无强买”。又如晋文公围南阳,南阳之民曰:“夫谁非王之昏姻?其俘之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盖当三代以前,君与民之相上,实如家人妇子焉,依于国家,而各有其所得之权利,故亦对于国家而各有其应尽之义务,人人知此理,人人同此情,此爱国之心,所以团结而莫解也。
圣哉我皇上也!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有曰:“海内之民,皆上苍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皆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于戏!此言也,我四万万同胞之臣民,所当感激起舞,发奋流涕,日夜熟念,而不可一日忘者也。夫天子而有职也,有职而自忧其未尽,自责其未尽也,此何等语耶?此盖自唐虞三代以来,数千年所号称贤君令辟,未有能知此义、能为此言者也。皇上之意盖曰:我有子弟,我饮食之,我教诲之;吾子弟之学业,吾之责也,吾子弟之生计,吾之谋也。其心发于至爱,其语根于至诚,此非犹夫寻常之诏令而已,其贤父慈母噢咻其子弟而卵翼其家人之言也。故吾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民之自居奴隶,固无足怪焉;若真能以子弟视其民者,则惟我皇上一人而已。我四万万同胞之臣民,生此国,遇此时,获此圣君,依此慈母,若犹是自居于奴隶,而不自居于子弟,视国事如胡越,视君父之难如路人,则真所谓辜负高厚、全无人心者也。此吾所以仰天泣血,中夜椎心,沈病而不能自制也。
哀时客曰:吾尝游海外,海外之国,其民自束发入学校,则诵爱国之诗歌,相语以爱国之故事,及稍长,则讲爱国之真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则相告以爱国之实业。衣襟所佩者,号为爱国之章;游燕所集者,称为爱国之社。所饮之酒,以爱国为命名;所玩之物,以爱国为纪念。兵勇朝夕,必遥礼其国王;寻常饔殆,必祈祷其国运。乃至如法国歌伎,不纳普人之狎游,谓其世为国之仇也;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赠朵,渭其将为国之患也,其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呜呼,何其盛欤!哀时客又曰:吾少而居乡里,长而游京师,及各省大都会,颇尽识其朝野间之人物。问其子弟,有知国家为何物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入学,如何而可以中举也。问其商民,有知国家之危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谋利,如何而可以骄人也。问其士夫,有以国家为念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如何而可以得官,可以得差,可以得馆地也。问其官吏,有以国事为事者乎?无有也。其相语则曰:某缺肥,某缺瘠,如何而可以逢迎长官,如何而可以盘踞要津也。问其大臣,有知国耻、忧国难、思为国除弊而兴利者乎?无有也。但人则坐堂皇,出则鸣八驺,颐指气使,穷侈极欲也。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妻勖其夫,友劝其朋,官语其属,师训其徒,终日所营营而逐逐者,不过曰:身也,家也,利与名也。于广座之中,若有谈国事者,则指而目之曰:是狂人也,是痴人也;其人习而久之,则亦且哑然自笑,爽然自失,自觉其可耻,箝口结舌而已。不耻言利,不耻奔竞,不耻媒渎,不耻愚陋,而惟言国事之为耻,习以成风,恬不为怪,遂使四万万人之国;与无一人等。惟我圣君慈母,咨嗟劬劳,忧愤独立于深宫之中。呜呼!为人子弟者,其何心哉?其何心哉?
今试执一人而语之曰:“汝之性,奴隶性也;汝之行,奴隶行也。”未有不色然而怒者。然以今日吾国民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习俗,如此之言论,如此之举动,不谓之为奴隶性、奴隶行不得也。夫使吾君以奴隶视我,而我以奴隶自居,犹可言也;今吾君以子弟视我,而我仍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今世之言治国者,莫不以练兵理财为独一无二之政策,吾固不以练兵理财为足以尽国家之大事也,然吾不敢谓练兵理财为非国家之大事也。即以此二者论之,有民权则兵可以练,否则练而无所用也;有民权则财可以理,否则理而无所得也。何以言之?国之有兵,所以保护民之性命财产也,故言国家学者,谓凡国民皆有当兵之义务。盖人人欲自保其性命财产,则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卫之,名为卫国,实则自卫也,故谓之人自为战。人自为战,天下之大勇,莫过于是。不观乡民之械斗者乎?岂尝有人焉为之督责之、劝告之者,而摩顶放踵,一往不顾,比比皆是,岂非人人自卫其身家之所致欤?西国兵家言曰:“凡选兵不可招募他国人。”盖他国应募而为兵者,其战事于己之财产性命,无有关系,则其爱国之心不发,而战必不力。夫中国之兵,虽本国人自为之,而实与他国应募者,无以异也。西人以国为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中国以国为一人之私产,辄曰王者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云者,犹曰奴虏云耳。故彼其民为公益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也。驱奴虏以斗贵人,则安所往而不败也?不观夫江南自强军乎?每岁糜巨万之饷以训练之,然逃亡者项背相望,往往练之数月,甫成步武,而褰裳以去,故每阅三年,则旧兵散者殆尽,全军皆新队矣。未战时犹且如是,况于临阵哉?其余新练诸军,情形莫不如是。能资之于千日,而不能得其用于一时。彼中东之役,其前车矣!今试问新练诸军,一旦有事,能有以异于中东之役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奴为主斗,未有能致其命者。前此有然,后此亦莫不然也。此吾所谓虽练而无所用也。
国之有财政,所以为一国之人办公事也。办事不可无费用,则仍醵资于民以充其费。苟醵之于民者悉用之于民,所醵虽多,未有以为病者也。不观乎乡民乎?岁时伏腊,迎神祭赛,户户而醵之,人人而摊派之,莫或以为厉己也。何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故西人理财之案,必决于下议院。有将办之事,议其当办与否,既人人以为当办矣,则必其事之有益于公众也,于是合公众以谋其费之所出。以一国之财,办一国之事,未有不能济者也。而又于先事有豫算焉,于既事有决算焉。豫算者,先大略拟此事费用,逐条列出而筹之也;决算者,征信录之意也。一切与民共之,民既知此事之不可以不办也,又知其所出之费确为办此事之用也,夫谁不乐输之?又不惟办事而已,即国家有不幸,如战败赔款之事,若法国之于普国,赔至五千兆佛郎之多,亦一呼而集之。何也?当其开战之始,既经国民之公议,以为不可不战,人人为其公事而战;战之胜败,全国之民固自愿受其利害矣。其赔款也。亦由国民知其不可以已。公议而许之。虽多其奚怨也?若夫当战与否,未尝商之于民焉;战之方略如何,未尝商之于民焉;休战与否,未尝商之于民焉;赔款之可许与否,未尝商之于民焉;一二庸臣,冒昧而行之,秘密而议之,私相授受而许之,一旦举其所费而尽委负担于吾民,其谁任之?夫我朝之于租税,可谓极薄矣,而民顾不以为德者,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而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中国则司农仰屋于庙堂,哀鸿号嗷于中泽,上下交病,而百事不举,此其故可深长思也。今之言理财者,非事搜括,则事节省,浸假而官吏之俸,扣之又扣,兵士之饷,减之又减,而民之受病也如故;民债之借,酷于催科,昭信之票,等于胜箧,而国帑之溃乏也如故。岂中国之果无财哉?岂中国之民之吝财大异于西国哉?无亦未尝以民财治民事之所致也。此吾所谓虽理而无所得者也。
吾闻之西人之言曰:“使中国而能自强,养二百万常备兵,号令宇内,虽合欧洲诸国之力,未足以当其锋也。”又曰:“以中国之人之地,所产出之财力,可以供全欧洲列国每岁国费两倍有余。”嗟乎!凭藉如此之国势,而积弱至此,患贫至此,其醉生梦死者,莫或知之,莫或忧之,其稍有智识者,虽曰知之,虽曰忧之,而不知所以救之。补苴罅漏,摭拾皮毛,日夜孳孳,而曾无丝毫之补救,徒艳羡西人之富强,以为终不可几而已,而岂知彼所谓英、法、德、美诸邦,其进于今日之治者,不过百年数十年间事耳。而其所以能进者,非有他善巧,不过以一国之人,办一国之事,不以国为君相之私产,而以为国民之公器,如斯而已。故不能以一二人独居其功,亦非由一二人独任其劳,而日就月将,缉熙光明,不数十年,而彼之国民,遂缦缦然将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呜呼!吾国独非国欤?吾民独非民欤?而何以如是?问者曰:“民权之善美,既闻命矣。然朝廷压制,不许民伸其权,独奈之何?子之言但向政府之强有力者陈之斯可耳,喋喋于我辈之前胡为也?”答之曰:不然。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损害天赋之人道一也。夫欧洲各国今日之民权,岂生而已然哉?亦岂皆其君相晏然辟吗而授之哉?其始由一二大儒,著书立说而倡之,集会结社而讲之,浸假而其真理灌输于国民之脑中,其利害明揭于国民之目中,人人识其可贵,知其不可以已,则赴汤蹈火以求之,断颈绝脰以易之。西儒之言曰:“文明者,购之以血者也。”又曰:“国政者,国民之智识力量的回光也。”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有语之曰:“尔固有尔所有有之权。”则且瞿然若惊,蹴然不安。掩耳而却走,是直吾向者所谓有奴隶性、有奴隶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此吾所以后顾茫茫,而不知税驾于何所也。
问者曰:“子不以尊皇为宗旨乎?今以民权号召天下,将置皇上于何地矣?”答之曰:子言何其狂悖之甚!子未尝一读西国之书,一审西国之事,并名义而不知之,盍速缄尔口矣!夫民权与民主二者,其训诂绝异。英国者,民权发达最早,而民政体段最完备者也,欧美诸国皆师而效之,而其今女皇,安富尊荣,为天下第一有福人,其登极五十年也,英人祝贺之盛,六洲五洋,炮声相闻,旗影相望。日本东方民权之先进国也,国会开设以来,巩自治之基,历政党之风,进步改良,蹑迹欧美,而国民于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宪法中定为神圣不可犯之条,传于无穷。然则兴民权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法王路易,务防其民,自尊无限,卒激成革命战栗时代,去衮冕之位,伏尸市曹,法民莫怜。俄皇亚历山·尼古剌,坚持专制政体,不许开设议院,卒至父子相继,陷于匕首,或忧忡以至死亡。然则压制民权,又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彼英国当一千八百十六七年之际,民间议论喧俯,举动踔厉,革命大祸,悬于眉睫;日本当明治七八年乃至十四五年之间,共和政体之论,遍满于国中,气焰熏天,殆将爆裂。向使彼两国者,非深观大势,开放民权,持之稍蹙,吾恐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惨剧,将再演于海东西之两岛国矣。今惟以民权之故,而国基之巩固,君位之尊荣,视前此加数倍焉。然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而彼愚而自用之辈,混民权与民主为一途,因视之为蜂虿、为毒蛇,以荧惑君相之听,以窒天赋人权之利益,而斫丧国家之元气,使不可复救,吾不能不切齿痛恨于胡广、冯道之流,不知西法而自命维新者也。
圣哉我皇上也!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谕云:“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主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生人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於戏!臣每一读此谕,未尝不舞蹈感泣呜咽而不能自胜也。西国之暴君,忌民之自有其权而务压之;我国之圣主,忧民之不自有其权而务导之。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黪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翟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欧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
注 释
(1)本文发表于1899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33册。
(2)本文分别发表于1899年2月20日、3月2日、7月28日,《清议报》第6、7、22册。
(3) 金山。即旧金山,今美国圣弗兰西斯科市。
(4)檀香山,今译火奴鲁鲁,今属美国夏威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