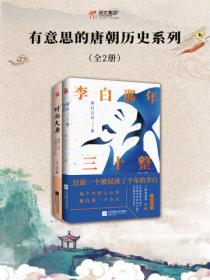第19章 至死不渝
李白上书的对象裴长史,并不是游戏中可有可无的NPC,他是史上最优秀的职业官员之一。
《旧唐书》有裴宽传:“宽通略,以文词进,骑射、弹棋、投壶特妙。”刺史韦铣为按察使时,引裴宽为判官,欣赏其“清干善于剖断”之才,以女妻之。时任中书令张说欣赏裴宽“明识”,举荐为刑部员外郎。有“万骑将军”之号的马崇白昼杀人,裴宽秉公执法,谁说都不好使。
“宽性友爱,弟兄多宦达,子侄亦有名称”,家族在东京洛阳聚居,八座院落相对,每到饭点,击鼓而食,老百姓都觉得,他们家的日子,真是无上恩宠。玄宗回京,改裴宽为蒲州刺史,州郡久旱,可裴公一入蒲州境,上天立降甘霖;“迁河南尹,不附权贵,务于恤隐,政乃大理。”
“宽以清简为政,故所莅人皆爱之,当时望为宰辅。”之所以来到安陆,是遭人陷害及亲人所累,裴宽被贬为“安陆别驾员外置”。
以才华、人品、官声、业务能力论,裴宽的简历堪称完美。令人感慨的是,在大唐的盛世里,竟然连裴宽这样的人都混不下去。既如此,那“盛世”两个字,又究竟“盛”在哪里呢?
一辈子官场生涯,裴宽什么阵仗没有见过?当朝权相李林甫把裴宽视作眼中钉,即便在由李林甫组织的诬陷之下,裴已被贬到安陆,李林甫仍然放心不下,把他视作必须除掉的对手——李林甫仍派出杀手对裴宽实施刺杀,“林甫使罗希奭南杀李适之,纡路至安陆过,拟怖死之”,准备通过恫吓来逼死裴宽。
当时的裴宽显然并不想死,幸好罗希奭也是性情中人,居然在裴宽的叩头哀求之下,“不宿而过”。
宦海浮沉数十载,据理力争、怒发冲冠有时;委曲求全、百般斡旋有时;百口莫辩、心如死灰有时;明枪暗箭、生死存亡有时。一生不畏权势又如何?晚年的裴宽,在死亡面前,不得不像一条可怜的丧家犬一样摇尾乞怜,求杀手给自己留下这衰老的生命。
到处都是烦恼,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是恐惧,到处都是麻烦,谁又能真正超脱?这样的时刻,一个叫李白的年轻人给你写信,吹捧你“倚剑慷慨、气干虹霓”的英雄气概,夸赞你仿佛凝脂的细腻皮肤,请问你会有什么感想?
这样的裴宽,不可能会喜欢李白来信里洋洋洒洒的漂亮字眼,尤其是最后一段看上去幼稚可笑的“威胁”。在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老玩家面前,李白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天生我材必有用”并没有错,只是,轻薄极了。
李白像一个向往江湖的农夫,但他不知道江湖是什么,江湖的血雨腥风,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或者说,他当时还没有考虑官场错综复杂关系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他不是不想考虑,他没有考虑那些问题的能力。
裴宽品行端正,政绩突出,深受朝廷倚重和地方士民爱戴,在做官这件事上,他干得异常出色。事实上,就连遭到李林甫的刺杀,也是他“咎由自取”:太优秀,太正直,于是遭到嫉妒,宵小们对他感到畏惧,必欲除之而后快。杀手之所以临阵放弃,也是裴大人一生德行护佑的结果:这是个好人,杀不得。
唐玄宗说裴宽:“德比岱云布,心似晋水清。”
从韦铣的“以女妻之”,到张说的“举而行之”,再到玄宗亲自赏赐紫金鱼袋,再到官履所至,裴宽是“人皆爱之”。全天下的人,除了那些极少数公认的坏人之外,都爱裴宽。相较之下,李白的待遇差了点意思,“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如果你是皇帝,你会录用李白为官吗?如果你是当时的裴宽,你会被李白的书信打动吗?如果你是大唐的子民,你会想要一位李白这样的行政长官吗?
李白是个文学天才和罕见的有趣的人,可是讲到从政,李白又有何德何能?
即便做到翰林之位,也不过短短的一年多便弃官而去。政绩是没有的,我们听到的传说,最多的是他如何的戏弄贵妃、太监和权臣,如何的视朝廷如儿戏,如何的陪皇帝写情诗。
从政绩的角度看,李白甚至还比不上前文那个更加狂傲甚至透出猥琐的王泠然。
王泠然虽然是从九品下的郎官,但他一生效力于朝廷,虽然终生没做过大官,但他死在了自己的任上。从一开始理直气壮地找领导要官,到后来成为芝麻小官,王泠然怨言不断,但他真的喜欢当官,哪怕不爽,他也当了一辈子。用庸俗的话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王泠然对得起自己的初心,以大唐给他的待遇看,他一辈子的努力大概也对得起大唐吧。
与王泠然比,李白就是个玩票的,他很不尊重官吏这个职业。李白有很多做官的朋友,大官小官都有,他爱的不是他们做官的身份,他只是恰好交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职业恰好是做官而已;李白对“官”并没有什么意见,但他终究把“做官”这件事看得儿戏了。
无论从个人的荣华富贵铁饭碗的角度看,还是从造福一方为民请命的角度看,做官这件事都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严肃,意味着专业、忍耐、积累、复杂和不那么自由。
李白想要和裴宽交换人生吗?大概不会。李白羡慕的只是裴宽的高位,那位置的后面是什么,李白并不想了解——因为太麻烦了,太沉重了,太琐碎了,一点都不爽快。
晚年的裴宽想要和李白交换人生吗?大概会吧。裴宽几乎丢掉性命之后,一度想要出家为僧,在荒郊野庙里了此残生,这是真诚的愿望,从心底冒出来的渴求,是绚烂至极、心如死灰的救赎。史书上对他的动机讲得很清楚,“惧死”:“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然崇信释典。常与僧徒往来,焚香礼忏,老而弥笃。”
造化弄人,最终裴宽还是没有当上和尚,只能烧烧香、谈谈佛,“徒有羡鱼情”。孟浩然年轻时所羡慕的,是裴宽这样的人,不料有一天裴宽也会羡慕孟浩然的“白首卧松云”。
孟浩然之所以“红颜弃轩冕”,不是真的缺乏机遇,只是在机遇来临之前就已经做了决定,他自己选择了山水与田园。多年之后,好友王昌龄路过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孟浩然欣喜若狂,“浪情戏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背上的毒疮快痊愈的时候,一顿纵情饮宴直接导致病情恶化,在五十二岁的年纪死于南园。
裴宽之所以拼尽全力,一生与权贵争斗,努力做一个无愧于心的官,光耀自己的家族和门庭,也是他自己毅然的选择。与孟浩然的区别是,到晚年的时候,裴宽后悔了。
裴宽后悔的时候,皇帝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皇帝的考虑是:既然你这么会当官,为什么要做和尚呢?“累迁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银青光禄大夫,入拜礼部尚书。十四载卒,年七十五。诏赠太子少傅,赙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入台省,典郡者五人。”——这样的结局,这样的人生,有惊无险,不算太差。
与裴宽的晚年顿悟相比,李白的仿仙学道,更像年轻人骑车去拉萨涤**心灵——不是说那不好,不是说那不应该,不是说那不痛快,只是太浅。不是说浅不好,不是说浅没价值,但浅终究是浅,没什么深度,没那么真实,不怎么能打动人。
伟大的事业,荣耀的地位,不羁的自由,长生的快乐,世人的称颂,帝王的器重,痛饮的放浪,修行的寂寥,朋友的欢聚,心底的骄傲,李白想同时拥有。艰苦的求索,耐心的练习,琐碎的积累,谨慎的经营,漫长的忍耐,荒诞的仪式,精巧的伪装,不得已的妥协,李白一个都不想要。
好巧啊,跟你我一样。
小时候,很容易喜欢李白,就像少女们很容易被骑破摩托的小混混吸引。
长大了,会觉得裴宽那样的人生,才是勇敢者的道路,因为这一生,他为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忍耐过。
在李白的那个年代,干谒权贵并不算一件丢人的事。一个年轻人干谒官员名士,就像今天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孩子在各大网站疯狂海投简历一样,这种敲门自荐争取进身之阶的个人营销,让很多年轻人获得了社会阶层迁移的机会,从这个方面说,干谒得以成为备受年轻人热衷的活动,恰是隋唐之世最珍贵的特质之一。
被干谒的裴宽们没有问题,干谒本身也没有问题,李白有点小问题:超出常人的自负,是李白一生最大的拦路虎,这种自负年轻时最为显著,年老时仍未消散,至死不曾改变。
李白年轻时的干谒活动很多,“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在干谒这件事上,他曾经拦住大官的路,勇敢上书,搞出过类似拦轿告状的血气方刚之举,孤注一掷的勇气为他赢得了上文苏公的赞誉:“此子天才英丽。”
为了进身,李白充分利用了自己一天中难得的清醒时间,花费心力,认认真真地写过许多干谒权贵名士的诗文,但这些诗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开头把自己夸耀得过高,结尾又常带威胁。这种行文风格,读信的高位者们不喜欢,一点都不奇怪。
王泠然的干谒文说自己是难得的进士,“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光华藉甚”,言语虽不甚谦恭,但人家起码并没有一味地夸大其词——他确实是进士,进士确实很难考,这些都是基于客观事实的自我炫耀,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自抬身价行为。
再看李白的干谒文,动辄将自己类比为管仲、乐毅、鲁仲连、刘桢等古之圣贤,动辄将自己比喻成大鹏、天马,这种毫无根据的吹嘘与自负,真的很难打动具有务实精神的官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句子出现在给李邕的干谒诗里,并不是很理智的行为。
上李邕
李白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别人看到我天天说大话,对我报以冷笑。那我为什么还能谈笑自若、心安理得地说大话呢?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大丈夫,都懂得莫欺少年穷的道理。那些笑话我的人,他们有病,不是坏就是蠢,根本不值得搭理。李白那时候大概二十岁上下,正处于敏感骄傲的巅峰,在写这首诗之前,他应该已经和时任渝州(重庆)刺史的李邕接触过,李邕对他的印象和态度都很一般。于是,和王泠然给高老师的信一样,李白的这首赠诗里也有对李邕的怨气,以及情不自禁的威胁。
一个二十岁的男孩,有狂傲的资本,李邕不喜欢李白,但他不能不羡慕李白。无拘无束的青春,做事不需要理由的年少,哪怕犯了错,那错犯得也特别过瘾。大把的机会,大把的时光,大把的未来,等着你去挥霍。此时不嚣张何时嚣张?此时不狂何时狂?
李白令人震惊和不得不服的地方在于,到了六十多岁,临死的那刻,回望这一生,他仍然和二十岁时一样,仍旧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大鹏,李白临终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临路歌
李白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所谓的心如铁石、志比金坚、耿耿于怀、至死不渝,不过如此。你知道李白的一生都经历过什么吗?丧妻、飘**、安史之乱、嘲讽冷眼、无数挫折、无数生死考验,杨贵妃的容颜、永王的楼船、放逐的冷风、大唐的反面,他都见识过。六十岁之后的李白早已不是年少时坐井观天的李白,他见过了世上的一切,他积攒了一生的故事,他已经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了。
然而,他还是不曾看低自己,他还是不愿意对命运投降。人之将死,李太白还需要通过吹牛来换一些关注度吗?人之将死,李太白还需要用狂言炒作人设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只能相信,这是来自李白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我李白就是牛,不服来战。
死前三年,即将六十整的李白刚刚遇到大赦,侥幸获得自由,他的雄心又立刻燃起。今天,六十岁是退休养老的年龄,可这样年龄的李白仍然在做那件他从年轻时一直在干的事情——干谒。甚至,他的手法、文风及老毛病都没有任何改变,仍然习惯于说大话,仍然习惯于把自己比喻成特别高大的事物:
赠崔咨议
李白
绿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
长嘶向清风,倏忽凌九区。
何言西北至,却走东南隅。
世道有翻覆,前期难豫图。
希君一翦拂,犹可骋中衢。
五十三岁的曹操形容自己是“老骥伏枥”,六十岁的李白觉得“伏枥”太过低端,那是凡马的□样子,我是天马,这一生骄傲地飞行,注定属于清风和长空。诗歌的末尾,六十岁的李白仍然希望得到推荐和重用,“希君一翦拂,犹可骋中衢”。
六十一岁,李白仍然没有放弃,他写了一首《赠刘都使》,把自己比喻成三国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之所以选择刘桢而不是孔融或徐干,大概是考虑到他和“刘都使”都姓刘,也许会让刘都使感到更加亲切。
赠刘都使(节选)
李白
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
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
和敲打李邕一样,和威胁裴宽一样,六十一岁的李白仍然改不了他文末一定要撂狠话的毛病:如果您不搭理我,我可要怒而隐居了,您可就没机会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文学知识,不需要高深的古文功底,每一个人,都能轻易读懂李白文字中那永远无法拂去的三个字:不甘心。眼看人生日暮途穷,被逼到绝路的李白甚至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北上参军,结果可想而知。
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李白那年六十二岁,卒。
如果李白真的想要进入幕府或者得到礼遇,进而施展抱负,可行的方法并不是没有。实际上,李白的命运很轻易就可以改变:他只需要在类似《上安州裴长史书》这样的干谒诗文里,去掉那些锋芒毕露的譬喻,另外,删掉最后一段。他不,他偏不,到死也不服。
正确的干谒应该是什么姿势?同时代的很多人给出了优秀的范本。
孟浩然最著名的作品,其实是一首干谒诗。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湖水浩**,天地混沌,在云海翻腾、波涛汹涌的世界上,我是一个找不到船和浆的迷失者。就这样隐居不出,我也不是没有想过,但在这样的盛世里,做一个闲人,实在是令人羞耻。我坐在岸边看那些钓鱼的人,心痒难耐,但是除了枯坐艳羡,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壮阔的诗句,稳健的笔力,不卑不亢的姿态,精准妥帖的诉求。一首合格的干谒诗,未必要怎样拍对方的马屁,未必要拼命践踏自己的尊严,只需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孟浩然做到了。孟浩然科举坎坷,但他的京城人脉却丰厚异常,每一个人都爱他。做官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只是来得太迟,对已经顿悟的修行者而言已经毫无价值。如果孟浩然真的想当官,以这样的干谒诗水准,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缺少机会。
只不过,孟浩然终于释然了,那些衣冠如云的京华往事真正地过去了,像鸟儿飞过天空,空气在它尾后重新合拢。“释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孟浩然再次做到了。这直接导致他笔下的一些诗句,李白、杜甫这样的热血儿郎到死都写不出来。比如,如此安静又如此寂寞的黄昏:“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又比如,如此恬静,如婴儿呼吸般的夜色:“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诗人朱庆馀最出名的诗歌,也是一首干谒诗:
近试上张水部
朱庆馀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临近考试,找领导套磁,讲究的就是一欲语还休、云山雾罩、婉转含蓄。以自己为新妇,领导为郎君,这种略带戏谑的“示弱”把敏感的套磁变成了撒娇卖萌的玩笑,拿到这首诗的张水部老师一定忍俊不禁吧。事实上,据说张籍非常欣赏朱庆馀的呈诗,并欣然回笔:
酬朱庆馀
张籍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你既然把自己比作新妇,我也只能按照夸女孩子的方法夸你了,你问我的妆容问题,我的回答是,世间一切的明媚都及不上你湖面上的新妆,人间一切的珍宝,都不及你的歌声。庸脂俗粉的映衬下,你是清流一般的越女;凡夫俗子的包围中,你是千金不易的人间精品。
这里,请允许我顺便吐槽一下朱庆馀的名字。这名字在唐朝诗人里不得不说有点土,充满了“庆余年”的欢快喜庆意思,简直像刚从春联里扒拉出来的,所谓“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所谓“人逢盛世情无限,猪拱华门岁有余”,看到他的名字,我第一反应居然是想吃饺子……
扯远了。总之,孟浩然、张九龄、朱庆馀、张籍们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合适的礼仪之下,在得体的格式之下,在深厚的学养加持下,在微妙的氛围把握下,平民与高官,布衣与卿相完全可以平等对话,互相之间也可以生出友情般的欣赏和倾慕。
李白不相信有这样的干谒,尽管李白向来希望自己能够“平交王侯”,与权贵们平等相处,但他始终无法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建立起不卑不亢的平等关系,要么他屈居人下,要么他凌驾人上,在与权贵和高官们的交往中,“平视”这个角度,他似乎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卑与自负在心底纠缠,出山与入山在心头交战,李白迟迟下不了决定。
所有的纠结都是胸中漆黑处解不开的乱麻,发之于外,便是自负、不羁、浪**和轻狂。
有的人一生不曾狂过,有的人狂着狂着便不狂了,李白愣是狂了一辈子。二十岁时,李白还未曾长大,便早已把狂浪不羁当成人生的审美对象;六十岁时,李白不再年轻,但他也不曾老去,倔强的诗句里,通篇写着“老子不服”。
大家都觉得李白不是个靠谱的人,他眼高手低,满口大话,应该没什么出息,但这样的评价有可能把李白说得过于浅薄。可能会有一些奇怪,但有时我真的觉得李白是夸父、诸葛亮、堂·吉诃德那样的人,这一辈子过得特别执着、特别倔强、特别玩命,飞蛾扑火,流星过天,硬生生扛下命运,一辈子都不曾真正服软。
李白活着的时候,他民间的狂热粉丝,除了魏颢,还有个叫任华的人。这个任华对李白的仰慕和喜爱远远超出了魏颢之于李白,甚至远远超出了杜甫之于李白。“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听说李白在长安,任华就去了长安,等他赶到的时候,李白又云游到了别的地方,这让任华感慨不已:“邂逅不得见君面。每常把酒,向东望良久。”有时人和人之间,大概真的要讲缘分,任华和李白都活在同一个朝代,但终其一生,他似乎都不曾有缘见到自己的偶像李太白。
然而,这个不曾见过李白的人,根据他对李白作品的阅读、朋友间相互的打听,以及街头巷尾各种关于李白的传闻,在托人给李白的信中,对李白下了一个评语:“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
意思是,李白不曾真的低头过。李白诗文中也有过浮夸的谀辞,面对皇帝和贵妃,李白应制的无聊之作,今天仍被津津乐道。这一切,任华当然听说过,但他仍然看透了李白的心,他知道那些卑微时刻,乃是每个肉身都有的不得已,李白不是神仙,他不可能在真空中活着,他只知道,李白并没有真的低头。
这个没见过李白的任华,也许是李白在大唐第一号知己。
李白与大唐,大概是老人与海的关系。
万一哪天可以穿越,想必很多人都会想见见李白。记住,在所谓“大唐盛世”的角落,街边杂乱的酒肆里,那个满面油光的酒鬼不是普通的小混混,他叫李太白,虽然这辈子没做出什么太大的政治成就,但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你了解一点:他千真万确、的的确确、如假包换、名副其实地——
是个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