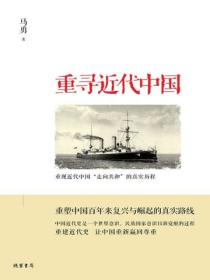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他们虽然生在当今世界,但其致思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并无根本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名称,但最通行的则为“儒生”“士”或“士大夫”。儒生的涵盖面较狭,而士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性格。士的最初涵义,或许如许慎《说文解字》所阐释的那样:“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段玉裁注引申发挥为:“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义》也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是指那些“知数知书”,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或阶级的人,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古希腊社会中的平民阶级,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也不必为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犯愁。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良好的传统,他们甘于清贫,“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生命境界。但在政治上,在人格上,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人格理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知识分子轻视专业知识,最看重的是“修齐治平”的学问。他们强调以经世致用的精神从事学术工作,总以为自己所事之学系天下之安危、社会之消长,故往往借学术攻击政治,攻击现实。这在一定范围内或许可行,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则势必导致统治者的镇压,形成新的黑暗时期,使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处在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中,而不见明显的大进步。
鉴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国知识分子欲为国家民族效力,必须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欲讨论政治,就全力讨论政治;欲探讨学术,就冷静地、独立地探讨学术,一不为政治所囿,二不与现实政治相瓜葛。果如此,其学术成果的真理成分才能增多,而社会成员各安其业,各司其职,中国焉有不进步之理?
任何社会,即使是极端黑暗的社会,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和有机构成。它的进步与发展有赖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较早接触新事物的人,固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面对这种责任,知识分子不应当以急功近利的经世致用思想从事学术,更不应处处时时以救世主的姿态与神情面对社会公众。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与发展,取决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各司其职,协调前进。因此,就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相互关联来说,最大的教训恐怕莫过于两条,一是淡化参与意识,下决心以自由主义的客观立场从学术和学理上,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的综合、平衡发展打下一个坚实而长远的基础;二是化解启蒙心态,既不能以救世主自居,又要深切体验中国社会全体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案建筑在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
参与意识与启蒙心态,虽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它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登峰造极的发展无疑是在20世纪,而其导源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欲正确说明参与意识和启蒙心态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便不能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入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逻辑发展和必然环节;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以在那个时代发生,主要的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强烈刺激而发动的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内在的思想依据,但其智慧资源和直接动力则是外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动因主要是外国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的一败再败。瞿秋白说:“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失利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的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想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然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学术上:二十余年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Mr.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331
很显然,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称中国启蒙运动,虽然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而激**出来的新思潮,但其智慧资源和直接动因则是外在的,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倡导与发动的一场运动。诚如孙中山当年所揭示的那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332
这“一二觉悟者”,显然是指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同事们。1915年,陈独秀有感于“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333,遂毅然独自创办《青年杂志》,欲以民主与科学唤醒国人,造就新一代自觉自立的国民,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说,欲救中国于危亡之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后——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绝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而“新鲜活泼”的新思想,在陈独秀看来,就是民主与科学,“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34
科学与民主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进步的两大直接动力。不过,科学与民主在西方社会的发生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在某种程度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而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此,陈独秀的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将民主与科学引进中国,足见其“先知先觉”的远见卓识。
作为文化资源的吸收与互补,民主与科学传入中国,自然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如果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的同志们持之以恒地坚持十年、二十年,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和理性精神便有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扎下根,中国社会经济逐步发展与演变也会为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提供现实的条件和土壤。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显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335从而,这种基于政治要求的启蒙心态不仅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夭折或变质,而且其政治氛围的加浓也势必导致本以理性精神为根本特征的启蒙运动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和不科学的成分。
推绎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的本意,他们最初的想法似乎并不愿意将启蒙运动与政治挂钩。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1916年开始,以学步慢行的危心,采取哀兵的策略,作动心忍性的功夫改造自我,建立全新的人格,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说:“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336胡适也说:“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因为漂泊乃是光阴的最大仇敌。无有方针,不知应作何事,又不知从何下手,不知如何做法,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成不可救。”因此,解救中国的“第一要务,在于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337。而这个主意和政策,就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338
胡适的这种主张虽然不足以代表《新青年》同仁的真实想法,但在《新青年》的早期,至少是1919年之前确实是这样做的。那时的《新青年》尽管避免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而以引进西方文化,促进国民性的改造为其根本任务。可惜,这种情况并未能持续很久,一方面,文化的革新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这不能不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学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而另一方面,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仁虽然暂时不愿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但在思想深处他们实在对政治有着无限的深情,一旦时机适宜,他们便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政治斗争。“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元培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民国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339
偏激和狂热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它给后世中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极其沉痛的。而这两种偏向本身似乎也不合乎他们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与民主。在现代社会,政治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公民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只是这种倾向和原则要运用的适度,要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通过民主的程序甲乙实现和完成。“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路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的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34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号称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使没受到1919年之后的政治热情的冲击,也注定它不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真正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五四启蒙者后来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初衷,这既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又是五四启蒙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这一结局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政治热情的文化传统外,似乎还有五四启蒙者的心态以及内在理路上的原因。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启蒙者的道路选择是不破不立,他们虽然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灵面对西方文化,呼唤民主与科学,但他们的骨子里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充满了没有丝毫缓和余地的仇恨。他们一方面批评学术上的独尊一家、好同恶异,导致专制、黑暗的恶果;另一方面则竭力排斥和自己学术见解、政治见解不同者,企图以新的文化独裁代替旧的文化独裁。陈独秀说:“学术与发展,固有分析与综合二种方向,互嬗递变,以赴进化之途。此二种方向,前者多属于科学方面,后者属于哲学方面,皆得谓之进步,不得以孰为进步孰为退步也。此综合的发展,乃综合众学以成一家之言;与学术思想之统一,决非一物。所谓学术思想之统一者,乃黜百家而独尊一说,如中国汉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欧洲中世纪独扬宗教遏抑学术,是也。易词言之,即独尊一家言,视为文明之中心,视为文化之结晶体,视为天经地义,视为国粹,视为国是;有与之立异者,即目为异端邪说,即目为非圣无法,即目为破坏学术思想之统一,即目为混乱矛盾庞杂纠纷,即目为国是之丧失,即目为精神界之破产,即目为人心迷乱。此种学术思想之统一,其为恶异好同之专制,其为学术思想自由发展之障碍,乃现代稍有常识者之公言,非余一人独得之见解也。”341
陈独秀的批判,其立论无疑是正确的,它不仅击中了旧思想营垒的要害,而且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学术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只能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和争辩才能实现,“思想、言论、出版三者,为精神之生命;三大自由,为精神生命之保护物,世界文化进步,即在于此”。342“从来一种思想,决非压抑的力量所能打消”,“吾国孔子的学说,只因禁止批评,所以变成一种锢蔽思想的枷锁”。343任何一种学说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更应该有一种多元开放的宽容心态,尤其应当容忍与自己的学说意见相左者。
五四启蒙者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导致正确的行动,他们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旧文化,没有丝毫的宽容精神,既无视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又武断而不容商量地主张彻底抛弃旧文化。1917年4月9日,胡适就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致信陈独秀说:“(文学改良)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种态度应该说是合乎现代理性精神的。而陈独秀的回答竟然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意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白话文学的价值是非如陈独秀所自信的那样,姑且勿论。而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本身便很难说是合乎现代理性的科学与民主。实在说来,五四启蒙者虽然在主观上追求民主与科学,期望以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但由于他们普遍怀抱有救世主的“启蒙心态”,因而在客观效果上,往往可能是假借科学与民主的名义而行一种新的文化独裁之实,五四之后的中国历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层面建立的启蒙心态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无限好处,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根基真正第一次发生动摇,但由于启蒙者无意识地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唯我独尊”“真理只在我手”的思想传统,缺乏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容忍精神,因而其负面效应绝不应当低估。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那样:“今天,面向21世纪,启蒙心态的弊端有目共睹。我们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来进行启蒙的补课,还得从根源处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以此为背景,发掘传统资源不只是民族再生的课题,也是人类自救的当务之急。启蒙心态(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一切生灵所带来的危机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来化解,基督教、回教、佛教、犹太教、兴都教、道教乃至巫教、神道,和民建宗教既然都有传统资源可以提供,儒家的人文精神当然也有滋养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344
我们不是要彻底否定五四启蒙精神,而是期望中国知识分子在淡化政治参与意识的同时,适当淡化一下启蒙心态,而以现代理性为指导,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开放心灵。既敢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成就,也敢正视西方文化的弱点;既敢批判中国旧文化与现实生活不合的消极成分,也勇于继承、利用中国旧文化中合理性的因素和要素。总之,以容忍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