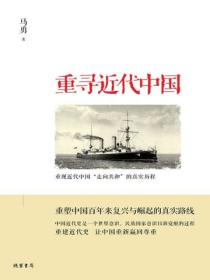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在政治上的选择只能是西方先发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经典模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一选择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将中国引上现代化的坦途,反而导致了比晚清更加混乱的社会、政治秩序,更加黑暗的政治统治,甚者一度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和行为。中国的未来前途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曾一度困扰着中国人。
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只是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必定具有发生的内在依据和原因。辛亥革命之后的帝制复辟思潮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洪宪帝制及更为短命的张勋复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怪胎”,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丑剧”,但平心分析这一思潮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这一思潮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原因,便又不能不承认,这一思潮以及由此思潮演化而来的行为,并不是某些人的异想天开或一厢情愿,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意味”,是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于此既不能证明民主政治、议会不合乎中国国情,更不能由此得出辛亥革命不合乎中国的需要,中国只能向后走,而不能前进的结论。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复辟思潮之所以发生的直接动因,无疑来源于权力危机。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在推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之后,建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54主张由国民选举共和国总统,选举议员,制定宪法,并最终实现国家的一切大事都按照宪法执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洋溢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然而,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奴隶制度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255绝大多数国民并不具备民主共和的基本素质,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下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意识,“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256在民众尚未根本觉悟的现实条件下实行民主共和,要么使这种制度流于形式,一般国民并没有条件和能力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要么居于社会之地位的革命党人也不得不趋从于一般民众的现实思想水平,当“革命破坏满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谓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经验,所以一般议论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凯时代,几乎大家说非袁不可。革命党自称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舆论说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257中华民国除了一块空招牌之外,其余一切照旧。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所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等自由并没有得到,中国依旧循着旧有轨道前进。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便到街上去了一通,满眼是白旗。”
“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258更有甚者,“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到努力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259民主共和的理想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变成现实,苦难的中国依然面对着艰难而不可预测的前途。
民主共和的构想和中国现实之间存在重大差距,当国民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时,职业政治家却在那里重新设计中国权力结构的新模式。旧式官僚依然将群众作为群氓来对待、来利用,而革命党人在被迫将政权交给旧式官僚的前后,则希望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和新的权力体制来约束旧式官僚的行动。
本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中华民国将参照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采用总统制。他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和三权分立虽然也不是尽善尽美,如监察权不独立,归属于议院,往往容易导致议院“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削弱总统的权力,造成“议会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总统如林肯、罗斯福者,便很难达到行政独立之目的。260但是,如果用五权分立改造美国的三权分立,既可以保障总统权力的实行,也可以分权限制个人的专权。他说,五权分立把其中所包含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作三个独立底权,来施行政治。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样是一样独立的”。261很显然,在孙中山的思考中,既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又要设法克服大权独揽、个人独裁的倾向。“如果用这种天然的资格(指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引者),再加以人为的功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262
强有力的政府是孙中山总统制权力结构设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合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孙中山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和施展。同盟会领导人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筹建过程中,就为未来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用内阁制,设总理。这种分歧在同盟会内部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但这种分歧的严重危害在于,它一方面为后来的权力危机埋下了潜在的因素,为此后的权力结构的争论以及各种解决权力危机的手段提供了借口;另一方面,孙、宋争论的关键毕竟涉及到由孙掌权,还是由宋掌权的具体问题。如果采纳宋的内阁制,实际上就架空了孙中山;孙中山或许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坚决反对内阁制。他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263不过,由于孙中山有黄兴等人的有力支持,最后多数赞成实行总统制,由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
然而,问题也正在于此。由于孙中山是同盟会内部众望所归的总统当然候选人,因而采纳了孙中山的总统制建议。但是,一旦孙中山不能继续总统之职怎么办?难道还要因人而宜修订政体吗?后来的事实恰好如此发展,于是为20世纪的中国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先例,即个人不受法律、制度的制约,而法律、制度则总是因人而宜地改来改去。
按照1912年1月2日颁布的《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大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务执行官,拥有“统治全国”“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一系列权力。264就其权力结构而言,颇合乎孙中山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构想。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权力模式并没有存在多久,就因人事的变动而作了根本修正。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尽快推翻清政府。从当时的实力看,南京政府举兵北伐并非全无可能,因为此时清政府正如袁世凯所分析的那样:“财政困难已达极点,万不能再以兵戎相见,只有退让,以维大局。”265但由于国内外势力的阻挠,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采取断然的北伐之举,转而期待南北议和成功,反复宣布只要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公开赞成共和,南京临时政府就将推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66
袁世凯基本满足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条件,孙中山旋即兑现诺言,宣布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一职,推举袁世凯代之。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毕竟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交出政权的,因而必然寄希望于通过法律制度和法律手续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和行为,保护革命成果。于是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
《临时约法》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最大修正在于放弃总统制,改用内阁制。它规定以“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而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则受到严格限制,既受参议院的约束,又受国务员的掣肘。267
这一重要修改的主观用意无疑是善良的,它期望以法律的手段来肯定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象征,束缚袁世凯的手脚,以国务员分割大总统的一部分权力,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袁世凯走向个人独裁。孙中山说:“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余犹虑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志不贰,然后许其议和。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268换言之,如果不是被迫将权力交给袁世凯,可能就不会制定这样的约法,《临时约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袁世凯一人所制定。
对于《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袁世凯起初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认为,既然采用内阁制,那么,他只要有效地控制内阁,就不仅不会使其权力丧失,而且可以增加自己的权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269因此当他得知《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时表示:“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专制之暇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270对未来似乎充满着信心。
不过,袁世凯或许没有料到,他所期望的控制内阁,也正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制定《临时约法》过程中所期望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孙中山等人认为,他们可以把政权从形式上让给袁世凯,但责任内阁的主脑——国务总理这一重要职务则应由同盟会会员来担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务员副署权对总统约束的有效性,否则依然难以保证袁世凯不走向个人独裁。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想法和袁世凯的设计形成了鲜明冲突,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由立宪派官僚赵凤昌从中调解,采取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提名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唐必须同时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暂时缓解了南北冲突,使权力结构一度实现了平衡。但对唐个人来说,由于处于权力冲突的夹缝之间,内心的不平衡自然难免。于是唐在任职仅3个月之后,便因“王芝祥事件”而自动辞职。责任内阁的第一次实践遂以失败而告终,权力危机在辛亥革命之后再一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