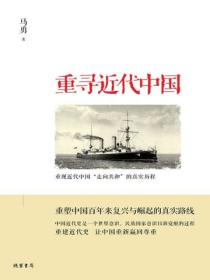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基于对立宪与共和两种方案的比较,力主舍弃立宪,实行共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相信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以及共和之制优于立宪制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他们对清廷的普遍失望。一方面不相信清廷有能力实行立宪政体。宋教仁说:“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而成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也。故其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以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89先不说清政府是否真的愿意就此放弃部分君权,即其能力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怀疑清廷的立宪诚意,以为清廷所允诺的预备立宪只是清廷在灭亡前夕所玩弄的骗局,其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消弥革命,维护满族人的政治统治。吴樾说:“吾国今日之行政、军事、教育、实业,一切国家社会之事,必经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进步,决非补苴罅漏、半新半旧之变法,足以挽此呼吸间之危亡也。以满族而宰制中国,无论专制、立宪,决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则?专制、立宪乃形式上之变更,至根本问题,满人抱持唯一排汉主义宁死毋二,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190不消说,这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结而对清政府的不信任。
立宪不足以救亡,共和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然而共和比立宪更进一步,清政府更不可能同意。于是辛亥革命的先躯者决计彻底打碎那个旧世界,然后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人人平等的共和政体。朱执信说:“今之非革命者,则曰:立宪易,革命难。呜呼!是乌知立宪,是乌知革命。夫欧美孰有不革命而能立宪者,况中国之立宪不可同于欧美也。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国立宪难。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彼满洲即欲立宪,亦非其所能也。……凡此诸难,一以民族不同之故而迄,则欲救其难,舍革命更无他术。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何则?其难既已去也。”191
确实,就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彻底的革命远比渐进的改良来得痛快和容易。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当)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口,一攻就垮,日益削弱下去了。人民不得不由自己,即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的上层建筑的毫无用处已成尽人皆知的事实。革命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了。现在的任务是确定究竟由哪些阶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新的上层建筑。”192很显然,以暴力基本手段,以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由于立足于彻底的打碎和破坏,因而它必然比那种在旧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良来得痛快和容易。
但是,革命的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毕竟是极其少见的现象,它不仅需要革命的时机,如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统治者也不愿就统治方式进行丝毫变革,而且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其充分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或交往方式已经无法容纳这种发展。否则,“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基础,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些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93
由此反观辛亥革命,我们明显地感到,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于此时爆发,完全是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汪精卫说:“中国苟欲立宪,舍革命外,更无他策。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知非革命无以立宪,则惟当奋起而实行革命。使所遇之敌而坚也,则虽艰难百折,终求达其目的;使所遇之敌而脆也,则事半而功倍,目的既定,不以敌之坚脆而殊其趋也。使怵于敌之坚,而趑趄退伏,以为不如希冀有开明专制之一日为愈,斯则大逆不道,而中国之罪人也。至于革命之际,流弊或所不免,然但当思患预防,力求所以免之者,不当以革命之有流弊,而至于不敢革命也。且天下岂惟革命乃有流弊,世界一日未至于至善之域,则无事不有流弊。世之言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此就比较上言之也,若自根本上言,则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当望之本族,不当望之矣族故也。而革命之后必为民权之宪,何也?其时已无异族政府,只有一般国民故也。”194
很显然,革命党人既未彻底排除中国实行立宪制度的可能性,但认为立宪制度的实行无法凭借清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改良措施,而只能采取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由汉族人建立自己的立宪政权。只是在推翻了异族之后,立宪体制实际已无实行之必要,于是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便是在建立民权共和政府。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在对待满族问题上,已如我们说过的那样,陷入了民族主义误区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之爆发的前提条件便不足以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环节,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而采取的革命手段。因此,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其主观目的虽然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这一运动本身几乎完全凭借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而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所以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与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完全吻合,许多方面甚至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
辛亥革命的倡导者对革命的迷信,除了相信人的能力能够改变一切外,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中国旧体制以及清政府倡导的君主立宪制的评估。也就是说,革命者对于共和政体的渴望,实际上是他们对立宪政体失望的必然反映。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的这种失望有多少扎实的内在依据。换句话说,他们的失望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上?
清政府的立宪政体如欲获得真正实现,至少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清政府拿出诚意来;二是举国同心,上下一致。如果第二个条件真的具备,那么即使清政府一时没有诚意,也迟早将在人民的推动下完成立宪。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是,革命党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抱定推翻满清的宗旨,在推动清廷立宪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和可能。于是,共识建立不起来,清廷的诚意也便迟迟无从表现。
从革命者方面说,他们自信其的历史责任是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国家。因此,他们对清廷的失望和彻底的不合作,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当革命者揭诸革命的纲领和目标时,并不是举国赞成和拥护,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提出许多的反对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康梁的反对意见没有辩倒革命者。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革命者对康梁的辩论,实质上并没有逐一正面回答康梁对革命的责难,相对说来是以武断的方式、以取消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
康梁认为,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来观察,共和政体不是中国目前可以立即采用的最佳方案,革命不是中国问题获得真正解决的最佳道路。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躐等前进,中国目前只能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然后由政府进行有“秩序”的改革,“拾级而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将来中国的整体是什么样子,而在目前最宜采用的“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便只能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这是中国未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政治上正当之要,实救国之唯一手段也。然则中国之能救与否,惟视人民之能为要求、肯为要求与否以为断。夫彼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者为何事,固无冀焉矣。”195也就是说,当国民程度尚未达到共和革命水平的时候,强行进行共和革命,便不可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对于康梁的责难,革命党人确曾给予有力的反击。关于前者,一如我们前已分析的那样,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普遍地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只循天演的规律,而应超前发展,躐等前进:“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196至于后者,革命党人不相信康梁对中国国民程度的基本估计,以为自由、平等、博爱为“人类之普遍性”,是任何民族都天然具备的,“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197
革命党人对康梁的反击干脆明确,但我们也不难觉察,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答康梁所提出的问题。此点或许正如梁启超所分析的那样:“昨某报印号外,发表与本报辩驳之纲领十二条。虽其词意之牵强者甚多,然以为彼既干预强辩,则必能将本报重要之论点,难倒一二,殷殷然引领愿听,而不意见彼报第四号,乃使我大失望也。何也?彼文皆毛举细故,或枝蔓于论点之外,而本报所以难彼说者,于根本上无一能解答也。本报论文最要之点曰: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欲论共和国民之有无,则必先取共和国民资格之标准,而确定之。然后按诸中国现象,视其与此之标准相应不相应,则其已有此资格与否,较然易见。共和国民之资格不一端,或非吾之学所能悉知,或非吾之文所能悉举,然吾隐括言之,吾所以认为重要者,则曰‘有能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此吾所命之标准也。论者如欲难吾说也,则于吾所命之标准,或承认,或不承认,不可不先置一言。若可承认之,则还按诸中国现象,指出其已与此标准相应之确据,夫如是斯吾之说破。若不肯承认之,则说明吾所命标准不正确之理由,夫此如此则可谓已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而中国现象实已如此如此者也,夫如是斯吾之说益破。不幸而论者所以相难者不尔尔,于吾所谓‘凡国民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者,皆其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之一前提,避而弗击。吾读其文至再三,其果承认此前提与否,渺不可见。而惟悍然下一断案曰:‘吾之意以为中国国民,必能有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198
梁启超的自负我们大可不必相信,但他的这段分析无疑指出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当他们的目的已经确定之后,不论条件具备与否,他们都将义无反顾地为之献身,为之奋斗。他们坚信:“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能事半功倍乎?”199很显然,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建立共和,这便是信奉改良主义信条的梁启超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于是,革命派不仅“辩倒”了改良派,而且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在人为的推动下,革命并不是不能发生,共和也不必是不能超前实现。至于后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