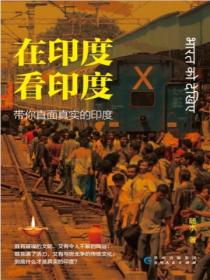如果你问我,印度所有的大城市里我最喜欢哪一个,我很难回答。孟买和加尔各答这两座城市让我难以取舍,虽然这两座城市并不在传统的印度热门旅行目的地列表上,但它们的魅力和丰富性在我看来远在那些知名的旅游城市之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加尔各答都曾经是我的最爱。加尔各答曾经是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印度独立之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大量的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被保留下来,像一个会呼吸的标本。加尔各答有些地方看起来就像香港的市井,有些地方又像老上海的租界,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人力拉的黄包车、英式风格的黄色老爷计程车都在街上跑着。另外,加尔各答原属于孟加拉省,在文化上与典型北印度也有所不同,老百姓相对更为善良友好。
然而随着对孟买的深入了解,我意识到孟买才是印度乃至这个世界上最魔幻、最有意思的地方。我对孟买的感情很复杂,这个城市既不宜居,也没有印度其他地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底蕴,绝大多数正常的游客都不太容易喜欢上这个地方,甚至可能会讨厌它,然而随着对它的了解越多,就会越来越被其文化的多样性所折服。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是与孟买相似的,它不同于上海、纽约的海纳百川,也不同于伊斯坦布尔千百年历史的沉淀,甚至完全不同于同属英国殖民时期的重镇加尔各答。孟买那种独特的多样性在于现代与传统、富有与贫穷、进步与落后、现实与梦想的对立统一,印度最有钱的人和最底层的人都生活在这里,印度最好的和最糟的一面也都能在这里找到。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座城市就像一台蒸汽时代遗留至今的无比庞大而又老旧的机器,在努力地排除故障以保持运作。你可以看到当年建造这台机器时的精巧设计,透着一股蒸汽朋克的气息,也可以看到历经岁月的千疮百孔,看起来破得随时要散架,却又处处焕发着自我修复的生机。
魔幻现实主义:孟买
在2014年第一次踏足孟买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贫民窟。由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这部电影,孟买的贫民窟可谓“享誉全球”,即便是许多从没到过印度的人,想必也听说过“达拉维”(Dharavi)这个名字。这座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不仅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取景地,关于它的许多传闻也让人十分好奇——诸如全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口密度高到爆炸,1440人共用一个厕所,房屋的月租金只要6美金,等等。
因此探访贫民窟在当时几乎是我去孟买最主要的目的,我在抵达孟买之前,就提前在卫星地图上看哪里有高密度的贫民窟,在达拉维附近的西昂(Sion)找一个酒店住了三晚,天天清晨和傍晚钻进贫民窟里拍照。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类似的地方,对贫民窟充满好奇心;而那几天的探索过程,颠覆了我之前对孟买贫民窟的全部想象。
然而我所见到的达拉维,除了某些公共地带垃圾较多之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棚户区并没有太大区别。
2014年在孟买Sion贫民窟拍的。如果一个孟买人跟你说他们家门口有条小河,你千万别太当真
2020年去孟买达拉维贫民窟,河道治理比过去有所改善
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达拉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挤。通道如同迷宫般蜿蜒曲折,线缆像藤蔓般伸展,猫狗鸡羊等动物和谐相处,忙碌穿梭的身影无所不在。在这异常逼仄狭小的空间中,人们井然有序地生活着。
贫民窟里面的许多居民也并非是我们概念中的“贫民”,早上从这些地方走出来的不少年轻人一个个都衣冠楚楚,穿衬衫系领带,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学生和公司白领,就外观上来看,跟“贫民”似乎搭不上关系。这是因为大城市有着更多的资源和工作机会,使得大量务工人员涌入德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令贫民窟发展壮大。这种高度拥挤的棚户区乃是大城市的特色,我居住的哥印拜陀这种二三线城市,虽有贫民,但数量不足以聚众成“窟”。因此孟买贫民窟颇有些从前香港九龙城寨的神韵,层层叠叠通风极差,私拉的电线密如蛛网,但自来水管很少,大部分当地居民需要自己去供水点取水。虽然没有高层建筑,但由于私搭乱建向上发展,许多角落依然是终年不见天日,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可能要住一家七八口人,全无隐私和私人空间可言。
神奇的是,即便是如此拥挤的生活环境,贫民窟内部却并不脏。那些小小的房间都收拾得纤尘不染,人们会尽自己所能布置自己的房屋,使其变得更加温馨舒适。当然,居住空间之外的公共卫生就一言难尽了,尤其是那些小河流,污染极为严重,生活废水和垃圾都直接排放其中。
我在贫民窟里逛了两天,终于还是受不了那里而仓皇而逃。但你们一定想不到我受不了的是什么——被大量围观。
这个贫民窟的结构,其实有点像养鸡场,一个个小房间就像鸡笼子。我这种外人一跑进去,里面立马就会沸腾,消息在这个没有隐私的地方迅速传播,所有人都立刻知道有外人来了,一个个把脑袋从“鸡笼子”里伸出来张望。大人们还比较节制和矜持,可小孩子就不一样了,在他们看来我哪儿是外国人啊,简直就是外星人!一见我进了他们的巷子,立马兴奋地呼朋引伴,成群结队追在后面,搞得我好像长了根尾巴似的。这些小孩既不要钱也不要糖,就要我给他们拍照。最夸张的是,为了强夺镜头前的核心位置,他们互相之间甚至还会大打出手……起初我倒还喜闻乐见,到后来实在应付不过来,不得不落荒而逃。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2014年印度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拍照片在当时是个稀罕事,印度人本身就热衷于被拍,小孩子自然是加倍狂热。我太太说她小时候看到外国游客也是抢着要他们给自己拍照。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印度人的“被拍欲”通过自拍得到了充分满足,这两年再去贫民窟就没有碰到过这种事。
虽然热情得有些过度,但不管怎么说,我头一回接触到的这些孟买人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外国人的友好,这令我对孟买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后来我又去了很多次孟买,也去钻过其他一些贫民窟。孟买的贫民窟远远不只是达拉维,但达拉维无疑是其中历史最悠久并且最具特色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觉得将之称为“达拉维贫民产业园区”更确切。
在前海洋文明时代,孟买跟纽约、上海一样,早年都是近海的滩涂、沼泽。孟买原先是七座小岛,达拉维过去则是个红树林渔村和大片沼泽地,英殖民地时期填海造陆,才把孟买建成了一个半岛深水港。在英国人的规划中,孟买半岛南区是作为城市来规划的,最南端则属于城市行政金融中心,都是些“高大上”的地方,相当于上海的外滩。于是在1884年,殖民政府把南区的一些工厂和穷人搬迁到达拉维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当然这个“荒郊野外”是19世纪末的情况,对比上海的话,达拉维的地段大致相当于徐家汇田林新村那一带,搁改革开放前,田林在上海人眼里也是乡下农村。
当时搬迁到达拉维的主要是古吉拉特邦来的陶工,殖民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为期99年的土地租赁权,而在此之前,达拉维已经有一些皮革制造业入驻,河对岸就是个屠宰场,于是在达拉维形成一个产业中心,各种各样的工匠都涌入达拉维,仅仅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100万人(1)。虽然达拉维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政府却一直没有为这个地方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卫生系统、下水道、自来水、道路,居民区和小作坊在这里野蛮生长。由于公共卫生情况恶劣,1896年,孟买爆发霍乱,造成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
印度独立之后,随着孟买的发展,达拉维成了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与此同时,城市向北扩张将这个贫民窟包围起来,所以确切来讲,达拉维应该算是非常典型的“城中村”。这里本来就有两条城铁线路,分别经过达拉维的东西两端,按照城市大规划来看,这里绝对是个黄金地段。印度政府当然也知道这块地的价值,搞过好几个重建计划,但改建达拉维是一项不亚于建设三峡大坝的工程,以印度政府的动员能力,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年,达拉维其实一直都在发展和变化,比方说,最早的时候,这里连路网都没有,这里的道路系统是政府进行郊区开发的时候修建的。国内媒体写达拉维贫民窟的时候,采用的数据都极其落后,很大程度上是以讹传讹:首先,达拉维早就不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了,早在2011年,在孟买就已经有另外四个贫民窟的规模都超过了达拉维,但达拉维依然是名声最大的一个;第二,网传达拉维1440个人才有一个公共厕所,这是2006年的数据,当然最新的数据也好不到哪里去——约500个人共用一个公共厕所;第三,6美金一个月的房租,也早已是年深日久的老皇历,如今达拉维一个比较典型的棚户区小房间,月租金价格在300多元到700多元人民币不等(3500~8000卢比),售价从30万元到150元万人民币都有;第四,达拉维的识字率高达69%(2011年数据),位居全印度贫民窟识字率之首,这地方并非很多人想的那么不堪,而是一个成熟完整的产业社区,成百上千不见天日的小作坊每年的产值高达几十亿美元。
达拉维都生产些什么东西呢?除了传统的皮革、陶器、服装纺织品、黄铜、食品、珠宝之外,目前最主要的产业之一是废品回收。
废品回收是达拉维的一大支柱产业,因为这显然是成本、门槛都最低的行业,甚至几乎没有年龄的限制。我第一次走进达拉维废品回收片区的时候被深深震撼了,这片迷宫一样的工坊区被无数废弃物填满,其中尤以电子废弃物居多。这些废弃物被分门别类地存放,堆积如山的纸箱,一袋袋的电脑键盘、电话机,一桶桶的彩色电线……那些工人或将成堆的电线剥开取铜,或将塑料切碎按照颜色分类。工人通过原始的“泡水法”来分离金属和塑料——塑料会漂浮,这种方法就跟从前的人淘金似的。地上的积水都是五颜六色的,而许多工人就在毫无防护的作业条件下进行拆解、分类、粉碎等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咋舌。在这边回收区有一个特别不和谐的存在——面包房,除了正常的烘焙之外,过期面包会被收集到这里回炉,做成干脆的烤面包片,打那儿之后,我就不太敢吃印度的脆面包片了。
在家里的时候,我经常惊叹于自己制造垃圾的速度——为什么垃圾桶总是这么快就满了?这些垃圾最终会去哪里呢?尤其是那些精密复杂的电子废弃物,使用各种材料制作的电路板怎么处理呢?
孟买达拉维贫民窟里的居民,只能定时定点排队打水
跑到达拉维的回收工坊,我才发现——原来垃圾最终的归宿是这样的。
在空间如此狭小的环境里,集中了数量如此庞大的电子废弃物,使得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电子消费品对环境的影响。我们购买的每件电子产品,当初都如此光鲜亮丽,令人爱不释手,然而它们的生命周期很少有能超过五年的,最终都免不了沦为一堆难以拆解回收且很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电路板、电池、液晶屏。
生平第一次,我对消费电子产品产生一种罪恶感。
达拉维废品回收区中的空气弥漫着废弃物和金属尘埃的味道,这样一个地方,空气乃至水土的污染程度可想而知。有一次同去的朋友很感慨地说:“这样的生活环境,人不会长寿吧?”我苦笑道:“他们的目标应该只是活下去。”
贫民窟里虽然有一部分是在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阶层,但更多的还是那些生活在孟买这座繁华大都市最底层的人,他们干着一些最脏最累的活,通过挣取微薄的薪金来养家糊口。由于空气污染,肺癌、肺结核、哮喘等疾病在达拉维居民中很常见。
在工作之余,他们的生活就跟我们一样,欢声笑语、无拘无束,当我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也不会有尴尬、难堪和羞怯——这绝非苦中作乐,印度人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作为贫民窟里的居民,这正是他们最自然不过的生活,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的。我相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卑微还是宏大,终归还是有的。
达拉维内部的人口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世世代代扎根在这儿,而是有阶层流动性的。这里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的城中村——许多住在这里的人都只是租户,而非业主。不少早期的业主早已经通过资本积累或政府组织的搬迁改造离开了这里,他们把自己原来住的“老破小”租给那些到孟买“掘金”的后来者。
虽然政府的大规模改建规划一直都阻力重重,但地产资本的运作始终都在进行。开发商在局部区域进行拆迁,建起了高层公寓楼,一些居民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同时多余的公寓住房也吸引新的居民在这里置业。更聪明一些的当地人,联合自己的社区,找开发商给他们改建成高层公寓楼,一转身就成了包租公和包租婆。当然,由于产权关系的错综复杂,这种联合并不容易达成,所以达拉维内部的高层公寓总是东一幢西一幢,缺乏大环境的整体规划。
总之,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的强力加持下,达拉维如今成了孟买的一个知名景点,当地有专门的达拉维观光项目,会有导游带着那些游客参观这里的产业区和居民区,介绍达拉维现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能够与达拉维平分秋色的另一个贫民窟景点当然是千人洗衣场——“Dhobi Ghat”。
我在前面讲种姓制度的章节里提过,印度的种姓跟职业有关,“Dhobi”种姓是洗衣服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洗衣工,源自印地语洗涤(Dhona)一词。在种姓分类里面,洗衣服、熨衣服等职业在过去都属于贱民种姓,如今叫作“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总之,就是一种法律上受保护,但在社会上受歧视的种姓族群。
“Dhobi”在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种姓群体,比方说,在比哈尔邦,有18%的人口都是“Dhobi”种姓,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祖上都是以洗衣为生的。但最有名的“Dhobi”种姓社区莫过于孟买的“Dhobi Ghat”,“Ghat”是一个在印度次大陆被广泛使用的地名后缀,有河坛、台阶的意思,具体词义取决于上下文,这里的“Dhobi Ghat”就是洗衣场的意思。考虑到孟买是一个移民城市,也不排除这些“Dhobi”种姓群体是从比哈尔邦来的。
那么这个洗衣场有什么特别的呢?
与其说这是一个洗衣场,倒不如说是一个贱民社区。在印度教的传统中,种姓和职业相互绑定,如今虽然已经松绑,但巨大的传统惯性依然存在,在社区中有很多人仍旧从事着祖传的洗衣职业。这里是工作场所,同时也是他们的家,居住着来自200多个家庭的5000多名“Dhobi”种姓洗衣工,对他们来说,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十分模糊——洗衣场就是家,家就是洗衣场。出生在这里的“Dhobi”,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关于洗衣的一切知识,个个都是洗衣专家。其实洗衣服本来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才需要专门的干洗店,别人洗不干净的衣服他们能洗干净,对于不同衣料的分拣、洗涤、熨烫、上浆、染色,他们也都颇有心得。
想要进千人洗衣场,要先给看门大哥交“保护费”。按照2020年最新的行情,每个人头至少得500卢比,这个价钱赶上印度那些世界文化遗产景点的门票钱了。人数少的话可能更贵,人多可以跟他砍价,但由于其垄断的性质,砍也砍不了多少,反正你爱看不看,咱们收费的规矩不能乱。而且洗衣场只有一个门,不太可能逃票。其实从“Mahalaxmi”城铁站出来的天桥上,就能看到整个洗衣场的全景,有不少游客嫌“保护费”收得太多,于是就在路边看一下,拍个照片,好歹也算是来这里打过卡了。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路边那个最佳“观景点”,居然修起一个正儿八经的观景台,且完全免费。
交了“保护费”之后,看门大哥会指派一个向导给你,带着你参观不同的区域。当你走进这个地方,就会觉得收这个保护费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这里本身是一个类似于工场的经营场所,你要是自说自话在里面到处乱逛,会影响人家工作,万一丢了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一两个人乱逛或许影响不大,但大家要知道中国那些成群结队的“老法师”的战斗力有多强,把相机凑脸上拍,叫人家还怎么干活?因此收点保护费,一来能设置门槛,二来也能让参观拍摄更为有序,三来按照看门大哥的说法,收这个钱,他们是用来进行社区建设的,也算是“扶贫帮困”吧。
千人洗衣场始建于1890年,妥妥的百年老字号。洗衣场开建的时候,孟买还远没有如今的规模,所处地段相当于上海的静安寺。这里晾晒衣服的场面确实颇为壮观,你会怀疑是不是整个孟买的衣服都拿到这里洗了。他们晾衣服的方式倒是值得推广一下,不需要夹子,拿两根粗麻绳绞紧绷直,晾衣服的时候找两个衣角往麻绳之间一夹,收的时候一扯,对衣物的形状完全没有限制,小到袜子大到床单都能这么晾。
千人洗衣场一共有731个混凝土洗衣池,每天要洗超过10万件的各种衣物,这些衣物、织物主要来自酒店、医院、社区洗衣店、餐饮服务商、服装经销商以及婚庆公司,他们的业务不光是清洗,还包括染色、漂白、熨烫等,最多的时候,据说有7000多名洗衣工,许多人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
2011年的时候,千人洗衣场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最多人同时手洗衣服的地方。
印度人手洗衣服跟咱们的洗法不一样,他们把衣物甩起来然后砸在石板上,观赏性比较强。咱们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里是“孟买洗衣场,千人甩衣声”。不过如今的传统手洗已经变得越来越少,有些洗衣工挣了钱之后,买了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进行产业升级,如今洗衣场内的传统手洗已变得越来越少,高效率机洗的普及也会加快淘汰的速度,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到手洗了。
据估计,千人洗衣场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0亿卢比(2017年数据),按现在的汇率就是1367万美元,按照7000名洗衣工的话,每人创造了近20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等于印度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点都没给国家经济拖后腿。
我们平时总说印度人“开挂”(2),除了他们善于突破人类忍耐力极限之外,其他方面也不含糊。你们看连个洗衣场都能搞成世界纪录,然而千人洗衣场绝非孟买唯一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我所知还有一项世界纪录,是一个叫“Prakash Baly Bachche”的“达巴瓦拉”(3)(Dabbawala)创造的,他一次性将三个饭盒板条箱顶在头上。这个饭盒板条箱可不一样,每个能装45个饭盒,装满饭盒的板条箱我估计绝不少于50公斤,那玩意想要靠自己一个人举起来都难。把三个这样的大家伙顶在头上,而且还得保持平衡,这可不是“开挂”嘛!
说起“达巴瓦拉”,可算是孟买的一张名片,“Dabba”是波斯语中的一种盒子,通常用来装饭;“-wala”这个后缀代表执行者,“达巴瓦拉”的意思就是送饭盒的人。
这些“达巴瓦拉”大多数都是文盲,不依靠任何现代化技术,却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每800万个饭盒只会送错一例,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通用电气的“六西格玛”(Six-Sigma)(4)管理水平,震惊了哈佛商学院……
这些大同小异的故事被传播的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以讹传讹。
孟买的“达巴瓦拉”
1998年,当时《福布斯》杂志有个叫苏布拉塔·查克瓦提(Subrata Chakravarty)的记者采访了孟买“达巴瓦拉”协会(Mumbai Tiffinmen's Association)的主席拉古纳斯·麦吉(Ragunath Medge),问及送饭盒的出错率,主席随口就说:“几乎从来没有,或许两个月有一次。如果我们一个月送错10次,那没有人会用我们的服务。”(5)记者按照这个回答,推算出每800万次或1600万次(算上饭盒回收)才会出错一次的结论,然后把这个推算写在了一篇名为《快餐》(Fast Food)的稿件中,这可能是关于送饭盒小哥最早的一篇媒体文章。
2002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记者问到主席拉古纳斯·麦吉,你们这个协会算不算是一个“六西格玛”组织,主席说他根本不知道“六西格玛”是什么,记者告诉他这代表每10亿次只会发生1.9次错误,那个主席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那我们就是,问福布斯去。”(6)于是这个记者在写稿件的时候就写了——“《福布斯》已将孟买饭盒小哥协会认证为六西格玛组织。”
结果“六西格玛”说法就被传开了,如今“达巴瓦拉”自己的官方网站上,也宣称已经得到“六西格玛”认证。最初的那个《福布斯》记者苏布拉塔·查克瓦提后来其实发表过文章辟谣澄清,他说《福布斯》从未认证过这个所谓的“六西格玛”组织,他也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六西格玛”其实是最早摩托罗拉创立又被通用电气推广的一套商业管理工具和流程,而非统计数据。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个道理放诸四海而皆准。大家看明白了吧?一千六百万分之一、八百万分之一的出错率,其实是“达巴瓦拉”协会负责人自己随口说的,关于饭盒配送的准确率其实从未有过正式的统计。哈佛商学院确实将“达巴瓦拉”作为案例研究,但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以低成本、简单的操作来提供高水平服务;而所谓的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指的是某个小哥——一次头顶三个饭盒板条箱,并不是指这一服务的水准和效率。
我觉得关于送饭盒这件事,从印度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会更有意思——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业会出现在孟买而不是别的地方?
孟买跟上海、香港、深圳一样,早年都是渔村,随着城市的兴建和发展,涌入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印度有个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各种忌口多得离谱。这个在之前的章节里写过,南亚地区由于天热,食物容易变质腐败,从而导致食物中毒,因此发展出各种饮食禁忌。有些禁忌和宗教相结合之后变得教条化、极端化,并且这种“食品卫生”的强迫症不是靠分餐制就能解决的,连对厨房的“洁净度”都有要求,有些人的强迫症甚至严重到只吃自己家里做的东西。大食堂、大锅饭这种形式在印度根本就没有市场,即便在今时今日,还有很多印度人不太情愿吃外面的食物。
这种饮食禁忌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问题不大,因为过去人们的活动半径小,一般跑不出一嗓子能吼到的距离,能够保证顿顿都吃上妈妈的味道;然而在不同族群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人们来到城市工作,这些禁忌显然跟新时代不相适应。
城市化没能帮助印度人摆脱传统饮食禁忌,反而催生出送饭盒这个职业。
送饭盒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晚期的一位帕西族(Parsi)银行家,他想在办公室里吃自己家里做的饭菜,于是专门雇了一个人每天给他送饭,这种“有钱任性”的做法引得他人纷纷效仿。这里我得说明一下,在印度社会,分工之细是独一无二的,比方说有钱人家请佣人,买菜、做饭、打扫都得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工作的“洁净度”不一样,他们在情感上显然接受不了同一个用人既打扫厕所又给他们做饭。送饭这种活儿肯定要专门找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不然这饭菜就被“污染”了。帕西族信的是拜火教,虽然不同于印度教,但毕竟融入印度社会将近一千年,受到很大影响,也跟印度教一样有着“洁净”和“污染”的概念。
这种市场需求出现之后,1890年的时候,有个叫马哈迪偶·哈瓦吉·巴切(Mahadeo Havaji Bachche)的人组织起了一百多个人的送饭盒团队,一直成功运营到现在。
在不少文章中,把这种送饭盒的需求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孟买上下班高峰时段城铁拥挤,不方便带饭盒;二是孟买天气炎热,早上带过去到中午就坏了。我觉得这两点都不是根本原因,一百年前的银行家哪来的挤地铁问题?就算孟买天气再热,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也不足以让食物变质吧?而且如今的大公司配个冰箱和微波炉也不是很难吧?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印度男人觉得自己带饭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
印度人有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观念,他们会觉得做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是很不体面的。我在印度见过不少男人都是家里油瓶倒了也不会去扶一下的那种,他们觉得这是女人的职责范围,自己一旦做过一次,就会坏了规矩,是坚决不能做的。像我这种“买汰烧”(7)什么家务都干的男人,在印度引起过无数次吃瓜群众的围观,我的印度铁哥们儿家的钟点工、邻居乃至我的丈母娘,看到我忙个不停地做家务,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基于这种社会文化,在印度一些观念传统的地方,一个男人如果拎着饭盒上下班,会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就好像他越俎代庖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左邻右里会觉得这户人家的妻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连丈夫的饭菜都没有安排好。
另外还有两点也很关键,一是在许多印度人的习惯里,是不吃隔夜饭菜的,他们每顿都要吃新鲜现做的。我们如果带饭上班上学的话,大多数带的都是前一晚的剩饭剩菜,但印度人没有这种习惯。二是因为传统印度家庭中,妻子都是全职家庭主妇,不然怎么可能专门在家做饭?据我所知,在印度北部一些地方,丈夫要是让妻子出门工作,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特快专递”这个词,觉得非常上档次,只有很有钱的人、很重要的东西才会使用“特快专递”,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快递会变得如此平常。送饭盒服务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是一种被平民化的特殊服务,这种原本是富人专属的服务,被发展成规模化产业之后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平民也有能力负担,成了一种面子的象征——身为堂堂公司白领,人家都有专人送饭,你还得自己带饭盒上下班,岂不是很丢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