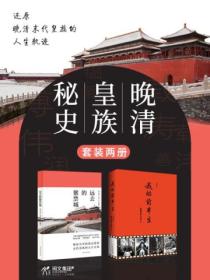第六篇 回到了祖国
第十二章 我在当时的心情
一、我的惶恐不安
当我在伯力收容所内,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听到阿斯尼斯所长对我宣布了要把我们这一批伪满汉奸送还祖国的时候,我不由得心里头想:
“万事休矣!”
本来因为害怕回国,才三次上书苏联当局请求长留在苏联的,可是三次的请求的结果,并未发生任何效力,不管我愿意与否,送还这件事,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除了认命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固然是阿斯尼斯所长说他将来亲自送我,并把我安置在列车内特别厢间和他在一起,并给我买了一瓶洋酒和饼干糖果等等物品,但是我的这颗心,总是跳**不住,认为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反正这条命活不多久了。
尤其是当我们这列列车开到了中苏国境绥芬河车站之后,在那里停了达一夜之久,到了第二天早晨,当听到远处嘹亮的军队起床号的时候,这固然是我耳朵所熟悉的祖国军队喇叭的声音,可是这时的我,与其说是听到了多年来未曾听到的一种非常耳熟的声音而感到了久别重逢的怀慕的情谊,倒不如说是听着有些心惊肉跳的异常情感,我觉得这倒还比较恰当些。
天空由鱼肚白色逐渐像染透一般,渗出了由浅而深的朝日光辉,渐渐一轮耀眼的红日从地平线爬上了云霞罗锦的天空。这时,阔别了五年之久的祖国山河面貌,也都依然无恙地由浓黑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终于清清楚楚地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所不同的是:在过去是沦陷在日寇的污黑浊雾里,而今日则是显露在清新纯洁的空气里。悲惨的噩梦已经过去了,现在则是在无限光明远景的前程之中,呈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朝气勃勃的新气象来。我就是这样百感交集地从列车玻璃窗口,茫然无目的地在眺望着。接着祖国人民的蓝色衣服也看到了,渐渐地素日所熟悉的祖国语言也被凉爽的晨风,给送到我的耳中来了。我是对这些觉得有些怀慕呢?还是兴奋呢?或是惭愧呢?就是我自己在当时也是说不上来,只是觉得好像是打翻了餐桌上摆的五味瓶一样,酸、辣、苦、甜、咸的味道真是样样俱全的,并且还在这种混合滋味当中,更加了一种形容不出的强烈的味道,那就是害怕的滋味。
祖国的人民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消灭了狐假虎威的汉奸政权,并且把近代化的美式装备的八百万蒋匪军队完全打垮,像是这样站起来的新中国人民,尤其是曾在敌伪血腥统治下,饱受了十四年煎熬的东北人民,对于像我这样的头号大汉奸,还能够不红眼来和我算一算数不清的血债吗?能够不向我报那血海冤仇吗?况且共产党一贯对于汉奸、卖国贼是绝对不会稍留情面的。在苏联的报纸中,也曾经常看到祖国在土改的革命斗争中,什么“净身出户”什么“镇压土豪恶霸”等的记事,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件切身的威胁,经常使我触目惊心得不能自禁。对于乡间的地主劣绅、地痞之类,尚且如此,何况……
当我想到这里时,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身子,就好像在一片秋风中从树枝上被刮下来的枯黄落叶一样,只有任凭无情金风的吹拂,不能丝毫自主地落下去罢。至于被吹到什么地方,落到什么地方,那只有听任未知的渺茫安排罢!
愈是愁肠百结地在思前想后,光阴的前进速度就好像是故意要开慢车似的一秒一秒慢慢地踱着。但是,尽管它如何的慢,结果仍是应该到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时阿斯尼斯所长便告诉我:
“中国政府派来接收你们的工作人员来了,要和你见见面。”
我听了心中猛起一震,就在心中暗想:
“见了面之后,不定会对我怎样呢!”
于是,心神不安地进入到列车中的另一个房间去。看见有一位首长和一位解放军的指挥员在那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那位首长并没有拿对犯人的态度来对待我,而是和和气气地和我握了手并和蔼地对我说:
“你现在回到祖国来了,我是奉周总理的命令来做接收工作的……”
谈了一些话便走了。这是我回到祖国大地上,第一次和祖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见面,这种和蔼的态度,这种亲切的谈话,简直弄得我又惊又喜!
过了些时候,我们这批汉奸,便一个一个地被叫下车来点了名。这时便有许多苏联兵士争着看我,并问哪一个是溥仪。我当时真觉得有个地缝也要钻下去,但是避无可避,只好是佯作不感觉的样子任凭他们看吧!当大家从苏联方面的警戒线走向祖国人民解放军所担任的警戒线时,我们这群人在手里都拿着大小不同的包裹提包之物,无精打采地低着头走着,而我呢,则是单独下了列车和阿斯尼斯所长一同进入到祖国特为来接的一节车厢之内。并且公安人员还替我提着我那黑色的大皮箱哩!
这时特别映入到我眼帘的,就是缝在公安人员右胸衣兜上的那个标志,在那标志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个大字。
这时我就想,上了车之后,像我所预想的冷嘲热讽、手铐脚镣甚至老拳和皮鞋的接待等,眼看着就要一齐来到眼前了。不料上车后的情况,和我所预想的完全相反。不过是在这个时候,唯一把我的心弦拧得绷绷紧的一个当前最为悬念的重大问题,就是死与活的问题,特别像我这一贯以胆小多疑作为支配我前半生绝对力量的脆弱心灵,便越发把我全身的神经,都昂奋到了无可再兴奋的地步。也就是说,现已到了绝望的时候,不豁出去也不行了。
但是接踵而来的眼前事实,却完全和我所预想的结果不一样。接收我们的首长却是拿慈祥的笑脸迎接了我,以温和的声音和我谈了话。请想一想,在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之外的大变化中,又怎能不使我疑心是在做梦,怎能不对于这种完全意想以外的现实,疑心是自己的一种幻视和幻听!
然而事实究竟仍是事实,我的眼睛既没有花,我的神经也没有任何异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叫我又怎能加以否认呢?
当我坐在被指定的座位上之后,便听得一位干部向我们宣布了登上祖国列车以来第一声:
“你们都回到祖国来了!你们都可以放心,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于你们的问题,早已有了决定和安排,你们大家都放心好了!”
最后更是出人意外地继续宣布道:
“有病的人,可以前来报名,我们可以给你们医治!”
在事后我曾听说在这些同犯之中,确有一些人因为听到了“祖国”这两个字而流了泪;有的则是因为听到了这篇温暖的发言而放下了心。可是我在听了这番话之后呢?当然也是由于完全出乎我的意想之外,而愣了一下神,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而放了心,但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能,却又一转念:
“什么‘放心不放心’?什么‘给我们治病’?还不都是一种安定人心的‘法术’!那些公安人员又怎能知道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只不过是他们为了自己在途中的押送责任,怕我们或许在列车中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故,所以才要拿这种‘好听的好话’来安慰我们罢了……”
结果是完全没有相信这一篇话。同时在另一方面则是:
我的这次回国,本是抱着万念俱灰的心情回来的。本来吗,从什么地方去看去想,像我这样的人,还不是早被注定要被判处极刑的?可是眼前在摆着的现实却又不是那种样子。所以反倒又使我愈想愈糊涂起来,愈想愈觉得忐忑不安。因为事实和我的预想完全相反了。特别是在我亲眼所看到的这种亲切照顾的同时,却又看到了列车玻璃窗上所糊上的严密的报纸,以及那武装部队的森严戒备,真使我如同堕入到五里雾中一个样,简直分不出东南西北来了。
不久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这时有一位负责干部,便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分配给一个饭碗和一双竹筷子,并含笑对我们说:
“小心不要把饭碗打了,因为在旅途中,不容易补充新的!”
这固然只是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可是听到我的耳中,也是使我感到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不过是这种轻松之感,不久又被狐疑和害怕的心情所代替了。这时我又发生了一种另外的感觉。就是那双竹筷子也只是一双普通的长竹筷子,并没有任何出奇之处;饭碗也更是平日习见的富有民族风味的瓷饭碗,尤其是谈不到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可是这个普通的竹筷和平凡的饭碗,对于我都仿佛是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情感的,觉得它对于我是毫不陌生的,是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密之感,不由得使我在心内想:
“到了祖国了——我们的祖国!”
跟着热气腾腾的白米粥端到车厢里来了。那位负责的工作人员不但是分菜分粥地忙着,并且还把我们痰盂内的脏纸片、烟头、洋火头等,不嫌污秽地亲自下手替我们收拾。这种作风,在当时我固然还不能知道这就是新中国新社会的普遍工作作风,但也使我在默默之间受到极大的感动,因为这样事是我有生以来初次看到的缘故。
大块的酱疙瘩——酱甘蓝疙瘩的咸菜分到手了,足够往饱里吃的热粥也盛到碗里了,咸菜的味道、粥的味道,实在是使人难忘的一个味道,这时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只觉得鼻子一酸,两个眼睛一热,于是我也就从我的本能中,忽然喊出一声:
“好吃极了!”
那位负责人当我们吃到正进入“**”的时候,更亲切地对我们说:
“现在正在旅途中,天气又热,只能做出这样简单的东西来,等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地吃了。”
“简单的东西”?“好好地吃”?凭自己良心说,这样的吃喝以及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了。因为在当初尚未回到祖国领土以前的时候,所预想的是:
能把高粱米饭吃饱,能把窝窝头吃饱,就是万幸了。谁还能想到有精米粥和酱甘蓝疙瘩吃?现在不但如此,还说这只是些旅途中的简单的食物,真是,除了低头紧吃之外,还有什么话说。
结果是在大家的放心大吃之下,把我们这些人应得的部分都吃光了,这些位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种舔嘴抹舌的样子,知道我们有些人还没有吃够,便又忙着到车外去取。固然是我们都齐声说:“已经都吃饱了,已经都吃饱了。”但是这种虚伪的“客套”话,是瞒不过这些位新中国的工作人员的,他们当然是不会理会我们这种言不由衷的“客气”话,而把又一大木桶的热粥端进来了。当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桶粥的来历的,于是又把它吃了大半桶之后,才算是沟满壕平地人人吃个大饱。事后才知道这桶粥原来本不是我们这批人应吃的部分,而是公安部队工作人员的应得部分。只是因为我们吃得过了分,所以这些位公安工作人员才把他们自己的东西让给我们吃了。因此,那些位工作人员迟延了很长时间,才又弄来些东西吃。
我当时还认为:公安工作人员是不会和我们吃一样东西的。可是这一判断我又估计错了。公安人员不但是吃的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并且还尽先让我们这批人吃饱,然后才自己胡乱弄些东西来吃,这在旧社会,不用说封建清朝时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就是在中华民国号称共和制度时代,也是看不到这种工作作风的,当然我在当时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是瞪眼看着而已。
我们在列车中头一顿吃的,固然是白米粥和酱咸菜,第二顿,第三顿……还吃到了越发出人意外的腌鸡蛋、熏鱼和白面包……之类的东西哩!
不但如此,一位工作人员还特地从怀中掏出钱来买了一瓶啤酒和一大包花生给我。
一切一切都是和我的意料相反,在当时的我固然不懂得这就是新旧社会的种种根本不同之处,但也在不识不知中觉得事事新鲜,事事奇怪。
尽管这一系列的活生生现实,明明白白摆在我的面前,尽管那些位公安人员的态度作风都是那样温和和亲切,可是做贼心虚的我,依然是把疑团和鬼胎装满了一肚子。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这条命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真是余光已经无几,于是越这样想,心里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觉得心里越发窄了起来。可是载着我们的这列火车,却是无情地不停蓦进着,让人觉得它好像是故意和我为难似的越发加快了速力,就仿佛是非要尽快些把我带往死路不可一般。等到过了哈尔滨之后,这节车厢便又挂到一列快车的后面,小站也不停了,一直向南,向南朝着长春急进着。
我这时越发沉不住气了,真像快要溺死的人,见一根草茎也要抓一把一样,于是便对于坐在我身旁的公安干部大谈其佛学,并驴唇不对马嘴地表示了一些追随日寇乃是自己的不得已的所谓“苦衷”。最无耻的就是我更把我在过去如何捐助罹灾人民的种种陈谷子烂芝麻也都倾了出来,为的是借着它来达到急来抱佛脚的目的。越发接近了长春,我越便由长春这两个字,联想到过去的所谓“新京”,由“新京”又联想到过去的一切一切。于是便由神经极度紧张变成了疑心,变成了兴奋甚至形成幻听和幻觉。觉得周围的空气也都不对头了。例如,看到有些公安人员彼此在小声谈话,便认为这是在谈论自己,看到某些公安战士持枪坐在车中,便又认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在车中对我下手。就是这种春蚕自缚的自我折磨使我差不多成了疯子。当火车在长春停车时,因为听到了唱歌的声音,便认为这是人民在庆祝抓到了汉奸而在高兴歌唱,于是我的神经过敏便达到了顶点。
当入夜睡觉时,由于疑虑的纷扰,形成了幻听错觉的状态,觉得在朦胧睡梦之中,听到有人在讲要对我进行处置;后来又仿佛听得像是有人在骂斯大林大元帅该死,我于是就想:
“骂斯大林岂不等于自求速死!”疯子般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
“谁在骂斯大林大元帅,我要和他决斗!”
因为无人“应战”,又在公安人员的安慰下躺下合上了眼,但是,仍然觉得自己所表示的进步程度不够,便又做出向公安人员“买好”的态度来,根据自己适才的“幻听”,将对苏联没有理解的人,作为“告密”的材料向公安人员讲了,目的不用问,是要表示自己的“进步”,尽管做了如是的丑表功,做了如是的“进步”表示,但仍然认为自己的这条命不见得,不是不见得,而是绝对脱不了危险,便如醉如痴地又做了一连串的丑态,最后在公安人员的安抚下,才抱着闭目等死的心情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从昏梦中醒来时,自己还惊讶自己没在昨夜被杀死,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又活到了今天哩。
也许是由于所谓“良心”的谴责,也许是由于神智的昏迷,曾向同犯某大磕其头,又对同犯某连说对不起你,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就是对于在昨夜由于幻听而成为我告密材料的受害者来做热烈的忏悔;同时又因为看到了一辆公安部队的汽车停在附近,竟认为这就是一辆设有绞架的专用汽车,于是就荒谬地认为:由于我的告密,他们也定将不免,所以才特意向他们叩头企图“解冤”的。
据我弟弟事后对我讲:说在我当时在怕极成疯时,我右颊上的肉和筋都在猛烈抽搐着。并说我曾肆无忌惮地在车厢中来回乱踱,并且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叨念着一些什么,致使他和其他的同犯每当我走到他们身旁时,都低下了头不敢看我……足见我由于怕死而做出的种种丑态是怎样大有可观的了!
当火车由长春开到沈阳时,我的丑态一直没有演完。例如,看见有公安部队在车外排队走过去,便以为这就是准备押犯人赴刑场执行死刑的武装部队,看到车站上乘客们跑着换车,便又认为这是争赴刑场去看枪毙汉奸的……诸如此类,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
当车中公安干部在呼唤我和几个伪大臣的名字,让我们下车时,我就想这更是千真万确的了,一定是要把我们这批首恶的分子押赴刑场无疑。
不过是,除了我和几名伪大臣之外,还有一个例外的人物,就是有我的一个侄子,我就想他也是要陪同我去挨枪杀的。
我当临下火车便对我弟弟溥杰和其他留在车中的同犯高声说:
“再见吧,祝你们平安无事!”
当我上了开进站内的一辆公共汽车之后,看见了手持武器的公安战士在车门附近站着,我就越发认了命了。于是我就在心内说:
“既是‘准死不能活’,我绝对不能在临刑前丢丑。”并在心中预先定下了“临死前的表演节目”——预定要在临刑前,高呼“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清朝第一代皇帝)万岁!”
我认为就是这种濒死挣扎的丑态,也仍然可以看出我那满肚子的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本能来的。真是既卑怯懦弱,又顽固到底,同时还可以看出自欺欺人的阶级本质来。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这辆满载了惊慌失措人群的汽车并没有把我们载到刑场,而是把我们送到了沈阳市内的公安部。下了汽车之后,我们都在命令之下被排列起来,这时我站在后尾,遂命令我站在前面,我便悄悄对我侄子说:
“我带着你去见祖宗于地下吧!”
本来他现在已如同是惊弓之鸟一般,再加上听了我的这种鬼气森森的话,据他事后对人讲,他当时觉得两只腿都吓得发软了。
这时我因为已经横了心,反倒不怎样害怕了。于是就把外衣团成一个乱团团,挟在肋下,在人引导之下,大踏步地进了大厅并上了楼。这时整个大厅的楼上楼下都挤满了人,都在争看我们这一群在东北干了十四年卖国勾当的大罪犯。上得楼来,看见有很多的椅子围着一个长桌,在桌上还摆有不少点心、水果、西瓜、啤酒、新茶和香烟之类。我固然看到了这种当前的现实,觉得和我所预想的种种大有出入,但仍是由于已经认定了非死不可,就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情,拿起一个苹果来,狠狠地咬了一口。我不但是自己这样做了,还劝我的侄子也来学我的办法,但他却没好意思这样地做。
这时,人民政府的首长各位都进来了,我当时也不认识谁和谁。但是首长对我却非常和蔼。可是我则是仍然处在痰迷心窍的状态中,不仅是不明了政府的意图,反倒错误地联想为:
在过去旧时代,曾听说每当犯人被处刑之前,辄给他一顿最后的饮食吃,现在岂不是让我来吃那最后一顿的“送终宴”?
因为我是在这样地想,所以尽管首长劝我可以随便地吃,我仍是难于下咽。并且越是和蔼地让我,我就越发起了一种反感。于是我竟抱着绝望的心情对首长说:
“快走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不必让我吃东西了,要杀我就快些杀罢!赶快把我送往刑场去吧”的意思。
但首长仍然是悠然不迫地和我谈了半天话,例如,问了些我在伪满时的事情以及关于吉冈安直的事情等。并把张景惠的儿子叫了来,使他们父子见了面。然后更把我的族侄宪东等事情和我叔父载涛现在身任政协代表的事情,对我讲了。并说现在宪东等都在人民解放军中给人民服务,甚至还问我想见宪东等不。我在当时因为觉得没有脸面见他们,便说我不想见他们而做了婉谢。首长并耐心地对我讲:
叫我可以安心,不必胡思乱想。并说共产党是为人民办事的,所以共产党对谁都没有所谓私怨,也不做报复行为,并举对蒋介石的事情为例,说他曾对共产党做了残酷的五次围剿,杀害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但是在西安事变时,共产党却为了团结全国抗日力量一致对外的关系,不念旧恶地说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才使蒋介石保全了性命。足见中国共产党是一贯抱定了对事不对人的政策。
并对我安慰说,你们的事情,已是事过境迁,现在给予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改造,并谆谆嘱咐我说,现在政府对你们所期待的,就是要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学习!
当我听到了这种仁至义尽的谈话以后,我才如梦初醒地认识到:
原来我的想法完全错了。
可是我仍然有所不解:
为什么共产党会对我这样的宽大?
二、开始了学习
据说留在沈阳车站上列车中未被指名叫去的那帮人,也都对于我和这帮伪大臣的被唤下车,做了种种的猜疑揣测。就以我弟弟溥杰为例,他说当我们被指名唤去以后,他就想:
伪皇帝和伪大臣中的绝大部分都被叫去了,还不是第一批先处置了他们,然后再对我们进行处理。
尽管列车中的公安干部向他们说,是因为这些人都上了年岁,并且旅途既长天气又热,怕他们身体疲惫难支,所以叫他们下车休息休息去。
可是这帮被留在车里的人,并未信赖这位公安干部所讲的话,他们都认为这也不过是为了安戢人心的一种假话而已。
可是这是假话还是真话呢?终于我们都喜笑颜开地回到车里来了,并把和政府首长见面谈话的概略情形对他们发表了,同时还把从公安部拿回来的香烟分给他们一人一支,这些人都是从回到祖国以来初次尝到解放以后的祖国香烟,所以便兴奋地口里喷着烟圈挤作一团一团地问长问短。
这时车厢里的空气活泼起来了,把自从在绥芬河中苏国境上车以来的沉沉死气,变成为有说有笑的明朗气氛了。特别是张景惠的儿子也来到车上,把祖国人民对于在一个月以前回到国里的他们,所给予的无微不至温暖关照事情,做了简单而生动的介绍,于是在我们这帮人之中,便有人说出了一百八十度转换的得寸进尺的梦呓来了。
某人便得意忘形地在讲:
“抚顺我从前是到过的,我想少时我们到了抚顺之后,一定是先让我们到抚顺市的俱乐部里,先洗一个澡,再换换衣服,然后便可各自回家了!”
还有人兴高采烈地这样附和着说:
“对,对。我知道在抚顺市内还有矿泉浴池哩。说不定还许让我们先洗个痛快的澡,再休养几天哩!”
于是这些无自知之明的人民罪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了成套的连篇梦话来。
不久便到了抚顺车站。
于是这帮忧尽而喜的人便一个一个下了火车,然后更一个一个地分上了来接的几辆大卡车,在前后左右武装部队的森严押送下,穿过了在当时尚未拆毁的抚顺旧城,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时,这些人因为既看到周围设有岗楼的监狱大墙,更被分别领入一排的监房之内,于是乎便又从忧尽而喜转入到喜尽而忧的心情中。
当然,我也并不例外。当我被领入到监房之后,房门便立即“咔哧”一声地上了锁。这时候,我便又狐疑满腹地不安起来了。同时同在一个号内的同犯们,便都在默默无言之中,彼此做了一下互相心会的眼色。
不久,崭新的被褥发下来了,新衣服、帽子和鞋也发下来了,牙粉、肥皂以及香烟之类的日用品等也都发下来了,铅笔、钢笔、墨水以及书刊报纸等也都陆续发给了我们,接着所方便让我们开始了各小组的学习。
五年以来未曾入口的馒头、大饼、饺子、汤面之类都吃遍了,真是餐餐是精米白面,顿顿是有鱼有肉的出人意料的生活。并且每天还在休息时间从扩音机中给我们经常放送京剧、音乐、歌曲的唱片等。尤其是所长以次的各级工作人员,不论是谁对于我们,都是做着亲切的关怀、周到的照顾。例如:不但是大兴土木地给我们修理了暖气并给我们改造了浴池。当修理完成初次让我们洗澡时,因为水管尚未接好,所内干部就一担一担地从远处去挑水。当我看到那位干部满头大汗不辞劳苦地往浴池内放水时,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心情来。在这种说不出的心情中,我觉得是把感激和惭愧的成分都混在一起了。
这时我不由得从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又生出一种随歪就歪的新念头来:
政府既是这样亲切地关怀照顾,又给我学习改造的机会,大概是不会再办我的罪了。说不定将来我还有到社会去做事的可能哩!
在乍一开始学习时,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新鲜的东西。同时有许许多多词句,对我都是生疏的,很多不懂的,特别是最初在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尤其感到如此。因为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有生以来,初次所看到的名词,所以在相当的期间内,就把“抠名词”当作了讨论中的重点。
在乍一读报时,也是如此。也只是由室内同犯轮流地照章宣读一遍,便算是当天的任务完满达成。既不懂得什么是应当作为重点讨论和分析的地方,也不懂得学习报纸的重大意义,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地开始了时事政治的学习。
此外,还学习了“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两个文件。于是,才初步了解旧中国之所以变为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以及过去清朝的封建统治和北洋军阀以及蒋介石政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种种关系。特别是这种新认识的开始获得,才使我渐渐认识到,原来自己在过去所一贯坚持不放的“恢复祖业”的思想,正是使自己给日本帝国主义去充当走狗的主要相引相吸的媒介物。这时,我也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略意义。
但是,这绝不是说,我在那第一次抚顺生活的仅仅两个多月中,就能得到这样的学习成果,我只是说,我开始能够懂得了有生以来初次看到的新社会的人民语言,开始对于“恢复祖业”的牢固反动思想有了一点点和旧日不同的阙疑看法,开始一步一步地认识新事物。总之,这只是意味着我嗅到了新社会新空气的一个最初开端,也就是说,这仅仅是我接受对我启蒙教育的第一步。
在这开始学习不久的时候,便从报纸上看到了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上了陆,致使朝鲜人民军自从开战以来连战连捷,几乎把胜利的旗帜插到釜山的战争有利局势,来了一个差不多一抹到底的大转换。可是我那崇美、恐美的唯武器论旧思想,又重新抬起头来。特别是正在这个时候,所方又突然向我们宣布了移往哈尔滨的命令,并且是在命令刚一发表之后,就让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这就更把我的满腹疑团扩大到最大限度,认为这一定是为了避免美帝的空军轰炸,所以才这样匆促地把我们远远送到松花江北的哈尔滨去。我在汽车上更看到了在沿途有些商店和住宅玻璃窗上的防空纸条,于是更感到一种火药气味,似乎已经飘到了跟前。等上了火车之后,我便悄悄地问我弟弟溥杰:你对这次的移往哈尔滨有什么看法?他也说这一定是因为朝鲜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关系,他并说,他也看到了糊在窗户玻璃上纵横交错的防空纸条。他更满有把握地判断说,也许沈阳以南,不久或将沦为战场也未可知。
于是,我们这批刚刚开始了学习改造的汉奸,便又在胡思乱想的心情下,到了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