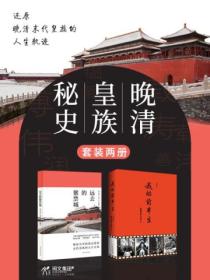第十一章
一、赤塔市郊的莫洛阔夫卡
我由通辽飞到苏联的赤塔以后,天气差不多就要黑了。从东北起程时,所穿的衣服,当快到赤塔的时候,便觉得单薄起来,越往北飞就越觉得寒气加重。这时苏联军官便把皮外套借给我穿在身上,这才使我渐渐觉得有了一些暖意。当这架飞机飞到了赤塔机场之后,便在机场附近停留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坐上了给我们特意准备好了的小汽车,于是两个人一辆车从赤塔市出发,这条小汽车的长蛇阵便驰向愈走愈荒凉的原野。这时,在我们这一行人之中,便有一位不大沉得住气的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是不是要把我们拉到无人之处去枪毙?”
固然这句话引起了车中同伴的笑声,但是在这种比较沉得住气的笑声中,也是含有几分不甚摸底的成分在其中的。等到这些汽车在黑暗中穿过了树林,爬过了小山坡,驶过了平坦的汽车路,钻过了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渡过了木船摆渡之后,忽然一辆辆汽车,便一个挨着一个地停了下来。这时,忽然听到一声很清晰地道的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车在这儿小便!”
我不觉大吃一惊,不由得心中又忐忑不安起来,想道:
“莫非是蒋介石派人来接我的?这可要糟!”
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那位说中国话的人姓李,是个苏联籍的中国人。军队中的阶级是个中尉。这个人一直在赤塔照顾我们多少天,等到由莫斯科派来的专门负责人渥罗阔夫中校到来以后,他才离开我们。
解完手之后,又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开进了一个山环,从这里又走了一段比较宽阔的路,才开到一幢明灯辉耀的楼房前停住。
这时我们这一行人中,又有人小声地说:
“这是一家饭店啊!”
进了这所楼房之后,便有一位四十多岁身穿洋服的苏联人和不少身着军装的人在等着我们,我就想,这穿西装的大概是这家饭店的大掌柜。
这位大掌柜便庄严地向我们宣布说: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进行拘留!”
然后又和和气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在这里住,并指着桌上的一个盛有满满清水的玻璃瓶子说:
“这是这里有名的矿泉,喝了可以增进人的身体健康。”说着就倒了一杯,一扬脖子喝了,并劝我也尝尝。我喝了一口,觉得它的味道和苏打水差不多。乍喝有些不大受用,后来简直爱喝得不得了。在这所风景幽美的莫洛阔夫卡疗养所内,有两种有名的矿泉,一个就是这个含有苏打成分的,对于胃病很有益,另一个则是含有铁质成分在内,说是常喝可以使身体健康。
经过了这位饭店掌柜——赤塔市卫戍司令官少将某简单对携带物品检查后,便在深夜大约两点钟的时候,给我们准备了一顿极其丰美的俄国饭。我们是正在跋涉了好几小时的夜路之后,正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忽然吃到了这样美味,每一个人都像是把刚才的紧张不安以及疲乏等忘了个一干二净似的,而有说有笑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了这顿夜宵之后,便一个个地被分别领到预先准备好了的房间之中,立即躺到那平软舒适的铁**,钻入到轻暖洁净的俄国长毛毯子之中,入了梦乡。
第二天差不多到了九点钟以后,我们才一个个地睁开了眼睛。吃完早饭之后,又洗了一个痛快的淋浴,并换上了所内准备的新内衣,从这天起便开始了有规律的“疗养生活”。
按照苏联当地的习惯,早晨十点多钟吃早饭,下午一两点钟吃午饭,还有一顿午茶(牛油面包等),到了八九点钟还有一顿晚饭。
我们到了赤塔的第二天,因为在我们头脑之中,是有一个“一天三顿饭”的影子,所以在吃完了那顿茶点之后,便认为一天的三餐已毕,所以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脱衣上床睡下了。等到开晚饭的时候,那些照顾我们的苏联姑娘,便来叫我们吃饭,有不少人因为已经躺到**,甚至也有的已开始做着好梦,所以就纷纷说“我们不吃了”,当然这些姑娘很觉得奇怪并扫兴的了。第二天李中尉听到了此事,便笑着对我们说:
“我昨天忘了对你们讲,我们苏联是照例每天吃三顿饭的,你们因为不知道这种习惯,所以昨天晚上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吃晚饭……”
有的人便抢着插嘴问道:
“我们昨天不是已经都吃了三顿饭的吗?加上晚上那一顿,不就是第四顿了吗?”
李中尉越发笑了起来说:
“不是的,你们所说的那个第三顿那不是晚饭,是一顿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的吃茶……”
又有人在抢着说:
“我们不知道那是吃茶,所以就大吃了一顿面包牛油,到了真正吃晚饭的时候,简直是饱得吃不下去了。”
自从经过这次“老赶失败”之后,才习惯了吃茶的事情。
在这两个多月的莫洛阔夫卡的生活中,苏联当局真是对于我们这一帮人,给予了极温暖的人道主义宽大待遇。先就精神食粮方面来说,不但是急急忙忙就给我们安上了广播收听器,有时,还有苏联军官把广播中的事情消息择要地译给我们听。此外,还经常给我们报纸和介绍苏联事情的小册子看。在衣、食、住方面,尽管苏联正当艰苦的卫国战争初告胜利,对日寇的正义战争甫告结束,人民一般的物质生活,还未脱离战争状态的时候,却对我们做了极其丰裕的待遇。不仅衣食住方面如此,就是在医疗卫生方面,也都是做了十二分的关怀,有医生护士,经常和我们住在一个角落内,甚至连牙医、专门治痔疾的大夫等,也都特意从远处接到这里来给我们医治。洗澡理发等等方面,真是专人专职地分别被派到这里来。日用品以至纸烟等,更都是从来就没有缺乏过一次。可是我呢?却是在这种仁至义尽照顾下,仍旧面从心违地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做着专门替自己一身做打算的卑鄙事情。例如,我曾屡次上书于斯大林元帅,求允许我留住苏联,不愿意回国;还在每次写有关自己罪行材料时,不但经常避重就轻,并且一贯地抱定了推搪遮盖的不老实态度,企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蒙混过关。
就拿我请求留住苏联这件事来说,难道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对苏联有了相当正确认识,致愿意永留苏联,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些力量?难道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到反动国民党的反动罪恶,而不愿意回到它的势力下面来?难道是真个地不愿意重回生身祖国的怀抱,而偏偏愿意永住在在一个当时来说一无认识二无情感的苏联国土内?
当然不是的。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厚着脸皮死乞白赖地去做苦苦哀求,简单一句话,就是害怕回到祖国之后,会被治以叛国的重罪。所以既根本不是对于苏联在当时就有了什么憧憬,尤其不是对于国民党的反动有什么在政治上的正确认识,更不是甘心情愿永离祖国而葬身于外国土地之上。而只是为了自己的这块臭皮囊——这个无可原宥的万恶大罪身子,才这样违反恒情去做这样请求的。乍一看似乎奇怪,为什么愿意留住苏联呢?其实是说破不值半文钱的事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怎样违背本心的事情都能够像是变幻术似的在人们面前干出来。除了当汉奸出卖自己可爱的祖国以外,还宁愿在平素毫无认识甚至是一贯抱有阶级反感的苏联内了此一生,不充分说明了我这是为了自己利益的私心吗?另外,由于我那根深蒂固的剥削、寄生反动思想的严重存在,所以我对美、英资本主义的腐朽寄生骄奢**逸生活方式,总是有些留恋,所以在我当时的心中就曾这样想过:
“如果能够被允许留住苏联,首先我的这条命是可以平安保住的;还说不定有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去住的哩。”这就是我要求留住苏联的终极目的。
总之在那个时候,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一不是从为了自己不顾其他的一点自私自利观点而来。当反动统治者失败的时候,在外形上是看不出他的本性来的,即使是怎样奇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都会怡然地做得出来。不是在马列主义科学分析眼光下,是不会也不可能洞烛其隐而把他的反动阶级本质暴露出来的。我真是由于学习改造才真正认识了什么是反动阶级本质,才真正认识了我自己。
固然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为了怕死而愿意留住在苏联,而那帮伪大臣呢?他们也同样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认为他们的罪恶比较小,或者不至于回到国内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所以又产生了另一种看法来。那就是他们认为回国以后,不但不会有性命之忧,甚至还可以借着他们自己认为的“声望地位”,说不定还可以钻着“国共矛盾”的空子,能够捞一把也未可知,于是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三人便代表着这帮伪大臣全体的意见,要求我向苏联当局替他们说说情,快些把他们放回去。不但我对于渥罗阔夫中校曾先后两次把他们的意见反映过,就是他们自身也曾在临离赤塔之前,于赤塔市卫戍司令官的晚餐招待会上,纷纷表示了愿意早得释放回国的心情。当然是苏联当局对于自我以次的这帮汉奸的利害不同而愿望各异的意见,认为是一丘之貉般同样肮脏的东西。既是我的请求永住在苏联是个不屑作答的龌龊事,当然对于他们的“别具慧心”的请求回国,也同样是得不到人家理睬的。
这就是这帮汉奸由于自己的利害不同,而产生出来的不同意见。尽管反动本质——为了自己不顾其他的阶级本性,是同出一源的货色,可是在实际表现上则发生了两个绝对相对的愿望与要求,我认为这件事实中,也可以证明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当反动统治者失败了的时候,在外形上是见不出他的本性来的。
那位渥罗阔夫中校,平日对于我们,当然是在阶级感情方面,把是非爱憎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例如,对于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于这帮伪满的汉奸傀儡,即在他言谈中,也能充分看出了这一点来。但是在对于我个人和这帮伪大臣则是极鲜明地表现出对事不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温暖情谊。例如,替我们准备各人的房间,布置家具,供给我们娱乐用的苏联棋、苏联牌以及钢琴之类,还经常拿来各种的酒菜罐头、糖果等物特别地招待我,还有时带着我们到附近的高峰丛林中去散步,等等。真像是待客那样地招待我们,使我在这段时期中,没有感到过什么不舒服不愉快的地方。特别是他那种豪迈诚恳公平无私的态度、作风,自然使我会对于他生出一种信赖的心情。
二、红河子
到了十月初,赤塔早就变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但是自从我们到了赤塔第二天的各个房间内,便都在早晚烧起了俄国式的火墙,一直在过着室暖如春的生活。到了十月底,渥罗阔夫中校就对我们宣布说:将要把你们送到离中国近的地方伯力地区去。于是我们这一行人,便又坐上了苏联当局特给准备的特别软席带各个单间的列车,携带着极其丰富的旅途食品,前往伯力。渥罗阔夫中校还亲自送我们一直到了伯力市郊避暑别庄地带的红河子,把我们交到当地负责人员手中,才殷勤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和我的侄子们,都情不自禁地和他做了拥抱。
在这个红河子我们所住的房舍,是一所背临乌苏里江江汊子的避暑风景地区。从我们所住的楼上,就可以在夏天远眺那在浩**烟波之间,参差纵横张开绿荫遮盖的群柳,以及翱翔在沙洲之畔往来于金波碧浪之中的钓艇和渡船。还时常可以听到悦耳的黄鹂和苏联青年男女的手风琴和歌声的抑扬合唱。每当明月当空,暮江如练的时候,还可以使人在那江风徐来的楼栏旁,去领略一下饱含诗意的境界。就是到了严冬的时候,也经常在那皑皑无垠、一望坦平的冰雪上去散步。我虽然不会滑冰,但也可以踏着积雪的地方缓步游览。这种生活,不但我在北京时,未曾遇到过,就是在天津以及长春时也是从未领略过的。特别是在夏天时,到江中去洗澡的快味,更是我平生未曾尝到的一个难忘的回忆!
在当时我也曾自己怀疑过:
这就是拘押生活吗?这就是苏联对于我的拘留吗?
在这里负责管理我们一切事务的是一位青年的少校,名叫节尼索夫。他虽然因为兼任着伯力市内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专门收容日伪A级战犯的一个收容所所长,不能经常住在红河子,但也时常到这里来看望我们。特别是到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或是新年的时候,还有时从市内带来酒糖果和种种的饭菜招待我们。日常对于我们的待遇,也是和在赤塔时差不多,后来还有一名中国人给我们做菜饭哩!
不过是,在这里担任屋中院内清洁整理和一切日常生活杂项工作的,已不是苏联的姑娘,而是十名内外的伪满俘虏——大多数为伪满兵士和伪警察等,所以在这里的生活环境,日常空气,便不能像在赤塔时那样的宁谧平静了。例如,有的俘虏则对苏联当局有不平不满;有的甚至和苏联士兵动手打架;有的则企图夺船脱逃;也有的则居然在江边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据说是一个姓董的中将,是为了交涉引渡我们而赴苏联的——私通了声气,致被苏联当局查知,因而对他们分别做了讯问和调动;还有的则装出“跳大神”的样子,来迷惑那些专门盼望回家的人……真是奇形怪状,笔难尽述。
在这里,不但有苏联的报纸经常可以看到,并且还有中文的“实话报”经常拿来给我看。此外,苏联当局还时常地把日帝关东军俘虏在苏联所刊行的日文报纸送给我们看。因此,我对于国际国内的重要事项能随时知道。
不过是在当时,尽管有这样的人道主义温暖好环境,然而我对于祖国正在进行着的人民解放战争,却是一向漠不关心。因为在当时,我对于共产党和蒋记反动国民党同样都是没有什么认识,当时使我最关心的问题,只是自己前途一点而已。我曾认为无论是共产党或是反动国民党谁战胜了谁,反正对我都是没有什么好处,只要我一回到祖国,不问可知,都是对于我绝对不利的。由此而得出结论是:
“唯有留住苏联,才是我唯一平安的道路。”
这种只顾自己不计其他的想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从我那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而来,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一身,至于祖国的前途如何,祖国人民命运如何,在我当时眼中看来,都是漠然不足以关心的东西。
还有在苏联的这段相当长的时期中,苏联当局也是本着启发我挽救我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想由渐而入地使我以次的这一帮大大小小寄生虫中比较年轻些的分子,能够从事于自己生活环境内的轻微劳动,如刷饰屋宇,除草栽花之类的工作——当然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劳动,不过是在我这寄生虫成习的眼中看来,那些不足称为劳动的劳动简直是一种“苦役”了——因此,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在这种由浅入深的善诱善导下,逐渐地改变了一些一贯轻视劳动避忌劳动的旧思想观念,而渐渐地干起收容所小农场的耕种收获工作来了。可是我呢?虽然也同样受到了这样温暖耐心的启发,但仍是由于自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茶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旧习性,仍然是轻视着劳动和过着酷使自己带去的侄子和用人的奉尊处优不劳而食的生活。总之,我在那个时候,成套的反动阶级思想意识和扎根极深的“人上人”习惯,还是完全在支配着我的日常语言行动。所以,像是请求留在苏联,而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以及随时随地竭力替自己的罪行打掩护,并种种数不过来的欺人自欺的心劳日拙行为,等等,就整个概括了我在苏联那几年的生活全部过程。
在这段时期内,我还把携往苏联的一些民脂民膏——由伪满带去的封建统治者的贼赃,珠玉宝石之类,献给苏联。但是这一“捐献”的动机是不纯的,是要想借此买好,达到投机取巧的目的,而把其中好一部分的东西悄悄藏到皮匣箱底,以备日后在苏生活之需。但对于在箱底藏纳不下的东西——许多珍珠,穷于处置,于是就在我弟弟的“深谋远虑”建议下,把这些无法藏匿的余赃珠子使我侄子投入火墙炉中烧毁掉。像是这种献纳动机不纯和毁坏人民财产的罪恶行为,以及隐匿余赃的欺骗行动,从今日回想起来,不仅觉得脸上发热,而且是又一次加重了罪行。
此外,我在当时,还曾费了不少日子,每天从红河子到伯力市内苏联的内务局去,暴露了不少日寇在伪满十几年来的重大罪行。固然在当时,对于自己应负的罪责做了不少的推诿逃避,但总的说来,那些日子的揭发和暴露,也是曾给我后来到日本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做证——为和日本法西斯战犯首魁的当面对质提供了条件并开辟了道路的。因此,我认为对我说来,确是一种值得感到痛快的事情。
在红河子住了约九个月之后,就移到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去了。
三、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虽然在那里收容着有日本侵略军少将以上的法西斯战犯(日寇最后一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都在内)和伪满的那批伪大臣等将及二百余名之多,但是在一起初,仍是让我和我的弟弟妹夫侄子等,另住在楼下的一角内,不和他们混在一起,我就是在院中散步时,也是在另一角落内,过着别有天地的生活。就连我每日三餐也是从不到大饭厅去吃,而是由我侄子等给我端到我所住的房间里来独自享用。因此,在关起我住的房门后,在我的那间居室中仍是由我说了算,我仍然是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而后,收容所当局更指名我弟弟溥杰和我五妹夫万嘉熙二人,轮流给我们这批人讲一些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简明教程和列宁主义问题等的文件。在那个时候,讲的人只是照本宣读,口是心非地在讲;这些听讲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身在而心不在地听着。虽然这样地学习了有一年以上,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认识和收获。
我在当时的每日生活概况是:除了三餐之外,时常静静地念念佛,或是悠然地在院中散散步,有时也有苏联军官等人来到我居室内和我闲谈,后来我也学了最简单的苏联语,有时候,所方当局还特让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把苏联的有名小说等讲给我听。
而那些伪大臣呢,差不多也是在每日三餐之后,不是在院中散步,就是在走廊上摆好桌椅打牌和下棋,甚至还有的在房间内大开其宝局,用纸烟当作赌注来赌。
固然日寇的那些俘虏军官,都是另外住在楼上,但是在院中散步时,则是和这些伪大臣混在一起。所以在庭院中,经常可以听到我国的西皮二簧,乃至昆曲和日本的歌声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莫可名状的骚音;同时也可以看到我国的太极拳、八段锦之类和日本的体操或西式健康法的气功运动,等等。汇合成为一种千奇百怪的人身动态。真是使人大有叹为观止矣之感。
可是,苏联当局对待这批日伪的反动分子,却是始终一贯极其人道的而且温暖的。在这段时期中,我们不独经常有俄文报纸可看,后来还特意给我们订了旅大苏联军发行的中文报纸——“实话报”。每月还给我们多次电影看,广播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能收听得到,后来还曾组织我们逛公园,看足球运动,或是到附近江边洗澡。后来还领我到市内电影院看过电影,也到市内剧场听过音乐和歌唱,还参观过市内的儿童文化宫。那些伪大臣当然也不例外,有的曾参观了博物馆,有的参观了七年级的学校,甚至还有的去看了马戏杂技等。
苏联当局每月还发给我和伪大臣们三十卢布,为的是让我们可以随便购买一些日用的东西,如铅笔、针线、维生素、各种食品等之类,每月差不多还把市内的杂货售卖员叫到收容所内,专门给我们开一个临时的贩卖所。糖果、罐头、牛油、面包、香肠、酒类,甚至连冰激凌等真是应有尽有,随心所欲,购买方便。总之苏联当局对于我们这帮人的待遇,真可以说是至矣尽矣无微不至的了。
尽管如此,可是在我临回国之前不久,我还欺骗了苏联当局,例如,我曾和我的侄子们商议,把私藏在手未做捐献的一些珠宝首饰,为了销赃起见,竟命我侄子把它塞到暖气筒里边,不料在修理暖气筒时发见了这些东西,苏联当局就把它拿出逼问我们这批人,是谁藏的。问到我的时候,我又把死不承认的穷余之策使了出来,给它来一个矢口否认。不过是,在那金银首饰上还打有北京某某首饰店的店号呢,虽然苏联当局也明明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但也未予深究而以不问了之。后来我还使我的用人,把几件首饰扔到房上烟筒内,才算是把那些余赃消灭掉。
这些都说明什么?
一来可以说明我那冥顽不知恩的本质,还可以说明我那怙恶不悛抵赖到底的反动阶级本能,同时还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对于我的人道主义待遇。我思前想后,越发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卑鄙可耻面目,在相形之下更感到苏联对我优厚待遇的恩情。如果是苏联不逮捕了我,我一定会被日本帝国主义残余分子给架到匪巢——东京去,不用问,结果是非得落到蒋介石之手不可。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结果,当然也就是我在当时的下场。当然像我这样卖国投敌的罪魁,是死不足惜并且也是死也不足蔽其辜的。不过是拿我这段人生说起来,再和当前事实两下加以比较对照,那么,我当然不愿意和汉奸陈公博等同走那条把汉奸皮带到棺材里去的毁灭之途,而是深自庆幸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所无的千载难遇的好时代,深自庆幸遇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不然像我这样早就应该不复存在的人类历史上的腐臭垃圾物还能活得到今天——活得到能够有学习改造而争取重新做人的今天?
我敢这样断定说:
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有今日的我。
同时没有苏联的拯救也是绝对遇不到这种唯一无二的重生机缘的。
喝水绝对不能忘掉打井的人,我之被苏联逮捕,是我和日本法西斯强盗永断葛藤的开始。我之在苏五年是我湔涤罪恶开始新生的起点。
没有这一开始的起点,我便不会有这样的今天。我既然感谢祖国人民、共产党和毛主席,我就得同样地感谢苏联。
共产党和毛主席既是我的重生父母,那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便是使我能够重生的慈善“收生婆婆”。所以我对于在苏联五年来的生活,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并且是使我抱有无穷怀恋之情的。
四、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我和日寇甲级战犯的初次“对垒”
我的前半生真是整个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给完全毁掉了。当然,我决不是想把我前半生的全部罪恶都推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身上,而是因为我现在既能在祖国人民的无比宽大恩情,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温暖无私阳光下有了这样的今天,我怎能不痛定思痛地痛恨那自己在十四年中忠实地帮助日寇残害了东北广大人民的罪恶,同时也痛恨那几乎把我一毁到底的日寇!并且还因为现在我既是认清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不独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死敌,也是我前半生中的唯一的大对头。所以我就越发对于在苏联的降魔正义宝剑下,曾经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并且还能得到在日本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和我前半生的死对头做了真刀真枪的对垒,不论是在赎罪上,抑或是在发泄自己的私愤上,都是使我感到了既感激又痛快的千载难逢唯一的好机会。
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苏联政府答应了日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要求,让我往日本去出席国际军事法庭,给日寇侵略我东北的战犯裁判做证。于是伯力地区内务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二名苏联军官,一位苏联翻译员便偕同我从伯力市乘飞机出发。
飞到半途中,忽然遇到一阵大雨,我从机舱玻璃窗口往下一看,只见山峰接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那时因为我不懂苏联话,再加上对于苏联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赖,于是我的老毛病——狐疑症便又犯了:
不是要飞往东京吗?怎么飞了这半天还看不到海?
特别是在飞机中苏联军官彼此之间的谈话,我又听不懂,只好是默然坐在一旁,一边在心里打着鼓,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不料在他们谈话之中,我忽然听到了我仅能听懂的哈尔滨三个字,于是立即把这仅能听懂的三个字,又结合到我的疑心病上,因而不由得又在心中暗想道:
“难道这是往哈尔滨飞而不是去日本?……也许是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之手,怕我害怕,所以才故意说是要让我赴日本东京去做证……这样一来,可就糟了,这不等于前往送死吗……”
就在我这遐思万里、疑虑横生的时候,这架飞机也在空中轻快地飞翔着。
当我这胡思乱想尚未有丝毫头绪的时候,这架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在一个机场上开始降落下来。
这时候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哈尔滨,而是离海参崴八十里地的一个地方。
这时我才化忧为喜地下了飞机,进入了当地海空军人俱乐部的军官宿舍,一共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才开始动身前往海参崴。
从这里赴海参崴的途中,差不多随处都能看到优美风景,我们所坐的这辆汽车不是从滨海的山道上迂回盘行,就是从奇岩怪石图画般的地方钻出钻进。同时,车中的苏联军官等还用手指着一所一所建筑规模巨大而宽阔的疗养院和美丽堂皇的文化宫等介绍给我。到了海参崴之后,风景就越发优美可爱起来。一幢幢的楼房,都是层次井然地排列在山脚和山腰上,这种风景,真是我平生第一次所看到的。
我所住的地方是个六层楼的大建筑物,从那里走到相当的地方,便可以看到碧绿的海波,有规律地翻腾着,此伏彼起的白沫,好像是从那无边的绿色中随时吐出了一团团白雪似的。这时我的种种疑团冰消云散了。尤其是每当想到我这次到日本东京,正是要和那帮日本法西斯头号战犯去做千载难遇的当面对质的唯一良机,因此,我的这颗心也就和摆在面前的大自然风景一个样,觉得真有一种海阔天空的心情。
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共有五个人,这里对于我的招待,也都是异常亲切和优厚的。但遗憾的是,在这里每天早晨都经常有浓厚的朝雾,加之天气又不好,所以每天只能在下午到海边去散散步。我真是每天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能够快些到东京去。可是这个坏天气仍是一天天地在继续着,于是就在这焦躁心情之中白白空过去了。一直过了七八天之后,才由海参崴出发又回到来时所住的海空军人俱乐部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附近的机场搭乘了一架水上飞机,从这里起飞了。
由中午起飞,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就飞到了日本横滨附近的某机场。
当我们这架飞机还没有降落的时候,立时就有几架美帝的驱逐机像是苍蝇一般围着我们飞翔,不问可知那是来做监视的。当我们下了飞机之后,美帝的警察就来对我们做了不少可厌的盘问,并且对于我们的前后左右照了不少张相片,光是办这样所谓“手续”,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机场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由苏联驻东京使馆武官把我们接走。于是我们就住在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所楼房内,一切待遇都是很好的。过了几天之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从事工作的苏联检察长和美国检察长以及蒋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副检察长曾在我住的地方,关于我当证人的事,对我进行了事务上的讯问,像是我国现在著名的法学家梅汝璈先生,就曾在这个法庭内,担任了法官的职务。
我一共出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由上午九点到正午十二点,下午由一点到四点才算完事。
这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终结。费时共达两年半之久,开庭次数共计达八百一十八次,出庭做证和书面做证的人近一千二百名,审判记录多达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判决书的页数也长达一千二百一十三页之多。我就是专门对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东北罪行去做证的。
不论是从哪方面来看,这个国际军事法庭规模都是远远超过了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战犯裁判。固然是在处理战犯的时候,曾受到美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拖延和包庇等,但是它确是不失为国际法律事业上的一种正义庄严大举动。
参加了这次审判的共有十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直接间接受害的。就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
因为在这个法庭上,按照法庭宪章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所以,每个被告的战犯都各自有自己选定的美国籍律师,以及日本籍律师替他们进行辩护。
而美国籍的某些律师当中,我认为他们是抱有一种别具深心的工作目的来替日寇战犯做着辩护的。
我出庭作证时,是把工作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首先我自己先介绍一遍我的履历。
(2)然后由法官发问,我做证言,对于日本战犯的罪行进行控诉。
(3)而后则是日、美籍律师替日本战犯做辩护;并对于我的证言控诉进行质问。
在当时我对于日本战犯所做的证言,主要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战犯们如何侵略了我东北,如何操纵着伪满傀儡政权去统治、奴役、镇压和掠夺东北人民来进行他们的侵略战争,并利用伪“神道”作为思想上的侵略以及我在伪满当时如何受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所派的吉冈安直的种种监视和限制,等等,用来证明东条英机以下的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强盗确是罪大恶极的战争犯罪人。
于是美国籍的某些律师便露骨地袒护着日本战犯而向我做了猛烈的回击。所以在我做证的后半段时期就成为我和美、日籍律师每天做着猛烈的辩论的时期。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籍的律师,曾大发雷霆地对我咆哮道:
“你说日本战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对于中国犯下了大罪的吗?你将来回国后,也还是要受到中国法庭制裁的!”
当时的检察长,因为他所说的话,已经超出了问题的范围以外,并且态度粗暴,遂制止了他的继续发言。
在日本战犯方面,却拼命地把罪行责任往我身上推个不已,而那些日美籍律师就是曾为此而特别大卖力气的。
现当我回想起来,最使我感到遗恨的,就是我在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擒贼先擒王地把头号大战犯裕仁的历史上一贯罪恶,加以尽情地揭发,而舍本逐末地只以东条英机以下的战犯,作为揭发的唯一对象。
固然东条英机以下各战犯,都是血淋淋的大刽子手,但是,在日寇所谓大本营中发号施令操纵全盘的中枢神经是谁?并且穷本溯源,那臭名昭著的“田中义一上奏”一文,是向谁奏上的?而且批准了这一罪恶计划的又是谁?不都是这个头号大战犯裕仁吗?
使我东北人民受尽十四年沦陷之苦的就是他!使我祖国大陆饱受八年余铁蹄**之灾,使我全国人民倍遭烧杀**掠无穷祸害的也是他!同样这个裕仁,也使亚洲各国人民都遭受了侵略战争的灾难,不但如此,就是日本人民,也饱受战争惨祸,无数青年也因为他才当了侵略炮灰,并使日本现在成为美帝战车上的利用工具!
然而裕仁却靠着发侵略战争财,养肥了自己。他所以能够成为日本第一的大资本家和封建大地主,都是由于他历次的侵略战争和一贯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而来。我真后悔为什么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地没有拿裕仁做主要揭露对象,而仅仅把东条英机以下的战犯,作为控诉的目标。
固然我在法庭做证以后尚未离开东京时,也曾想起了这件事,而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对裕仁的罪恶做了揭发,但由于日美反动派的狼狈为奸,未把我这篇谈话在当时报纸上发表。后来我又利用和法国记者会见的机会,也曾做了同上的揭发,至于发表与否,我因又回苏联便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