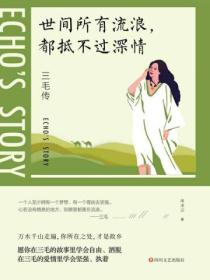流浪无需意义
总有一天她会不再是个女孩子,她会成长,她会毫不逃避的去摸索自己的痛苦,幸福的人会感受到某些人一辈子都尝不到的苦果。
——三毛《月河》
离开家时,三毛的口袋里只装了五美金现钞,外加一张七百美金的汇票单。
这一点微薄的资助,是父母仅能提供给她的关爱。临行前,她缓缓跪下,对着年近半百的父母磕了一个头,她没有流泪,反而是笑着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决然地离开,甚至没有转过身来,对着家人挥一挥手。
母亲扶着栏杆痛哭起来,父亲强忍泪水,他们心里知道故作坚强的女儿有多么难过。
三毛硬撑着,步履从容地上了飞机。其实她心里极为恐惧,此行前途未卜,要面对的是不可想象的艰难。
三毛乘坐的航班刚抵达西班牙时,父亲的朋友来机场迎接三毛,为她安排了住处。
异域求学的日子,开始时殊为不易。语言不通让三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三毛没有认识的人,也无法用熟悉的语言与他人畅快沟通,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形容她“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
可她那么坚强,尽管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家信,收不到信的时候会惶恐、流泪,收到了信便在房间里不停地写着回信,但她从不曾说过辛酸苦楚。
在半年的时间里,三毛始终在不间断地读书。她没有规划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办法做出规划。如果说,三毛离开台湾前的日子是封闭的、自我的,那么离开台湾便是她重新发现世界的一次尝试。在热情的马德里,三毛逐渐与时常厌弃生命的自己和解,也开始将胸襟打开,接纳世界的善意。
谁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啃下来那些厚厚的教科书,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了外语,结交到许多朋友。在正式进入马德里大学后,她终于得空在信中追问梁光明的消息,虽然无法直面这段感情的结局,其实还是挂念他的。
多姿多彩的异域生活,很快让她对世界产生好奇。一年后,她给父母的信已然换了新的内容,她不再苦苦哀求得到更多关怀,而是兴味盎然地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她在信中说,她每天可能是在去上“现代诗”抑或“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课程的路上;也可能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的作品;还可能坐在咖啡馆里,在明媚的阳光下品尝他乡的滋味;又或是与奔放的西班牙姑娘、小伙子跳着舞;甚至搭上便车,随便去什么地方旅行;然后三五同学邀约着去听一场歌剧……
总之,三毛变得不一样了。
三毛入住名叫“书院”的女生宿舍后,楼下开始响起西班牙男孩们浪漫的歌声。三毛这个中国女孩,受到了特别的欢迎和喜爱:最后一首歌,一定是特别指明送给她的。她也会接到来自宝岛台湾的催稿,有编辑惋惜她没有继续写作,但她忙于感受新生活的快乐,只叫人家等着。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或许只能等到她的灵魂实在忍不住倾诉之时,她才肯动笔。
这就是三毛希望拥有的,脱离了父母周到照顾的自由人格。可是离家的自由也要付出代价,首先便是要过好社群内的集体生活。尽管离别时,父母一再叮咛,要忍耐,要有教养,“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三毛想了想,如果忍让只会让自己难过,那还不如做真实的自己。
作为第一个入住的中国学生,又住在四人间里,自然会引来围观。同时,这也是三毛第一次进入集体生活,在家里,她总是被隔离开的。为了让父母放心,她殷勤地汇报着自己正在践行父亲要求的“处处退让”原则,外国学生也并没有欺负她。
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们很关照初来乍到的三毛,愿意教她说话,也会有男同学借给她笔记,三毛也保持着谦恭有礼,温和地对待每个人,一次也没有发过脾气。因为每天早上九点钟要检查内务,所以宿舍里的每个成员都要早早起床,整理好床铺,打开窗户换换空气,扫干净地面上的垃圾灰尘,擦擦桌子,换掉花瓶里的水……
一般来说,这些事情总要大家一起来做的,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三毛开始被迫包揽了这些工作。尽管她提出了抗议,室友们也愉快地答应下来,但第二天仍旧一如既往。
三毛带到西班牙的衣服很多,不出半年,她的衣柜竟然成了“共享衣柜”,每天都有不同的女孩子来“借”穿她的衣服,三十六个女孩子轮番上阵。大家赞美她是“太阳”“美人”,谈笑间打开衣柜,不问自取。
“糖衣炮弹”并没有击倒三毛,她开始感觉到这种相处不那么愉快。虽然中国人骨子里是谦逊有礼的,但也非常保守,注重私人空间。加之三毛没有男朋友,下课之后总在宿舍读书,便更容易成为众人使唤的对象——“帮我收一下衣服”,“帮我熨烫一下裤子”,“晚归为我等门”,“给我留份饭菜”,“帮我卷一下头发”,这些事情无比琐碎,让人不胜其烦。
大家都喜欢三毛,不仅因为她真诚可爱,更因为她简直是众人的“妈妈”。选举学生代表时,大家都高高举起手来投三毛一票,但显然是要让她来做这些杂事。
三毛不由得开始反思:怎么中国人这套“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论,到了西方国家就变成了把人当傻瓜的游戏?
一天晚上,众人违反规定,偷偷喝酒,疯疯闹闹,三毛开窗表示抗议,女孩子们的吼叫声引来了管理院长。三毛被欺负得忍无可忍,抓起扫把狠狠地教训了那些女孩子,也淋了院长一身的水。
三毛这次“发疯”,反倒让那些女孩子对她的态度变得恭敬起来。她们将借去的衣服洗干净,帮她整理床铺,任由她用唱机播放中国京剧,从前那些她被迫为别人做的事情,如今都有别人在做。
三毛思忖着:奇怪了,原来任着性子去做事情反而收效甚大。三毛本来被要求向院长道歉,但她执拗不肯,僵持了一个月之后,这次事件在院长主动邀请的会谈中,终于得到了解决,二人握手言和。
三毛总结出,“有教养的人,在没有相同教养的社会里,反而得不着尊重”。
这些都被写在信中,寄到遥远的东方,父母起初颇感欣慰,但很快不胜其烦,因为三毛有时一天就写一封信,事无巨细都要向父母汇报,还催促着父母尽早回信,以慰乡愁。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给不善表达亲情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个时候,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到来了。
1968年5月28日,这场运动达到了最**,占据法国人口五分之一的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整个西方世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想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
西班牙也不例外,每天到了中午下课的时候,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抗议的学生总是扭作一团,三毛好奇去闹学潮的女孩子们,为什么在谈起到街上游行的时候就如同“上街买了一瓶洗头水一样自然”,可身为外人,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革命也不能耽误考试,在宿舍为期中考试烦恼的学生们,为了能够及格、不被赶出宿舍,只好拼命苦读,念书的愁容随处可见,校园里没有吉他声,也不再有伴着音乐翩翩起舞的身影。
没过几天,因为学潮的关系,大学城里的学院停课了,复活节的假期提前到来,考试被取消了。
整个宿舍里总共三十六个女孩子,这一天,有三十五个都在兴高采烈地打包行李,准备回家。三毛孤零零地看着她们忙碌,内心不由得萌生了感触。她联系了班上的外国同学,谈好分摊汽油钱,开始了为期八天的旅行。
但是因为资金不够,三毛被迫结束旅行,提前回到宿舍,此时女佣人艾乌拉已经离开:宿舍要关闭,不能住在这里。
陷入如此困境的同时,她还要负责照料宿舍的“福星”——小鸟安东尼。
无奈之下,三毛只好又住到劳拉小姐那里。在进入学院宿舍之前,三毛曾经在她的房间住过三个月。尽管时时要操心水、电、煤气的问题,但与劳拉小姐相处还算融洽,这么看来,倒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栖身之所。
谁知刚刚抵达公寓,一只恶猫扑上来,吓得安东尼昏了过去,三毛因为抓猫也受了伤。清晨这只猫又突然袭击,在黑暗中抓着鸟笼往外拖,三毛顾不得太多,惊慌地去抢救安东尼,打开笼子才发现,那只脆弱可怜的小鸟已经断了一只脚。
她心疼地为安东尼包扎,又联系了同学,想要将安东尼寄存几日。没想到,这些人平时可以一起唱歌、跳舞、喝咖啡,但是一说到正事,全都表示拒绝。三毛心里更加苦闷,深感孤单与惶恐。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三毛带着安东尼在街上走了许久,最后还是回到公寓,从早到晚守着这只仿佛被全世界遗弃的小鸟。
他们成了临时相依为命的伙伴。在三毛心里,这不再是一只普通的鸟儿,而是她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第一次付出耐心与关爱的生命。
三毛为安东尼换水、喂小米。三毛写信、读书时,安东尼在阳光下唱歌舞蹈。很快,他们成为彼此心灵的依靠,哪怕回到学生宿舍之后,三毛也经常对小鸟倾吐心声。
可是没过多久,三毛就失去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