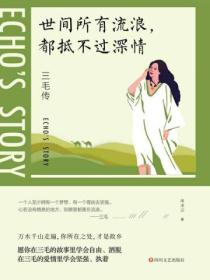人间故事多
我一面站在车内向他们挥手,一面大叫着我无法确定的诺言,就好似这样保证着他们,也再度保住了自己的幸福一般,而幸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就如同永远等待不到的青鸟一样。
——三毛《去年的冬天》
女孩子们以“春天来了”为由,将断过腿的安东尼放飞出去,惹得三毛哭了一场,又因为安东尼杳无音信,渐渐被遗忘。
一场冰雹过去,三毛在废园里的玫瑰棚下看到了安东尼的尸体,再也忍不住颤抖起来。
空气中充满玫瑰的芬芳,阳光下是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三毛的那个伙伴——异域的第一个贴心伴侣,安东尼再也回不来了。
在西班牙读书时,三毛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人萍水相逢,一起喝酒、品尝咖啡、跳舞、高歌,却很少能够走进她的心里。他们仅仅是过客罢了,尚不如小鸟安东尼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安慰。
在马德里,三毛不太安分。她总是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学校生活,尽管她读书非常刻苦,但只要有空,她总要出去走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旅费不足时,她便吃着最便宜的白面包,喝着自来水,只要心情愉悦,口腹享受完全可以抛之脑后。
马德里的旧货市场是三毛经常游逛的地方,那里总有很多“惊喜”等待着她,能得到“拾破烂”的幸福,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城市古老而鲜明的艺术气息。
来到西班牙不久,三毛便迎来了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
她在朋友家第一次见到了荷西。这个男孩子热情活泼,彼时刚刚十八岁,在读高中。荷西的父亲以撒拥有一大片橄榄树林,家境称得上富裕。荷西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上面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他的哥哥夏米叶是个钟爱艺术的人,妹妹伊丝帖真诚善良,都是三毛的好朋友。
荷西的功课并不好,而且家里对子女的学业供给其实非常吝啬,连买个练习本都要看父亲的脸色。当时的荷西还没有蓄起胡子,是个朝气蓬勃的英俊男孩,三毛也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可以做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也该是一种满足了”。可是他们的年龄毕竟悬殊——三毛出生于1943年,而荷西出生于1951年。
荷西带着十四块西币前来,尽管只能在附近影院一起看场电影,也很让人满足;旧货市场里“拾荒”的感觉,从沙里淘金的惊喜中收获快乐;踢球、打雪仗的简单游戏,也能在精疲力竭的同时得到愉悦……
尽管三毛只把荷西当弟弟来看,可是少年荷西并不这样认为——很小的时候他就许愿要娶个温柔的日本新娘,黑头发、黑眼睛、可爱、真诚的三毛虽然不是日本人,但完全符合他的择偶标准。他开始频繁逃学,捏着自己的帽子,在宿舍楼下紧张地等待这个东方女孩。同学们总是嘲笑三毛的“表弟”又来找她,这让她意识到,可能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
荷西爱上了三毛。
这个东方女孩那么神秘、美丽,仿佛有一种魔力。他对三毛说:你就是我理想爱情的样子!有一间小公寓,他工作养家,下班回来,推开门就能见到笑着为他洗手做羹汤的妻子。他请求三毛等一等,六年,只需要六年,他上大学、服兵役,然后就来娶她。
三毛想,相差太多了,不行,必须让这个男孩子赶紧死心。
她对荷西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回去吧。”
在雪夜里,荷西仓皇失落的背影,几乎让三毛软下心来唤回他。但是这份感情太荒谬了,三毛并不觉得荷西是适合自己的人。他还只是个孩子!
为了更彻底地拒绝荷西的追求,三毛很快交了一些其他朋友,其中有一个家境优渥的日本同学。这位同学家里经营着马德里最豪华的日本餐馆,以金钱为资本,向三毛发起热烈的攻势。三毛是庄重的女孩子,只敢收下巧克力糖和鲜花——所以宿舍里每天都会摆放着这位日本同学送来的花。
两人以日语沟通,日本同学很有耐性,对三毛非常疼爱。但是鲜花和糖果不是白送的,不久,他买了一辆新车作为订婚礼物,向三毛求婚。
三毛身边的人都劝她嫁给他,可三毛十分心虚,紧张到流下眼泪:哪里想到收了礼物就要嫁人呢?
日本同学也哭了起来:“不嫁没关系,我可以等。”
三毛慌了,然后又收了德国同学约根送的花。他们一起走在街上,遇到了荷西,荷西苦涩地笑着,故作大方地与情敌握手,亲吻三毛的面颊,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告别。日本同学更是伤心,甚至要自杀。三毛躲起来不肯见面,他就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痴痴地望着窗户,三毛躲在窗帘后面,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对不起”。
其实,这谈不上辜负。三毛很深情,这份深情足以让她看上去不那么凉薄。但并不是每一份爱意,她都能给予回应,或许在相处的瞬间有心动的感觉,但那绝没有走到婚姻的一步。在一段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三毛没有得到更多的指引,有爱也未能令她得到踏实的满足。她还是要走的,要不断地飞行,不停地离开。
为了筹措旅行和读书的费用,三毛在马略卡岛——肖邦和乔治·桑度过蜜月期的那个地方,做了三个月的导游,赚了些钱,体会到了这里的浪漫。
三毛拿着用工作酬劳买的机票去了德国。在这里,她被批准提前住进坐落在邻湖的小树林中、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组成的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
这次前往德国求学的机会,三毛是凭借马德里大学(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到的,目标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哲学系。
在一切都顺利的情况下,语言再次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学校要求她尽快进入歌德学院读语言,一年内如果能够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就可以进入自由大学。
那段日子里,三毛“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她眼中的德国,不过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歌德学院的学费昂贵,课程安排也非常紧,每天除了保证上课的五六个小时外,还有大量的功课和背诵内容。三毛每天要花费至少十六个小时努力学习,极为艰辛。
为了早一点对父母辛苦的供读有个交代,加之本就好强、不肯服输的个性,三毛在课业上从不懈怠,凡有考核,必求满分。三个月过去,曾经连“早安”都不会说的她,最终拿到了“最优生”的成绩单。
邮寄了成绩单之后,三毛激动得流下热泪,那咸涩的泪水里,除了满满的成就感,还饱含着每日以饼干、黑面包泡汤度日的辛酸。
三毛变得懂事,这与她年少时的叛逆并不矛盾。或许敏感的孩子总是容易激动,但这并不妨碍她心疼父亲为养活一家人付出的辛苦。独在异乡,除了凄苦孤单的悲凉心情,还有经济拮据的压力。
三毛说:“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等于是吃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所以她加倍努力,将物质上的欲望降到最低标准,希望早早达成学业目标。
很快通过初级课程的三毛,因为过度透支和努力,被老师心疼地劝说休息一阵再继续学习。但三毛怎么肯呢?生活费只有这些,如果停下来不读书,也要开销,所以她咬着牙,坚持继续攻读中级班。
随着课程的升级,难度也越来越大。即便有着擅长的德文配音科目,这也并没有减轻三毛的压力,听写时一千多字的报纸文字错了四十四个,这样的成绩令她号啕大哭,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物质上的匮乏,也让三毛过着窘迫的生活。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修补鞋子。时值冬日,三毛的鞋子穿脱了鞋底,还有一个大洞,因为上学路上要踏着雪,所以穿着两双毛袜还要套上塑胶袋,因为要等公交车,鞋子外面还要再包上一层袋子,然后用同色系的橡皮筋勒紧鞋底、鞋面,只有这样才能防滑。
进了大学城,遇到同学之前,爱面子的三毛便需要取下外面的塑胶袋。这样一来,走在路上,别人便看不出这是一双坏掉的鞋子。可破洞总是要渗进雪水的,进了教室,三毛便急急忙忙在暖气旁边坐下烤脚,但终究不可避免地生了冻疮。
同学们不知道她的苦楚,只当她爱美,零下十几摄氏度还不肯穿暖和的靴子。她们哪里知道因为鞋码太大,三毛在柏林根本买不到合脚的鞋子,定做又是一笔负担不起的费用,也不愿向父母讨要这笔钱,只好这样将就着,期盼着寒冬早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