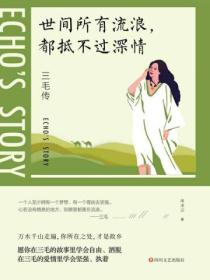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只要我们记得,没有一件事情会真正地过去。
——三毛《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宿舍的集体生活也并不愉快。初入大学城,听说宿舍是男女混住、每人一间时,三毛还是很高兴的。没有室友也没有管理员,似乎是独立自由的,自己为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负责。
三毛的房间在整条走廊的倒数第二间。她入住后不久,一个冷冰冰的金发冰岛女孩便搬了进来。这个女孩对三毛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却对男同学格外亲热,可三毛并不在意,毕竟她正苦读德文,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有心思关注这位室友了。
起初,冰岛女孩经常外出,夜里很晚才回来,基本上没有打扰到三毛。可是两三个月之后,女孩的男性朋友们总是在隔壁房间喝着啤酒狂欢,放着嘈杂的音乐,兴奋的尖叫声时不时响起,严重干扰了三毛的夜读。
一天夜里,在与三毛共通的阳台上,冰岛女孩与朋友裸奔,三毛终于忍无可忍,敲响了隔壁的房门。被允许进入后,三毛面对着**的三男两女,要求他们放低音量,却被推出门外。
三毛知道,与内心忠厚的西班牙人不同,这些人并不听劝。于是,三毛破天荒地旷了课,去寻求学生顾问的帮助。这位中年律师提出,并没有其他人投诉冰岛女孩,拒绝了三毛的请求。
既然需要证据,三毛很快准备好了录音带,要求学生顾问解决问题。一个星期之后,这个不安分的室友搬走了,三毛的生活又恢复了从前的宁静。
三毛身在他乡,孤立无援。虽然也有“中国同学会”,但因为三毛并不是从中国直接到德国求学,而是从西班牙辗转过来的,并且她当时交往的男朋友约根又是德国人,也没有时间参加集体活动,所以极少来往。
加之国人不但不能给她安慰,反而在背后议论她很不“中国”。他们谈论她来自西班牙,穿着漂亮的裙子,与隔壁同学争执,有个德国的男朋友。三毛忍了又忍,对待自己的同胞,她总能克制住暴躁的脾气,却在心里暗暗不忿。
三毛这位德国男朋友约根,也未能给三毛更多温暖。德国人骨子里的严谨认真,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求学时代,约根便以成为外交家为目标,日日苦读,撰写论文,最后的确实现了理想。
他绝对不肯将时间花在风花雪月上,睡觉时都要在枕头下放上录音机,播放白天读过的书,争取在梦中温习一遍。与三毛约会时一同念书,不可以讲闲话,更不可以说笑。而且,即便是这样的约会,也不是每天都有。虽然都住在宿舍村,但是只有当德国男友将台灯移到窗口,发出约会暗号的时候,三毛才被允许进入他的房间。
在那些向窗外张望的日子里,三毛坚守的是爱情吗?那可能并不是爱情,而是陪伴。
约根希望拥有的是配得上他未来外交家身份的妻子,当他看到三毛的听写成绩后十分不满,责备三毛一番后,还埋怨道:“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1)
三毛当然不会再忍耐,难道就那么稀罕做你的夫人吗?道不同,分道扬镳也罢。三毛奔过雪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湿到了膝盖的长裤和浸透雪水的鞋子放在暖气上烘烤。
三毛拿起笔,想给家里写封信,诉说这场不如意的考试以及对前途的困惑,可是写到中途又茫然地停下,不知道如何写下去。窗外猫头鹰仍在怪叫,让她连窗帘都不能拉开。静谧的夜里,三毛做完功课,准备睡觉之前,拿起那些绑鞋子的橡皮筋准备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再用,突然悲从中来,伏在床沿哭出了声音。
那是1969年的12月2日,她很清楚地记得。
她开始思索:这条路,终究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布满荆棘,还是覆盖白雪。自己在追求什么呢?在这样难以言说的艰辛中,自己执着寻求的、努力追赶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德国男友身上,自己是得到了爱,还是安全感?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是拥有了希望,还是理想?
三毛开始产生疑惑:自己怎么会放弃家中的温暖舒适,来到这个冷漠的国家受罪?现在的痛苦,较之小学、中学时代在学校遭受的屈辱,哪一个更让自己难堪?
哭得太累,冷得太甚,伏案太久,让三毛得了备受折磨的神经痛,但生活和爱情仍然未能给她一个答案。
第二天,三毛起床迟了,抓起书本就跑向公交车站。路上只觉鞋子一开一合,原来是忘了扎橡皮筋。神经痛更是作怪,导致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瘸一拐。
一定已经错过了第一节课。但站在路边的三毛,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些痛苦究竟所为何来。然而,这样长久地站下去绝不是办法。三毛骨子里的悲观早就压抑不住,她想着“死好了,死好了”,然后就那么决然地奔向柏林墙。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被一分为二,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则被美、英、法三国占领,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柏林也因此被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1961年,苏占区(即民主德国)修建了柏林墙,阻止东德居民向西流动。
三毛在西柏林求学,要办理过境手续才能去东柏林,这样一来就要接受毫无人道的排查。原本计划好的圣诞假期旅行,被提前实行。与同宿舍的男生约定好,为了省一张机票钱,在边境上要排很久的队,而三毛的身份是中国人,当时用的是台湾的旅行证件,很难被认可,一开始就会卡在签证问题上。
然而,三毛忙于学业,哪里有时间去解决过境签证的问题呢?巧的是,她这时被病痛和压力折磨得神志恍惚,索性决定择日不如撞日,就此在树丛雪地里埋下书本,带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美金和旅行证件,到了东柏林的关卡车站,去办理过境的签证。
在这里,如果西柏林的居民提出当日往返的申请,还是可以通过的。然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被允许到西柏林这边来。排了许久的队,旅行证件和申请表格被东德的文职军官收上去,等待问询。三毛如坐针毡——一方面是坐骨神经实在痛得厉害,一方面是总觉得有人透过办公室的窗子观察自己,如芒刺在背。
三毛十点多从宿舍出门,等到了一点多才被广播叫到名字。台湾旅行证件果然不被承认,三毛拒绝了问询军官提出的参加旅游团的建议——她没有那么多钱。三毛在车站随便走来走去,以观察人们脸孔透出来的故事为乐。不去就不去了,反正是逃学,死都是无所谓的,去不去东柏林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在这时候,三毛感受到的被观察的那股感觉越发强烈起来。她转过身,看到了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那样帅气逼人的青年军官。
这人长着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他帮助三毛拿到了临时通行证,送她过了关卡。在东柏林凄凉萧瑟的街头,他夸赞三毛的美,告诉她,再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见不到面的。三毛没空想太多,过了那道防线后,来到东德的外交部。那本来自台湾的旅行证件,仍被当作新奇物件传看。
三毛拿到签证后,顺便看了展出的越南战争的照片。猎杀者炫耀着他们的战利品,令身在异乡的三毛顿生“亚细亚孤儿”的悲哀。看不得饭店里茶房卑微祈求的笑容,三毛大方地支付了十美金,可心里仍旧憋闷,书店里齐白石的复制品吸引她驻足欣赏,可复制的终究不能带来水墨的美感。乡愁此时满溢出来,让本就昏沉的天空更加幽暗。
返程出关时,检查格外严格。也不知经过怎样的流程,原本以为永不再见的那位青年军官出现了,他接上三毛,送她回到车站。三毛不肯上车,不愿告别。谁都没有说话,黑夜已经淹没两个人的面孔。只有那双眼睛,似口深井,恍若恒星。风吹过来,带走温暖的体温,撩动纷乱的长发,最后一班车,既然已经觉得生命无望,那么……走吧,一起走吧!
三毛疯狂地叫起来:“你跟我走……”如同夜奔的红拂拉住将军的袖袍,仿佛绝望的祝英台扑向梁山伯的石碑。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三毛是西柏林的留学生,他是东德的军官,两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一起远走高飞。
是灵魂在震颤着共鸣,还是那陌生人给予的温暖太过诱人?三毛与生俱来的冷静与感性,交织成冰火,让她终于病倒。被送进医院之后,心如死灰的三毛并没有得到男友约根的探望。如果说爱情是两个不完整的灵魂的结合,那么三毛缺少的一半,如今看来并不是那位未来的外交官先生。
凄冷的病房里,三毛木然听着枯树枝头乌鸦的聒噪,心里默念着不为人知的名字,被人问到是不是去过东柏林,那时的她可曾流下冰凉的泪水?
(1)引自《倾城》,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