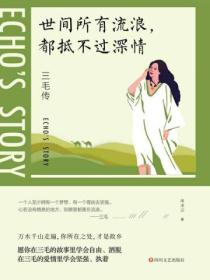永不止息的飞行
难道在我的一生里,熟悉过怎么样的风景吗?没有,其实什么也没有熟悉过,因为在这劳劳尘梦里,一向行色匆匆。
——三毛《梦里梦外》
对于每个努力的人来说,刻苦都是成功的筹码。
约根如愿以偿进入了外交部,那是在他们交往两年后了。刻板的约根没有求婚,带三毛去了百货公司,问她喜欢哪个颜色,然后就买下了那条双人床单。
在冰天雪地的柏林街头,他们没有对话,也没有拥抱。三毛想发脾气,最终却噙着眼泪保持沉默。直到退掉床单,约根问她是否“确定不要”,三毛才开口回答“不要”。在餐馆吃饭时,约根突然哭了出来。
一年后,当三毛即将登上前往美国的飞机时,约根又问:“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他等了吗?等了,他一直在等,甚至不远千里追到了台湾,可三毛坦诚地对他说:不要了,你是大使,每天要参加宴会、与人应酬,而我不喜欢这种事情。做朋友的时候还好,可以无话不谈,但论及婚姻,仍旧是“不要”。
二十多年后,约根还在等,等那个永远不会答应的女孩说一声“好”。这段感情仍旧没有谁辜负谁,连相爱的标准都不同的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在西柏林只学习了九个月,三毛就取得了德文教师资格。可为这正统的柏林口音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不如拿这时间好好了解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段风情。在柏林也并非毫无意义的,深夜街头飞驰的机车,毕加索的画展,都是德国给她的弥足珍贵的回忆。
在德国时,为了赚钱,三毛也会去打工。化妆品公司招聘外表靓丽的日本女孩做香水模特,三毛不解,为什么偏要日本女孩呢?虽然不满足要求,但三毛还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寄过去十几张彩色照片,竟然顺利拿到这份工作。为了两百美金的生活费,三毛在百货公司卖了十天的香水,没有骄傲的感觉,反倒是工作的艰辛和被“展览”的羞愧,让她难堪到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德国并非没有艺术,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需求远比欣赏艺术更重要。三毛无法停留在这样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里都没有她想要的东西。
这时,她得到一个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主修陶瓷的机会,于是,三毛再度提起行李出发。
三毛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但他们并不同意三毛离开德国,毕竟没有一技之长,在美国也是活不下去的。
的确,三毛在刚到美国的一段日子里,应聘工作并不容易。她步履沉重地走在路上,头压得很低,感觉前途是那么渺茫。一位陌生的金发青年递上一棵青草,拍了拍这个亚洲女孩的面颊,说着“快乐些”,然后揉乱了她的头发,微笑着送上鼓励。
那是三毛“到美国后第一次收到的礼物”——一棵柔嫩、普通、随处可见的小草,三毛心里万分感激。在遍布迷雾的异域生活里,这份简单的安慰和鼓励给了三毛莫大的力量。在人世间,活着是多么美妙,似曾相识也好,擦身而过也罢,都值得感恩。
到美国一个月后,三毛在学校的法律系图书馆找到了工作。但她的经验还是不足,第一天的工作就闹出了笑话,为两百本书的书页盖上了错误的日期:10月36日。
三毛稳定下来后,才跟堂哥通了电话,还得到了堂哥正在本校读博士的朋友的照料。每天中午休息时,那位朋友总会送来午餐: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点水果。他对三毛十分关切,偶尔也会忧伤地问起她,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堂哥不断地劝说三毛,不要错过这个踏实的好人。
可是,爱情是被照顾就能发生的吗?心存感激就要嫁给他吗?
三毛初到美国,第一个住处是朋友事先帮忙租下来的、与两个美国女生合租的木房。三毛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用钥匙打不开反锁的房门,只好用力敲打。屋里或坐或卧着一群男男女女,一个个**着身体,身上涂着银粉,吸着大麻,焚着印度香,不时敲响铜锣,像极了某种仪式。虽然不像西班牙求学时隔壁邻居那样扰人,但终归不是同路。
住满一个月,三毛便搬到了一个小型的学生宿舍,习惯夜读的她以为终于找到同类:对间的女孩正在读教育硕士,几乎每天都非常勤奋,打字到很晚。等她停下来,四周安静了,三毛才能就着台灯的光看上一会儿书。
然而,当你不去计较别人带来的麻烦时,恐怕反而会有以怨报德的事情出现。那位女孩埋怨台灯微弱的光亮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影响了她的睡眠,这让三毛既诧异又无奈。忍让是决计不会的,三毛在这个自私的女孩面前关上门,告诉她:你可以继续打字来“惊扰”我,正如我的灯光“惊扰”了你。
异乡数年,经历过病痛和贫穷的三毛变得更坚强,也更独立了。可是在感情上,她还是那么羞怯和纠结。听说“恩师”顾福生来到芝加哥,三毛无论如何也要去见上一面。在纷飞的大雪里,三毛抱着故人重逢的冲动和牵挂,乘坐火车奔赴芝加哥。只是,深夜抵达的三毛,住进旅馆后却开始犹豫起来。
三毛突然发觉,自己没有变得更好,那么在见面的时候,又该以怎样的面目寒暄呢?绘画没有坚持下去,写作也停了下来,一别十年,事业没有进展,“爱情也没有着落”。自己该说些什么,或是聆听什么?
这种复杂的感受,让她改变了主意。
虽然冒雪而来,虽然满腔思念,可是,如果重逢是相顾无言,又该如何面对呢?谈不上无语凝噎,也不必兰棹劳歌,如果彼此深深了解,那么这些形式反而显得矫揉造作。
算了吧,就当没有来过,我没有,你也没有。
三毛在窗前等来了天明,然后整了整衣襟,乘坐火车离开了雪花纷飞的芝加哥。
在爱情方面,除了堂哥介绍的照顾三毛的博士之外,还有很多倾慕她的男生。法学院的男生请她喝咖啡吃甜饼,又开车带她到湖边,打算来一场浪漫的露水情缘。三毛坚定而坦**地拒绝了他,表示不会再接受邀请,然而却被这个男生要求分摊咖啡店的消费。
三毛感慨,这就是美国,“真是不同凡响”(1)。
其实三毛对美国并没有偏见,也许她遇到的一些美国人恰好的确“有趣”。朋友卡洛会把吃不完的洋葱圈分给三毛,付账时也要她分担账单。对三毛照顾有加的中年夫妇希望“收养”她,让她永远与他们在一起,不必结婚和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就能获得一大笔遗产。
三毛不需要钱吗?并不是。她在德国求学期间,生活费并不多,所以吃肉都成了奢侈的事情。到了美国,她有了工作,也会把赚来的钱寄回家,给小弟支付学费,虽然只有一个学期,但是足见她的责任感。她很清楚,有钱能做很多事情,可这并不代表钱能买到一切。
三毛冷着脸拒绝了这份“好意”,然后不由得反思起来。究竟是她太过柔顺以致让所过之处的外国人都要欺负一下,还是她所遇到的都是包藏祸心的坏人?物质上如此富裕的人,“人格上可是穷得没有立锥之地”。华夏文明的温良恭俭让,这一刻都显得那么可笑,自己的教养终究没有办法换回应有的尊重,真让人失望。
虽然通过了公务员考试,但三毛并未从美国的生活中找寻到快乐。带着文化大学的工作邀约,三毛又要踏上旅程了。
那位一直对她关爱有加的博士,送她搭乘前往纽约的飞机。她要去看看堂兄,然后再回台湾。那位博士直白地**心迹,向三毛求婚:你当然可以回家去的,等到放假的时候,我就去台湾找你——三毛没有回应他,只是伸手替他整理了衣领:“你很好,但你不是我要结婚的人。”(2)
她渴望简单地活着,感受心脏的跳动和灵魂的战栗,而不是在纠葛的关系中左右逢源。
活着,是依靠对未知的体验,感知真实的存在;活着,是脚底真切地感受到木地板的粗糙,是手指真切地触摸到砂粒的坚硬,是咸涩的海水涌入唇齿之间,是凛冽的寒风吹皱了眉心。
有痛苦,有愉悦,有慨叹,才是真正活着。
要么,从空寂的梦境中解脱出来,要么,以行尸走肉般的麻木永恒地睡去。做人世的土木偶人,不是三毛的意愿。
(1)引自《西风不相识》,收录于三毛作品集《稻草人手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2)引自《求婚》,收录于三毛作品集《闹学记》,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