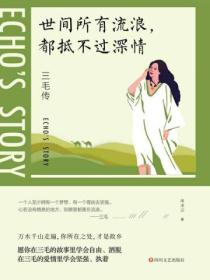时光里的隐约耳语
这些都不是很正确的看法。好在,别人如何分析我,跟我本身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三毛《白手成家》
三毛将这次行程称为“第二次归去”。在她心里,祖国大陆才是她真正的家乡。
1990年春天,在看过震撼人心的兵马俑之后,三毛途经万里长城来到敦煌,在飞天壁画前又一次体验到了灵魂出窍的感觉。上一次出现这种感觉,还是在中南美洲之行中,身处同为高原的厄瓜多尔的安第斯山脉。
对祖国文化与历史的痴迷,三毛不止一次在文字中体现出来。而对她来说,感受到的比表达出来的要更多。她的感受性太强,身体已经无法承载强大的灵魂,无论是来自秦朝的兵马俑还是修筑了千年的长城,对三毛来说,她不是以游人的心态在欣赏历史和传说,而是以游子的心情在感受母亲的脉搏。
大西北给三毛的感受,是类似撒哈拉那种熟悉的苍茫感。三毛听着“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罗大佑《恋曲1990》),又一次进入了幻境之中。她仿佛在不同时空中穿梭,恍惚得厉害。见到的人与听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前生今世的种种猜测,竟都感觉真实起来。
在干燥的寒风中,三毛感受到灵魂的痛楚,那是深刻的被撕裂又被粘合起来的感受,清晰得使人不由自主地战栗,她形容那是爱情。在敦煌,三毛对时光的终极探索已经走到结尾,“我的生命,走到这里,已经接近尽头。不知道日后还有什么权利要求更多”。
整个过程带来的感受是无法言喻的,三毛说:“那真正的神秘感应,不在莫高窟,自己本身灵魂深处的密码,才是开启它的钥匙。”(1)
这是永恒的归宿,这是灵魂的安憩之所。从前的她,随着母亲一起去做礼拜,跟着公婆去望弥撒,现在她匍匐在菩萨脚下,仿佛聆听到慈爱的教诲。神的存在意义是安慰和指示,为人提供解除痛苦的方法。三毛一直追求的和笃信的,是生命终极的完结点,归彼大荒是人世美梦的结束和开始,也是肉体的“好了”。
三毛感觉这里就是“大荒”,所以她拜托此行遇到的最令她感到熟悉的朋友伟文,“这也是我埋骨的地方,到时候你得帮忙”。现在的敦煌,这片她永恒的灵魂栖居地,那座荒野里看似凄凉的土馒头,深藏着游子对大地的眷恋与执着。
接着,三毛去探访了王洛宾。三毛自己并没有记述这次探访的过程,只是匆匆一面,媒体的报道和人们的猜测却甚嚣尘上。
分别后,三毛给王洛宾写了信:“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
在新疆,她找到了世界上另一个自己的灵魂,她在撒哈拉追求的,与王洛宾在新疆追求的,岂不相同吗?他们都为情所困,苦苦地守着逝去的爱情。在第一次见面后,三毛感觉自己遇到了同类。
可是,在人们的耳语中,她的“爱”被解读为恋慕。究竟有没有爱情,三毛的姐姐陈田心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三毛接受东方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开明思想的影响,在她的书中,曾经也提到羡慕西方人能够大大方方地表达爱意。拥抱和亲吻并不是爱情的专属,而是想念和爱重的体现,“爱”这个字也并非爱人之间的专属。
三毛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从小唱王洛宾的歌,现在却能认识这个人;王洛宾的年纪很大,所以她把王洛宾当作长辈。她谈到的爱,与对父母、姐弟、朋友的并没有分别,是一种情感上的互动而已。外界的传播和添油加醋,让这种单纯的欣赏变了味道,也让三毛与王洛宾之间产生了误会。
她原本想在新疆多停留一阵子,可是当时相处的感受并不好——她还没下飞机,记者们就蜂拥而至,加上相处的时候,王洛宾也要随时接受媒体的专题采访,记者甚至想要让三毛加入“摆拍”。这让本身就不喜欢这类活动的三毛非常厌恶,甚至在吃饭的时候大发脾气,说出“你想饿死我啊”“我要杀了你”这样的话。
三毛在歌曲专辑《回声》中说,她“一直在告诉自己,如果能够再活一次,天上的繁星不会总是挂在北天寒冷的地方。星星们总也挤在天的一角,即使一再跟自己说,如果再跨出一步,可以看见温暖的南十字星,而我不能”。
她没有爱上王洛宾,只是单纯认为自己找到了知音。
她第三次踏上大陆的土地,除了这次与王洛宾之间不够愉快的会面外,还选择了祖国西南的路线,去成都、重庆,她本就应该去出生的地方走走。
摄影师肖全陪同三毛走过这一段路。他看着她像个当地人一样,在街头巷尾游逛,长发披肩,举止洒脱。她像许久没有归乡的孩子,一路上与乘凉的老人打着招呼,看着孩子结伴游戏,听人们谈起古老城市的传说。她说自己是重庆人,因为本就出生于重庆黄桷垭。在记者的采访视频中,三毛笑得动人,她说成都是“与众不同的温柔之地”,还说“谢谢成都同胞给我这样有爱的接待”。
在西藏,三毛并没有尽兴。她很快就因为高原反应进了医院,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医生给出的体检结果是轻微脑水肿和肺水肿。这种健康情况实在不宜多作停留,三毛很快离开,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一年的中秋节,她是在上海与干爸爸张乐平一起度过的。他们仿佛真正的一家人,记者在此拍下了一张又一张其乐融融的照片。
三毛在杭州约见了倪竹青夫妇,匆匆见面之后又是别离,谁料原本约定的再见竟成永别。与叔叔的感情是从小建立起来的,作为与大陆为数不多的情感牵系,三毛无比珍视他们之间的情谊,她将倪竹青特意为她题写的“侠义襟怀堪自怡,骨奇气灏意难羁,柔肠淘尽千江水,情寄文坛志不移”珍藏起来,又把他画的一张“墨竹”发表在台湾《明道文艺》上。
回到台湾后,三毛参加了金马奖颁奖典礼,不料却失望而归,这让她情绪大为低落。不久,因为身体不适,三毛再度住进了医院。入院三天之后,三毛去世的消息见诸报端。
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在采访中提到,女儿并非因严重的病情住院,1991年1月2日手术后,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3日晚上,缪进兰曾经接到女儿的电话,三毛急切地说着什么,但那一切似乎都是幻觉。三毛一向睡眠不好,曾叮嘱不要医护人员来打扰。
因此,当这一晚过去,病房的门再度推开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三毛的遗体:以尼龙丝袜吊颈,身着白底红花的睡衣,现场没有遗书。
法医鉴定,三毛的死亡时间为1月4日凌晨2时左右。
倪竹青收到三毛1月2日写来的信,提到自己的心情,她说“非常累,写不动信”,癌症已经蔓延到身体很多地方,“下半年没法工作了,手边有四个剧本也不能做了”,“人生一场,劳劳碌碌,也不过是转眼成空”。
三毛似乎在作结论,又似乎在剖析自己的性情:“我内心不是没有感到孤独,但我丧失了去爱一个男性的能力,这真是一种深悲。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在情感上,尤其在男女的感情上自律很严,非常冷静。”她知道父亲对自己是了解的,恐怕也深信父母能够原谅自己的不告而别。她还说,“寿衣”应该很好看,应该做几件放着。
白先勇眼中的三毛,永远是那个“穿了一身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闺秀打扮,在人群中,她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惶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听到她去世的消息,白先勇却说:“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个拒绝成长的生命流浪者,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2)
杏林子、张拓芜素与三毛交好,是“铁三角”。杏林子常年坐在轮椅上,是积极进取的残疾作家,张拓芜则原本默默无闻,军旅出身,因三毛读了他的书,在报上发表了书评,他才逐渐被关注。这三个人中,三毛最心软,张拓芜经历最丰富,杏林子最坚强。因为不忍心看到杏林子为疾病所苦,三毛曾经出主意,说如果实在忍不了,就给杏林子一颗毒药,责任由她与张拓芜来承担。张拓芜当即表示不愿承担这个责任,杏林子则坚决反对:“我还没活够!”(3)结果,最健全、最年轻的三毛竟然最早结束了生命。
对此,杏林子在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之外,还表达出对她自杀的不满和批评,认为她不该伤害家人,这样的人生态度实在不该效仿。
三毛的猝然离世,在司马中原的意料之外,从大陆回到台湾之后,他原本是要设宴为她接风的,谁知她竟然离开了,让自己这一生都欠她一顿饭。可他也认为,“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4)。
王洛宾听到三毛去世的消息时,比其他人晚了一些。这位老人起初并不相信,确认后不顾健康,大醉一场,醒来后写下那首《等待》:“你永远不再来,我永远在等待。”(5)
痖弦在回忆三毛时说,她“就像一个光源,她希望普照到每一个角落,一个热源,她想把温暖分给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6)。那种对待陌生人的慈悲与真诚,是常人很难想象的。他不相信三毛是自杀而死的,更愿意接受她是因为过度劳累,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永远沉睡过去了。
三毛去世两天后,远在大陆的徐静波收到了一封寄出时间为1990年12月29日的信,信封里是一枚礼卡,上面是原本印刷好的祝福语,以及三毛亲手写上的“谢谢你”。
接到三毛于1月1日清晨2点写的信时,贾平凹已经得知三毛去世的消息了。贾平凹是三毛非常喜欢的作家,本已约定好见面,三毛还要他借一辆自行车给自己,在他笔下的商州好好转一转。贾平凹把作品寄给三毛后不久,没想到对方却失约了。在《哭三毛》中,贾平凹说:“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书,是她的魅力。”(7)
上海的张乐平一家闻讯哀不自胜,三毛是他们家庭的一员,接触虽短却情谊深厚。张乐平想念着自己的“女儿”,他说:“春节一天天临近了,大儿媳早就准备好一件中山装等她回来试穿,全家人仍在执着地等候,过节的时候,有一个座位将留给三毛,因为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三毛是永生的。”
旅行家、媒体工作者眭澔平是最后接到三毛电话的人。他与三毛相识不过一年,因采访结缘,因志趣相投成为密友。三毛3日晚上给他的电话留言听起来是迫切的需要,又像是自言自语:“我是三毛,你在不在家,人呢?你不在家。好,我是三毛。”
2日的时候,眭澔平与三毛还聊过未来的打算,她说新的一年要写剧本,她让他帮忙寄出写给大陆作家贾平凹的信件。三毛将一封信夹在《滚滚红尘》中送给了“小熊爱人”眭澔平,她说,“我走了,这一回是真的”。她走得洒脱,但是眭澔平责任重大。
失去“同志”的眭澔平成立了三毛纪念馆,还踏上了漫漫征程,用二十年的时间踏遍地球上近两百个国家,他说:“在旅行的时候,有一种特别感觉,像是在接续她的脚步,完成她没有走完的旅途。”(8)
每个人都爱她。
(1)引自《夜半逾城》,收录于三毛作品集《高原的百合花》,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2)引自《不信青春唤不回——写在〈现文因缘〉之前》,收录于文集《昔我往矣》,白先勇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
(3)引自《三毛1943—1991》,师永刚、陈文芬、沙林编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4)引自《他们说三毛》,收录于三毛作品集《温柔的夜》,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5)引自《中国新诗·最美情诗卷》,中国诗歌学会主编,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版。
(6)引自痖弦《百合的传说——怀念三毛》,收录于三毛作品集《高原的百合花》,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7)引自贾平凹《哭三毛》,发表于《当代青年》,1991年第2期。
(8)引自《三毛的最后一封信》,眭澔平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