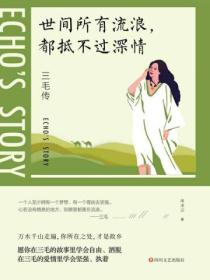云在青山月在天
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要过去,像那些花,那些流水……
——三毛《秋恋》
1991年1月4日,三毛去世了。
陈嗣庆在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提到,三毛多次提及《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在她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好了”这样的字眼),说自己“差一点就可以做神仙,只恨父母忘不了”。他对女儿说,“请你去做神仙,把父母也给忘了,我们绝对不会责怪你”。
这是父母之爱的极致,陈嗣庆对女儿的选择其实是肯定的,所谓“好了”,“其中也并不是没有责任”,只是经历了太多的三毛更能够接受生命结束的时刻。
人活着,有时是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在这周而复始的迷惑中,三毛选择早早结束这一切。与这世界的离别,真希望是她自己的情愿,是想清楚了、体会多了,轻轻叹息一声:“好的,明白了,原该是这样的。”然后付诸行动。
她来,是为了寻求梦的终点;她走,是回到那场梦里,为生命完成一个轮回的闭环。世俗加诸她的痛与常人所受一般模样,但玲珑水晶的承受之力又能强到哪里去呢?最后,她选择不再受苦,早早地归于天地间,完成宿命最后的一步。
当这个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时,有人扼腕叹息,也有人痛哭流涕。但是,仿佛所有人都不得不存了哪怕仅有一丝一毫的念头:是的,那就是她的归期。就像云就该与青山比肩,月就应该悬于中天。那就是她,她来了,她爱了,痛了,醒了,梦了,最后总要归去。
为什么死亡一定是结果?为什么离别一定要哭泣?世界予她伤口,给她悲喜,最后自然要收回这些,还她最初的平静沉寂。
古人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文子·自然》)宇宙无边无垠,其间,便有那么一种人,并非为“活着”而来,而是为“往来”而来。她是“本来无一物”,是“上善若水任方圆”,是“我”,是“滚滚红尘”,唯独不是那具肉身。
三毛就是那样一阵风:走过春天,催开蒙昧的花蕾也抚慰料峭的轻寒;隐于夏日,炙烤酷烈的骄阳,给万物神秘悄然的温柔;飞旋在秋天,既狂野地拥抱着收获,也悲凉地预告着终结;洞明在冬季,从来处来,往去处去,“好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她走了,她也来了。她不在,却又处处都有她的存在。
众生悲悯的从来不是她,她亦无需被同情被感恩,她得到爱,奉出爱,来时剔透,去亦淡然。她也不仅仅是她,或许苍生中有无数个“三毛”,有数不清的“陈懋平”,有千千万万个“某人的未亡人”,却唯独有一个洒脱的她,走过了这沧桑的人生,又丝毫不留恋人间地归去,留给轮回一个完满。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有人单纯地将三毛作为一个肉体凡胎来研究,认为三毛可能存在抑郁的症状,或者大概是失去爱人后,精神便不太正常了;也有人觉得,三毛是矫情的,是做作的,是消极的,是缠绵的,她的爱与恨、浓与淡都是刻意而为之,适宜将她放在林黛玉式的群体里,借以“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有一些人,打着爱的幌子、研究的旗号,给三毛冠以各类或雅致或奇绝的名号,为她随意定性、比较,把她当作玩偶娃娃;更有甚者,恶意揣度三毛的为人,扭曲事实,只为满足自己那一点肮脏的想法。
如果三毛还在,就如同那风,吹过这些零碎的文字,她的嘴角是否会浮现一丝释然的微笑,以她本来的样子,水晶似的,照出文字背后那些面孔真实的模样?
真实的三毛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许多人的疑问。斯人已逝,我们仅能从与她交往过的人口中略微了解她的模样,更多的则来自她的作品。有人说,撒哈拉是小说,是以虚构为主、掺杂了过多文字渲染的文学作品。那不是真正的三毛,也不是真正的荷西。可是,谁知道真正的三毛与荷西呢?谁又能坚定地说自己了解真正的沙漠?
她行踪不定,漂泊天涯,外界流传的那些拼凑的故事远远不及她真实的经历丰富。三毛骨子里的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在尚未开蒙的时候又吸收了大量西方思想,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西文化碰撞融合时期深受影响的国人,她思想上的矛盾既有先天的悲悯和消极,但大部分主要是后天累积而成。生在动**年代,太敏感就容易碎裂,太刚直则容易折损。三毛选择做竹子,柔韧怀虚,自成风景。
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她并非为活着而来,而是为经过而来。谁能温暖一块水晶,谁能温柔一阵风呢?她本来就是天地的一部分,不华丽,不修饰,原原本本地做她的红尘之水。
三毛并未因通晓世故而成为世故的人,她仍是那片水晶。文字、图画、风景,排成长队,踏着长歌穿过她的灵魂,蹉跎间留下的那片墨迹,仍旧回到书本上,仿佛这个生命从未开始,亦永无终止。
三毛的存在,也许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意愿。人间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段旅程;而她对世界来说,也只是个访客罢了。人间不是她的归宿,她人世的使命仅仅是折射出红尘的色彩。人间透过她的笔端、足迹,将悲欢离合展示给世人。她要的却只是最终的归寂,是万丈俗尘背后的回归天地。众生该悲悯的从来不是她,她亦无需被同情、被感恩,她得到爱,带来爱,奉献爱,来时剔透,去亦淡然。为什么死亡是结果,为什么离开一定要哭泣?这世界予她痛,令她喜,最后又将悲喜全部收回。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浮生一场大梦,身在其中,孰能辨别谁为庄周,谁又是蝴蝶?选择了离开的三毛,是真的不在乎了吧!正如李白所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1)也如苏轼所说:“天涯踏尽红尘。……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2)
在阅尽千帆的三毛看来,来来去去都是自然,我们未必是飞鸟,也不必参悟奥妙,更没有必要生生世世长相厮守——“毕竟人是必须各自飞行的,交掌都不能够,彼此能看一眼已是一霎又已是千年了。”
走吧,三毛!再会吧,陈平!“凭尔去,忍淹留”(3),你选择你的天地,“飞鸿雪泥,不过留下的是一些爪印”,但你从不停留,像极乐鸟,欢快地鸣叫一声,迎来血色灿烂的结局,“所飞过的天空并没有留下痕迹”。
三毛依旧是那个浪子,她且行且歌,“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4)。
她自飘零,自悲悯,自潇洒,千山万水走遍无用,物换星移看惯难平。没有多么雅致,也非尘埃里的凡俗,她是再平常不过的每个人,也是再纯粹不过的奇迹。世人要将她染俗了,要玷污她、埋没她、同化她,她仍然坚持本真,活出极致,乐就自在放肆,悲便彻骨锥心。
能够描摹形貌的是后来的三毛,是至简大道的回声。她时而是一阵温润的风,时而是一道跳跃在湖面的粼光,时而是一只翩跹的精灵。你如何看她,如何待她,她就是何种形貌。
三毛最爱贴近、体验世俗,但她能够坚定地永不融入世俗。在短暂的生命中,她穿过三千弱水,仍是本来面目,无相无色。人们爱她,亦是透过她看见了镜面映出的放大了、清晰了的自己。
既然三毛选择在作品中这样表达自己,希望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她,那么我们为何不收下这份期待?三毛爱做梦,不妨就把三毛当作人间的一场梦吧。
(注:本书中所有引述均出自三毛作品及相关人士采访。)
(1)引自《拟古十二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唐)李白著,安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2)引自《临江仙·送钱穆父》(《苏轼词全集》),(宋)苏轼著,谭新红编著,武汉:崇文书局,2015年版。
(3)引自《红楼梦》(脂汇本),(清)曹雪芹、高鹗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
(4)引自《红楼梦》(脂汇本),(清)曹雪芹、高鹗著,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