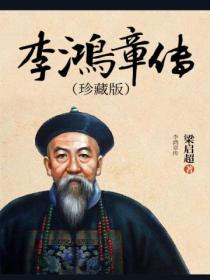第一章绪论
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令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廖耶?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要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