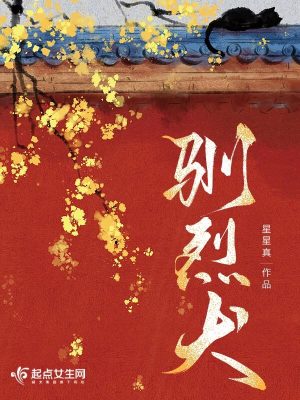刚出门就看到翟墨硕大的身子堵在门口,似乎要将外面的人彻底堵死。
他还没看清门外的人,只盯着翟墨:“你杵在这做什么?世子叫了你半天不应。”
他从翟墨身侧扰出来,看见来人,也愣了一下:“沈姑娘,原来是你。”
青毫是暗地给自己主子送了东西的,对沈宜亭的印象还算不错,同她行礼的态度也很恭敬,看得一边的翟墨更心急了几分。
你这蠢人,这人明摆着冲着世子来的,你倒好,对她毕恭毕敬,小心她勾了世子的魂,教你后悔都没地方。
沈宜亭只逗了一下,见翟墨的确心急了,便也不继续,本想同青毫说一声,将最好的药膏教给他。
却没料他们的声音刚听,院子中传出一个清冽的男声。
江寺推开了房门,正站在院子里,听到外面的声音,淡声问了句:“发生何事?”
青毫回头,朝边上后退一步,顺道伸手扯了下翟墨:“爷让你去倒水,你怎么这么慢,小心误了事。别在中间杵着了,快让开。”
便抬头,歪了歪脑袋,一只手伸向门内,朝沈宜亭恭敬道:“沈姑娘若是有事,不妨进去和世子谈谈,我家世子的伤也就不见好,正好想劳烦沈姑娘看看。”
青毫找了个托辞,只为沈宜亭扯了个理由让人进去。
他虽然脑子不聪明,但有一点好,便是识眼色。
知道主子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他拦着翟墨,硬是让他分毫不动的看着沈宜亭进门。
青毫话都说到这份上,沈宜亭也不推脱了,提了提裙摆,越过二人进了院子。
江寺的住处很清幽,院子里支着茶桌,边上放着一榻躺椅,能看出主人常躺在树下,晃着摇椅晒太阳。
倒是享受。
沈宜亭不由想到。
一进门便闻到一股刺鼻的药味,应该是刚上完要不久,她顺着气息最浓的位置看过去,便见到依靠着大树,阖目静憩的男人。
江寺眉间总是下意识皱着,不过几日不见,他唇色还是未见血色,看上去更虚弱了几分。
沈宜亭手便握紧了白玉瓶。
她并不知道,这些对江寺其实都是小伤,只是他一向体质如此,一但失血气色便就不见好,实际上身体倒比谁都硬朗。
“江世子。”
沈宜亭轻唤他。
身姿高大的男人听到这声音,不由得扬眉,一转头看见来人是她,有些惊异的勾唇:“沈姑娘,你怎么来了?”
江寺双手环胸,左肩靠着树,转身时双手放下,下意识朝右肩托了托。
见沈宜亭站在院子中央,风卷起几片残叶,连带着吹动她的裙摆,在地面晃悠几下,惊扰两人原本静谧的影子。
江寺朝她点了点石桌的位置,“坐。”
“可是有事?”
江寺直白问道。
他兴致并不高。
今日天气大好,原本很适合出门狩猎,赵清父亲回来,他也有好几日未能出门撒野,本身都约好了要出门,所致昨夜突然起风,伤口未曾保护好,受了冷气,今早起便恢复得不好,又见了血,致使出游的打算泡汤。
眼下看见沈宜亭来,才勉强提起性子。
两人在石桌前后对坐下,沈宜亭瞥了眼他的神色,目光扫视过右肩,语气平常问道:“世子肩上的伤可好些了?”
江寺觑了一眼,“不算严重。”
“虽说于世子只是小伤,也免不了要养一阵子”,沈宜亭想到他之前的言论,一句话将有些沉凝的氛围搅得生动起来。
紧接着也顺理成章拿出自己的回礼。
“世子先前着人送来的药草帮了我良多,宜亭也并不是不知趣的人,自然也投桃报李。”
“净心草于伤口恢复也有奇效,我自己便研了一瓶药膏,世子若是信得过我,每日换药时便可用上,想来也能快些痊愈。”
沈宜亭掏出白玉瓶,将之置于桌面正中。
江寺看了一眼,富又看向她。
他没说话,只浓眉微微动了动。
沈宜亭不自觉拧眉,还以为他一朝被蛇咬,怕不是担心她也在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因而不愿收下
她原想解释几句,却不想男人忽的抬头,嘴角悬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
清冽声线若玉石相击,并不显冷漠,反而有些轻柔。
“不生气了?”
江寺还记得沈宜亭那天在凉亭冷脸的模样。
有趣是真的有趣,事后也多少有点懊悔,觉得自己行事不太冷静。
他觑了眼沈宜亭的神色,却见女子怔愣了一秒,而后粲然一笑。
“自然不气,世子心思缜密,将我算计一道,也是我不够谨慎,想来下回便不会了。”
沈宜亭心底仿佛被戳中一下,难得展露几分真性情,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气和自得。
她一向精于算计,谋划人心,父亲过往最是不喜,甚至多次批判,倒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直白试探,事后还顾忌她的情绪。
并未因她失算或是心思过深而轻视、忌惮、防备。
“如此便好。”
见她没放在心上,江寺才放心接过桌面上的玉瓶。
那玉瓶看着玲珑剔透,小巧可爱,依稀能闻见一点沁人的药香,还没用在身上便觉得伤痛褪去很多,想来沈宜亭说的有奇效也是真的。
“药收下了,多谢沈姑娘,而今理我也算不打不相识?”
江寺挑眉看她。
沈宜亭也笑了笑,看他收了东西,便放心同他坦白。
“世子说的是,有一事,宜亭思虑许久,想来也该让世子知道。”
“我姐妹二人寄身候府,实为无奈之计,望世子宽宏大量,莫要介意我姐姐的事情。”
江寺听她主动提起,面上愉悦的神色淡了些,他静默的听着沈宜亭说话,等她说完,才抬眸看过去。
江寺有一双很亮的眼睛,眼角垂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湿漉漉的狗狗眼,但因为他神色一向带着几分下意识的凶戾,所以并不显得温顺,倒像一条疯犬。
眼下这疯犬一样的眼睛很复杂的看向沈宜亭。
内里浮现的凶戾神色很缓慢的散去,随着她说话,又有了一点惊讶和喜悦。
“你同我说这些,我父亲知道吗?”
江寺知道,永威候一定是知道的,但父亲从来没向他提起过。
可以说,如果不是他自己察觉,恐怕永威候也要用骗其他人的那一套来糊弄他。
说到底。
父亲连他这个儿子也不愿相信。
可沈宜亭竟然全都抖落出来。
江寺不可谓不惊讶。
沈宜亭被他一问句叫停,她愣了一下,没立刻理解,反问时显得有些懵懂。
此刻的神情倒格外符合她如今的年纪,显出几分少女的纯稚。
“为何不能说?”
沈宜亭很快收敛神色,拧眉看他,“世子难不成会广而告之么?”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几乎是呢喃的语气。
不像是疑问,更像是试探。
江寺定定看着她,语气很沉,“不会。”
他不会。
他从来都是和永威候府站在一边。
可惜父亲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