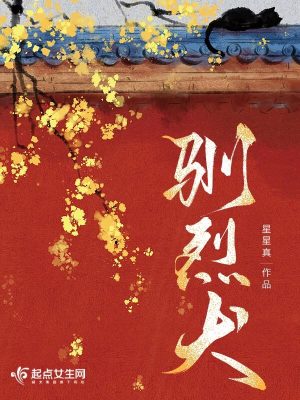江寺房内充斥着一股药味,桌上燃着一盏油灯,能照出桌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伤药。
沈宜亭刚推门,呼吸都没平稳,便着急的看向床上。
“江寺。”
她声音还夹杂着喘气的音调,显得有些不稳,像是下一口气便上不来一样。
江寺忙睁眼,从床上坐起来,神色有些心虚,看向沈宜亭,神色有些关切。
沈宜亭却忽的睁大眼,她盯着江寺上下打量,中医望闻问切,她先是看了看江寺的神态,又转眼看到他身上。
江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衣襟系好,背后隐隐有些血迹渗出来,蔓延到肩上。
他虽然面色有些苍白,但远远没有到能让青毫失态到那样的地步,更不像青毫说的那样。
沈宜亭忽然明白过来什么,一只手撑着门扉,呼吸慢慢平稳下来,她脸上的焦急之色褪去,目光又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和锐利,好像刚才失态只不过是幻觉。
江寺见她神色变化,隐隐知道自己这出戏恐惹了沈宜亭不喜。
他抿了抿唇线,决定主动坦白。
“沈宜亭。”
“我受伤了。”
他说着便垂下头,灯光将眼睫和碎发打下一层浅浅的阴影,看上去像一只颓靡的小狗,显得很是狼狈可怜。
沈宜亭看出他有心使苦肉计,但心里还是有些被欺骗的怒火,因而她反手重重关上门。
门扉‘啪’一声合上。
门外守着的翟墨和青毫都担忧的朝里面看了一眼。
青毫眼中还有些淡淡的幸灾乐祸,翟墨倒很为江寺担心,他不知道沈宜亭为何过来,但人是青毫带过来的,应该是世子爷的吩咐。
见她如此大火气,不免为世子担心。
“沈姑娘如此重的怒火,不会动世子身上的伤吧?”翟墨吞咽一下,战战兢兢看向青毫。
对方面容恢复一贯的冷肃,看上去格外可靠,安慰他:“放心吧,将军心中有数。”
沈宜亭合拢门,转头看江寺,语气凉凉:“不省人事?血肉模糊?”
“恐怕明日要抬着出去?”
她一一复述青毫的说辞。
她说一句,江寺便眨一下眼。
等到她声音停下,江寺便抬头看她。
“我真的受伤了。”
他身影压低,似乎平静的叙述,但男人身上裹着绷带,衣裳隐隐见了血,面色也有些苍白,显得格外可怜。
沈宜亭心里一动。
面上却依旧维持一副冷脸:“那也不至于让青毫在我面前哭求,非要我大半夜来一趟。”
“世子当我是什么,任你玩弄吗?”
沈宜亭语气没什么波澜的反问。
江寺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出口。
他抬头,看向沈宜亭。
那双如星璀璨的眼睛闪烁着明黄的烛光,同时眼中映出一个小小的沈宜亭。
眼神格外认真,也格外无奈。
他叹了一口气,语气淡淡,但莫名让人听出了几分委屈。
“你生我的气。”
“若不说的严重,你不会来。”
沈宜亭脑子懵了一秒,还没反应,就听见他继续道。
“沈宜亭,为何生我的气?”
沈宜亭下意识反驳:“我没有。”
“我同世子交情不深,你又没有得罪我,我凭什么生气。”
“我有”,江寺看她,眼神格外坚持,他语气坚定的好像真的招惹了沈宜亭不快,“我一定有什么得罪你。”
他在床栏靠起来,目光放空,细数他的罪证。
江寺:“你同我疏远,不愿见我。”
沈宜亭在一边搭腔解释:“你我不是约好,出门在外,要装作不合,我如何去见你,去同你客气一番,让盛京众人都知道不合只是谣言?”
江寺垂眸,为自己辩解:“不合言论便是我穿的,只要传言够凶猛,谁能知道。”
沈宜亭没理会。
江寺便继续数:“你称呼我世子,过分生疏。”
沈宜亭:“那我应当叫什么,叫大将军么?”
她脸色无端一红,沈宜亭却是存着心思,从称谓上便疏远了江寺,却不想他心思这么敏锐,一点变化便察觉出来。
江寺凉凉瞥了她一眼:“房产你推门进来时,直呼我大名,叫了一声江寺,以往你总会不自觉叫出来,这几日你见我便叫江世子。”
江寺停下,没再继续,只在心底默默道:
我不喜欢。
沈宜亭一下哑口,她确有此意,被他戳穿,她不否认。
江寺继续:“你不同我说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我告诉你昨日我封大将军,你并未笑。”
沈宜亭想到夜晚时江寺特意来一趟,又见他眼底有些青黑,突然心里触动,问他:“你做题刚封,便连夜从西山军营回来,可是为……”
“我想同你分享,我说的如今已经做到了。”
江寺打断她,顺着接上话。
他倚靠在床上,脊背挺得很直,“如今别人说起北策军将军,便会提及我姓名。”
他不再是活在父亲光芒下的永威候世子。
此后便是北策军将军,能独当一面的将领。
沈宜亭目光闪了闪,有些愧疚。
她确实常同江寺说话,在候府遇到便会交流几句趣事,互相笑一笑,似乎心情便会好很多。
然而从佛寺回来,她有意避开江寺,为避免见面无言,便不再出门。
沈宜亭沉默几秒,喉咙有些哽咽,她艰难缓过气来,“我并不是、不是不为你高兴,我只是……”
沈宜亭一时说不上来,她能怎么说,说她春心萌动,时常会被江寺撩拨。
还是说她对江寺动了几分不寻常的心,而他仍旧未曾察觉。
沈宜亭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偏那人还一副认错的模样,诚恳发问:“沈宜亭,我到底哪里惹你不快了?”
“你同我说说,我尽量……嗯,避免。”
江寺措辞一番。
沈宜亭每一次呼吸都用尽力气,她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分明决定好疏远的也是她,可面对江寺如此真挚的挽回,她又忍不住心软。
“你身上的伤要及时处理,眼下不要说这些废话。”
沈宜亭见药箱放在桌上,从中取出治伤的金疮药,准备给他处理伤口。
她逃避得实在太明显,江寺几乎不用细想便能看出来。
“这不是废话。”
他语气淡淡,轻飘飘重复了一遍。
看沈宜亭拿着药的手颤了颤,江寺颇有几分无所谓。
“这些小伤,不必太在意,总之明日我能安然进宫就是。”
沈宜亭心里窝火,一是为他戳穿自己的小把戏,二是为江寺不将身体放在心上,即是小伤为何还要着急请她过来。
她压着脾气,学着江寺的语气道:“这不是小伤。”
江寺突然哼笑了一声。
“这伤不必在意,等秋猎过后我便要前往韩州,在此之前能好就行。”
沈宜亭是第二次听见他说要去韩州的事,她心里微微泛起一些波澜。
“你要去韩州?何时出发?”
沈宜亭拿着药在他身侧站定。
江寺瞥了眼她,“下个月十八。”
眼下已经是九月底,秋猎就在十月初九,看来也没几天,难怪他毫不在意。
沈宜亭并不由着他。
她已经来了这,来都来了,便是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
“躺下。”
沈宜亭没再管他,只轻轻觑了一眼,那眼神轻飘飘,但带着一股无言的威胁。
江寺被她眼神刮过,心尖微微一颤,面上无奈笑了笑。
他正欲解开衣裳,突然想到沈宜亭先前同他划清界限说的话,手还放在衣襟上,半解未解间抬头看她。
“沈姑娘,先前你说男女有别,不愿与我同乘,眼下为何不说男女有别,孤男寡女不可居于一室。”
沈宜亭被他一再怼的哑口无言,眼下已经习惯,便只端着药,有些无奈的看他:“是我的错。”
江寺眼神颤了颤,抬眸看她。
沈宜亭将手中的药朝他的方向递了递。
“以后不会了。”
她面无表情,眼神平静如死水。
似乎是有几分怄气,便做出这副样子。
江寺眼底染上笑意,他解开衣襟,露出精壮的肌肉。
沈宜亭只见他平日长身玉立,看上去虽然气势威严,然而没想到江寺身躯看上去倒是健壮有力,肌肉结实却并不显夸张,甚至因为上面纵横交错的红痕,显得有些可怜。
他本身肤色便有些白净,血色在身上一时显得极为吓人。
沈宜亭原先见他还能同自己说话,算起旧账,却不料江寺身上竟然伤的这么严重。
一时间,青毫除了一句高热是胡编的,其余也能算都对上了。
“侯爷……下了如此狠手么?”
沈宜亭敛了敛鸦羽似的长睫,语气有些低沉。
江寺原本背对着她,听见她说话,下意识偏头,却不慎扯动伤口。
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伤,若是平日他忍一忍也没什么。
今日不知是昏黄的灯光将沈宜亭五官都照的柔和,还是女子点在他背上的那根手指轻柔擦过,带着不易察觉的怜惜。
让江寺心思活络起来。
“嘶……”
他感受到伤口扯动,便下意识疼得抽气。
沈宜亭果然立刻紧张起来,手指停下,点在他温热的肌肤上,有些冰凉的触感似乎又将心底那不能言说,甚至主人都未曾察觉的躁动点燃了几分。
“别动”,沈宜亭空出一只手,贴了贴他的脖颈,将他本欲转过来的头轻轻推回去,“小心扯到伤。”
她力道不大,但江寺有意纵容,便任由她将自己动来动去。
“好。”他应道,声音略带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