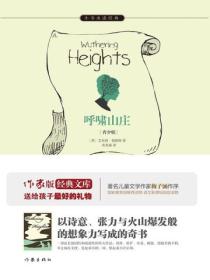第十七章 客人成了主人
那个星期五,是一个月来最后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到了晚上,天气就变了,南风变成了东北风,先是带来了冷雨,接着是雹子和雪花。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客厅里,把一个哇哇啼哭的婴儿放在膝头,来回摇着,一边看着依然漫天飞舞的雪片在没拉上窗帘的窗口越积越厚。这时候,门打开了,有人走了进来,只听得又是喘气,又是笑!
“我是从呼啸山庄一路跑来的。”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除了飞奔之外,一路上我数不清到底摔了多少跤。啊,我浑身都痛!用不着惊慌,待我缓过气来能说话时,我会解释的。只是现在先做做好事,去吩咐马车夫套车把我送到吉默屯,再叫个女仆到我的衣橱里去给我找几件换洗衣服来。”
原来这位不速之客是希思克利夫太太。看她那光景,实在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她的头发披散在肩上,让雨雪淋得直滴水。
“我亲爱的小姐呀,”我大声嚷嚷道,“我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听。等你把湿衣服一件件全都换下来,穿上干的再说。今天晚上你怎么也不能去吉默屯,所以也用不着去吩咐马车夫套车。”
“我说什么也要去,”她说,“不管是走着去,还是乘车去。不过要我穿得像样点,我倒不反对。还有——哎哟,你瞧,这会儿血都顺着我的脖子淌下来了!火一烤,伤口痛极了!”
她坚持要我先办好她吩咐的事,然后才肯让我碰她,直到我吩咐马车夫备好车,又叫一个女仆为她收拾好一些必需的衣服后,她才允许我替她包扎伤口,帮她换好衣服。
“好了,艾伦,”她说,这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她坐在壁炉前的一把安乐椅里,“我是出于无奈,才到这儿来暂时躲一躲的。而且,要不是我知道他不在这儿,我定会待在厨房里,洗个脸,暖和一下,叫你去把我要的东西拿来,然后就离开,到任何一个我那该死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够不着的地方!啊,他是那样的暴跳如雷!要是让他抓住就糟了!可惜的是,论力气亨德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亨德利有能耐做到的话,我才不会逃哩,我要亲眼看着他整个儿给砸烂!”
“嘘,别说了!他是个人啊,”我说,“你要宽容一点,比他坏的人有的是呢!”
“他不是人,”她反驳说,“他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宽容,我把我的心交给了他,他却拿去把它捏死了,再扔还给我。人是用心来感觉的,艾伦。既然他已经毁了我的心,我也就没有能力宽容同情他了。哪怕他从此到死都为凯瑟琳痛苦呻吟,哭出血来,我也绝不会给他一丁点儿同情!是的,真的,真的,我绝不会给他!
“昨天晚上,我坐在厅堂壁炉边我那个角落里,读几本旧书,一直读到将近十二点。外面狂风怒号,大雪漫天,我脑子里老是想起那片教堂墓地和那座新坟,这时候上楼去,真让人感到凄凉啊!我的两眼几乎都不敢离开书页,因为只要一离开,那番凄凉的景象立刻就映入我眼帘。
“这种凄凉的死寂终于被厨房门闩的拨动声打破,希思克利夫守夜回来了,比往常回来得早。我想是因为这场突然来临的暴风雪吧。
“这扇门的门闩是锁住的,我和亨德利听到他正绕道打算从另一扇门进来。我站起身来,我自己也从嘴上感觉到正流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神情。这神情引起了亨德利的注意,他原来一直朝门口盯着,这时转过头来望着我。
“‘我要让他在外面多待五分钟,’他大声嚷道,‘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为了我,你可以让他在外面待上一整天,’我回答说,‘就这么办吧!把钥匙插进锁孔,锁上门闩。’
“没等他的客人走到前门,恩肖已经把钥匙插进锁孔,锁上门闩了。然后他回到壁炉跟前,搬了把椅子坐到我桌子的另一边。他探过身来,眼睛中冒着仇恨的怒火,想从我的眼睛中寻求同情。‘希思克利夫太太,我要求你什么也别做,只要你静静坐着,不要吭声。我敢肯定,亲眼看到那个恶魔完蛋,你会像我一样高兴的。答应我,在时钟敲响之前别吭声——再过三分钟就到一点——你就是个自由的女人了!’
“他从胸前掏出武器,正想熄灭蜡烛,可我把蜡烛一把夺了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臂。‘我不会不吭声的,’我说,‘千万别碰他。就让门关着吧,别作声!’
“‘不!我已经下了决心,老天做证,这事我非干不可!’那个不顾死活的人嚷道,‘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跟他去争论,还不如跟熊去搏斗,或者跟疯子去讲理。我唯一的办法是奔到一扇格子窗前,警告那个他蓄意要谋害的人。
“恩肖怒气冲冲地对我破口大骂,只听得我身后的窗子砰的一声,被希思克利夫一拳打落在地,窗口的铁栅太密,他的肩膀挤不进来。
“‘伊莎贝拉,让我进去,要不你会后悔的!’希思克利夫在用拳打破的窗口外,像约瑟夫说的那样‘狞笑’着。
“‘我可不想犯谋杀罪,’我回答说,‘亨德利先生正握着刀子和实弹手枪在这儿守着哩。’
“‘让我从厨房门进去。’他说。
“‘他在那儿,是吗?’我的同伴大叫,冲到破窗前,‘要是我能把胳臂伸出去,就能射中他!’
“艾伦,我怕你会把我看成是个十足的恶毒女人,可是你并不了解全部情况,所以还是先别下断语吧。即使是企图谋害他的性命,我也绝不会去帮忙或者教唆的。我只是巴望他死掉,我怎能不这样呢?因此,当他突然扑到恩肖的武器上,把它从他手中夺过去时,我感到万分地失望,而且也让自己那番奚落话会引起的后果给吓坏了。
“枪砰的一声打响了,装在枪上的弹簧刀弹回时,正好切进枪主人的手腕,希思克利夫使劲儿把它拔了出来,刀过处皮肉已被割开了一条口子,他把那件血淋淋的凶器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接着他又捡起一块石头,砸掉了两扇窗子之间的窗档,跳了进来。这时,他的对手由于剧痛和流血过多,已经昏倒在地,鲜血从他的一条动脉或者一条大血管往外流着。
“那恶棍对他又是踢又是踩,还不断把他的头往地上撞,同时还用一只手抓住我,以防我去把约瑟夫叫来。
“他使出了超人的自制力克制住自己,才算没有当场结果恩肖的生命。他自己也已累得直喘气,终于也就罢了手。然后他把那个奄奄一息的躯体拖到了高背椅上。
“拖到那儿后,他撕下了恩肖的外衣袖子,用野蛮粗暴的动作包扎住他的伤口;包扎时,一边吐口水,一边咒骂,跟刚才踢他时一样恶狠狠的。”
伊莎贝拉没有再说下去,她喝了一口茶,接着就站起身来,要我给她戴上帽子,披上我给她拿来的一条大披巾,不听我要她再待一小时的请求,站到一把椅子上,亲了亲埃德加和凯瑟琳的画像,又亲了亲我,就带着芬妮[1]钻进了马车。那狗由于又找到了自己的女主人,高兴得汪汪直叫。她乘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到这一带来过,不过等到事情安排得比较妥帖之后,她和我的主人之间,就开始有了正常的通信联系。
我相信她的新住处是在南方,在伦敦附近。在她逃亡之后的几个月,她在那儿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林敦。打一开始她就来信说,他是个体弱多病而又任性的小东西。
大约在凯瑟琳去世后十三年,伊莎贝拉死了,那时小林敦已经十二岁,或者稍大一点儿。
我说过,有好几天,我的主人似乎对亡妻留下的小后代漠不关心,不过这种冷漠就像四月里的雪那样很快融化,还没等那小东西会结结巴巴说话,或者摇摇晃晃走路,她就已经盘踞在他的心头,成了他的小公主了。
小东西也取名凯瑟琳,可是他从来不叫她全名,总是把小东西叫作凯茜,他觉得这种叫法,和她的妈妈既有所区别,又有着联系。他对她这样宠爱,与其说因为她是他的亲骨肉,还不如说是出于她和凯瑟琳的关系。
恩肖的死,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这事就发生在他妹妹去世后不久,两者相隔几乎不到六个月。有关他临死前的情况,我们田庄里的人从没得到过哪怕是最简短的消息。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去帮忙料理丧事时才听说的。来给我家主人报告他的死讯的是肯尼斯先生。
“亨德利·恩肖死了!你的老朋友亨德利,”他说,“也是我的自甘堕落的老相识,虽说这一阵子来他对我很不像话。瞧!我说过我们会掉眼泪的。不过别难过了!他死得完全符合他的本色——酩酊大醉而死。”
我决定请假去一趟呼啸山庄,去帮忙料理料理后事。
我坚持丧事要办得体面些。希思克利夫先生说这事可以由我做主,只是他要我记住,整个办丧事的钱都是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
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酷、淡漠的态度,既没有高兴的表示,也没有悲伤的神情。如果说有什么流露的话,那就是一项艰巨工作胜利完成后的一种冷峻的快意。有一次,我果然看到他脸上流露出一种近乎狂喜的神色,那是在人们把灵柩抬出屋子的时候。他居然假惺惺地装成一个哀伤的送葬者,可是在跟着哈里顿走出去之前,他把这不幸的孤儿举起,放在桌子上,带着少见的兴致咕哝道:
“哦,我的好孩子,现在你是我的了!让我们来看看,要是让同样的狂风来刮扭这株树,它是不是也会跟另外一株一样,长得弯弯曲曲。”
那个天真无邪的小东西听了这番话还高兴哩,他扯弄着希思克利夫的胡子,还摸摸他的脸。可是我听出了其中的意思,便尖刻地说:
“这孩子得跟我回画眉田庄,先生。哪怕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你的,这孩子也不是你的!”
“是林敦这么说的吗?”他问道。
“当然——是他吩咐我来领他的。”我回答说。
“好吧,”那恶棍说,“这件事现在我们先别争论了。不过我很想亲自来抚养一个小孩,所以你还是回去转告你家主人,要是他打算带走这个小孩,那我就得要我自己的孩子来补这个缺。毫无疑问,我绝不会答应放哈里顿走的,除非我完全有把握让另一个回来!记住,别忘了告诉他。”
这一暗示足以缚住我们的手脚了。回去后,我转达了希思克利夫的这一意见。埃德加·林敦打从一开始对这件事兴趣就不大,他听了之后再也没有提干预的事。就算他想这么做,我想他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这位客人如今已成了呼啸山庄的主人,他牢牢地掌握了所有权,并且向他的律师证明——律师又转而向林敦先生证明——恩肖为了借钱来满足自己的赌博欲,已经抵押出他拥有的每一寸土地,而希思克利夫,就是接受抵押的人。
[1]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