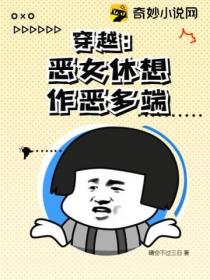此时,地面正是炎热的仲夏季节。而在二十四平巷的地层深处,却显得有些寒气逼人。刘竹山浑身不觉有些寒冷。走出几米,他就要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一是要辨别一下方向,二是怕伍继良在什么地方摔伤了,站不起来了。看见有人来了,会发出呼救声或是喘息声。不知不觉,刘竹山已经在金洞里寻找了两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现伍继良,也没有碰上邓友贤和郝坑长。他们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找着他了呢?刘竹山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又站起身。他想再找一会儿,如果找不着,施出去,和友贤他们碰碰头再说。他往前走了一段路,来到一条狭窄的井口。他举着矿灯,探头向里面张望,里面是一个不大的掌子面。他想起来了,这条狭窄的井口通往天井。他探头向里面张望了一阵,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团灰蒙蒙的东西。他连忙爬过去,那团灰蒙蒙的东西原来是一堆矿石。
矿石上还粘着许多岩尘,岩尘很新鲜,是从岩壁上刚刚刨下来的。刘竹山不由一喜,继良叔来过这里。他提着矿灯走近那堆矿石,拿起一块矿石掂了掂。又在矿灯下认真看了看,知道矿石的含金量不低,那里有一支金脉还没有开采完。继良叔已经发现了,他肯定是高兴了,刨了许多矿石摆在这里。那么,这支金脉在哪里呢?他又到哪里去了呢?刘竹山提着矿灯钻进天井,天井壁上有刨过的痕迹。金脉肯定就在这里。刘竹山连忙退回来,一边注意继良叔会不会在地上留下什么。他肯定。继良叔是在这一带出了问题。刘竹山走走停停寻找了半个多钟头。这时,他突然发现,他又回到了原处。他不由大惊,自己回到原处却全然不知,莫非自己也迷失方向了?他坐了一会儿,歇了一口气,心想,自己一个人找不行,得赶快出去叫人。不然,继良叔有个三长两短就来不及了。刘竹山这么想的时候,就提着矿灯急急地往外走。他清楚地记得,从网状支井的任何一条井洞往外走,走到主矿井,不过半个多小时。而他,整整走了一个小时,却仍然没有看见主矿井。
他心里不免有些迷糊起来。觉得自己在这一个小时的行程中,好像过了一条岩坎儿,好像还攀援了一道天井。他记得,网状矿井里是没有岩坎儿的。那么,这岩坎又是哪条支井里的呢?他觉得自己是彻底地迷失方向了。这时,他觉得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退回到继良叔找到矿脉的地方去。退回到那里之后,再认真辨别一下方向,就不愁走不出去了。他走得很慢。他想,这个时候是千万急不得的。一着急,只怕连继良叔找到矿脉的那条天井也找不着了。看看表,他已经下井近四个小时,时间不允许他再在这里兜圈子了。矿灯里的电石被用完,他就只有等着大权他们带着人来寻找自己了。
他走过了那道岩坎儿之后,转了一个小弯,前面是一条斜斜的井巷。他突然记起来了,那阵,他带着青年采矿突击队追赶一条红矿脉,从前面的矿井采过来,那金脉在这里却一直往上延伸。后来,金脉干脆就跳过一道岩坎,在不远的断岩上重新又出现了。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劈开这条井巷,在这里越过一道岩坎,打出了前面的那条斜井。将一条富矿脉全掏了出来。那么,走过这条一百米长的斜井,再转一个弯,就会有一条石阶。过了石阶,就是网状支井的正中点了。他的脑海里这时已经铺开了一张网状支井的地图。从正中点往前走,只要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到了二十四平巷主井了。刘竹山长长地舒了一日气一心中的一丝紧张也完全地松弛下来。斜井前的石阶过去没有这么滑,实际上,这是一道窄窄的石级道,一边靠着石壁,另一边下面是一个大大的石窝。是采矿留下来的。也许是多年没有人从这里走路,加上长年潮湿,石级上长了苔藓什么的。刘竹山从石阶上走过的时候,他险些滑下去了。
他不由地勾下头去,他看见下面是一汪水潭。他记得那时这里是没有水的。时过境迁,这道采去矿石的石窝竞积满水。他突然觉得有些口渴,想跳下去捧点水喝。这时,他看见水潭的下方有一个灰白色的东西。他揉了揉眼睛,定睛看去,那是一顶矿帽。他不由大惊,心想完了。飞身跳进水潭之中。水潭并不深。不过淹过他的腰部。他果然发现水潭里有一个人。他将那人拖出水面。
是继良叔,已经死了。只是他的一只手抓着矿灯,另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一块矿石。刘竹山将他扛在肩上,好不容易爬上石阶,才哇地一声哭起来,“继良叔,你是为我们老牛岭金矿找矿死的啊。”只是,伍继良却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的浑身已经僵硬,手中的矿灯和矿石被抓得紧紧的,分也分不开。这时,刘竹山发现,伍继良的头上有一个洞。他断定继良叔是摔下石级的时候,矿帽被摔掉了,脑壳砸在水潭旁边的石头上,摔成重伤,在他挣扎的时候掉进水潭被淹死的。刘竹山背着伍继良,一只手举着矿灯,一步一步往前走。大约走了二十几分钟,来到几条支井交汇处。
他记得,这是网状支井的中心地段了。他觉得很累,将伍继良轻轻放下来,坐在一旁喘了口气。他想,再有二十分钟,就十四平巷的主矿井了。突然,刘竹山听到远处的金洞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他听了一阵,那种嗡嗡的声音又一次传过来了。他知道,是大权他们找来了。在矿井里,呼叫的声音经过狭长的洞子的传递,就变成这种嗡嗡之声了。他也大声地呼叫着。让他们知道,他就在这网状的支井之中。休息片刻,刘竹山又吃力地背起伍继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走几步,他就大声叫喊几声。大约走了五十多米,前面突然传来了清晰的说话声。接着,就看见前面的支井里透过一缕光亮。刘竹山大声叫道:“我在这里,我找到继良叔了。”那边支井里的人听见了刘竹山的叫喊声,一齐奔过来,是邓友贤和郝坑长。他们身后还跟着三个工人,“竹山,我们找你找得好苦,继良叔在哪里找到的,他还好么?”刘竹山哽咽着说:“他死了,我在斜井下边的水潭里找到的。”刘竹山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身子就软瘫下去了,连同伍继良一块滚在了地上。邓友贤连忙叫两个工人扶起刘竹山,自己和郝坑长抬着伍继良。急急地向主矿井走去,“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大权和光召他们正带着人在那边矿井寻找。我们要赶快通知他们,不然,他们会很急的。”凌晨五点,刘竹山、宋光召、李大权、邓友贤几个人好不容易将寻找伍继良的人们召集在一块,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地面。
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竖井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上千人。他们都眼巴巴地盯着竖井的吊斗。当刘竹山等人从吊斗走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一齐围上来,询问伍继良找到了没有,询问刘竹山是怎么和大家失去联系的。这时,刘竹山才知道,老牛岭金矿的人们不但知道伍继良失踪了,还知道他刘竹山下矿井之后也失踪了。他说:
“我怎么会失踪呢?我是去寻找继良叔啊。”过后,他将怎样找到伍继良的经过向人们说了一番,“继良叔已经死了,只是,请你们看看,他的手中还抓着金矿石呀。”刘竹山心情沉重地说,“继良叔是为寻找金矿死的啊。”人们将伍继良从吊斗里抬出来,果然发现他的一只手中还紧紧地抓着一块石头。刘竹山说:“我在天井外面的跳槽内发现了一堆被刨出来的矿石。就断定一定是继良叔去过那里。于是就在周围的井洞里寻找,终于在斜井旁边的石阶下面的水潭里找到了他。根据现场分析,他是在石阶上踩滑了脚,在摔下去的时候,矿帽被摔掉了,脑壳被摔破,掉在水潭里被淹死的。可是,他手中抓着的那块金矿却没有丢掉。继良叔发现二十四平巷的天井里,还有一线没采完的金脉。”人群中有哽泣的声音。大家都被伍继良的这种精神感动了。
一个工人说:“都要像老工人那样,我们老牛岭金矿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这时,在一旁等李大权的王银香却走过来,带着责备的口气对刘竹山说:“要老工人下井找矿,不能说安全也不要了啊。”邓友贤对王银香说的这话有些气愤,说:“老工人下井找矿是我安排的,还有青年工人带着。就是采矿队下井采矿,还会发生意外事故呀。”宋光召见状,说:“都快回去吧,天亮了,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开个会,认真研究一下才是。继良叔这样的事故,的确不能再出现了。”八月二十八号上午,老牛岭金矿给伍继良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友贤主持大会,李大权致悼词,刘竹山还讲了话。只是,这天伍继良的追悼会却没有他的亲人到场。周如兰和她女儿伍冰去省城之后,母女俩就没有回来过。刘竹山将电话打到省肿瘤医院,伍冰才说了一句话就哭了起来。刘竹山要她妈接电话,周如兰也是哭。刘竹山心里难受极了,找不到劝她们的话,说了句什么时候他去省城一定去看望她们的话就将电话挂了。将伍继良送上山之后,刘竹山主持召开了个党委会议,着重研究安全生产问题,坚决杜绝意外事故的发生。李大权说他已经听到议论了,矿里许多人对矿党委在老牛岭金矿当前的严重困难面前,措施很不得力,只是被动地要大家勒紧裤带,少发工资。
轮流上班共渡难关的意见很大。说矿党委并没有拿出得力的措施让矿山尽快走出困境。要说办法,就是让那些老弱病残的退休老工人到废了的旧矿井去找矿,结果活活地丢了一条命。李达伟当即就带着不满的口气问李大权,说大权你自己也是老牛岭金矿的主要负责人,工人们的这些意见你是怎么看的呢?刘竹山却不生气,说:“正因为他自己是老牛岭金矿的主要负责人,他才会把听到的话说给大家听。你们还听见什么了没有?听见了,都说出来,我们好一块研究,一块解决。”宋光召说:“我接连到机修厂去了两次,都是大权接到电话说是机修厂的工人对小义和大龙有意见我才去的。其实,我家小义和大龙两人根本就没有回来。六月份的工资也一直没有领取。
我问他们做出决定没有。对于小义和大龙那天夜里做私活罚多少款,要张榜给群众一个说法。他们说小义和大龙六月份的工资抵罚款了。机修厂财务室已经开出了罚款单据,还有什么说的呢?他们倒是希望机修厂多一些像小义和大龙这样的人,他们就不要轮流上岗了。留下来的人可以天天上班拿工资。在那里,我倒是听到一些议论,说我们老牛岭金矿多年来一直是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内部管理也全部沿袭的过去计划经济那一套,勘探、采矿、选矿、冶炼、销售一条龙,而机修、供销、后勤、医院、贸易、公、检、法、司甚至学校,全部都是为前面的生产中心服务的。
说白了,我们老牛岭金矿一万五千多口人,吃的全是井下八百工人的饭。八百采矿工人养活着全矿一万五千口人。也不管工作的好和差,有效益,大家都有饭吃,都端一只铁饭碗。实际上,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早就该打破了。”李大权说:“上次我们搞分流待岗,实际上已经让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减少了一半。如果还要打破什么计划经济体制,砸烂什么铁饭碗,我们金矿非大乱不可。”邓友贤说:“光召说的这个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人家外面许多大型厂矿都在大刀阔斧地搞改革,砸铁饭碗。我们为什么就不司以试一试?”龚启明说:“我们矿山和别的矿山多少还有一些区别。几十年来,我们老牛岭金矿经济效益一直不错。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都很好,上交国家的利税也多,几十年累计已有三个多亿了。
只是近两年黄金生产才开始滑坡,我们金矿的日子才艰难起来。
要一下在矿山动大手术,甩包袱,恐怕还不行。可能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龚启明顿了顿,“还有一个事,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不要在困难的时候,忘记了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
今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对于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也抓出了成效,破获很多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
我们金矿过去对这项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也没有出过什么大问题。
今后还是不可松懈,千万不要在经济问题摔跤子。”邓友贤说:“我们金矿的几个领导在这上面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我们这一群人,要腐败也没有机会和条件。”刘竹山沉着脸,瞅了一眼李大权,说:“不管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条件,警钟长鸣是应该的。我们要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是老牛岭金矿的后代。我们的肩上挑着一副很沉重的担子。千万不要忘本,千万不要被外面世界一些不良风气所影响,千万不要做了金钱的俘虏。不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呀。”李大权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要说机会,我的机会比你们多。
要说条件,我也有条件。要不,我们轮着去广州吧。”刘竹山说:“大权你那说的什么话。启明这么说没有错。他的话并没有针对谁。的确要告诉你,眼下我们矿山十分艰难,我们的精锑能多卖钱,就一定要多卖钱。商场如战场,你一定要多个心眼才行,千万不要上人家奸商的当。”李大权有些不耐烦地说:“这个话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不说为了老牛岭金矿一万五千多人的生存问题,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在老牛岭金矿当这个家,我也要想方设法争取精锑多卖一些钱嘛。”刘竹山说:“上级把这个矿山交给我们几个人,我们就要全心全意把这个矿山管理好,弄得大家都饿肚子,我们的脸面过不去。”李大权说:“我还是那句话,老牛岭金矿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行,不然这一步就跨不过去。”刘竹山说:“我们的每一次会议,都有这样的内容,就是商讨渡过老牛岭金矿眼下困境的办法。
光召刚才说的,启明刚才说的,目的都是如何让老牛岭金矿将这一步跨过去。你们谁还有好的主意,说出来大家再研究一下,形成集体意见,再往下面贯彻。”邓友贤说:“大权,你在外面的时间多,走的地方也比我们多,见识比我们广,有什么好的得力的措施没有?”李大权有些生气地说:“不要以为我提了建议,就问我有什么得力的措旎没有。说起来,这些事,竹山应该想得多一些,我们各人都管着具体的事,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全盘的问题。大的主意,还得竹山自己拿。”刘竹山心里打了一个怔。过去,大权从来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是金矿的事,不论大小,不论轻重缓急,几个人坐在一块,总是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商量。从没有说谁该多想,谁该少想,寻找解决的办法。
他说:“我是老牛岭金矿的一把手,老牛岭金矿这副担子,主要应该由我来挑。眼下,老牛岭金矿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我这个一把手应该考虑得多一些,肩上的责任也应该大一些。如果老牛岭金矿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个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是想,我们老矿长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时候,不论大事小事,总是要认真征求每一位党委成员的意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充分利用大家的智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我觉得这种民主作风不能丢,特别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宋光召说:“别把话题扯宽了,研究安全生产的问题,就把这个问题研究好。
我觉得,今后我们还是不让老工人下井去找矿了。他们那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当然,他们的那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说实在话,我们金矿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人心稳定、社会治安良好,与老工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刘竹山说:“什么时候,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老工人大会,说一说眼下金矿的严峻形势,请他们还要多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他们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未尝不可,但要注意安全。我还是那句话,要依靠群众的力量,要让大家共担艰难,坚持到找到新的矿脉的时候。”过后,对邓友贤说:“继良叔在二十四平巷斜井上面的天井发现还有一支没有开采完的金脉。你是不是跟郝坑长说一声,让他派人再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开采的价值。另外,其他的被废弃的矿井还有没有重新开采的可能。你跟郝坑长商量一下,是不是组织一支熟悉地形,又有经验的找矿小组再从二十三平巷往上实地考查一下。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勘探队没有勘探出新的矿脉之前,坑口的工人没有事做的情况下,让他们找些活干。这不是拯救矿山的根本办法。
要想让老牛岭重新走出困境,只有找到新的矿脉。”邓友贤说:“勘探队那边的工作是竹山自己在抓,那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困难没有?我看,现在我们老牛岭金矿能不能走出困境,什么时候走出困境,关键就在勘探队了。”李大权说:“听我家安文说,勘探队不是没有问题,大家的思想也不是很一致。”李达伟说:“他说了些什么问题?大家的思想还有什么不一致的?如今他是主持工作的副队长,有问题,就应该想办法解决,思想不一致,就要想办法统一思想。”李大权说:“竹山自己在那里蹲点啊。”刘竹山说:“我跟着勘探队下了这么些日子的矿井,大家的干劲还是很高的,情绪也是比较稳定的。安文这孩子虽然年轻,工作还是比较负责的。
要说有什么情绪,大家就是担心老牛岭再没有矿脉可找了,担心老牛岭金矿的矿藏已经采完了。我觉得他们有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谁又能保证什么时候能找到矿脉,谁又能保证我们老牛岭金矿还有五号脉、六号脉甚至七号脉?”李大权笑说:“你只看到表面,没有深入进去。”刘竹山不知李大权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确没有看出安文和他的队员们还有什么思想情绪。他说:“过几天,我还要去勘探队的,过细地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这样吧,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我们还是按以前安排的,各自抓各自的事。大权要经常和广州那边保持联系,如果精锑的价钱上浮了,就赶快将货运过去。现在我们只有吃这点老本了。我担心的是库存的这点精锑吃完,新的矿脉还没有找到,我们老牛岭金矿会是个什么样子。”过后,刘竹山交待宋光召,“你把你的设想再完善一下,拿出一个详细的方案出来。我看,不管找没找到新的矿脉,体制改革、转变机制这一步迟早是要走的。不然,就适应不了新的形势。”散会之后,龚启明跟着刘竹山来到他的办公室,说:“匿名信的事,下一步,该怎么办?”刘竹山沉思良久,说:“从今天开会的情况来看,大权像是有情绪,他会不会听到了什么了?”龚启明说:“我的直觉,可能是希望你走。”刘竹山说:“你说,我该不该走?”龚启明说:“老牛岭金矿眼下的处境,你是不该走的。
就个人的前途来说,你又该走。说实在话,谁也不知道老牛岭金矿今后会是个什么结局。”刘竹山说:“老矿长说最近可能要到老牛岭金矿来一趟,也一直没有来。”刘竹山顿了顿,“匿名信的问题,你有什么考虑没有?”“我想给老矿长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办。因为,大权毕竟不是我们管理的干部。但我一直没有给老矿长挂电话。这个事,还得你点头才行。”刘竹山说:“是不是跟光召和友贤他们通一下气?”其实,刘竹山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实在是不希望把这件事捅出去,那样,对大权不好。“你决定啊。”龚启明说:“如果去广州调查落实有这么回事,大权只怕就不是纪律处分的问题了。”刘竹山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说:“先跟光召、友贤通一下气,做做大权的工作,让大权自己把问题说清楚,退出赃款,争取主动。”“问题是,大权他肯像你说的那样做么!你没看见开会时他的态度。
他的自我感觉很不错的,希望你早走,他好接你的手。”刘竹山想一阵,说:“这样吧,我去找他谈。能解决问题,当然好,谈不拢,再对老矿长说不迟。”“什么时候找他谈?”“谈之前,我还是准备跟光召和友贤他们通通气,听听他们的意见。”这天下班回来,刘竹山发现王桂花一边在厨房做饭,一边掉眼泪,不免有些心烦,问她怎么了,是不是小莹回来又跟她吵嘴了。自从金来脚被压断住在医院里,小莹的脾气就特别的大,动不动就跟她妈怄气。王桂花说:“小莹没有跟我怄气。”王桂花这么说的时候,就瞅了刘竹山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刘竹山说:“有什么话,不能说么?不说你就不要当着我的面掉眼泪,我见不得那个样子。”王桂花用袖口抹了一把泪水,急急忙忙将饭菜办好。刘竹山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轻轻说:“竹山,我有一个话,对你说了,你别发脾气。”“什么话,你说吧。”刘竹山仍然勾头吃他的饭。“外面有人说,省里要调你,你不愿去,是因为如兰的原因。”刘竹山的脸一下板了起来,“你听哪个说的?”“其实,我并不相信这些话,”王桂花说:“我知道,你是看见老牛岭金矿这么个样子走了不放心。”“我现在问你是听谁说我不愿走,不是问你相不相信这话。”“大权他家银香对我说过,还有别的人也对我说过。”“还有别人,是哪些人?”“贸易商店的。我昨天去商店买洗衣粉,她们说我差,太迁就你,这样的好机会,还不走呀,到那时,只怕有我哭的时候。”
刘竹山没有做声,他觉得王银香希望自己走,大权才有机会上,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她却用这种手段挤自己走,就有些太让人生气了。他交待王桂花说:“我走不走,省里还没有决定下来。人家怎么说,让人家去说,你只别在里面瞎掺和。”王桂花说:“有福不在了,如兰有病,你关心她,体贴她,我也理解。你要不去她那里,我心里反倒过意不去。我跟你这么多年,小莹都二十多岁了,我心里还不踏实么?”王桂花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就又出来了,“你是矿长,金矿这么困难,大家的日子不好过,我也着急哩。还有小莹的事,金来残废了,他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小莹回来总是发脾气,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她了。”刘竹山说:“小莹长大了,懂事了。
她的事,由她自己做主,你别在里面说三道四就是。”王桂花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能不担心么?”刘竹山看见她老是夹一泡眼泪,有些不耐烦地说:“别说了,快吃饭吧。”王桂花就端起碗扒了两口饭,又不由地问道:“如兰去省城这么多日子了,也不知道检查出结果来了没有?”刘竹山当地一声将饭碗放在桌上,也不做声,就出门去了。那天晚上,刘竹山去了宋光召家。宋光召住在石床溪居委会,离猫儿沟比较远。刘竹山到他家的时候,宋光召正在洗衣服。宋光召的房子也是他父亲六十年代分的那种竹片上抹灰的平房。后来实在不能住了,后勤处才整修了一下,将竹片换成了煤碴砖。
儿子去了德州,家中就宋光召一个人住。由于工作忙,家里也没有收拾一下,桌椅凳子十分零乱地摆在并不宽敞的客厅。吃过的饭菜也没有收拾,连同碗筷一并摊在桌上。平时刘竹山不常到宋光召家来。有什么事,挂个电话,跟宋光召去办公室说。跨进门的时候,刘竹山心里就生出了一种歉疚,觉得对宋光召个人的问题过问得太少了。这个家,实在太需要一个女人了。他说:“光召,你的想法只怕要改变一下才行,这样,你实在是太累了。”宋光召不知道刘竹山这个时候会到他家里来,连忙给他摆凳子坐。过后,就洗杯子给他倒茶,说:“我习惯了。”“我知道,你是那阵侍候怕了。”刘竹山笑着说,“你不要讨了一个生病的老婆,就认为天下的女人都是病人。不要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