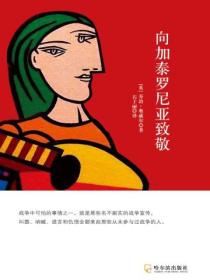巴塞罗那,开战了!01
五月三日的晌午,我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路过旅馆的休息室时说了一句“听说电话局那边出事了”。不知为何,我当时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话。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正走在兰布拉大道上时,突然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了枪声。我回头一看,一群年轻人正端着步枪,脖子上裹着无政府主义者统一佩戴的红黑相间的领巾,沿着兰布拉大道渐向北去了。显然,与他们交火的正是埋伏在那座高耸的八角塔(那应该是一座教堂,整条街道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里的一伙人。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开战了”!不过,这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人们随时都在等着战争的爆发。我马上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回到旅馆,我要确保妻子的安全。可是那帮无政府主义者把守着街口,对着人群吼叫,勒令人们往后退,不要穿越火线。枪声越来越紧了,子弹从高塔飞向大街,笼罩在恐慌中的人群为了逃避战火,不得不沿着大街比肩接踵地往后方撤退。此时,夹杂在枪声中的还有街道上的店老板们噼里啪啦地紧关百叶窗的声音。我发现有两个手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借着路边树的掩护而警惕地一步步撤退。前方蜂拥的人群正冲向兰布拉大道中央的地铁站寻求庇护。我决定避开他们,否则我很可能会被困在地下长达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曾和我们在前线并肩作战的美国医生突然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快!我们得马上赶到猎鹰旅馆(这是一家由马统工党负责的寄宿旅馆,专供民兵休假时居住)。”“马统工党的兄弟们要在那儿会合。现在是危急关头。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见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追问道。
医生只管拽着我拼命地跑,此时,他已是惊慌失措、语无伦次了。看来,他一定是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亲眼看见了大批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卫队的卡车驶向电话局并发动了突然袭击,车上几乎全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紧接着,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便赶到了那里,冲突就此爆发。前不久我听说,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政府提出了接管电话局的要求,显然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跑,突然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驰而过,车斗里站满了手持步枪的无政府主义者,最前面还有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趴在堆起来的垫子上,护着一把轻机枪。当我们到达兰布拉大道尽头的猎鹰旅馆时,那里已经挤满了**的人,他们聚集在旅店的入口大厅里乱作一团,面对当时的情景,大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我们该干些什么。这里除了大楼里充当人民警卫队的少数突击队员身上有装备以外,其他人都手无寸铁。我横穿过街道,走到马统工党当地所在的委员会,那里的楼上有一间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屋子,里面乱哄哄的,挤满了人。其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长相很英俊的男人,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他穿着便装,脸色有些苍白。他一边试图维持着秩序,一边从墙角的一堆东西里给大家分发皮带和弹药筒,目前大概还没有枪。这时我忽然发现,那位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才明白过来,一定是出现了人员伤亡,需要医生。而此时,又来了一个英国人。这时,那个高个子和几个人从里面的办公室里抱出了一些步枪,开始分给大家。由于我和那个英国人是外国人,他们对我们还稍有芥蒂,所以一开始没有人肯给我们发枪。后来,还是我在前线认识的一个民兵走进来认出了我,他们才比较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把枪和几颗子弹。
远处响起了一阵枪声,街上空无一人。大家纷纷议论,说想去兰布拉大道是不可能了。警卫队已经占据了所有大楼的制高点,对过往的人群无不开枪扫射。我原本打算冒险回到旅店,但是考虑到委员会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击,于是我决定还是留下来为好。整栋大楼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人,无论是在楼梯上还是在外面的过道里,到处是熙攘的吵闹声,人们个个情绪紧张,慌忙无措。似乎并没有人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是警卫队攻占了电话局,他们占领了一切有利地位,控制了原属于工人的所有高楼大厦。在诸多大众的意识里,警卫队总是排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人们听不到一丝对政府的埋怨。在巴塞罗那,贫民阶层把警卫队视为走狗级别的暴力团伙,所以,他们自发组织发动突然袭击可能也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我得知事情的真实状况后,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对于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我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以他的血肉之躯与武装精良的警察,与他的天敌奋力斗争时,我知道我再也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立场了。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们这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我甚至没有想过给我妻子所在的旅馆打个电话,确认她是否安全,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中断了一切工作,然而事实上,电话局仅仅是短短几个小时的停滞运作而已。在这两幢楼里,聚集了三百多人。他们大多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穷苦人民,从码头那边的穷街陋巷跑来这里避难的,其中有很多妇女,有的怀里还抱着孩子,还有就是一群衣衫破烂的小男孩。我想,他们中多数人应该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慌乱中逃到马统工党的大楼里来寻求庇护吧。这栋楼里面还有一些正在休假的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我估计,在这三百多人里面大概只有六十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索要枪支,却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已经没有多余的枪支了。民兵队的后生们似乎认为这只是一场热闹的聚会,他们只是不停地四下徘徊,想方设法地去讨好那些有幸分到枪支的人,或许干脆趁其不备顺手偷来一把。不一会儿,我的枪就被一个小家伙偷走了,还未来得及察觉,那家伙已经纵身逃走,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我身上还有一把手枪和一盒子弹,我就只能赤手空拳了。
天色暗了下来,我的肚子也开始抗议了,而放眼望去,似乎在猎鹰旅店也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于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便偷偷地跑到他住的旅店去弄点晚上吃的东西,恰好那个旅店离这儿不算远。此时大街小巷都已经陷入一片漆黑而寂静的夜色中,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所有商店都门窗紧闭,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用钢质的百叶窗封了起来,不过街上的壁垒还没有建起来。朋友住的旅店已经反锁上了大门,还用重物挡起来作为防护措施。他们对于我们自然是很警惕的,在一番大惊小怪的盘问之后,终于放我们进去了。回来之后,我才得知电话局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跑到楼上办公室,想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当然,这栋大楼里是不会有电话簿的,我又不知道我的妻子所在旅店的电话号码。无奈之下,我只得挨个房间搜寻,找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本旅行指南,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电话号码。然而我没有联系上我的妻子,不过,几经周折后最终我还是与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奈尔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且关切地问我马统工党委员会这边是否安全。我调侃地说道,要是能有烟抽就更好了。我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麦克奈尔竟然带着两包好彩香烟站在了我的面前。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只身一人穿过街道,冒险穿梭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视线中。他们先后两次拦住他,用枪口指着他检验了他的所有证件。他这个小小的英雄壮举让我永生难忘。当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们真的有烟抽了。
那帮人几乎在楼上的所有窗口旁边都安排了武装守卫。在街上,一队突击骑兵正在对几个过路人进行盘问。一辆装满了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孩,十七八岁的样子,腿上放着一挺轻机枪,她在小心地摆弄着。我在大楼的周围转悠了很长时间,这里倒是个闲逛的好去处,不过要想了解到一点地形情况是绝无可能的。满眼望去,处处是废弃的垃圾,破旧的家具,还有那些被人们随手撕掉的宣传单和海报……而这些似乎都是革命的必然产物。每每路过人群,只见大家都姿势各异地在沉沉地睡着。在走廊边的一个破沙发上,还躺着两个从码头那边逃过来的妇女,她们总是发出有节奏的呼噜声。这里曾经是一个卡巴莱剧场,后来才被马统工党接管。有几个房间里还留着表演的小舞台,其中一个舞台上摆放着一架大钢琴,此时的它显得如此落寞、孤独。走着走着,我的眼睛忽然被牢牢地吸引过去,我终于发现了我一直求而不得的东西——那是一个军械库。我来不及想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只知道我迫切地需要武器。以前经常听说,加统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这些对立的党派都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武器,所以我相信除了在这两幢大楼里我们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之外,一定还有武器储藏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此之前我一直这么盘算着。这个军械库周围没有任何安保措施,门也很破旧,我和另一个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之后才发现,他们讲的全都是实话——武器确实没有多少了。我们只找到二十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而子弹却一颗也没找到。我赶忙跑到楼上办公室,问他们是否还有多余的子弹,答案是没有。不过,这里倒还有几箱手榴弹,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辆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尽管都是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匣子里。
地上到处都睡满了横七竖八的身体。不知道哪个房间里还传出了婴儿的哭声,哭声响个不停。虽然已经到了五月天,晚上却越发冷了。有个房间的舞台上还挂着幕布,我便用刺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打算睡几个小时。然而,我却总是被噩梦惊醒,睡梦中一想到那些手榴弹我就担惊受怕,想到如果我稍微用力翻个身,压在身体下面的那两颗手榴弹就会把我炸飞。凌晨三点的时候,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叫醒了我,他给了我一支步枪,让我在一个窗户旁边站哨。他跟我说,带头发动突袭的警察局长萨拉斯已经被逮捕了。(后来我们才得知,实际上萨拉斯只是被解除职务而已。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是警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天刚破晓,大家就开始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道街垒,一道建在马委会外面,另一道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鹅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道墙,而且鹅卵石下还有很多小石子,很适合装沙袋。这两道街垒的修建过程简直称得上是一道奇妙的风景,我想要是能有什么东西能把它们拍下来那该有多好!对于一件下决心要干的事情,西班牙人总是会奉献出他们无限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排着长长的队伍,无不挥洒着汗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就连那些年纪尚小的孩子也都成群结队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用一双双孱弱的小手将那些鹅卵石一块一块地击碎,又将它们一捧一捧地装进麻袋里,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装满石子的麻袋拖到一辆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上,他们乐此不疲地推着装满沙袋的车子,摇摇晃晃地来来去去。在当地委员会的大楼门口,有一个德国的犹太小女孩,穿着一条民兵长裤,裤子膝盖位置上的纽扣正好在她的脚踝处,她笑眯眯地四下张望着。几个小时后,已经砌好的街垒有一人多高,射击口旁边都站上了士兵,在另一道街垒后面,有人烧起了火,打算好好地享用他们的煎鸡蛋了。
他们又把我的枪拿走了,对此我似乎无能为力。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旅馆去。虽然仍可听见远处接二连三的枪声,但似乎兰布拉大道上没什么动静。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去食品交易市场上看了看。只有不多的几家商贩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大街南面的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刚到那里,便听到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枪声,屋顶上方的玻璃也被震得颤动起来,人们都飞奔着向市场的安全出口拥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是选择继续营业。我们俩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还买了几条山羊奶酪放到了装手榴弹的袋子里。几天后,当我还能吃上奶酪时,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无比庆幸。
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那个街角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现在这里已经筑起了街垒。站在街垒后面的一个人朝我大声喊,让我注意安全(我当时在街道的另一面)。已经占据了教堂钟楼的警卫队站在高处不分青红皂白地朝所有的路人开枪。我停了一下,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好险啊,一颗子弹从我肩膀的一侧飞了过去,近得让我不寒而栗。当我还在街道的另一侧,快要接近马统工党的行政大楼时,站在大楼门口的突袭骑兵向我大声地发出警告——可我当时没听明白他们在喊些什么,因为中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在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根本看不清他们在比画什么。我跑进大陆旅馆,觉得这里应该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于是,我洗了把脸,然后又回到马统工党的行政大楼里请命,大陆旅馆和行政大楼之间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此时,大楼外面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枪声足以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楼下接二连三响起令人胆战心惊的爆炸声,那声音响彻天际,我想一定是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手榴弹,因为手榴弹在石材建筑之间爆炸,所以爆炸声响起来时要比平常高出两倍之多。混乱中我找到了柯普,问他我们该做些什么。
柯普朝窗外看了一眼,将手杖从背后收起来,说道:“下去看看再说。”接着,他便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下楼梯,我也紧跟着一起下了楼。结果发现,就在大楼的门口,一群突袭队员正在扔手榴弹,他们就像扔保龄球一样将手榴弹扔出去,让它顺着台阶滚到人行道上。手榴弹在二十米以外的地方爆炸了,和枪声交织在一起,发出了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个人偷偷地探出了头,此时此刻,他的头就像是琳琅满目的展会上摆放的一颗椰子那样惹眼——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美国民兵。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紧挨马统工党大楼的是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摩卡咖啡馆。开火的前一天,有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卫队员住进了咖啡馆,冲突发生后,他们便第一时间占领了整个大楼,而他们自己也困在了里面。或许他们是提前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之后突袭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而当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时,与突袭队民兵交了火,结果,有一名突袭队员身负重伤,而警卫队中有一名人员死亡。后来,警卫队撤回到了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警卫队便向他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里并没有武器。美国人急忙躲到报亭后面,这时,突袭队员看到警卫队出来放枪,便向他们扔手榴弹,想将他们再次逼回咖啡馆内。
大致了解了情况之后,柯普径直走过来,一把将那个正用牙齿咬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头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紧接着便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到大楼,并试图用各种语言让大家明白,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牺牲。随后,他便走出大门,站在一处可以看得见警卫队动向的人行道上,从容自若地解下手枪,轻轻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随之卸下手枪放在了地上。三个人缓缓地走向聚集在门口的那些正处于高度紧张、恐慌的情绪之中的警卫队人员。这件事若换作是我,就算给我二十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他们赤手空拳地朝着那些装有真枪实弹的警卫队士兵走过去,可那些士兵却被他们吓坏了。一个穿着衬衫、脸色吓得发青的士兵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的手一直指着放在人行道上的两枚手榴弹,情绪显得十分激动。柯普回来之后告诉我们,最好去引爆那两枚手榴弹,否则路过的行人会很危险的。于是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的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他没有击中另一枚。我要过他的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了一枪。很惭愧,我也没击中。
这是我在这场暴乱中开的唯一一枪。人行道上撒满了从摩卡咖啡馆的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车中,一辆是柯普的军用车,车上布满了被子弹打出的窟窿,挡风玻璃完全被爆炸了的炸弹震碎了。
柯普又带我上了楼,并向我解释了一下目前的情形。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守住这里,但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们命令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开火。这栋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作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它的屋顶比其他正常的建筑高出很多,屋顶上还有个双拱形的瞭望塔。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控制整个街道,只要有士兵拿着几把枪守在那儿,就可以抵御一切向大楼发来的攻击。电影院的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我们在电影院进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被困在摩卡咖啡馆的警卫队,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太大威胁的,他们不想打仗,让别人活着,同时也能给自己留条活路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时,柯普重申了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任何人不许开枪。虽然柯普没有说出来,但是不难推测出,马统工党的领导们对被牵连到这起事件当中是非常愤怒的,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们已经在瞭望塔上安排好了守卫。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溜进对面的旅馆吃饭时能短暂休息一下,我一直守在波利欧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没有遇到任何危险。我所忍受的最大的煎熬便是饥饿和无聊了,然而,这却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难熬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经历能比这场巷战更让人感到厌恶、绝望、身心疲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