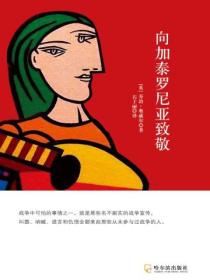02
当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还有科特曼在一片建筑用地附近的草丛里睡了一宿,夜里郊外的野地还十分寒冷,我们几乎没睡多久便早早地醒来了。我记得,我在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后才喝到一杯咖啡。那天,是我来到巴塞罗那之后第一次得闲去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不过似乎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四个酒瓶状的塔尖平行而起,远处望去像锯齿一样高耸入云。不过,这座教堂没有像其他教堂建筑那样在革命期间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具“艺术价值”,可我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本可以毁掉它,之所以让它幸存下来多半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品位太过低俗,尽管他们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那爪牙般丑陋的塔顶中央。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前去探望了柯普,除了道别,还留了一些钱给西班牙的朋友,除了拜托他们给柯普买些食品和香烟以外,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然而,就在我们离开巴塞罗那后不久,柯普就被单独监禁了起来,甚至连吃的东西都送不进去。那天晚上,我们去兰布拉大道,路过摩卡咖啡馆时,看到那里仍由警卫队重兵把守着。冲动之下,我走进了咖啡馆,并和两个怀里抱着步枪,斜靠在柜台上的士兵攀谈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同志中有没有在五月战斗时曾在这儿执勤的人。他们都说不知道,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该从何打听这件事——这种从不追根究底的性格完全是西班牙人的特质。我说,我的朋友乔治·柯普被捕了,因为受了五月战斗的影响将被审判,当时在这里执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这里的战斗,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证明此事。其中一位神情木讷,一味地摇头,可能是因为交通嘈杂听不清我说的话,而另一位士兵则对我的话做出了反应,他说他曾经从战友那里听到过关于柯普的英勇行为,柯普是一个好伙计。我知道,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如果柯普接受审判,他们便会像对待其他的兄弟一样,想尽一切办法来罗列伪证以落实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旦他被枪毙(这是我最担心却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的碑文上将会刻上这样的话:他是警察眼中的好伙计,身在黑暗的制度中,他却保留了一颗人类特有的能辨别真善美的心。
我们过着一种非同寻常、精神近乎崩溃的生活。夜晚我们是罪犯,而白天我们又不得不伪装成潇洒风光的英国游客。尽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修理一下胡子,洗个澡,擦擦皮鞋,整个人就会显出些许光彩照人的模样。目前,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像个资产阶级。我们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生活区,在那里没有人会认识我们。我们只光顾高档餐馆,在服务生面前表现出英国绅士的风度。我生平第一次在墙壁上题字,在一些装修精致的餐馆走廊里,我用尽全力画上了几个大大的字眼:“马统工党万岁!”虽然我一直在有意识地隐藏,但我似乎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这是一种多么荒唐的想法——英国式的教条思想使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你没有触犯法律,“他们”是不可能逮捕你的,然而在一场充满杀戮的政治较量中,这种教条式的思想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已经下发了对麦克奈尔的拘捕令,很有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也包括我都被列入了拘捕名单中。多少天来大范围的搜捕、突袭从未停止过,截至目前,许多我们认识的人都已被捕入狱,只有那些还奋战在前线的人能够暂时幸免。警察甚至登上了定期输送难民的法国轮船来抓捕托洛茨基分子的“嫌疑犯”。
多亏英国领事馆的热情相助,我们才总算办好了护照和其他的出境手续,一周以来,那位领事一定为此事费尽了心思。我们应该尽早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当天晚上七点半有一趟开往波乌港的火车,不过通常会晚点一个小时才能出发。我们已经事先有所计划:我的妻子预定一辆出租车,然后打点行李,结算账单,尽量能在出发前最后一刻离开旅馆,这样才能避免过早地打草惊蛇,否则旅馆的人一旦发现她要离开,肯定会去报告警察。然而事情总是不如人所愿。大约七点钟,我来到了火车站,却发现那趟火车已经开走了,事实上六点五十就已经发车了——火车司机大概又临时改变了主意。所幸我及时通知了我的妻子。第二天早晨还有一趟开往波乌港的火车。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餐,谨慎地打听了一番后才知道,这家餐馆的老板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为人相当和善。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三人房间,而且并没有向警察透露我们的消息。五天以来,这是我第一次能够脱掉外衣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妻子顺利地从旅馆里溜了出来。火车晚点了近一个小时。我利用这段时间给作战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讲述了关于柯普的事情——柯普无疑是被误抓的,前线迫切地需要他,有无数人可以证明他没有犯下任何过错……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人看到这封信,信写在一张从笔记簿上撕下来的纸上,由于我的手指还有些麻木,再加上我那生疏的西班牙文,字迹写得歪歪斜斜,十分潦草。可是无论如何,这封信,以及此前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半年过去了,柯普仍旧被关在监狱里(如果没有被枪毙的话),既没有接受审判,也没有获得释放。起初我们收到过他的两三封来信,是几个被释放的囚犯偷偷带出监狱后从法国寄过来的。信里反复讲到,他们被关在肮脏晦暗如洞穴般的牢笼里,吃的东西酸腐难忍却又整日食不果腹,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已经疾病缠身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护理,对于这些我已然十分了解,无论是从英国还是法国方面的朋友那里都能得到证实。不久前,柯普已被关进了一个“秘密监狱”,已经无法再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柯普只是几百名遭受迫害的外国人之一,而那些遭受如此迫害的西班牙人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终于,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边境。我们乘坐的火车有一节头等车厢和一节餐车,这还是我来西班牙之后第一次看到这样先进的火车,不久前加泰罗尼亚的火车还只有普通车厢。有两个侦探在我们的列车上来回转悠,挨个记下了每个外国人的名字。当他们在餐车上看到我们时,似乎立刻流露出了一种尊敬而略带兴奋的神情,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让人不得不感叹世事无常。就在六个月之前,那时无政府主义者仍权力在握,似乎只有无产阶级模样的人才能受到尊敬。当初来西班牙时,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斯的路上,一个推销员还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穿戴成这个样子去西班牙。赶快脱了那件高领衬衣,摘掉那条领带,否则巴塞罗那人会替你把它们从身上拽下来的。”虽然他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至少代表了当时多数人对加泰罗尼亚的认识。果然不出所料,进入西班牙边境后,一对穿戴考究的法国夫妇便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卫兵盯上了,我想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太像资本家了。然而,时至今日,一切都已是天壤之别。伪装成资产阶级已然成了一种逃命的手段。在签证处,他们仔细查看了嫌疑犯名单,幸运的是名单上并没有我们的名字,甚至连麦克奈尔的名字也不在名单上,这还要多亏了西班牙警察低效能的业务水平。我们从头到脚被搜查了一遍,但没发现任何相关的犯罪证据,除了我的那张退役批文。而搜查我的那位士兵并不知道我所在的二十九师就是马统工党的民兵队。我们总算闯过了这一关。再次登上法国的土地已是半年之后。那时,我仅有的西班牙纪念品是一只羊皮水壶和一盏阿拉贡农民用点燃的橄榄油来照明的小铁油灯,这个小油灯是我在一个废弃的小屋里捡到的,其形状酷似两千多年前罗马人使用的赤陶灯,我把它塞进了行李箱。
事实证明,我们走得非常及时。我们看到的第一张报纸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间谍罪缉拿麦克奈尔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宣布这一消息时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在法国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是不在引渡范围之内的。
不知人们是否想过当离开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烟草店,买了满满几口袋的雪茄和香烟,直到衣服口袋装不下为止。然后我们进了一家自助餐馆喝了一杯茶,这是多少个日日夜夜以来我喝到的第一杯加了鲜牛奶的茶。几天以前我就曾想,到了法国就可以任何时候都能买到烟草了。然而我也会偶尔幻想烟草店的大门紧闭,窗口挂着“暂无烟草”的告示牌的那种情景。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打算去巴黎,我和妻子则在巴纽尔斯车站下了车,巴纽尔斯火车站是铁路沿线的第一站,我们已经感到十分疲劳,迫切需要休息。然而,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当知道我们来自西班牙时,人们便接二连三地问:“西班牙?你是作为哪派参战的?政府一边?哦!”接下来就是明显的冷落。这里的人看上去都在坚定地支持佛朗哥,当然,这无疑是受了那些一批又一批逃到这里避难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个拥护佛朗哥的西班牙服务生,每次给我上饮料时都会仰着头轻蔑地看我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人对西班牙政府的党派很抵触,同时不同的派系间也在不断地明争暗斗,与巴塞罗那的情形不相上下。那里有一个咖啡馆,只要你进了那个咖啡馆并提到“马统工党”几个字,就能够立刻结交到法国朋友,服务生也会对你笑脸相迎。
我们在巴纽尔斯大概停留了三天,这三天我一直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困扰着。这里只是一个安静的海滨城市,听不到手榴弹和机枪的声音,没有排着长队抢购粮食的人群,没有漫天飞舞的宣传性言论和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我本应感到轻松、欣慰。可是,我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在这里并没有消失或淡去半分;相反,那一切似乎仍在我的眼前,并且越发地清晰起来,我们总会想起那段岁月,会不知不觉地谈起曾经的经历,过往的一幕幕常常偷偷地袭进我们的睡梦里。那个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说,“只要离开西班牙”,我便穿越地中海,去往随便哪个地方,在那里过一段安安静静、闲适垂钓的日子;可是,如今我身在巴纽尔斯这个海滨小城,心中却是无尽的厌烦和失望。海风阵阵,凉气袭人,暗淡的海面上波涛翻滚,漂浮的泡沫、木渣、动物的脏腑和成坨成堆的垃圾一股脑朝海边的岩石冲刷过来。说出来也许会被人认为是我精神失常,但是此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尽管这样做可能对我没好处,甚至是引火烧身,但我最希望的还是能和那些人关在一起。我想我无法更加详尽而真切地描述那几个月在西班牙的经历对我一生的意义,虽然我记录下了具体的事件表象,但我无法形容这段经历留给我的亲身感受,仿佛在品尝一道充斥着视觉、嗅觉和听觉的大杂烩,那种感受是文字所不能够穷其意味的。战壕里泥土的气味和着汗水和雨水;山脊后黎明的曙光缓缓升起,照亮无垠的大地;呼啸的子弹和炸弹发出声声震耳的鸣响和刺眼的寒光;腊月里清新而寒冷的早晨,兵营中留下的士兵们晨练的足迹,那时候的他们还满怀着对革命的信仰;排着长长的队伍抢购食物的人群、红黑相间的马统工党旗帜,还有民兵们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尤其是那些与我一起战斗在前线的兄弟,如今却已天各一方,杳无音信,他们有的惨死沙场,有人落得终身残疾,还有人已经身陷囹圄。但是我真心地祝福他们,祝他们平安、健康,期待他们能够早日赢得战争,驱逐敌寇,将那些德国纳粹、苏联共产党还有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统统赶出西班牙。在这场战争中,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战争留给我的只有噩梦般的回忆,但我为有这样的一场经历而无怨无悔。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它终究是一场令世界震惊的灾难,它所造成的伤害远不止肉体上的残害和屠戮所带来的痛苦。然而奇怪的是,当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它所带来的也许并不是理想的幻灭或对现实的讽刺,而是让我更加坚信人类崇高而神圣的品质。
但愿我的叙述不会造成人们太多的误解,但是我相信,面对一场规模如此宏大,过程如此复杂的战争,没有人能够完全真实地将它描述出来,若非亲眼看见,任何事情都无法确定,任何人的描述都会有意无意地站在某一党派的立场、掺杂了某种党派情感。如果之前的内容忽略了这些,那么请允许我在这里做一些补充:请注意我的党派身份,在此基础上请原谅我在某些事实的描述中存在的错误,由于我所目睹的事情缺乏综合的视角,在部分事实的描述中难免以偏概全。同时,这也是人们在阅读每一本关于记录这场西班牙战争的书籍时应当注意的几点。
我和妻子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而在这里我们完全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决定提前离开巴纽尔斯。随着列车向北行进,这片土地变得越来越葱绿,越来越柔媚。离开了山峦和枯藤,又看到了草地和榆树。在我去年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已是一片萧条和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成本低,人们还不知道希特勒。而今的巴黎已是米珠薪桂,人们都生活在对战争的恐惧中,那些我所熟悉的咖啡馆多半已经因为生意惨淡而关门,不过对于刚刚离开西班牙的我们来说,即便是现在的巴黎也是那样明快艳丽而富有生机。那里有一个大型展会正**迭起,但是我们却无心去理会。
终于回到了英国——这里是英国的南方,大概也是世界上风光最秀丽的地方了。长时间在海上颠簸后,我从晕船中逐渐恢复过来,发现自己坐在接船的专用列车上,身体下面是豪华的丝绒坐垫,你很难相信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日本在地震、中国在闹饥荒、墨西哥正在掀起一场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依然会有牛奶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星期五依然能够看到《新政治家》报。这里远离重工业的都市,污染的浓烟和惨淡的生活被掩藏在了地平线的背后。这里依然是我儿时熟悉的英国:火车驶过深陷的路堑,两侧是漫山遍野的花朵;马儿在郁郁葱葱的草地上时而恬静地吃草,时而低头沉思;低垂的杨柳下潺潺的溪水轻轻地流淌;榆树上榆钱朵朵,沉沉地挂满枝头;农舍周围的红花绿叶,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泥泞的河滩上停泊的船只,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是记忆中的模样;海报栏上继续书写着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士们依旧戴着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鸽子依然在纵情嬉戏;红色的公共汽车,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仿佛一切都在大地的怀抱中静静地沉睡。沉睡中的英国啊,真希望我们永远不会醒来,希望那咆哮的炸弹永远不要惊醒我们甜美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