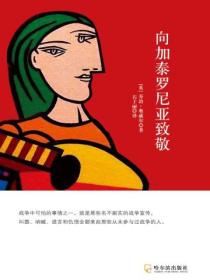向着战场前进
巴尔瓦斯特罗,虽然距离战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也同样衰破而荒凉。民兵们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地在街头走来走去,试图让自己暖和一些。在一堵残壁上我看到了一张去年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强壮的公牛”将会在某某日在决斗场上被干掉。这张海报看上去是那么的破旧,像是被人遗弃的。如今那些强壮的公牛和斗牛士都去哪儿了呢?似乎即使在今天的巴塞罗那也很少看到斗牛表演了,由于种种原因,最好的斗牛士恐怕都是法西斯主义分子了。
我们的队伍被卡车送到了谢塔莫,然后又往前到了阿尔库维耶雷,在战场对面的萨拉戈萨背后驻扎了下来。谢塔莫是十月才被无政府主义者拿下的,之前已遭受过至少三次攻击,多数都遭受过炮轰,房屋都已弹痕累累,很多地方已被战火炸成了碎片。我们在海拔五百多米的高地,这里天寒地冻,烟雾四起。在谢塔莫和阿尔库维耶雷之间,司机迷路了,在战争中这种事已是家常便饭。我们一直在迷雾中徘徊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赶到阿尔库维耶雷。我们被带着穿过一片沼泽地,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骡厩,于是便一头倒在谷壳上很快地睡着了。如果谷壳干净的话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比不上干草,但是比稻草好多了。然而我们直到第二天天亮时才发现,谷壳里满是面包屑、报纸碎片、骨头、死老鼠和被老鼠撕碎的牛奶盒。
快到前线了,我好像已经闻到了战争的味道——凭经验,应该是粪便和食物的腐臭味。比起战场后方被炮轰过的村庄,阿尔库维耶雷的状况要好很多。可是直觉告诉我,即使没有战争,你也会对阿拉贡村庄——这块西班牙的土地——脏腐不堪、恶臭难闻的状况感到吃惊。每座村庄都像一座城堡,泥浆和石头堆砌的小土屋一座挨一座地挤在教堂旁边。这里没有花红柳绿的春天,更没有花园,只有在后院的马粪堆里觅食的羽翼残缺的家禽。天气十分恶劣,时而雨雾迷蒙。狭窄的小土路已经完全被雨水冲成了泥浆,有时候泥水竟达到一尺多深,车轮不得不以疾驰的速度转动。农民们赶着一群骡子拉来了笨重的大车,有时候不得不用到六头骡子,甚至更多,骡子前后纵列地拉着大车。整个村庄被接踵而来的部队搞得十分肮脏。这里从未有过厕所,或任何形式的排污沟。几乎没有哪怕一平方米的地方可以不用仔细察看一下便能落脚。长期以来,教堂被当作厕所使用,教堂周围一百二十米内的所有地方,也被派上了同样的用场。每当我回想起参战前的那两个月,眼前总是那些严冬里粪便林立的土地。
两天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拿到武器。如果你去作战委员会看过墙上成排的弹孔——这些弹孔是步枪齐射造成的,各类法西斯分子在这里被执行枪决——阿尔库维耶雷的一切便在眼前了。前线一切都很平静,几乎很少有伤员。最让人振奋的是,那些法西斯战线的逃兵从前线被押着回来。我们的敌人中有很多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而只不过是在战争爆发前正在服役的士兵,他们只是急于逃跑而已,偶尔有几个在冒险通过我们的防线时被抓到了。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很多人的家属都还在法西斯领土上,还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所谓的法西斯。我没有想到他们除了穿着卡其布军装外,和我们并没什么不同。他们个个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连续两天在无人区东躲西藏,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人们总是将这些作为胜利的证据,宣扬法西斯分子们都饿得食不果腹。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俘虏在农民的家里吃东西的情景,他十分可怜。二十岁的小伙子,大高个子却衣不蔽体,露出被风吹裂了的皮肤。他蹲在火炉旁,迅速地把一碗鱼汤倒入嘴里,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环绕他的敌人。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们是嗜血如魔的“赤字军”,会在他吃完断头饭后立即枪决他。押解他的士兵不住地拍着他的肩膀示意他放宽心。有一次,十五个逃兵被押在一位骑白马的军官身后绕街游行以示胜利,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拍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后来还被别人偷走了。
第三天上午,终于要发放武器了。一个褐色皮肤,外貌粗糙的队长在骡厩里发放步枪。当我拿到那把步枪时我简直绝望了,那是一把一八九六年的德国毛瑟枪——已经过时四十年了!枪身已生锈,扳机已经发涩,很难扣动,枪身后端已经裂开,我瞄了一眼枪口,枪膛已经锈蚀,这把枪几乎已经不能用了。几乎所有的枪都是如此,有些甚至更糟糕。然而没有一个人曾想到把最好的武器发给会用它的人。这批武器里最好的要算是一支十年前制造的步枪了,它被分给了一个十五岁还有点弱智的男孩,大家都叫他“maricóon”。队长给我们做了五分钟的“指导”,包括如何给枪装卸子弹。很多人前半生从未摸过枪,我想几乎没有人知道瞄准器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发了五十颗子弹,这样队伍就算组成了。我们跨上装备,向三英里以外的战场进发。
一个团,八十号人加上几条狗,就这样七零八落地上路了。每个排都至少有一条狗来作为吉祥物,其中有一个家伙身上还刻了“POUM”几个大字,那家伙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奇怪的形象,怯怯地跟在队伍后面。队首骑着黑马,和旗手并列行进的是一位粗壮的比利时指挥官,叫乔治·科普。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像土匪的民兵队伍里的年轻士兵,他骑着马不停地前后奔跑,每逢高坡便驾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顶点时便摆个别致的造型。这些骑兵队里的好马都是革命期间四处征集后才转交给民兵队的,可他们却只顾着将它们骑到累死为止。
这条路自从去年秋收后就再也无人问津,孤独地沿着两边贫瘠的黄土地蜿蜒地伸展开来。前面就是夹在阿尔库维耶雷和萨拉戈萨中间的低山脉了。一切都越来越近了——战场,泥土,冲锋枪还有炮火。说实话,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知道,此刻的战场只是暂时的安静罢了,我脑海中浮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景,虽然那时我还没到参战的年纪。战争对于我来说,就是咆哮的子弹和疾速穿扬的钢片,更是泥土和虱子,寒冷与饥饿。奇怪的是,我惧怕寒冷更甚于惧怕敌人,在巴塞罗那的那段日子里,这种困扰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我:当我在深夜里躺在冰冷的战壕中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当恐怖的黎明时分我们不得不做好战斗准备的时候;当我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抱着冰冷的步枪站岗的时候;当那冰冷的泥浆淹没我的靴子的时候;还有当我看到这些和我一起行进的人的时候。我承认,我的确感到了一种恐惧。人们一定无法想象我们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就像一群游牧的羊群一样散漫地走在人群中,毫无队形可言,没走两英里后面的队伍就不见了。所谓的男人多半都是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孩子,最大的也就十六岁。然而,每当想到战场时他们都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快到前线时,队首围着旗手的几个孩子开始高呼“马统工党万岁”“法西斯猪”。然而,这些类似战争和恐吓的口号从这些孩子气的嗓音里出来,就像小猫的哭声一样楚楚可怜。如果共和国的守卫者必须是一群扛着破旧的步枪,对打枪一无所知,衣衫褴褛的孩子,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当时甚至怀疑,即使法西斯的战机从我们身边飞过,他们都会不屑于俯冲下来用步枪开出对我们毫不费力的一击。可以肯定,即使在空中,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判断出这绝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
小路伸向了连绵起伏的小山,我们拐向了右边的岔路,跟着马蹄印顺着蜿蜒的小路向山坡上爬去。这里的小山十分奇特,形状颇像马蹄形,山顶扁平,而山坡却非常陡峭,俯瞰下去是无边无际的沟壑。山坡高处,除了一些矮木丛和石楠类植物外,没有生长任何其他东西,满眼望去,只有白色的石灰岩。在这样的山区地带,前线不可能是相连接的战壕,而是一系列设在每个小山顶上的、有加固防御工事的岗哨,也就是常说的“阵地”。远远地,你便可以在那座马蹄形山顶上望到我们的阵地:简陋的沙袋筑成的壁垒,风中飘扬的红旗,防空洞里升起的炊烟。稍近一点,你就会闻到一股略带甜意的刺鼻的臭味,这种令人作呕的臭味一直在我鼻孔里好几个星期,挥之不去。在紧挨着阵地后面的小沟里,几个月的垃圾都被一股脑儿地堆在那里,有与粪便混在一起的腐烂的面包和锈蚀的罐头盒。
由我们轮换的一个分队正在打包行李,他们已经在前线待了三个月了,制服几乎变成了泥巴壳,脚上的靴子已经皮开肉绽、四分五裂,胡子像杂草般凌乱不堪。指挥这个阵地的队长从自己的防空洞里钻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他叫莱温斯基,但是大家都叫他本杰明,他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不过他的母语是法语。他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头发又黑又硬,苍白却不乏热情的脸在这样的战争时期总是免不了带着污垢。几颗流弹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我们的阵地是个直径约五十米的半圆形,阵地的护墙一半由沙袋组成,一半由石灰岩筑就。大约三四十个像老鼠洞一样的防空洞直通到地下。我,威廉和他的西班牙小舅子就近发现了一个可住人的还未被占领的防空洞,便飞快地冲了下去。前面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周围的山石上传出连绵不绝的回声。当我们刚刚扔下装备,打算钻出防空洞时紧接着又是另一声枪响,队里的一个男孩从护墙里冲回来,脸上冒着鲜血。原来是他自己放了一枪,当他试图拉紧枪栓时弹盒突然爆炸,他的头皮也被炸掀了好几块。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伤员,而且是典型的自伤。
下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防护。本杰明带我们环顾了一下阵地。护墙前面的岩石缝中劈出了一条狭长的壕沟,还用岩石堆出了一些简陋的射击孔。那里有十二个岗哨,分布于战壕和护墙内的不同的部位。战壕前面是铁丝网,再前面就是在陡峭的山坡下一眼看不到边的峡谷。战壕对面是毫无遮拦的群山,到处是壁石悬崖,暗淡而凄凉,飞禽不栖,寸草不生。我小心翼翼地透过射击孔往外瞄了一眼,试图找到法西斯的战壕。
“敌人都去哪儿了?”
本杰明使劲儿地挥着手臂,对我说:“Over zere.”(等同于Over there,意为“那里”,这里形容本杰明的英语口音很重)。
“可是,在哪儿呢?”
根据我对堑壕战的了解,法西斯战壕可能在五十到一百米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很明显,敌人的战壕极为隐蔽。失望之余我朝着本杰明所指的方向望去,在隔着峡谷至少有七百米距离的对面的山头上,隐约可见胸墙的轮廓和红黄相间的两色旗帜,那就是法西斯阵地了。此时,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沮丧。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靠近敌人,这个距离根本做不了任何事。然而就在这时,传来了一声激动的呐喊声。远远望去,两个只能看到淡灰色身影的法西斯士兵正在顺着对面的光秃秃的山坡往上爬。本杰明拿起身边伙计手里的步枪,瞄准其中一个,扣下了扳机。只听“咔嗒”一声,原来枪没打响,我立刻觉得这是种不祥的征兆。
那些新哨兵一跳进战壕便开始漫无目的地开枪射击。我看到那些法西斯分子,渺小得像蝼蚁一样,在护栏后面来回躲闪,时而还会有个黑点大的脑袋有恃无恐地在外面暴露片刻,此时开枪简直毫无意义。然而,这时我左边的士兵突然离开了他自己的岗位——这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做派——侧摸过来,劝我赶紧开枪。我努力向他解释,在这么远的射程外,就凭这种步枪,除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击中对方。但他毕竟是个孩子,不停地用他的枪试图瞄准其中的一个脑袋。他咧着嘴,龇着牙,急切地等待着,好像一只猎犬等待一颗被扔过来的石头一样。终于,我瞄准了七百米之外的一个地方,开了一枪,那颗黑点消失了。真希望子弹够近,能够让他哪怕被吓一跳也好。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活人开枪。
这便是我看到的战场,我对这一切深感厌恶。他们竟然称之为战争!我们甚至根本没碰到过敌人,我都不曾想到在战壕里将头低下去躲避一下。然而,顷刻之间,一颗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砰的一声射进了后躲避面的背墙中。天啊!我急忙躲避。前半辈子我曾经发誓,我绝不会躲避向我射来的第一颗子弹,但这似乎是一种本能,而且似乎每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至少躲避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