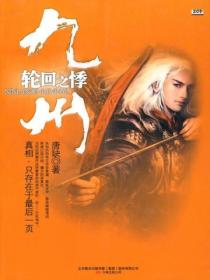夜色下的南淮城有着迷人的景致。那些破烂的棚屋、泥泞的小道、堆满垃圾苍蝇乱飞的街区,以及浑身汗臭的力夫与衣不遮体的乞丐,在暗淡的光线下都隐去了身形,不再像白昼那样丑陋而刺眼,南淮城剩下的只有一片流光溢彩的明丽。这时候站在高处俯瞰南淮,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座城市的贫富差别,以城中心王宫附近为分界线,越往北走,越是灯火通明,那些据说能八班边城照亮的灿烂火烛,与天空中的皓月繁星交相辉映,体现着繁荣的南淮的勃勃生机。
往南却正好相反,灯火越来越疏,越来越少,完全不成气候。等到了这座高塔的脚下是,除了亲王府内部之外,外围一圈几乎是漆黑一片。暗夜隐藏了所有的污秽和罪恶,不安定的因素就在其中静默地流动。这里是贫困与犯罪的温床。
“我见识过各种稀奇古怪的有权有势的人,你这样的还真是第一次见,”云湛说,“非要住在这种穷人扎堆的地方做什么呢?当然你本身就是个黑道头子,倒也不怕有什么小偷来偷袭。”
“所以我遭受了报应,”石隆叹了口气,“让自己的女儿在家门口被人绑架走,之间音讯全无。”
说话的时候,两人正站在观景塔的高处,距离顶部约有五分之一的差距,因为再往上的石梯因为年久失修而毁坏了,而石隆也无心再去修葺。不过这个高度也足够了,可以一眼望到楚唐平原的辽阔远方,把南淮城的全景尽收眼底。这一层塔四周特意没有封住,视野很开阔,当然高处的风也很猛烈,但对两个习武之人而言,也不算什么。
“以前各族还打得热闹的时候,斗兽场里生意很不错,几乎天天都有精彩的角斗,其中夸父和狰的肉搏更是受人欢迎,”石隆伸手指着如怪兽般匍匐在黑夜中的斗兽场遗址,“那时候贵族们都以能在斗兽场里获得一个好座位为荣,为此还经常发生点纠纷。所以这座石塔最早的主人,一位品级不算太高、总不能获得好座位的贵族一怒之下开始兴建观景台,想要在斗兽场之外另出机杼地解决自己观看斗兽的难题。”
“于是他心满意足了?”云湛问。
石隆摇摇头:“没来得及。这座高塔足足建了有一年多,结果就在竣工的那一天,还没能等到看上一场角斗,南淮城就被敌国攻破了。这之后整个九州陷入了长时期的战乱中,知道和平重新到来,斗兽场再也没有启用过一次,终于完全被遗弃。”
“真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啊。”云湛没心没肺地感慨说。
“所以我站在这里远眺的时候,经常在想着那位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了的贵族的遭遇,”石隆凝视着远方,“那么挖空心思地想出来这个主意,又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营建,到了最后,却什么都没能得到。而这世上又有多少和他一样,殚精竭虑地做着注定没有收获的蠢事呢?”
云湛思索了一会儿:“你好像挺有感慨的,是在解释你从来不去参与政事的原因吗?”
石隆懒洋洋地往身前的石头栏杆上一倚:“政事?老实告诉你,我连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从来不去参与政事’的心情都没有,因为那件事半点也不好玩。我只做好玩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花费心力建造一座注定没有用的高塔,只要做这件事的过程合我心意,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原来我猜反了啊,”云湛揪揪鼻子,:“说来说去,你无非是想告诉我,你和那位无名贵族其实是同一种人。所以你才喜欢这座塔。”
石隆一笑:“这一点算你说对了。我当年打听清楚这座塔的来历之后,就很想成为它的新主人。我几乎可以想象那位无名贵族的心情:永远居于人下,永远不可能在斗兽场重争到最好的位置,虽然在平民们心目中是引人羡慕的阶层,但和其他贵族比起来,他又只是被挤在角落里的小角色。怀着那样心情的人,也许心里就憋着一口气,想要做出点什么来吧?即便是一次都没有使用就被敌国破城,即使是对旁人没有意义、完全属于彻头彻尾的蠢事,对他自己来说,却未必全无意义。筑建这座塔本身,就是意义。”
云湛本来想挖苦两句,石隆说的话却触动了他的记忆,让他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想起那段没落贵族的压抑生活。我又何尝不是在做着那样的蠢事呢?他想着。那时候不好好念书,不好好习武,拿着每个月的月例钱到赌场鬼混,图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想证明,尽管我是一个出身没落贵族的小虾米,尽管我是一个身为羽人却飞不起来的可怜虫,我的生活轨迹也该由我自己来把握,假如没办法把握的话,哪怕让他多转一个微小的角度也好。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很久没有说话。下方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窸窸窣窣扫地的声音,那是负责定期扫塔的一名仆妇一层层打扫上来。他大概是发现主人在上层站着,不敢惊动,于是停了下来,就在下一层静静地等着。
“夜深了,回去休息吧,”石隆说,“也不要耽误下人的时间了。你上来打扫吧!”
回到洪英为他准备好的客房后,云湛仍然思绪不断,难以入眠。他发现虽然自己背负着天驱的名誉和重担,仿佛是要为某种理想拼搏奋斗一生的样子,但实质上,自己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仍然只是那个在泥潭中拼命挣扎,想要把握住自己命运的不安分少年而已。
他又想到了石隆。石隆刚才的一番话,是不是也在暗示这点他自己的心情呢?所谓身居人下无法出头,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多种解读的方式。一个吃不饱饭的穷人是无法出头,一个赚不到大钱的游侠是无法出头,一个在斗兽场占不到好位置的小贵族还是无法出头。
同样的,一个当不了国王的王子,纵然身份再尊贵,是不是也算一种“无法出头”呢?因为在他的头顶,始终压着一国之君的巨大权势,让他无法翻越。就算他真的参与议政,也永远是那个没有决断权的人。
云湛忽然间睡意全无:石隆是不是在用所谓的筑塔,来隐喻他的心事?他是不是想要说明,他从来就对诱人的王权压根不感兴趣?
他越回味石隆的话,越觉得其中含有深意。这些事情,对大多数人而言意义重大,对某一小撮人却并无用途;与之相反的,旁人浑不在意的弹丸小事,对其他人却可能关系重大。石隆决不会无缘无故邀请自己上塔,他一定是想表达些什么。
这是石隆试图为自己撇清么?云湛躺在黑暗中,双眼虚空地望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回想着自己与石隆两次会面时他语言中的细节,想要努力揣摩这位枭雄的性格和思维。这个人生性好武,不爱受拘束,喜欢混迹黑道;这个人脾气古怪,和国主关系冷淡,和其他王公贵族都不亲近,唯一感情不错的偏偏是性格孤僻生人勿近的太子;这个人年轻时鲁莽冲动,听说是个满嘴脏话的粗鲁汉子,人到中年却开始收敛,把自己装扮得活像一个道学先生,那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宝贝女儿,为了这个女儿,他好像做什么都可以。
很随性,很固执,很不通常理的性格,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性格。
他叹了口气,内心有点沉重,因为他越揣测石隆的心理,越觉得自己的推理在被石隆的暗示所左右,以至于无法真正地揣测到他的用心。同时他也知道,石隆这样倔强不合群的偏激性格,一旦下决心要干什么事,就很难被人劝服收手。他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尊严,不管眼前这场重大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想要弄清楚根底并且化解掉,还真是困难重重啊。
正想到这里,他忽然觉得有什么突如其来的光线在他眼前闪过,确切说,那只是一道离得很远的闪光,在他的眼里留下微小的痕迹,换了常人,大概根本不会留意到。他也并不在意,抬起头来,闪光消失了,什么都没有。
但耳朵里却在这时候听到一点响动,像是有野猫从院墙上翻过。联想到刚才的微光,他忽然警惕起来:会不会是有什么人入侵?难道天罗一直追杀到了这里?他站起身来,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
其实不用他仔细听,因为亲王府里马上就喧嚣声大作,无数的脚步声乱纷纷地响起。反正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云湛把椅子搬回屋,慢悠悠循声踱过去想要看看热闹。他有些惊讶地发现,喧哗的源头竟然指向亲王石隆的寝室方向。
洪英自然已经带着侍卫们赶到,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一望而知身怀武艺的家伙围在石隆的寝室外,一定都是石隆的黑道朋友与手下,忠诚护卫之心可见一斑。石隆已经披衣出来,神情镇定自若,倒不愧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角色。他招呼云湛说:“不好意思,来了个小刺客,吵扰你睡觉了。”
他的语气很平淡,云湛却是一怔:“刺客?不是吧,谁那么大胆来刺杀你?”
石隆摇摇头:“那可不知道了,只能等天亮后把尸体送到衙门去认了。”
尸体?看来这不自量力的刺客已经偷鸡不成,反而把自己的小命蚀进去了。云湛上前几步,看着地上那具被黑色夜行衣包裹着的尸体。他的面罩已经被扯开,露出一张充满惊惧的年轻人的脸。看来此人虽然胆大包天前来刺杀石隆,临死的时候,毕竟还是知道害怕的。
“可惜没能抓活的,”石隆遗憾地说,“我的这些伙伴们为了保护我,下手稍重了点,不然还能问问有没有主使者。我不认识这个人的脸,也许是花钱雇来的刺客或者是什么仇家的后人吧。”
云湛没有接茬,蹲下身子,借着仆人们点起的火把,看着死者身上的伤口。他的夜行衣上有若干淌着血的破损,无疑是护卫石隆的武士们干的,但最致命的伤口却是在咽喉,那里有一个极小极细的血洞。
洪英在云湛耳边说:“已经搜查过了,身上没有任何表明身份的物品。”
“是谁杀了他?”云湛问,“手法干净利落啊。”
“大概是那些……那些黑道的……朋友吧,”洪英毕竟还是对江湖人士有点成见,说到“朋友”两字颇有点生硬,“我也不好一一追究,毕竟他们是好意保护王爷。你先休息去吧,刺杀这种事常见,我们都习惯了,不过敢到亲王府里来动手的还真不多。”
云湛点点头,站起身来:“这里没我什么事,我先回去睡觉了。”他一边往回走,一边试图接续在被这起深夜刺杀打断前的思路。但是倦意涌了上来,他并没有多想下去。
“如果真如你所料的话,事情就很不好办了,”石秋瞳面有忧色,“我这位可怜的伯父,郁郁一生,什么事都不顺,什么事都不被人理解,确实已经够恼火的了。他要是真想做什么大动作,那就绝对不会收手,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云湛呵欠连天:“困死我了,猜谜猜了一晚上,还参观了一具刺客的尸体。总之呢,石隆的心态相当不好,他专门向我提到那个筑建高塔的贵族,也许是想解释什么,但我觉得其实是欲盖弥彰。而女儿的失踪对石隆更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如果他本来就有政变的心愿,这件事算是把他想着歇斯底里又多推出了一步。我再问你个问题:就好比那个筑塔的无名贵族,当他发现建好了塔之后,仍然不会帮助他在斗兽场里获得一个好位置时,他会干什么?”
“把塔拆掉么?”石秋瞳问。
“从没发现你那么善良过,”云湛翻着白眼,“拆塔有什么意思?要拆就拆掉斗兽场,而且要拆得巧妙,让别人完全看不出痕迹来。”
石秋瞳打了个寒战,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想了想,紧皱着眉头:“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也不能明着不让亲王靠近太子吧?”
“装病!”云湛一瞪眼,“宣布太子染病,什么人都不见!再增加护卫人手,以防万一。”
石秋瞳点点头,忽然叹了口气:“幸好有你,这些事情牵扯到自己的亲人,我都有些手足无措了。”
“世道凶猛,人心险恶,”云湛做智者状拍拍石秋瞳的肩膀,“你还得多学着点。”
“人心是不是险恶也许我看不出来,但我知道你的近况很险恶,惹上什么麻烦了吧?”石秋瞳问。
云湛死要面子:“哪儿来什么麻烦,昨晚没睡好而已。”
石秋瞳哼了一声:“一两个晚上不睡觉可造不出您这样比金鱼还漂亮的眼睛。恐怕是有什么东西搅得你彻夜难眠吧?”
云湛差点冲口而出“因为惦记着你还不行么”,又觉得这样的玩笑千万不能乱开,所以只是无精打采地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会解决的,你就别掺和了,来了也是添乱。”
石秋瞳没有生气:“看来的确是很大的麻烦,你都不敢让我插手。”
云湛站起身来,没有回答,径直向着门口走去,忽然眼前一花,石秋瞳已经拦在了身前。他叹口气:“小姐,你不要什么事都想管一把成不?”
“别自作多情,”石秋瞳悠悠地说,“你现在正接受着我的委托,要是半道丢了小命,我到哪儿找人赔我的预付款?”
“那我现在就把预付款退给你。”云湛真的作势掏钱,然而手还没放进怀里,手腕已经被石秋瞳一把抓住。石秋瞳自幼习武,力气本来不小,这一下又毫不留力,捏得云湛哇哇乱叫:“我只退预付款,可不能连手一起赔给你!”
“如果你死了,陪什么都无所谓了,”石秋瞳狠狠一甩手,“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就算是一年前南淮被叛军围困时,我也没见过你这么忧心忡忡就跟死了娘似的样子。到底是什么事?”
云湛愁眉苦脸地揉着自己发青的手腕:“这个么……说来话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