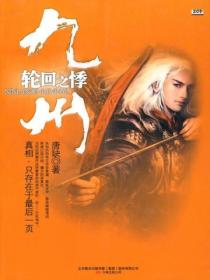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最紧要的线索,这是一切探案课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一句最大的废话。一方面这话不假,稍微有点头脑的罪犯就不会傻到让自己在某桩案子里显得醒目,唯恐别人不去抓他;另一方面,光南淮城就有几十万人口,要细筛每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只怕把真正的凶手找到时,他都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但是办案总是这样,绝大多数时候做的都是枯燥无比的工作,在一条街上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着千篇一律的无聊问题,然后再转向下一条街。席峻锋总喜欢充满感情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出道时做的这种体力活,并以此激励下属们继续替他玩命地跑腿。
“还有一句废话是这样的,”席峻锋还喜欢这么说,“嫌疑犯可能就是你调查的下一个人。这当然也是标准废话,但遗憾的是,真理往往包容在废话之中。”
“你不如直接明说,真理就包含在您老的命令里。”陈智撅着嘴。为了查找第二位死者所住的二层房子的买主,他已经把原房主、那位死去的赌鬼的人际圈子都问遍了,此人常去的几家赌场里的人都已经对他很熟了。但该赌鬼一直孑然一身,也没有妻子儿女,至于他当年赌场上的朋友,除了收钱和给钱,原本也不会在意其他。被问到的人当中,十之八九都已经忘记了曾经有那么一个人存在过。
不过席峻锋并不会轻易罢休:“再去城里其他那个赌鬼不去的赌坊也问问,赌鬼不去,不见得其他和他赌钱的人也不去,看有没有人还对那家伙留有印象。此外,问过的人再问一遍,记忆这东西就像女人的心,你只刺激一次未必能有反应,死缠烂打才能有所收获……”
这话说得轻松随意,却包含了更加巨大的工作量,陈智只觉得喉头一腥,直想一口血喷到席峻锋脸上。可恨的在于,席峻锋平时在工作里总是比自己的下属更卖命,这让他们没什么借口去推三阻四。
陈智嘴里嘟哝着出去了,席峻锋又转向了刘厚荣:“怎么样,那个奇怪的文身,有方向了吗?”
他所问的文身,指的是那具被抽掉骨头的死尸身上的文身,形状有点像枣糕,席峻锋凭直觉认为这不像是标榜个性的私人文身,而是某种组织的标志。他这一直觉不打紧,刘厚荣先是排除了已知的各地黑帮,又开始翻检历史存留的邪教资料,但始终一无所获。
刘厚荣都懒得回答了,只是大幅度地摇着头,然后把自己熬得通红的眼睛亮给席峻锋看。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罕见的文身被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解决了。
南淮城这些日子正好有一个几乎不为人所知的集会,那是一帮子来自九州各地的星相学家的聚会。事实上,除了部分愚民真的相信星相能够指引人的命运、并心甘情愿地给街头打着星相旗号的骗子送钱之外,多数人还是对此漠然置之,一个全九州水准最高的星相大师,或许并不比一个三流戏子更有名。简而言之,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没人认识他们,没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所以此次并不声张的聚会引起了衙门关注,那些来自外地的陌生的夸父、河络、羽人和人数更多的人类忽然凑在一起扎堆,难免让人联想到些带有危险性质的事情。而在两天的监视过去,终于弄明白他们是在研讨星相学时,这样的担忧不减反增。要知道,在历史上的历次大型战争中,总会有星相师跳出来胡言乱语指点天下命运,为自己拥戴的君主造势,眼下这些星相师来到南淮,谁能保证没点这方面的打算?
为防万一,直接受国主调派、不由兵部统辖的南淮猛虎卫直接介入此事,并随便找了个借口从中绑架了几名星相师拉回去审讯,确定他们只是在合法地讨论学术问题后才放人。此事不必详述,但在审讯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插曲,一名猛虎卫无意间发现,被抓去的河络族星相师的袖口绣着一个标记,这个标记看上去有点眼熟。
这位猛虎卫想了很久,终于想起来了,前两天他一位在按察司办差的朋友曾给他看过一个图样,好像和眼前的标记挺像的。于是这个不幸的河络眼睁睁看着其他同行们被释放,自己却被移交给了另一批人。该河络脾气倔强,颇有学者风骨,心里打定了主意,只要一见到准备审讯自己的第二拨人,就破口大骂,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结果蒙眼布一摘掉,他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具恐怖至极的尸体,就好像正在融化的蜡人一样,软绵绵的好不恶心。而第二眼,他看到了尸体右肩上的文身。他一下子张口结舌,已经准备好的骂人的言辞(要记熟这些东陆语的骂人话可真不容易呢)顷刻间忘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脱口而出的文法错误的惊呼:“这是部落我们的徽记!”
“你们是什么部落?”虽然河络用错了文法,席峻锋还是听明白了他的话。
“越州,塔颜部落,”河络慢慢地镇静下来,开始端详那张毫无血色的死人脸,“这个人,我认得。我们部落的记名弟子。”
席峻锋倒有点佩服这个矮矮小小的河络了,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他能够迅速回过神来,可见也是个不一般的人物。虽然他的东陆语说得比较生硬,但至少能表达清楚意思,很快地,这个失去了骨头的男人的身份弄明白了。
他是越州的河络部落塔颜部落的记名弟子,名字叫做张星,当然,也有可能只是化名。这个部落藏在沼泽深处,向来不爱与其他同族通气,只是埋头钻研星相学,更不用提与异族交流了。所以张星这样一个人类能成为他们的记名弟子,实在是太罕见了,难怪这位河络很快就认出了他。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执著的人,”河络回忆说,“我们河络部落的入口处通常有障眼秘术保护,外人很难找到,那时候他在附近足足找了三个月,嘴里不停高喊着他的目的,诉说着他的诚意。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让他进入,但我们感于他的诚挚,破例派出一位星相师,教授了他一段时间星相知识,所以他也算作我们的记名弟子,还在身上烙下了部落印记。你问我这个印记代表什么?哦,不是枣糕,它代表的是算筹,算学是星相学的基础……”
更多的信息他也没法提供了,因为这帮一心扑在学问上的河络们甚至没有费心去打听此人的身世背景,反正很少有人能用星相学去作恶。但他所讲述的那些,已经足够席峻锋去继续调查了,有黑道背景的人虽然多如牛毛,但在这其中会有兴趣学习星相学的却寥寥无几——那就像老虎吃草一样奇怪。在老虎群里找出吃草的那一只异类并不难,活资料库刘厚荣很快就找到了此人的真实身份:“真名叫张剑星,名字里虽然带个‘剑’字,却是个痴迷星相学的刀客,武功极高,但脑子有点一根筋。由于一次意外的巧合,少年时代一位星相师的预言碰巧成真,救了他一命,从此他总觉得自己的命运是由天空中的命星确定的,四处寻访星相名家,搅得别人焦头烂额的。他本来是中州大帮派锁河盟的头号高手,因为星相耽误了好几次大事,也因此被锁河盟忍痛驱逐了,此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也许就是去了越州拜访塔颜部落吧。再往后……再往后……”
席峻锋注意到了刘厚荣的迟疑:“怎么了?再往后发生了什么?”
刘厚荣吞吞吐吐地回答:“一年半之前,他过去在帮派里结下的仇家发现了他的下落,联合起来找他晦气,他寡不敌众,被逼得走投无路,幸好有人救了他,并从此收留了他,直到半年前,好像就没有听说他的动向了。”
“谁收留了他?”席峻锋追问。
刘厚荣的声音很无奈:“国主的哥哥,隆亲王石隆。”
查出张剑星真实身份的第二天清晨,第二位死者的身份也终于有了重要进展,不过不是通过查询房主这样的迂回线路,而是从死者的遗物里找到了一点线索。
第二位死者是女性,房间内遗留了不少杂物,席峻锋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手下把所有东西都一股脑搬回去,然后指派了一名叫做霍坚的捕快分析遗物。霍坚已经五十出头,驼背瘸腿,头发掉了大半,眼神也相当不好,不戴着河络磨制的眼镜根本看不清东西,但所谓人不可貌相,此人年轻时可是个风流人物,在九州各地到处流窜,靠着出色的手工艺制作千奇百怪的小玩意儿,勾搭良家妇女。他的瘸腿就是在这样的生涯中不幸被某良家妇女的丈夫发现而打折的。由于去过的地方多,对各地风土人情、尤其手工制品有相当了解,霍坚被慧眼识英雄的席俊峰看中,破格录用到手下,负责替他鉴别证物。
霍坚有一张大到可以供几个人在上面站着跳舞的大木桌,需要鉴别的物品在上面堆积如山。他就趴在桌前,在镜片后面眯缝着眼,面对着一大堆梳子、镜子、木屐、女人的内衣之类的玩意儿伏案工作,但从来不肯早到和晚走,严格遵循着规定的工作时间,到点就回家吃饭睡觉。捕快们心急如火,却也没人好意思去催促这么一个身带残疾的老头子。
所以老头子注定要先把大家折磨够了,在带来点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在确定了张剑星的身份之后的翌日早晨,霍坚撑着拐杖慢腾腾走进捕房,在桌前坐定后说:“哦,我昨晚找到了一点线索。这个女人要么是从雷州来的,要么在雷州客居过很长一段时间。”
捕快们两忙围上来,席俊峰很不满意地问:“你昨晚找到的,为什么今天才说?”
“因为我找出线索的时候,已经到收工的时候了,”霍坚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是会儿告诉你们,你们肯定得逼着我解说,那就耽搁我的吃饭时间了。”
众人气得牙痒痒的,却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乖乖听他解释。他拿起了一把伞骨粗大,伞面厚实的雨伞:“比如这把伞,几乎是雷州女人随身的物品。别看它有点笨重,却是在雷州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因为雷州的城市大多靠海,又多风多雨,天气变化很大,经常在半天之内轮番出现烈日当头和暴雨倾盆,雨伞是必不可少的。而海边风大,宛州女人用的小油纸伞只怕几分钟就被吹散架了。我当年在雷州的时候,遇到过……”
“闭嘴,”席俊峰很有经验地打断他,“说下一样,别回忆你的情史了。”
霍坚遗憾地放下伞,在桌上的破烂里左翻右翻,又找出了一把普通的牛角梳子:“这梳子的做工用料没什么特别,但上面装饰用的花纹是波浪形,也比较符合雷州人崇拜海神的特色。我当年在雷州的时候,有一个……”
“闭嘴。”席俊峰说。霍坚叹了口气,又拿起几样东西,一一指点出其雷州特色并试图回忆他的浪漫史,这时候接连熬夜工作而一直睡眼朦胧的刘厚荣一个不小心,整个身体趴到了桌上,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撞到了地上。霍坚吹胡子瞪眼,近乎咆哮着指挥捕快们把那些“重要的物证”一一捡起来,但有一个小瓷瓶还是不幸在地上跌破了,装着的膏药流了一地。刘厚荣正像那簸箕来清理,霍坚却忽然费力地蹲下,用手指头蘸了一点膏药放在鼻端,用力嗅了嗅。
“这瓶子是柳妍坊的,那是宛州本地的胭脂坊,所以我一直没留心,没想到她用空瓶装了别的,”霍坚摇着头,“要不然答案早就出来了——这个女人不只在雷州住过,恐怕本身就是雷州人。”
“这是什么?”刘厚荣凑过来,闻到一阵刺鼻的药味。
“雷州人毛发比较重,爱漂亮的女人如果一伸出胳膊就露出汗毛,未免不大好看,所以他们会准备一种特殊的膏药来脱毛,保持皮肤的光洁,”霍坚又陷入了对往事的遐想中,“我当年在雷州的时候……”
这次没人打断他。所有人都离开他的木桌,继续商议去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唠叨不休。
死者来自雷州,只是解决了第一步的问题,毕竟南淮是宛州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来往于南淮的雷州人数量不少,总不能一一盘问他们吧?再说这具女尸变成了这副模样,只怕自己的老公来了——如果有的话——也没法认出来。
就在大家都有些愁眉不展的时候,陈智步履蹒跚地回来了。按照席俊峰的指示,他真的又到了那位死去的赌鬼基本不去的通宵营业的赌场里去,继续打听赌鬼的信息。这项工作自然导致了他一夜未睡。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眉宇间充满了得意之情,这让席俊峰立马意识到,他问出了点什么。
“还真找到了一个赌客还记得那个死掉的赌鬼,”陈志往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去,满眼血丝,脸颊似乎都瘦得少了两块肉,“那家伙一向以记性好著称,在他面前翻过的牌就能过目不忘,所以在赌场里颇能赢点钱,也只有他那种记性,才能记得死赌鬼的事情。他这样的人不受赌场和其他赌徒们的欢迎,总是换地方,难怪我之前没有找到他。”
“以前我说过,听我的话总是没错,鲜花往往开在最远的山谷。”席俊峰颇有几分洋洋自得,“那家伙告诉了你些什么?”
“他也曾经对死赌鬼的房子很感兴趣,但那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开价比他高,最后没有拿下来,他很不服气,曾经找了几个兄弟想要去找那个不知名买家的麻烦,结果打探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后,吓得再也不敢动这个念头了。你们猜,高价买下那层房子的人是谁?”陈智做神秘状。
捕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智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神情都有点怪异,好像都明白过来点什么。
“你们不会真猜到了吧?”陈智嘟哝着。
席俊峰没有回答他,而是直接把头转向了刘厚荣:“隆亲王果然是有钱人,他的手下不会有很多来自雷州的女人吧?”
刘厚荣想了想:“我能想得起来的只有一个。桑白露,出生于雷州北部城市白露弥,但自幼在毕钵罗港长大的女神偷,同时是公认的江湖上数一数二的探险者,精通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技巧。她曾在南淮被捕,但被亲王保了出来,并替她偿还了所盗窃的赃款。以后她就跟着亲王,直到半年前失踪。”
“亲王的这个习惯我倒是有所耳闻,”席俊峰说,“这个人从年轻时代开始,就以讲义气、够朋友而著称。他在宛州各地都化名购置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房子,算得上是未雨绸缪;万一手下或者朋友犯了什么事,就把那些事先买好的房子交给他们住下避难。也亏了那个赌徒为了想复仇而真的去调查了,不然她的身份还揭不出来呢。”
“也就是说,这个桑白露在半年前犯下了什么事,于是到这个房子里躲了起来。”陈智若有所悟。
“头儿,张剑星也从半年前开始不在旁人的视野里出现了。”刘厚荣插嘴说。
席俊峰思索了一阵子,缓缓地说:“这两个死者都是石隆的手下,都在半年前失踪,然后都在这几天被杀。这不大像是巧合啊。”
众人默然,脑子里不约而同地想着:这件事要是和石隆有关系该怎么办。那可是国主的哥哥,一条几乎不可能碰的大鳄鱼,即使他犯了什么事,只要国主不想管,只怕别人也管不了。不房里的气氛变得凝重,捕快们无论入行早晚,还从来没有碰过这样身份的角色。该怎么处理这种经常凌驾于律法之上的巨大权力,他们还真是心里没数。
席俊峰咳嗽一声:“别想那么多。现在只是证实了死者曾经是石隆的属下而已,其他一切都不能确定,也许石隆和本案是完全无关的。”
这话说得很勉强,至少桑白露所住的地方就是石隆提供的,但在这种时候,总得有点类似的救命稻草来捞。席俊峰接着说:“别的先不管,按部就班,继续查案。”
不知不觉间,人们都开始用名字来称呼这位尊贵的亲王了。一名捕快发着牢骚:“怎么继续查?打上亲王府去,直接追问石隆?兄弟们的脑袋还要不要啊。”
“不到万不得已,别去惊动石隆,”席俊峰沉思者,“只能拐弯抹角,从他们的其他关系上入手。真的把苗头引到了石隆身上……那就再说。我不新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大得过律法。”
这句话倒是说得挺坚定,但从捕快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真的被鼓舞。律法就好比一把大小固定的菜刀,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外露锋芒,毕竟刀身太短太小,宰鸡屠狗还好,想要用来杀死一只老虎,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一群人正在满腹牢,一件早已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补房的门被推开,一个捕快匆匆进来,对席俊峰耳语了两句。
席俊峰嘴角浮现出一丝含义不明地微笑:“好了,大家一直期待的第三宗杀人案出现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这个死者会不会又是石隆的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