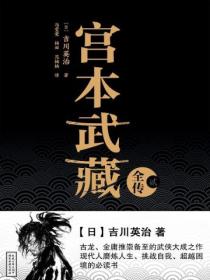木曾冠者
一
那个路人告诉武藏,有一个浪人在离关卡的茶馆不远的地方截住了那位女子,然后鞭打那牛,连人带牛一并劫走了。这一消息立刻在街内炸开了锅,搞得人尽皆知。
武藏一直待在山丘上,所以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一变故的就只剩他了!
从出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刻钟,要是阿通真的遇到什么危险,那还来得及去救她吗?武藏立刻跑到了那家茶馆前。
“老板!老板!”
关卡的木栅门在下午六点关闭,茶馆的老板正在收拾桌子。他回头望着气喘吁吁的武藏,问他:“你落什么东西了吗?”
“不是,大约半刻钟之前,有一位女子带着一个小男孩从这里经过,您看到了吗?”
“你是指那位坐在牛背上像普贤菩萨的女子吗?”
“嗯,没错!听说他们二人被一个浪人给劫走了,您知道去哪里了吗?”
“我没亲眼看到,不过听来往的人说,他们从前面首塚那个地方被拐到了旁边的小道,往野妇池方向去了。”
顺着老板手指的方向,武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在苍茫暮色中。
综合路人的说法,武藏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架阿通。
武藏万万没有想到下手的正是本位田又八。武藏从比睿山的无动寺前往大津的过程中,在山顶的一间茶馆内碰见了又八,两人尽释五年前结下的仇怨,恢复了幼时的朋友之情,并且还约好一起去江户。
武藏紧握又八的双手,眼神中饱含真诚和期待。
“之前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它随风飘散吧!你要认真修行,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武藏的鼓励令又八感激涕零,又八欣然地说:“嗯,我要认真修行,重新做人。你是我的兄长,要多多指教我呀!”
就是这样一个又八!武藏根本不可能将他和劫持阿通的人联系到一起!
武藏猜测,劫持阿通的人可能会是浪人中的卑鄙小人,也有可能是在世间投机取巧的小蟊贼、人贩子,甚至还有可能是劫道的武夫。如果这些都不是,那极有可能就是地方上彪悍的野武士了。
武藏现在根本搞不清对手是谁,他现在既着急又紧张,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去野妇池寻找线索。此时,天已经大黑,天空虽布满星光,地上却是伸手不见五指。
武藏按照茶馆老板的指示,去野妇池寻找,但是找遍了所有的地点,也没发现一块像池塘的地方。田地和森林都是倾斜的,道路也在一点点变陡,武藏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驹岳山脚的某个地方——武藏是彻底迷路了!
“好像走错路了?”
武藏环顾四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在驹岳的巨大山体底下,有一处被防风林包围着的农家院落。透过树林可以看见熊熊燃烧的炉火,将周围的木篱笆映得通红。
武藏走向前去,一眼就看到了院子里的那头花斑母牛,但是没有发现阿通。牛被拴在了厨房外面,正在无聊地“哞哞”叫着。
二
“……哦!花斑母牛!”
武藏松了一口气。
牛在这里,那毫无疑问,阿通肯定也被劫持到了这里。
可是……
这处民宅位于防风林中,住的究竟是何许人呢?武藏思虑再三,决定先观察一下,以免打草惊蛇,对阿通不利。
武藏躲在外面窥探屋内情形。
“娘,您休息一下吧!您老说自己眼睛不好,可还偏要在那么暗的地方干活,快别干了!”
声音有些大,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传来,旁边堆放着一些柴草和稻壳。
武藏屏气凝神探听屋内的动静。厨房的隔壁有一个房间,里面生着炉火,火光摇曳,映得整个屋子通红。可能是从这间屋子,也可能是从隔壁有着破格子门的房间,传出了轻微的纺线声。
那位母亲听到儿子的劝说,赶紧停止手头的工作,纺线声戛然而止。
儿子在隔壁的屋子里,似乎在忙着什么。他起身出来,顺手带上了拉门,对母亲说:“娘,我出去洗洗脚,然后咱吃饭!”
厨房的旁边有一条引水沟,清清的泉水正在静静地流淌。儿子拎着一双草鞋,来到引水沟边,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石头上,用清水涮了两三次脚。这时,那头花斑母牛悄悄地将头探到那男子肩膀后。
那男子摸摸牛鼻尖,对始终没有作声的母亲大喊:“娘,等您忙完了,快出来看啊!我今天可捡到大便宜了!您猜是什么?一头牛!而且还是一头优质母牛。不仅可以耕地,还可以挤奶呢!”
武藏站在篱笆门外听得一清二楚。如果他当时再耐心一些,搞清楚对方的底细之后在行动,就不会酿成后来的过错了。武藏觉得自己侦察得差不多了,就找到入口,悄悄地潜入院子。
虽然是一处农宅,但非常宽敞。墙壁有些破旧,应该是一处老宅。
屋子里没有长工,也没有女佣。茅草屋顶上长满了青苔,没人打理,远远望去,像一座废宅。
“……?”
武藏来到亮着灯光的窗前,踩着窗下的石头向屋里窥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长刀,正挂在对面的墙壁上。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拥有这种刀,至少也是颇有来头的武将才能使用。皮革刀鞘上的金箔花纹虽已褪色,但仍依稀可辨。
看来——
武藏思前想后,更加狐疑。
刚才,微弱的灯光映射着洗脚男子的脸庞,那眼神让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
那人身着及腰粗布衣,裹着满是泥渍的绑腿,腰上还别着一把刀。
大圆脸盘子,头发蓬乱,自眼角处用稻草束起,眼角上挑,显得炯炯有神。胸肌强健,腿脚麻利。武藏一见此人,就觉得他非常可疑。
“肯定是这家伙干的!”
铺着蔺草的房间内空无一人,松枝在巨大的火炉中熊熊燃烧着,释放的浓烟“呼”的一声从窗户中顶出来。
“……咳!咳!”
这下把武藏呛了个够呛,他赶紧用袖口捂住口鼻,但还是发出了咳嗽声。
“谁?”
厨房内传来老太婆的声音。武藏赶紧躲到窗户底下。那老太婆貌似走进了有炉子的房子,吆喝儿子说:“权之助,仓库的门锁好了吗?好像又有小偷来偷栗子了。”
三
“来了更好,我正愁抓不到他们呢!”
武藏打算先抓住那壮汉,然后逼他招出把阿通藏在了哪里。
那名壮汉看起来非常勇猛。武藏怕过会儿缠斗起来,如果再从里面窜出几个壮汉来,那可就麻烦了。如果只对付这一个,那还好说。
武藏趁老太婆喊着“权之助、权之助”的时候,赶紧从窗下逃走,躲到外侧的树底下去了。
那名叫权之助的男子大步流星地跑过来。
“在哪里?”
他大声地问:“娘,贼呢?在哪里呢?”
老太婆靠着窗边。
“在那边,刚才我还听到咳嗽声呢!”
“您不会是听错了吧?娘,您最近不是有些眼花耳背嘛!”
“不会错的!肯定是有人站在窗子外面偷看,结果被烟给呛了!”
“真的吗?”
权之助像巡逻城墙一样,在屋子周边转了几圈,嘴里嘀咕着。
“经您这么一说,我还真闻到生人味了!”
武藏见权之助眼中充满杀机,所以没敢贸然现身。
权之助将自己从脚趾武装到胸口,没给对手留下任何偷袭的空隙。
武藏想弄清楚他手上究竟拿了什么东西,所以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最后武藏终于看清了,原来在他的右手内侧一直到肘部之间,藏着一根四尺长的圆木棍。
那不是普通的擀面杖,也不是简单的棒子,更不是随随便便的树枝,而是一种闪着光泽的武器——在武藏看来,圆木棍已经和权之助合二为一,无论何时,权之助都不会将棍离手。
“喂!谁在那里?”
权之助猛地挥出木棍,带来一阵疾风。风从武藏鼻尖吹过,武藏稍一闪身,木棍从他肩旁落下。
“我来向你要人。”
权之助盯着武藏,沉默不语。武藏厉声说道:“赶紧把那女子和孩童交出来。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二人的背后就是一道天然屏障——驹岳山。每当夜幕降临,从驹岳山的雪溪中经常会吹来阵阵刺骨的寒风。武藏第三次要求:“赶紧把人交出来!”
武藏的语气比寒风还要冷峻。权之助反手握着木棍,那眼神宛如要将武藏吃掉一般,头发一根根全都立了起来,远远望去,活像一只大刺猬。
“你这狗杂种!你以为是我掳走的啊?”
“肯定就是你。你看他们两人好欺负,于是就将他们劫持到了这里——快点把人交出来!”
“你,你说什么?”
权之助突然挥出四尺多长的圆木棍——速度之快,让人难以分清究竟是木棍,还是手臂。
四
武藏除了躲闪之外,别无他法。权之助的武艺精湛,再加上他体力超群,这让武藏吃了一惊。武藏后退数步,警告他说:“赶紧把人交出来,不然可别后悔!”
权之助将一根木棍使得上下翻飞,没有一点纰漏,厉声回应说:“少啰唆,看打!”
二人缠斗在一起,难舍难分,武藏后退十步,权之助紧跟十步,后退五步,权之助紧跟五步。
武藏在躲闪过程中,一度两次抓住了自己的刀柄,但是对方速度太快,武藏根本没时间将刀拔出,迫于形势,最终被迫放弃。
因为在手握上刀柄的那一瞬间,肘部就会暴露在敌人面前,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武藏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小心,这也因敌人而异。有时敌人比较弱,他就不需要顾及这么多,但一旦碰到强敌,就不得不戒备了。权之助的攻击速度远远超出了武藏的预想,如果小看他是一介草民,逞一时之勇,那可能就要挨闷棍了。虽然对方显得有些急躁,但是呼吸均匀,出招过程中无半点破绽,这让武藏觉得此人绝非泛泛之辈。
武藏在一开始步步躲闪,处处戒备,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摸一下权之助的底细。
权之助的棍术中藏着固定的章法,他的步伐矫健,身姿灵敏,在武藏看来,这俨然就是“金刚不坏”之身。乍看上去,权之助浑身上下透出泥土的气息,但是挥起棍来,从内到外却无不透出武术之道。武藏碰见的高手无数,但其中无人能匹敌此农夫的武艺。而且权之助身上散发出“武士道精神”的光芒,正是武藏梦寐以求却尚未达到的境界。
众位看官,见我如此叙述武藏的内心世界,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慢悠悠地对峙了良久。其实,这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权之助的木棍没有片刻停息,一直如雨点般进攻。
“噢!”
权之助用全身的力气发出一声闷吼。
“呀!”
他拳打脚踢,而且还不断变换出棍的招数。他嘴中骂骂咧咧。
“你这狗东西!”
“王八蛋!”
权之助将一根木棍使得如同一把长刀,他有时单手握棍,有时双手握棍,或打,或抽,或刺,或旋,变化万千。
长刀一般分为刀刃和刀柄两部分,而且只有刀刃可以伤人,但木棍就不一样了,它不分前后上下,哪里都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根木棍被权之助使得如同糖果店里的软糖一样,可长可短,让人看着都心生胆战。
“阿权,小心啊,对方可不是泛泛之辈哟!”
他的老母亲突然从堂屋窗口喊道。权之助的老母亲虽然没有参战,但是已经发现眼前的这名年轻人是自己和儿子的大敌。只听权之助宽慰母亲说:“娘,您别担心。”
权之助得知母亲在一旁观战,愈加勇猛。武藏闪过权之助的一记攻击,然后趁此间隙,“嗖”地抓住了他的小臂。权之助犹如巨石压顶一般,“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跌了个四脚朝天。
“等一下!浪人!”
那名老母亲担心儿子安危,猛捶窗子大喊。凄厉的叫声透过窗户的竹格子传出,愤怒的面相也让武藏开始犹豫要不要进一步攻击。
五
母子连心,骨肉之情让老母亲急得毛发竖立。
看到儿子被摔到地上,老母亲也颇感意外——按照常理,武藏摔倒权之助之后,要在对方爬起之前,冲上去补上一刀。
然而武藏当时并没有那么做。
“哦!我等你!”
武藏骑在权之助的胸口,用脚踩着他的右手腕,抬头望着老母亲刚才在的那个小窗口。
“……?”
武藏面露惊讶。
窗口内,已经没了老母亲的身影。被武藏压在身下的权之助还在拼命地挣扎,努力想挣脱武藏的束缚。他拼命地蹬着腿,企图靠腰部和腿部力量挽回败局。
老母亲觉得大意不得,于是赶紧跑回厨房,拿上武器,冲了出来,指着权之助的鼻子大骂:“你这臭孩子,太不争气了!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你可不能再输了啊!”
武藏本以为那老母亲让自己等一下,是为了跑上前来,跪在自己面前,乞求饶她儿子一命。可没想到,这老太婆是为了激励她儿子,陪他继续战斗。
武藏瞧见老母亲的腋下夹着一把没鞘的长刀,在星光的照耀下,现出点点寒光。她站在武藏背后,喊道:“你这个瘦猴子!别以为欺负我们这样的草民就能帮你扬名立万,你还真以为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
武藏身子底下正压着一个大活人,他根本无暇去顾及身后的一切。
如果老母亲这时突然从背后攻击,那么武藏将很难应付。更何况权之助还在地上拼命地折腾,背上的衣服和皮肤都磨破了,只为给母亲赢得一个有利位置。
“这就是一个浪人!娘,您不用担心!您不用靠得太近,看我现在就打倒他!”
权之助虽被压在地上,但依旧嘴硬。老母亲嘱咐他:“你别急躁!”
又接着说:“怎么能够输给这种野浪人?我们的先祖那可是大英雄,木曾家族大名鼎鼎的大夫房觉明的血流到哪里去了?”
听母亲这么一说,权之助大声喊道:“在我身上。”
他一边喊着,一边抬起头,一口就咬在了武藏的大腿上。
权之助已将木棍扔开,现在双手也自由了,再加上咬着武藏的大腿,弄得武藏难以招架。背后的老母亲也前来助阵,挥舞着长刀,向武藏砍去。
“等一下,老妈妈!”
这次换作武藏喊暂停了。武藏知道争斗并不能解决问题,再这样下去,双方肯定是不死即伤。
如果再继续下去,如果能够救得了阿通和城太郎,那也罢了,主要是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两人劫持了阿通和城太郎。武藏想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武藏要求老母亲先将长刀放下,但老母亲却没有立即答应,她问儿子:“阿权,你说怎么办?”
她想和被压在地上的儿子商量一下,看看要不要妥协。
六
火炉中的松枝燃烧得正旺。母子二人和武藏交流之后,才发现双方存在误会,最终冰释前嫌。
“哎呀!哎呀!真是好险啊!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
老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坐下休息一会儿。权之助也想坐下,可被老母亲制止了。
“权之助。”
“娘,什么事?”
“你先别坐下,带这位武士参观一下屋子——让他看看咱们没藏那位女子和孩童!”
“好的!您怀疑是我在大街上绑架了那女子和孩童,我实在是太冤枉了——您跟我来,这屋子您可以随便翻,随便看!”
武藏跟在权之助身后,脱掉草鞋进入屋内,坐在火炉前的草席上,和他们母子二人聊着天。
“我就不看了,你们是清白的!刚才怀疑你们,真的很抱歉!”
武藏诚挚地向对方道歉,权之助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做得也不对,要是先问清楚,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事儿了!”
说完,盘腿坐在火炉边。
话虽如此,但武藏依然没有打消心中的顾虑,刚才在门外看到的那头花斑母牛,确实是自己从比睿山带来的,途中把母牛让给了病弱的阿通来骑,而且城太郎还在前面牵着牛绳,怎么这会儿就给拴在了这家民宅的院子里了呢?
“你就因为那牛才怀疑我啊?”
权之助恍然大悟,赶紧将自己捡到母牛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武藏。
“不瞒您说,我在这附近有些田地。傍晚的时候,干完农活,我拿着渔网去野妇池捕鱼。当我走到池尻河的时候,发现那头花斑牛掉到了里面,正在淤泥里挣扎。淤泥很深,那牛越挣扎越往下陷。它难受啊!
就在那‘哞哞’地叫!我见它可怜,就把它拉上来了!拉上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一头还在哺乳的母牛。我去周边找它的主人,但没人认识,于是我就猜测这肯定是被哪个盗贼偷出来,然后给扔在那里的。您也知道,一头牛能顶得上半个劳力。我家里太穷,都不能好好供养老母亲,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可怜我,特意赐给我的礼物,于是就把它牵回家了!既然您是牛的主人,那就把它带走吧!至于您说的阿通和城太郎,我可是一概不知的呀!”
说到这里,一切都清楚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是什么强盗,而是一个率直质朴的农村汉子。率直是他的优点,可是正是这优点造成了刚才的误会。
“如此说来,您一定很担心他们吧!”
老母亲用慈爱的口吻对儿子说:“权之助,你快点吃,过会儿和这位武士一起去找找他那两位可怜的朋友。如果还在野妇池附近,那就好说了。如果被带到了驹岳山区,那可就麻烦了!那地区盗贼横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有时候连庄稼都偷。要是真被他们给劫持了,那他们二人可就凶多吉少了!”
七
火把的火焰在山风中摇曳。
一阵强风从山脚下出来,席卷草木,发出凄冷的声响。强风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武藏屏息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四周静悄悄的,唯有天幕中繁星在闪烁。
“朋友!”
权之助举起手中的火把,等着后面的武藏。
“真遗憾,没人看到他们。从这里到野妇池的途中,也就是那片杂木林的后面,还有一户人家,要是他们也不知道,那可就真没办法了!”
“今晚上谢谢你了!我们已经问了十几家,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可能是我走错方向了吧?”
“也许吧!那些绑架妇女的歹徒非常狡猾,他们是不可能往人多的地方去的。”
夜已过半。武藏和权之助几乎找遍了野妇村、毋口村等驹岳山脚下的所有村庄,就连附近的山丘和树林也都找了。
武藏本希望能够打听到一点线索,可是现在连见过他们的人都没有。
阿通姿色出众,凡是见过她的人,应该都会留下印象。可是,那些农民却都摇着头说:“没见过!”
武藏非常担心阿通和城太郎的安危。此外,权之助和自己毫无交情,却如此卖力地帮助自己,这也让武藏有些过意不去,更何况他明天还要下地干活。
“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真是对不起!我们再去问一家,如果还不知道的话,那我们也回去吧!”
“没关系了,就是走几步夜路而已!那名女子和孩童是您的仆人,还是家人呢?”
“他们是……”
武藏无法开口告诉对方那女子是自己的恋人,而那孩童是自己的徒弟,于是随口敷衍说:“他们是我的家人。”
也许是权之助同情武藏丢失了亲人,他没再接话儿,径自走向通往野妇池的杂木林的小路。
虽然现在武藏满脑子想的都是阿通和城太郎的安危,但又不得不感谢上天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也可以说是恶作剧吧!
要是阿通没有被人劫持,那么武藏就不可能遇见权之助,也就不可能领教他棍术的精彩。
武藏现在过的是流浪生活,难免不会与阿通走散。如果走散了,只要阿通安然无恙,那就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但在武藏的一生中,如果他不能领教权之助棍术的精彩,那肯定会成为他武士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武藏打从刚才就暗自盘算,一定要找机会问问他的门第,还要向他讨教棍术,但他同时也知道,问这些信息,提这些要求,都是非常不礼貌的。他内心有些犹豫,只好紧紧地跟在权之助后面。
权之助指着树林中的一间茅草屋对武藏说:“朋友,您先在这儿等一下——这户人家好像已经睡下了,我去把他们叫醒,问一下!”
权之助一个人拨开草丛,迈着大步走向前去敲门。
八
不一会儿,权之助就回来了,将询问的详情悉数告知了武藏。
住在那里的是一户猎户,他们的回答也是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不过据那女户主介绍,傍晚时分,她外出购物,途中遇到的一件事可能对武藏有所帮助。
当时天色已晚,天空中露出点点繁星,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寒风吹着两旁的行道树飒飒作响,显得非常冷清。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哭着向她跑来。
那孩子手上、脸上全是泥巴,腰上挂着一把木刀,向薮原的客栈方向飞快跑去。女户主拦住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孩子哭得更厉害了,问道:“能告诉我官府在什么地方吗?”
女户主有些好奇,就问他找官府干什么。那个孩子回答说:“我姐姐被坏人劫走了,我想求官府的人帮我找她!”
女户主告诉他,他去找官府也是白搭。因为官府的人,只有大人物从这儿经过,或者上级下命令时,才会手忙脚乱地捡拾马粪,甚至用黄沙铺道。至于市井小民的事情,根本入不了他们的耳朵,更甭说帮他去找人了。
尤其像绑架妇女、打家劫舍这样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根本不足为奇。
然后,女户主建议那男孩去找大藏先生。大藏先生就住在客栈后身的奈良井附近,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旁边。这人开了一间药铺,平时采集百草,治病救人,遇到别人有难,也都会积极帮忙。大藏先生和官府的老爷们完全不同,他态度温和,喜欢扶贫济弱。只要他觉得有必要的事,他都会倾囊相助。
权之助原封不动地将女户主的话语转告给武藏。
“那女户主还说,那个腰佩木剑的小男孩听完之后,立马停止了哭泣,一溜烟跑去找大藏先生了——她所说的小男孩,会不会就是您要找的城太郎呢?”
“嗯,肯定是他。”
武藏脑海中浮现出城太郎的身影。
“看来,我把方向给弄反了!”
“嗯,这里是驹岳山的山脚,而奈良井是在另一边,还很远的!”
“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这就去奈良井找大藏先生——今儿多亏你了,我现在稍稍有些头绪了。”
“反正您也得沿原路回去,不如回我家休息一宿,明天吃完早饭再去找!”
“那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我们渡过野妇池,然后从池尻回去,可以省一半的路程。我去借条小船。”
他们稍微往下走了一段,来到一个被杨柳环绕的池塘边。池塘不大,也就方圆六七百米。驹岳山以及漫天的繁星映满了整个池塘。
杨树和柳树在这一地区并不多见,不知为什么,池塘四周却长满了那么多杨柳。权之助将火把交给武藏,然后拿起船桨,向池塘中心划去。
火红的火把映在幽暗的池塘上,使得湖水也变得红亮。就在这时,阿通也看到了池塘上移动的火把。也许是命运弄人?也许是两人缘分尚浅?两人相隔如此之近,却彼此不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