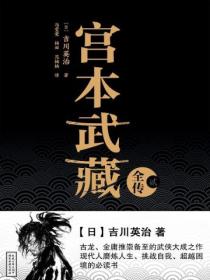焚虫
一
其中一个人将火绳衔在口中,好像正在推弹上膛。
另外一个人弓着腰,观察着对岸的动静。他们亲眼看到武藏倒了下去,但内心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应该死了吧!”
他小声询问伙伴。
拿着猎枪的那个人回答说:“肯定死了!”
他点点头。
“打中了。”
两人这才放下心,踩着独木桥向武藏走来。
当拿枪的那人走到桥中间时,武藏一跃而起。
“啊!——”
对方发出一声惊呼,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由于没有瞄准,子弹自然打空了,在天空中发出一阵声响之后,就消失在茫茫黑夜里。
两人连滚带爬,沿着河流逃走了。武藏异常气愤,在后面紧追不舍。
“喂!喂!跑什么啊?就一个人,我藤次就能应付得了,赶紧回来帮我!”
没带枪的那人停下脚步,招呼另一个人回来。
那人自称藤次,从他身上的装束来看,应该是此处山贼的头目。
“好——”
经他这么一吆喝,另一个山贼也转身回来了。
在一片慌乱中,火绳已经被他们弄丢了。只见那山贼反手握着猎枪,一步步向武藏逼近。
武藏马上觉察到这两人绝非简单的浪人,单从他们挥刀的动作来看,多少还有点水平。
但是,他们哪是武藏的对手,双方刚一交手,两个山贼就败下阵来。拿枪的那个山贼的衣服被武藏从肩膀开始划了一个大口子,山贼从岸边一下跌落到水流中去了。
山贼头目藤次捂着自己小臂的伤口,屁滚尿流地向上爬去。
在他的踩踏下,脚下的土石不断滑落,但武藏依然紧追不舍。
这是和田峰和大门峰的交界处,山谷中长满了山毛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山毛榉谷。武藏爬上山坡,发现一处被山毛榉围着的民宅。民宅由一根根山毛榉建成,比普通的山民住宅要大一些。
屋内透出亮光——
武藏发现一个人正拿着纸糊灯笼站在屋檐下。
山贼头目慌慌张张地逃向小木屋,压低声音呵斥道:“快把灯熄了!”
那人立即用袖子捂着灯笼,并问道:“出什么事了?”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哎呀,怎么这么多血——你受伤了没有?刚才我听见山谷方向有枪声,正担心呢!”
山贼头目回头观察,看有没有人追过来。
“笨……笨蛋!快点熄灯啊!屋里的灯也给灭了!”
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呵斥那个女人。
山贼头目连滚带爬地躲到屋内,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女人的身影也消失在一片夜色中。
武藏来到房前,发现屋内没有半点亮光,门窗也都关得紧紧的。
二
武藏怒不可遏。
但他并不是因为那浪人的卑鄙和虚伪而发怒,而是觉得这些像蝼蚁一样的渣滓竟然还能存在于这个世上,这着实让人心生气愤,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公愤吧!
“开门!”
武藏咆哮着。
当然对方是不会开门的。
木门破旧不堪,一脚就可以踹开,但武藏为了慎重起见,还是与木门保持了大约四尺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武藏,就是稍微有点经验的人,也不会贸然上去敲门,做那种破门而入的傻事。
“快开门!”
屋内依然一片寂静。
武藏抱起一块大石头,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向木门砸去。
石头正好砸在了两扇木门的接缝处,两扇木门应声倒地。就在这时,屋内突然飞出一把尖刀。接着,那个浪人连滚带爬地朝屋后逃去。
武藏一个箭步冲向前去,抓住了那人的衣领。
“啊!壮士饶命!”
坏人在阴谋失败,被对方捉住后,必然会这样低三下四地告饶。
那个浪人像一只大蜘蛛一样,被武藏紧紧地按在地上。虽然他口中告饶,但心中并未投降,他一直在找机会逃脱。正如武藏一开始所料,这个山贼头目确实有几把刷子。他很快就挣脱出来,挥拳打向武藏。他的拳法不错,凌厉且富有威力。
武藏也不敢大意,封住了对方打过来的每一拳。最后,眼看武藏就要制伏他了。那山贼开口骂道:“浑……浑蛋!”
山贼用尽全身的力气,腾空跃起,拔出短刀,向武藏刺来。
武藏赶紧闪躲,顺势喊道:“你这个鼠贼!”
武藏趁机捉住他的身体,“咚”的一声把他扔回到屋子里。大概是四肢撞上了炉子上的挂钩,使得挂钩上腐朽的竹子断裂开来,霎时炉口有如火山爆发般扬起一阵白灰。
在白茫茫的烟灰中,有人将锅盖、木柴、火钩子和陶器等所有能够抓到的东西全扔向武藏,以阻止武藏的逼近。
尘埃落定,定睛一看,往外扔东西的人原来不是那个山贼头目。他可能受了猛烈撞击,已经躺在柱子底下奄奄一息了。
貌似山贼妻子的女人抓起够得着的东西,拼命地向武藏砸来,口中还大骂着:“畜生!畜生!”
武藏迅速将女人按在地上——女人虽被压在下面,但她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朝武藏狠狠地刺去,口中依然大骂:“畜生!畜生!”
武藏眼疾手快,安全躲过了她的发簪,然后用脚踩住她的手。
“老公,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会败给这么一个臭小子!”
那女人咬牙切齿,失望地骂着已经失去意识的丈夫。
“啊?”
武藏不自觉地放开那个女人。她却比男人更为勇猛,立刻爬起身子,拾起丈夫掉落的短刀,又砍向武藏。
“呀,你是阿甲?”
女人愣了一下。
“欸?——”
她气喘吁吁地端详着武藏的脸。
“啊!你?……哦,你不是阿武吗?”
三
武藏面露诧异之色,毫不拘礼地凑上前去看那女人的面孔。
“哎呀!阿武,你都长成一名真正的武士了啊!”
女人的声音好生熟悉。她就是住在伊吹山的艾草屋——后来将女儿朱实卖入妓院,并在京都经营茶馆的阿甲。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这么一问啊,我还真是有些羞于启口。”
“那个倒在地上的人……是你家男人吗?”
“你可能也认识他,他是以前吉冈武馆的祇园藤次。”
“啊!那人竟是吉冈门下的祇园藤次,怎么会沦落到……”
武藏赶紧闭口,后面的话就不再说了。
吉冈一派没落之前,藤次卷着建武馆的所有钱款和阿甲一起私奔了。当时京都的百姓骂声如潮,都说这么卑鄙的男人,不配做一名武士。
武藏对此也略有耳闻,但没想到藤次竟然落魄到如此境地。虽然此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心中也不免替他感到悲哀。
“阿甲,您快去看看他吧!要是早知是您丈夫,我就不下那么重的手了!”
“哎呀!别说了,我现在就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阿甲扶起藤次,给他喂水,包扎伤口。藤次仍处于半昏迷状态,但阿甲还是向他介绍起武藏。
“啊?”
藤次猛地惊醒过来,抬头望着武藏。
“原来你就是宫本武藏——哎呀!我真是没脸见你啊!”
藤次抱着头表示歉意,久久不愿抬起头来。
放弃武学,带着女人私奔,然后落草为寇,这一切若从大处来看,也许是他命运使然,是今生已定的安排,但若从小处来看,活得如此落魄,真的是又可怜又可悲。
武藏将刚才的怒火全都抛到脑后。他帮这对夫妻扫屋子,擦炉子,还给灶膛添上薪柴,就像要迎接贵宾一般。
“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先喝点酒吧!”
武藏看他们要去温酒,就赶紧劝住说:“别麻烦了,我刚才在山上吃饱喝足了!”
“我们好久没聊天了,就尝尝我做的酒菜,一起聊聊天吧!”
说完,阿甲便将锅放在炉子上,并且还拿出了酒壶。
“这令人想起在伊吹山的山麓的日子。”
屋外,山风怒吼着。虽然闭着门,但山风还是透过门缝吹了进来,刮得炉火噌噌地往屋顶蹿。
“朱实后来怎么样了?你有没有什么消息?”
“我听说她在从比睿山到大津的途中,在山上的一家茶馆逗留了数日,后来拿着又八的所有盘缠跑了……”
“唉,这孩子……”
阿甲觉得女儿朱实的遭遇比自己还要坎坷。
四
不只阿甲觉得惭愧,祇园藤次也是异常惭愧,他希望武藏能将今夜发生的事情全部抛到脑后。他恳求武藏:“若他日我能重振雄风,我必将以祇园藤次的身份向您道歉。如今我无脸向您说道歉的事儿,就先让今夜的不愉快随流水而去吧!”
已经沦为山贼的藤次即使恢复成以前的祇园藤次,那也不可能有大的变化,但考虑到自己和他同是天涯沦落人,武藏也就原谅他了。
“阿甲,您也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
武藏略带酒意,说出了自己的忠告。
“什么啊?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做这样的勾当。我们离开京都之后,本打算去新开发的江户谋生。可谁曾想到,走到半路,这个人在诹访的赌场把身上的钱全给输光了。实在没办法了,只能重操旧业,我们在山里采点草药,然后拿到城里去卖,换口饭吃。……今夜我们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
阿甲一喝点酒,就现出以前的媚态。
这个女人的姿色一点也没有受到年龄的影响。她就如同一只娇媚的母猫——如果被主人养在家里,会跳到主人的大腿上撒娇;如果被放到山里,那她就会变成两眼在暗夜里发出璀璨光芒的野猫,会觊觎那些得病路人的肉,也会爬到荒郊野外的棺材上,把里面的尸体吃个精光。
阿甲就是这种人。
“喂!亲爱的!”
阿甲回头望着藤次。
“听武藏刚才介绍,朱实那丫头好像也去江户了。我们也该离开这深山,去过正常人的日子了。要是能碰到她,说不定还能给我们出一些做生意的点子呢!……”
“好!好!”
藤次抱着膝盖,漫不经心地回应着。
本位田又八被这个女人抛弃之后,内心后悔不已。现在和阿甲同居的藤次,内心的苦闷应该和又八差不多吧!
武藏望着藤次的脸,感觉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可怜了。他又联想起又八,觉得又八也被这女人害苦了——想到自己差点受这女人的引诱而坠入万丈深渊,全身就禁不住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外面下雨了吗?”
武藏仰头看着黑乎乎的屋顶。阿甲抛着她那因酒醉而更增添几分娇柔的媚眼说:“没下雨!没下雨!就是风太大而已。树叶子啊,小树枝啊,经常会被刮过来,砸得屋顶“啪啪”响。在山里,一到晚上,没有一天天上不掉东西的。有时候,即使皓月当空,繁星满天,也还是会有树叶子、沙土什么的吹过来。有时起大雾,会有像瀑布的水珠飞溅过来。”
武藏点头回应道:“哦!”
藤次抬起头来。
“眼看天就亮了,武藏先生肯定也累了,你快去铺被子,让武藏先生休息吧!”
“好的,好的。阿武啊!这边黑,你先别过来啊!”
“恭敬不如从命,那我今晚就在这儿借住一宿了。”
武藏起身,随阿甲走入黑暗的走廊。
五
武藏睡的地方是一栋从悬崖上搭出的小木屋。夜里太黑,无法辨识下面的一切。也许在地板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慢慢地,山雾起来了。
在狂风的裹挟下,水珠击打着门窗。
每当一阵狂风吹过,小木屋都会摇晃几下,就好像在大海中行进的小船一样。
阿甲踮着白嫩的双脚,踩着竹片铺成的地板,悄悄地回到刚才的房间。
藤次盯着炉火,陷入沉思。听到阿甲回来后,他立刻瞪大双眼问她:“他睡了吗?”
阿甲双膝跪在藤次旁边,回答说:“好像睡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把兄弟们叫来。”
“真要那么做吗?”
“当然了!杀了他,不仅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还可以为吉冈门报仇,一举两得啊!”
“好,那我这就去。”
阿甲卷起袖口,向门外走去。
深夜。深山。黑暗中的狂风。疾走的白嫩的双脚。身后飘扬的秀发。这女人,如果不是一只充满妖术的母猫,又会是什么?
在大山的褶皱里,不只有鸟兽,还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人。随着阿甲的嫩脚走过山峰,走过沼泽,走过田地,在她的身后已经会集了二十多人。
这些人训练有素,走路的声音要比在地上翻滚的枯叶还要轻。大家悄悄地聚集在藤次的屋前。
“一个人吗?”
“是武士吗?”
“带着钱吗?”
众人交头接耳,同时用手语和眼神来交流,很快就按照平时的分工开始行动。
这群人有的拿着扎野猪的长矛,有的拿着猎枪,还有的拿着大刀,武器是各种各样。一部分人站在武藏睡觉的小木屋外,向里窥探。另一些人从小木屋旁边下到悬崖底下,静悄悄地埋伏好。
还有两三个人先爬到悬崖的半腰,然后再慢慢爬到小木屋的正下方。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
从悬崖上伸出的那栋小木屋,俨然已经陷入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
此外,在小木屋的草席上,还堆放着很多晾干的草药,故意摆了一些研磨草药和制药的工具。其实这些草药都有安眠作用,以使进入小木屋的人尽快沉沉入睡。这些人也不是采药、制药的山民,他们就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山贼。
武藏躺下之后,闻着药草的清香,感觉好舒服。再加上他劳累了一天,现在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疲乏得不得了,真想就这么睡去。不过对山里生山里长的武藏来说,这栋小木屋还是引起了他诸多的怀疑。
自己老家的山上,也有采草药的小屋,那都是建在朝阳的地方。草药是非常忌讳湿气的,按理说不可能把储藏草药的小木屋建在这种树木苍郁、杂草丛生的树荫下,况且还有瀑布的水珠会将屋子打湿。
在他的枕边有一个碾药的研磨台,台子上面有一个锈迹斑斑的灯台。武藏望着微微摇曳的灯芯,又发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屋内四个角落都是用木材连接起来的,木材与木材之间用锔子箍着,但锔子的排列却非常不整齐,而且接缝处木材的纹路也不一致,有一两寸的错位。
“啊!我懂了。”
武藏昏昏欲睡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但他的头仍枕在木枕上。
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武藏感到一种恐怖的气氛正在向自己靠拢。
六
“阿武……睡了吗?睡着了吗?”
阿甲靠在格子门外,低声试问。
阿甲仔细听着武藏的气息,拉开房门,轻轻来到武藏枕边。
“水给您放这里了!”
阿甲边放水盆,边故意凑近武藏的脸,以进一步确认武藏睡了没有。一切妥当之后,她悄悄退出了房间。
祇园藤次则将主屋的灯全给熄灭了。
“睡了吗?”
他小声询问阿甲,阿甲以眼神示意。
“睡熟了……”
藤次胸有成竹地跑到屋外,观察了一下黑暗中的山谷,然后开始挥动手中的火绳。
那是他们的信号。
信号一放,立即有人拔掉了插入山崖中起支撑作用的圆木。小木屋“轰隆”一声整个掉入了万丈深渊,摔得支离破碎。
“好!”
这群山贼就好像猎人捕获猎物一般,发出兴奋的欢呼。然后一个个像猿猴一样,蜂拥着下到谷底。
他们看到手中宽裕的路人,就会想一切办法骗他到这栋小木屋住宿。等到那人入睡了,他们就撤掉支撑的木柱,然后将人摔死,再从死者身上搜刮钱财。
事情过后,他们又会在悬崖上搭起另一栋简单的小木屋。
预先在谷底埋伏的山贼,看到小木屋摔碎之后,就如同一群恶狗一般,迅速聚拢过来,寻找武藏的遗骸。
“摔死了吗?”
上面的人也下来了。
“尸体呢?”
大家一起寻找。不知谁说了一句:“没见尸体啊!”
“胡说!蠢货,怎么可能没有尸体!”
这人找了一阵之后,想法开始动摇,他大声喊道:“真的没有啊!
那他会去哪里呢?”
藤次也紧张起来,他两眼布满血丝,大声吩咐道:“不可能!也许是中途撞到岩石弹开了,你们去那边找找看!”
藤次的话还没说完,只见山谷中的岩石、流水、山草全都变得通红,仿佛染上了夕阳的红晕。
“啊?——”
“天啊!——”
所有山贼都抬起头往上看,在七十多尺高的悬崖的上方,藤次的房屋正在熊熊燃烧。门里,窗户里,四周都在往外喷着火红的火焰。
“啊!啊!快来人啊!”
阿甲在发疯般呼喊着。
“不好,快去看看。”
山贼们抓着藤蔓攀上悬崖。藤次的屋子已经完全被山风和火焰包围了。阿甲脸上落满了烟灰,被反手绑在附近的一棵树上。
武藏什么时候逃走的呢?事到如今,他们仍不愿意相信武藏已经逃走了这一事实。这时,一个小喽啰喊道:“快去追,他肯定还在附近——”
藤次知道武藏的厉害,所以他根本不敢去追。但是,别的山贼没和武藏交过手,不知武藏的实力,所以一窝蜂似的追了出去。
荒野中已经没有了武藏的踪影,不知他是沿小路逃走了,还是正在树上呼呼大睡呢!在熊熊大火之间,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和田峰和大门峰又迎来了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