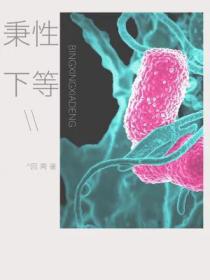白菱歌小时候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妈妈姓白,她姓白,哥哥季柠却姓“季”?直到十一二岁,有一次在学校和同学闲聊,她才恍然明白过来,原来这世上孩子都是要和爸爸姓的。哥哥姓季,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姓季。
倒也不怪她这方面知识匮乏,“父亲”在他们家至多只是个名词,从她出生起,听到的次数就屈指可数。为数不多的几次从他们母亲嘴里提及,还都伴随着崩溃的打骂。
凡是和“父亲”有关的,准没好事。这样的思想一旦产生,渐渐地,白菱歌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开始由好奇变为了纯然的排斥。
别人有爸爸,没事,她有哥哥。哥哥长得好看,会拉大提琴,学习好,性格好,还很宝贝她。
白菱歌与季柠差了八岁,季柠与其说是一个兄长,更像个长辈,在他们母亲忙于生活时,充当她的教导者,带她熟悉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
她依赖季柠,有时甚至比依赖母亲更依赖他。
对于哥哥的决定,她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就像季柠也总是包容她、支持她。
不过说到底,季柠从小到大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学习不用操心,练琴不用操心,听话懂事,还会替家里分担经济压力。作为儿子,作为兄长,他都是完美无瑕的,连最挑剔的人都没办法从他身上挑出毛病。
白菱歌以为他会一直这样完美下去的,但没想到,一场疾病打破了一切。
她的哥哥喜欢的是同性。
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信教,对男女之事管束得都很严,更不要说同性之间了。她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哥哥会喜欢上一个男人,这有点超出她的理解范围。
但因为是哥哥,所以哪怕不理解,不明白,她还是会支持他的选择,接纳他喜欢的人成为自己的家人,只要他快乐就好。
对于这一点,她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绝不轻易改变,但她不确定他们的妈妈是不是也存了同样的心思。
先前季柠生病,白秀英为儿子的事操碎了心,急白了头发,也没怎么表态。现在季柠病好了,不再有生命危险,白菱歌不确定白秀英还会不会同意两人的事。她不敢问,连提都不敢提。
整个暑假她们都在忙季柠生病的事和搬家的事,等好不容易空下来了,她也要开学了。
新生报到那一天,季柠和白秀英一道送她去学校,冉青庄负责开车。远远的屁股后面还坠着一辆,季柠让她不用在意,说那是保护他们的特警。
“案子不是结了吗?怎么还要保护。”她有些担心地问。
“保险起见还是需要再跟一阵子的,等确定了不会再有危险,他们就会撤了。”季柠原本剃掉的头发长回来了不少,虽然还是比以前短,但短得很精神,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时候,会有种从前没有的,温和又开朗的观感。
车里全是白菱歌与季柠在说话,季柠事无巨细地叮嘱她关于学习的事,关于和同学相处的事。白菱歌一个劲儿地点头,每句话都有认真听进去。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突然,白秀英毫无预兆地开口。
车内倏地一静,白菱歌整个紧张起来,心头涌起一种“来了来了,终于来了”的感慨。
季柠当然知道这话是问的他和冉青庄,停顿片刻,平静道:“我以后可能会在家里开设教学班,青庄的话,想在我们镇上开一家汽车修理厂。”
冉青庄的卧底过往,注定了今后需要小心谨慎的生活,无法做太过引人注目的工作,更不好回归警队。
其实政府每月都会支付他一笔“退休金”,让他不工作也能很好的生活,但他不愿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总想找点事做。汽修厂只是个设想,毕竟现在他们都还在接受警方的保护,没法自由行事。
白秀英闻言没有什么表示,表情沉着,一幅对季柠的回答不是很满意的模样。
前排开车的冉青庄在这时开口:“您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不会让季柠受苦的。”
白秀英哼了声,道:“你们有打算就好,我不掺和,随便你们。”
“哥,你们那时候军训热不热的?这几天感觉好热啊,我在想带的防晒霜够不够……”白菱歌赶忙岔开话题,心里想着,她妈嘴硬心软,既然说了不掺和,看来是不会棒打鸳鸯了。
到了学校,一车人下车。冉青庄开了后备箱,从里头取出大包小包许多东西,季柠想分一些,被对方避过了。
季柠只好去后备箱找剩下的行李,刚拿到手上,被白菱歌抢了过去。
“我来我来。”哥哥刚生病痊愈,怎么好让他来拿重物?而且哥哥的手可是要拉大提琴的,要好好保护,她跳舞用的是脚,所以没关系,她来拿就好。
季柠盯着自己空空如也的两只手,好笑不已,只得再去翻找后备箱里还有没有什么剩下的东西要拿。
见还剩两个盆,他端在手里,正要关后备箱,白秀英凑过来,十分自然地拿走了他手里的盆。
他愣愣地望着逐渐远去的三个背影,锁了车,快步跟上离他最近的白秀英。
“妈,我来吧,就两个盆,我能拿的。”
白秀英瞪他一眼:“拿什么拿?一边去。”
季柠被她一瞪,从小生成的条件反射叫他立马收回了手,至此只敢老实走在一边,不敢再瞎置喙什么。
白菱歌像只轻灵的鸟儿,拿到自己寝室号后,一马当先走在了最前头。
四人的寝室,已经来了两个人,一见她进门便都朝她热情地打招呼。
“你一个人啊?”扎着高马尾的女孩子看了看她身后问。
“不是,我和哥哥还有妈妈一起来的,他们走得慢,在后面呢。”白菱歌来到自己的床边,打开柜子观察了下,又去阳台上转悠了圈,很满意自己所看到的。
半开的门再次被人推开,高马尾与寝室里另一个平刘海的女孩看向门口,被拎着大包小包的冉青庄给惊着了。
好高啊,起码有一米九几。双手因为拎着重物,显出分明的肌肉线条,表情不苟言笑地虽然看着有些凶,但无论是发型还是五官都特别有男人味。
他什么都不用做,光是往哪儿一站,浓浓的荷尔蒙便呼之欲出,让人无法忽视。
要不是他手里拿着行李,两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表演系的哪位助教学长了。
“哥,这边,放着就好,我等会儿自己理。”白菱歌指着自己的桌子道。
冉青庄帮她把东西塞进柜子,见别人**都有蚊帐,问她:“蚊帐买了吗?要不要帮你系?”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好。”白菱歌瞥到两个室友都在看着这边,忙给她们介绍,“这是我哥。”
两个女孩不由自主地全站了起来,向冉青庄打招呼:“您好……”
“就是这儿吧?小妹也真是的,怎么走这么快,一下子没影儿了。”随着说话声,一个穿着宽松白T的年轻男人探头进来看了一眼。
就像他身上穿的衣服,他的整体气质乃至长相都给人一种干净无害的印象。头发有些短,这样的板寸,向来适合那些气质硬朗的人,但因为他头型很好,反倒没有很突兀,让他干净中仿佛染上了一丝阳光的气息,走哪儿都要发光。
“妈,是这儿。”他回头嚷了声。
白菱歌再次向她的室友介绍:“这也是我哥。”
长马尾忍不住小声“哇哦”了下,引得白菱歌不解地看向她。
对方立马尴尬地解释:“没有,我就是羡慕你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还都这么有型。
为什么别人的哥哥这么帅气这么宠妹狂魔,她的哥哥却只会和她打架偷偷往她的可乐里加酱油啊?这就是哥哥的参差吗!
白秀英带了些博城的特产,花生糖什么的,每个室友都分了一包,当做见面礼。
寝室的床都在上面,下头是一张书桌加一个边柜。白秀英怕女儿铺不来床,就想给她把床铺了,被季柠拦了下来。
“你本来就腰不好,我来吧。”他将铺盖往**一丢,利落地爬上梯子。
动作间,T恤上移,露出一小截腰身。高马尾无意间瞥到了花花绿绿的一片,像是纹身,正要细看,那T恤已经回到原位,而那高大的男人也站到两人之间,挡住了她的视线。
白菱歌无奈地在底下喊:“我真的自己来就行,你们干嘛呀,我都十八了,又不是八岁!”
季柠充耳不闻,迅速给他铺好了床垫,摆好了枕头:“那蚊帐你自己挂行不行?”
“行啦,你快下来!”白菱歌仍记得两个月前见到季柠的时候,他是多么苍白虚弱,现在看他这样矫健,心里还有点发憷,就怕他一个脚下无力给摔了。
也是怕什么来什么,她才说完,季柠下梯子的时候就脚下一滑,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往后摔了下来。
她惊叫着,吓得忙要扑过去,冉青庄却早早关注好季柠,护在他身后,见人摔下来,便稳稳将他接住,没让对方伤着分毫。
“你看看你,我就说我来我来,你吓死人了!”白秀英抚着胸口,脸都吓白了。
季柠讪讪笑了笑:“我这鞋有点滑……”
冉青庄牢牢从后头抱住他,长臂勒着他的胸腹,半晌才长长呼出口气,一点点松了自己的肌肉。
“你到一边去。”他蹙眉下令,禁止季柠再做任何体力活。
季柠摸摸鼻子,有些委屈地走到了一边,与白菱歌两人互相取暖。
白秀英替女儿整理衣橱,冉青庄拿抹布擦了桌子,两人合作无间,很快收拾完了白菱歌的床位。
冉青庄洗完手从洗手间出来,季柠马上往他嘴里塞了块糖。
“好吃吗?”
冉青庄盯着他笑得弯弯的双眼,点了点头。
嘱咐过白菱歌好好跟室友相处后,三人一同离去。
几乎是寝室门关上的下一秒,高马尾和平刘海就迫不及待地问白菱歌:“你哥都是做什么的呀?”
“高的那个年纪比较大还是矮的那个大?”
白菱歌正琢磨着怎么挂蚊帐呢,一心两用回答她们的问题:“一个是警察一个是拉大提琴的,两个人一样大的。”
“难道是异卵双胞胎?”高马尾惊呼,“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矮的那个看着更像妈妈,那高的那个应该像爸爸吧。”
白菱歌努力拆解着自己一团麻花的蚊帐,错过了向她们澄清误解的最佳时机,等回过神的时候,两人已经在打赌两人有没有女朋友了。
四只眼睛齐齐期待地看向白菱歌,她停下手头的活儿,没怎么多想就脱口而出:“结婚了,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两个女孩纷纷震惊,感叹这年头帅哥真是结婚得越来越早了。
最后一名室友没过多久也到了,是一个人来的,拖着个巨大的行李箱。几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分了零食,很快熟稔起来。
“你是错过欣赏白家两个绝世哥哥的机会了,可惜啊可惜……”高马尾摇头叹息。
白菱歌纠正她:“我跟我妈姓的,我哥不姓白。”
“那哥哥们叫什么名字?”第四位室友兴致勃勃追问。
白菱歌跟她们说了。
平刘海“咦”了声,道:“你跟你妈姓的,另一个跟爸爸姓的,那还有个呢?”怎么有三个孩子三个姓的?
白菱歌懒得解释,面不改色地胡说八道:“跟奶奶姓的。”
“嚯!”高马尾肃然起敬,竖起大拇指道,“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