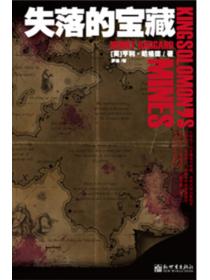特瓦拉的三支军队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慢慢向我们逼近。大约离我们500码时,作为主队的中间那队停在了开阔平原通往山上的入口处,给另外两支队伍充分时间,以便对我方形成包围之势。山的形状有点像马掌,两点伸向鲁欧镇,毫无疑问他们是要三路同时发动进攻。
“噢,如果有格林机关枪,”古德一边凝视着下面的密集方阵,一边叹息道,“我会在20分钟内扫清平原。”
“我们没有,所以光抱怨一点儿用也没有。但是夸特曼,你开一枪试试,”亨利爵士说,“看你能不能接近那个高个子,他看上去好像是指挥官。你在5码之内不会失手的。”
这句话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我把快枪装上子弹,为了更好地看清他的位置,我等那位朋友又走出了10码,只有一个勤务兵陪着他。我趴下来,将快枪靠在一块岩石上,瞄准了他。步枪像所有的快枪一样,射程只有350码,考虑到弹道的落点,我瞄准他脖子的下半部分,这样的话,我估计应该能射中他的胸。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可能是由于太兴奋,或者风的原因,或者这个人离得太远,我不知道,反正事情发生了。我以为自己已经瞄准,于是扣动了板机,烟雾消散后,令我郁闷的是,那个人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而左边离他至少有三步远的那个勤务兵脸朝上躺在地上,显然已经死了。我瞄准的那个指挥官迅速转过身,惊恐地朝着部队跑回去。
“好啊,夸特曼,”古德大声叫道,“你已经把他吓坏了。”
这让我非常生气,因为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失误,我最讨厌的就是当众失手。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技术,就喜欢在这一方面保持着荣誉,这是人之常情。稍微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之后,我做了一件鲁莽的事儿,迅速瞄准奔跑中的指挥官,放了第二枪,那个可怜的人伸出手臂,仰躺在地。这次我没有失手。我得说,这件事证明了当自己的安全、荣誉或尊严遭到怀疑时,我们很少考虑对其他人的影响。我真是残忍,看到这样的场景还这么高兴。
那些看到这一情况的军队由于白人的魔法而欢呼雀跃,他们把这当成胜利的征兆,而那个指挥官带的队伍——我们后来查明他确实是指挥官——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不可思议,顿时乱作一团,开始溃退。亨利爵士和古德也举起步枪开火,古德又用温切斯特连发步枪朝他前面密集的人群一个劲儿扫射,我也放了一两枪。据我们判断,打死了没来得及跑出射程的6个或8个士兵。
就在我们停止射击时,从右边的远处传来了不祥的吼叫声,左边也传来了相同的嘶杀声,另外两路人马从左右两路包抄过来,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听到这声音,我们前面的人群冲开了一道小口儿,继续向山坡上无遮无拦的草地上快步前进,边跑边唱着一首语调低沉的歌。他们一靠近,我们就有规律地放上几枪。伊格诺希偶尔也放几枪,解决掉几个人,但是在气势汹汹的武装人群中,我们放的这几枪就像朝激流中扔了几块小石子一样,肯定产生不了什么特别的影响。
他们呐喊着、挥舞着长矛冲了上来,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在山脚下的岩石间布的前哨。到那儿之后,他们前进的速度变慢了,因为尽管我们在那里并没有布太多防,但是进攻力量必须要爬上山,需要慢慢前进,以节省力气。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在半山腰,再向上50码是第二道防线,而第三道防线就在平原边缘。
他们一边爬山,一边大喊着战争口号:“为特瓦拉而战!为特瓦拉而战!杀啊!杀啊!”“为伊格诺希而战!为伊格诺希而战!杀啊!杀啊!”我们的人回应道。他们现在离得非常近了,掷刀开始飞来飞去,随着可怕的号叫声,战斗逼近了。
战斗的士兵左冲右突,伤亡的人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一片片地倒下去,但不久,进攻部队的优势开始明显起来,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已经慢慢地向后退了,直到进入了第二道防线。这里,战斗非常激烈,但我们的人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势击退了下来,又冲了上去,最后,经过20分钟的战斗,我们的第三道防线也投入了战斗。
这时,进攻的敌人都筋疲力尽了,而且伤亡十分惨重,要想突破我们不可逾越的第三道防线已经力不从心了。双方士兵在激烈的战斗中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反反复复,一时也无法看出结果。亨利爵士眼中充满了怒火,注视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接着二话没说就冲了下去,古德也一言不发跟着冲了下去,投入到这场激烈的肉搏战中。至于我,仍然停在原地没有动。
士兵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影也投入到战斗中,都大声喊道:“大象来了!大象来了!杀啊!杀啊!”
从那时起,结果便很明了了。勇敢的战士迫使进攻的敌人一寸寸向山下后退,最后敌人已经溃不成军。就在这时,信号兵过来报告左边进攻者已经被击退,我内心开始庆幸起来,感觉事情到现在总算要结束了。但令人惊恐的是,右侧防线上,我们的人正穿过平原向我们靠拢,身后跟来了大批敌人,很明显敌人在右侧取得了胜利。
伊格诺希站在我身旁,看到这个情形,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下了一条命令,马上,我们周围的预备队灰军四下分散开来,准备投入战斗,抵挡右翼的来犯敌军。
伊格诺希再次下了命令,首领们根据他的指示指挥军队,此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对来犯敌人的猛烈进攻之中。我尽量躲在伊格诺希巨大的身影后,在被杀的人群中东倒西歪。一两分钟后,撤退的人群在我们身后马上重新列队,我肯定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着听到了可怕的矛盾撞击的“隆隆”声。突然,一个巨大而凶残的身影向我冲过来,那个人充血的眼睛好像瞪出了眼眶,提着一根带血的长矛向我奔来。大部分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会不知所措,但是随机应变这一点上让我很自豪。此时,如果我站在那里不动的话,必死无疑,因此,当那个可怕的身影压过来时,说时迟,那时快,我机灵地就地一滚,还没有等他停下来,就从背后给了他一枪。
不久,我的脑袋不知道被谁猛敲了一下,后面的事情我就记不得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回到了小山,躺在地上,古德正弯着腰,用葫芦喂我水喝。
“感觉怎么样,老伙计?”他焦急地问。
我坐起来,晃了晃头,回答道:“还好,谢谢你。”
“感谢上帝!看到他们把你抬进来时,我都快晕了,我以为你完了呢。”
“伙计,现在不会。我想我只是脑袋上挨了一下,这一下把我打傻了,结果怎么样?”
“没有多长时间,三个方向的敌人都被击退了,人员伤亡惨重,我们死伤了2000人,他们死伤了有3000人。看,看那里!”他指出长长的四人一组的队伍。
在四人一队中,都有一个盘状的东西,库库安纳人都是携带这样一些两头有柄的盘子,也就是担架。在这些担架上躺着无数的伤员,一抬过来,医生都马上进行检查,一个军队里一般配有十个军医。如果伤员的伤势不是很重,就会被抬到允许的环境里进行细心的照料。但是,如果伤员伤势太重,没有希望治好的话,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残酷,但有时也只能这样。一个医生假装进行治疗,突然把锋利的刀子插入病人的动脉,一两分钟后,伤员就毫无痛苦地死了。那天,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身上的伤口多数是这么处理的,因为库库安纳人通常认为大宽长矛扎出的深长的伤口无法治愈。大多数情况下,可怜的受伤者已经处于无意识的昏迷状态,再加上切这种致命的动脉伤口非常迅速,因此他们看上去毫无痛苦,还没有恢复意识,就已经死了。但场面仍然十分可怕,每当看到有人逃过这种厄运,我们都非常高兴。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记得有什么事情比看到这些英勇的士兵被医生染血的双手送走更让我震撼,对我造成的影响更深。不过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我看到斯威士人埋葬仍然活着的无法救治的伤员。
匆匆离开这可怕的场景,我们在小山较远的那边找到了亨利爵士,他手中仍然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战斧,伊格诺希、因法杜斯和一两个首领正在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感谢上帝,你在这里,夸特曼!我弄不懂伊格诺希想做什么。尽管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特瓦拉正在集结大量的援军,看来要围困我们,想要把我们活活饿死在山头上。”
“那就棘手了。”
“是的,因法杜斯说水已经快喝光了。”
“我的主啊,确实是这样,”因法杜斯说,“泉水无法供应这么多人饮用,水位下降得特别快,晚上前,我们就会断水。听着,马楚马乍恩,你很聪明,毫无疑问你一定见过许多战争——应该说那是星星上的战争。现在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特瓦拉又调集了许多新兵,他已经吸取了教训,鹰不会去攻击做好准备的苍鹭的巢穴。但我们的嘴已经刺入了他的胸部,他不会再攻击我们了。我们也受了伤,他会等着我们死去。他要像一条蛇缠绕公羊一样包围我们,打一场围而不攻的围困战。”
“我听你的。”我说。
“那么,马楚马乍恩,你看我们这里没有水了,但还有一点儿食物,我们有三条路可以走,必须作出一个选择——要么像饿狮子一样困死在洞穴里,要么从北方突围,努力杀开一条血路,或者”——他站起来,指着敌人密密麻麻的队伍——“直接扑向特瓦拉的喉咙。因楚布,伟大的勇士,今天他在战场上像一头野牛,特瓦拉的士兵在他的战斧前像被冰雹打倒的小麦一样,我亲眼看到的,因楚布说‘冲啊’。但大象总喜欢冲锋。现在说马楚马乍恩什么呢?老谋深算的老狐狸,总是喜欢观察,然后在敌人背后咬上一口。最后是伊格诺希国王,因为国王的权力是决定战争。但让我们听听你和那个透明眼睛的人的声音,尊敬的马楚马乍恩,你是那天晚上看得最多的人。”
“伊格诺希,你意下如何?”我问。
“不,我的父亲,”我原来的仆人回答道,现在他全身披挂着一身原始战争中勇士的装束,像一位勇猛的国王,“你说吧,在你的智慧面前,我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让我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我和古德、亨利爵士匆忙地商量了一番,然后简短地发表了意见。我们的意思是:就目前我们缺乏供水的情况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对特瓦拉发动进攻。随后我建议进攻应该马上进行,“在我们的伤口变硬之前”就进行。因为看到特瓦拉大军压上的情况,士兵的心“会像在火炉上烧烤的肥肉一样慢慢变小”。另外,我指出,如果时间拖得太久,一些将士可能会改变主意,与特瓦拉进行和谈,甚至有可能背叛我们。
从总体来看,这个建议似乎得到了认可,其实,在库库安纳,我的意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但真正的决策权还掌握在伊格诺希手中,自从他被承认为国王,就行使着王国无上的权力,当然包括重大军事的最后决策权,此时,所有的人都看向他。
终于,经过一段深思,他开始说话了:
“勇敢的白人们因楚布、马楚马乍恩和布格万,我的朋友、我的叔叔因法杜斯和首领们,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向特瓦拉发起进攻,这一攻击关系着我的命运、我的生命,也关系你们的生命,咱们的命运拴在一根绳上。听着,就这样,今天发动进攻。你们看到这座山如何弯成半月形吗,这个平原如何像绿色的舌头一样伸进山里吗?”
“我们看到了。”我回答道。
“好,现在是正午,苦战以后,疲惫的士兵需要吃饭、休息。太阳落山天刚擦黑时,我的叔叔,把你的军队和另外一支军队带到山下绿岬地去。那时,特瓦拉一定会重兵出击。但是那个地方很狭窄,军队一次只能上来一个人,因此可以把他们一个个击溃。所有特瓦拉的军队都会看到这场战斗,以前还没有人看到过类似的战斗。我的叔叔和我的朋友因楚布一起去。当特瓦拉看到因楚布的战斧在“灰军”的第一线上闪耀时,他的心可能会变得很脆弱。我会带上第二个军团,跟随在你们身后,因此如果你们寡不敌众被消灭,还有一个国王留下来继续战斗,聪明的马楚马乍恩和我一起去。”
“很好,国王。”因法杜斯说,看得出他对于可能的全军覆灭表现得相当镇定。说真的,这些库库安纳人真是了不起,履行职责时,他们对死总是表现得无所畏惧。
“特瓦拉多数士兵的眼睛正盯着这场战争,”伊格诺希继续说,“看,将我们剩下的士兵的三分之一从山右侧爬下去,到特瓦拉左翼。另外三分之一从左侧下去到特瓦拉的右翼,我和剩下的三分之一正面攻击特瓦拉。幸运的话白天就属于我们了,晚上前我们就会平安地坐在鲁欧了。因法杜斯,准备吧,严格执行计划,让我的白人父亲布格万随右路人马下山,因为他闪光的眼睛可以鼓舞士气。”
于是,完美的进攻计划立刻执行起来,不到一个多小时,食物就按定量发给了士兵,大家狼吞虎咽吃了下去。然后,将队伍分成三路,向首领们解释了进攻计划,除了留下照顾伤员的人外,其余的18000人准备出发。
不久,古德向亨利爵士和我走来。
“再见,伙计,”他说,“按照命令我到右翼,所以我过来握手,万一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们知道。”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
我们默默地握了握手,并没有表现出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情感。
“真是一件怪事儿,”亨利爵士说,他的声音深沉而有点儿颤抖,“我承认我从来不期待自己会看到明天的太阳。据我所知,我要跟随的灰军,为了能够让两翼出其不意地下山,并从侧翼包围特瓦拉,要血战到底。唉,就这样吧,人早晚都有一死。再见,老伙计,上帝保佑你!我希望你能闯过这一关,活着把钻石戴到脖子上。如果真能这样,要记住我的忠告,要知足,不要做贪心的人。”
接着古德紧紧地握了我们的手,转身离去;因法杜斯过来把亨利爵士带到了灰军最前线。与此同时,我也忧心忡忡地与伊格诺希分别,去了第二路进攻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