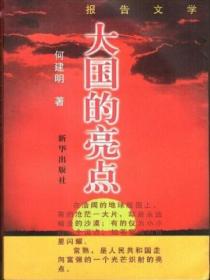常熟人,常——德——盛。
我越读上面这六个字,越觉得意味深长。不信你读读看,包括常熟人自己。
有人说中国人起名很有些“历史远见”,绝对不像外国人仅把自己的名字作符号一般不加重视。据持这种理论的人佐证道,你看“毛泽东”这三个字,他老人家后来不是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你再看看某某某,现在不是也做大官了?信不信由你。
我想信不信也是由你。但不信之后你仍可以再细细品味一下,这其中倒底有什么奥秘?也许有,也许根本就没有。信不信仍然由你。
但是在我采访常熟人的“常一德一盛”和那个叫“常德盛”的常熟人时,我着实细细品味了一阵,但十分遗憾的是至今我没有品味出它们与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想或者根本就属子虚乌有之事,也许就是像中国的(易经)那样深不可测——还是留给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常熟那些学子们自己去解释吧。
常德盛自己告诉我,他出生时父母穷得连半间茅棚都找不到——当时他家唯有的是那条连雨都不能掩的小破船。如果不是一家好心人腾出一间茅棚让其母亲临产,那常德盛的命运不知该怎样写?没什么文化的父亲后来给儿子起了“常德盛”这个名字。我问过常德盛是否知其父亲起这个名字的含义。他想了半天也还是摇摇头,倒是他所在的蒋巷百姓为我解释了这名字的深刻含义——“常积德者,事成业成百姓盛”。
(易·乾·文言)中有道:“君子进德修业。”《管子·心术上)曰:“德者道之舍。”而章氏的(国故论衡)中则更明言道:“实、德、业三,各不相离。”可见,今古圣贤对德早有注解,而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行德者,天下盛;行恶者,必自灭。德,既为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也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做人的立身之本。
常德盛自己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他自己名字的意思,但他用几十年的行动实现了对“德”字的全部注释。
“共产党的干部讲德,就是为国家、为集体、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常德盛告诉我,他是30年前的1966年5月入的党,那会儿他才22岁。他说他当时的入党志愿书里也说过不少又空洞又高调的话,现在已经记不得什么了,但有一句话他是记了几十年,而且还立志要一直记到去见马克思。他清楚地记得在党旗下向组织作过下面的一段庄严承诺:“……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这个穷孩子从苦水里解放了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有一天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后,我将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党的事业,领导百姓过上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在党旗下宣誓后的5个月,他当上了蒋巷大队的大队长,不久又接任党支部书记。
事过30年后的19%年11月,我到蒋巷村采访,间了几位当年参加讨论常德盛入党会的老同志,他们的常德盛同志在入党后的这几十年里,是不是“基本”或者“差不多”做到了他自己曾经对党作出的承诺。我听到的回答都感到吃惊和意夕}一
“我们的常书记可不是啥‘基本’或‘差不多’,他可是真正说到做到了的,三十年来没走过样。”
“我泥蒋巷村能有今天的富裕日子,全靠常书记实无出来的。”——在我采访的那些日子里,这句话几乎是蒋巷村民们的口头禅。
村文书小孙给我讲起了一件事,这事发生在我到蒋巷采访的前几个月:按照基层组织选举法,19%年6月,蒋巷村将产生新的一届村委会。在这之前,乡亲们见上级一个劲儿地又是《决定》又是“专题”的宣传他们的常书记,又传闻上面要调常德盛当什么什么去了。蒋巷村的村民们这已是第三次听说上面要“动”他们的常书记了。不行,你上面可以把我们蒋巷村大大小小企业创下的利润一箍脑儿全端走,但绝不能“动”走常书记!绝对不能!为了显示大伙儿的这份坚定心,在选举的那一天,谁也没有事先通知,谁也没有事先串通,在家养病的从**支撑着起来了,千里之外的个体户丢下手头的生意也赶了回来。600多号村民们那天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长辈小青年,都穿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缺地早早地来到会场,还没等宣布选举开始,村民们就已经把“常德盛”三个字写在了纸上。当后来听说村党部书记不在这次选举之列、常德盛自己也站出来保证“不离开蒋巷”后,全村人这才如释重负地乐呵了一场。
常德盛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农村普通干部,他在三十年前向党所作出的庄严承诺,现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豪言壮语”的味道,其实对他常德盛、对像他常德盛这样年龄的人,那几句话是从心窝窝里用不着任何半点“添加剂”就能往夕附的大实话。因为他们都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啥叫苦水,有旧社会的头上压着大山、没穿没吃没住、逼得要你命的苦;也有到了新社会后因天灾人祸而害得走投无路的苦……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能知道和理解这一点了。那种因贫穷和灾难所造成的苦,它给人带来的痛楚与折磨,只有经历了那种贫穷和灾难的人才能真正体味。
蒋巷村地处苏南水乡福地的常熟、太仓、昆山的交界处,属常熟市的任阳乡。常熟素有“江南天堂”之称,但蒋巷村及它所在的任阳乡在历史上则是这个“天堂”里的“地狱之域”。这是因为此地有两大公害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一谓水害,二谓吸血虫病害。蒋巷村和所在乡地势低洼,是真正的“水乡”。有首民谣如此唱道:“蒋巷泽坞锅底塘,十年九涝一旱荒。泥垛墙,茅草房,树皮菜根拌青糠。”问起上了年纪的蒋巷人这儿到底受过多少水灾,他们会说那等于是问他们生下来后共吃了多少顿饭似的。一位老人说,他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40年前的1956年那场雨造成的水灾。那场雨共下了整七七四十九夭,河道里的水就不去说了,单田里的积水就是一米来高……说起蒋巷一带的“吸血虫病”害,那更是毛骨惊然。有个叫“白米A”的自然村落,1937年时有30户、110人住此,过了20年,到1957年时有近一半人家、一半人口因患吸血虫病而死绝,成为名副其实的“万户萧疏鬼唱歌”之地。即使到了解放后,大多数蒋巷人还是那种“颈项像丝瓜,肚皮像冬瓜,四肢像黄瓜”的“活死人”。蒋巷村和蒋巷村所在乡的吸血虫发病率高达70%以上……当年的蒋巷村非富有的常熟人所去之处,留在那块“一斤黄金一斤谷,一天一顿糠菜粥,脸黄肚大皮包骨,三更半夜有人哭”的土地上,都是些从苏北或安徽、河南等逃荒、讨饭的“野人”(本埠人这样称呼流落此地的外乡人)。
常德盛就是这些后来成为蒋巷村主人的那些“野人”中的一个。
他的母亲生他那年,父亲已经44岁了,为了感谢这家腾牛棚的好心人,父亲给儿子起了“德盛”这个名字,意在让儿子长大后行德行善,报恩于收留和栖息他全家的这块土地。
常德盛从小接受的就是这以恩报德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影响。
在四周皆是富土与富民包围之中的蒋巷这块“鬼唱歌”的土地上,常德盛从小所受的苦对他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这种苦,既有恶劣的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贫穷之苦,也有被别人歧视的屈辱之苦。
既为蒋巷人,就得做蒋巷的主人。既当蒋巷的主人,就得做呱把全部心思放在蒋巷土地上并被大伙瞧得起的人。’——这是常德盛从孩提长大后就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立人之本。后来没过几年,看·位“干活不要命”的瘦小年轻人,被众乡亲推到了大队当家人的岗位。面对镰刀和铁锤组成的红旗,常德盛向父老乡亲们许下了如下诺言:‘。老老实实做党的人,勤勤恳恳当百姓的黄牛……’,升
从1966年到今天,常德盛作为蒋巷村的当家人,作为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名支部书记,整整30多年光阴,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向乡亲、向党许下的诺言,并且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为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谱写了人人赞颂的乐章。
-30多年过去了,4巷村还是那么个地盘,可早已不见了那“万户萧疏鬼唱歌”、“穷水恶土人潦倒”的旧貌,如今已是锦绣田野年年丰、灿灿金杯立满堂,外乡邻村的小伙姑娘想进蒋巷还得凭思想先进有技术哩!蒋巷村打80年代开始,差不多年年被省、市评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村或先进集体。
-30多年过去了,常德盛的足迹在蒋巷村没有挪动过一步(尽管上级有几次要对他升迁,但他没走),他的支部书记一职也从未因时势的风风雨雨而变动过。乡亲们说,常书记唯有的变化是他头上的白发和脸上被风蚀雨袭而生的纹痕……
作为一名干部,无论他的职位大小,几十年呆在原岗位不动窝,除非他或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者兮或是沉淀在最底层的平庸者,此外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
然而常德盛既非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者,也非是最底层的平庸者。他上面的一级级官阶比山还高,随便谁一句话都可以压得他三天喘不过气来。而他抽屉里积下的荣誉证书,则比共和国元帅的战功奖令还要多出半个头高。常德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干了30多年,并且还在继续……
蒋巷人最难忘的是常德盛书记带领他们改天换地的那些岁月和那些经历。
前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行官员慕名到蒋巷参观,当他们站在一马平川,绿荫成行,道渠规整而充满生机的田野上,听主人介绍这儿曾经是满目苍凉荒芜、河洪泥塘错汉、茅草坟堆遍野、猫狗野狼横行、沟谷洼地间到处是吸血虫丛生、大小田块高低零乱不堪的“苏南泽国”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奇目光。其实,惊奇的不仅仅是那些黄头发绿眼珠的外国人,就连蒋巷村上了年岁的人谈起此事时,同样会流露出那般充满自豪的奇异神色。
22岁便上任村支书的常德盛与每一位蒋巷人一样,祖辈吃尽了水害之苦。作为全村的领路人,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治理蒋巷村的穷土恶水。为此常德盛折弯了一身骨、熬白了一头发……而他就是用这瘦小的身子骨和傲挺的白发,带领全村不足400个劳力完成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四大战役”。这便是后来给蒋巷村以全新面貌的1968年至1969年间平坟墩、倒杂树、开深沟战役;1975年开始的平整土地、填河填irr,战役;和1986年开始的筑路建渠、建设规格田战役,以及1992年以后的路、渠、田、林标准化等四个战役。
在我来到蒋巷村采访时,村里没有任何实物资料,可以看到过去的30多年间常德盛这位身高不足1.65米、体重只在一百来斤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年复一年带领众乡亲战天斗地的场面,但有那么多的老乡告诉我下面这么多的事——
那一年平到某家一块祖坟地头时,有人不近人情地挥起铁锹把常德盛操在了刺骨的河塘里。常德盛从水里爬起来没顾回家换衣服,打着颤儿做了几小时的工作,直到人家甘心情愿把祖坟移走为止;
那一年夏季中,为使千亩水稻不受涝,常德盛手持一把铁锹,身披一件蓑衣,连着十三四个昼夜巡视在田埂河堤上,直到累晕在浸草地上支持不起来……;
那一年农历大年初一,天色朦朦时,有人上镇上吃早茶,忽见地头有人影在晃动,不禁上前细看,原来是常德盛书记在独自默默地挑土填河呢。“常书记,今天是啥日子了,你还起这么早来干活?”常德盛一笑,说我睡不着,就来这里了。那人望着常书记瘦小的身影,心一酸,知道劝他回家休息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便回村叫醒左邻右舍一起上了工地,后来人越来越多,大伙越干越欢,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一天是什么日子。
就是这样,蒋巷人在常德盛的身先士卒下,靠一锹一挑,经过近20多个春秋,填平了一个又一个河塘沟洼,规整了一块又一块斜田曲洪,形成了今天的田方地平、水渠成网、大田通公路、小田有平道、家家门前进得汽车、户户四周绿荫环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格局。昔日为人所歧视、闻声躲一边的“泽国”加“吸血虫病重灾区”的蒋巷村,在这“四大战役”之后,彻底改变了往日的形象,成了苏南天堂中的天堂。
本村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过去他们蒋巷人取媳妇一般女的总要比男的大上好几岁,甚至十几岁。为啥?就为一个穷字和一个“虫”字。现今这两个字,早被常德盛和他的众乡亲给深深地埋在了十八层地底下。
然而所有这些,在常德盛的眼里仅仅是他作为村支书应该和必须走的第一步路。“农村共产党人干工作不单单是为穷山恶水变成金色的田野,更重要的是让金色的田野长出金色的谷子……光会苦干,不会巧干,就不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常德盛如是说。
他当干部几十年,这话也说了几十年。为这,他同样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和捍卫实事求是原则,就历经了自我否定、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等好几个艰难过程。
常德盛是工作和生活在最基层的一名党员干部,三十年间他所要承受和做到的,何止是时时处处苦干在前、重担抢先这样一些肉体上的负重,更多的是来自不同时期有时是一夜之间几种变化的精神负重。
在中国农村,几乎每几年就有一种全新的政策出台。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再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到八十年代的分田到户……每一次政策出台,对农民而言,差不多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不管你那儿适应不适应,你都得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就是“对党对上级的不忠”的路线错误。农村干部就得在这种情形下工作。然而我们那些高高在上的决策者们常常并不考虑百姓种的还是那块地、吃的还是那口饭,有时决定的一些政策不从实际出发,一味要求用一种模式来规范十亿农民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样的结果不仅没能解放农业的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相反常常造成劳民伤财,怨声载道的局面。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便是突出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