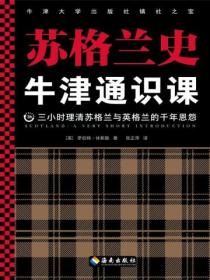第四章 社会
人口
1700年时,苏格兰大约有100万居民,此前的苏格兰人口估算都要靠猜,不过可以制定一些人口统计指南。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稠密,生活水平可能也一样好。人口统计的第一个标志是“黑死病”,这场传染性瘟疫在1348至1350年间袭击了不列颠,可能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时的瘟疫是地方性的;随后暴发的疫病没有那么强的致命性,往往局限在城市里。苏格兰最后一次大瘟疫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不过迟至1720至1721年,仍然有少量的疫病。瘟疫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破坏与死亡的威胁一样,令人恐惧。有了隔离措施之后,尸体被马车运到集体墓穴,没有往常的仪式,对死者的朋友和家人而言,这种死亡尚能忍受。
黑死病暴发期间,欧洲也进入了小冰川时期。因为工人极少,气候又不利,高纬度的定居点被遗弃。糟糕的天气、极低的生产力、少得可怜的交通运输,这些意味着食物短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最后一次严重的全国性饥荒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末,那时,八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或疾病。低地的农业生产力在18世纪翻了一番或三倍,但在18世纪40年代,甚至到了19世纪头十年,糟糕的收成仍然会导致饥饿和死亡。19世纪四五十年代,“高地大饥荒”可归因于与长期贫困和匮乏有关的疾病,而非只是饥饿(主要原因是土豆歉收)。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在30多岁,但如果人们能熬过婴儿期和童年,就可以活到六七十岁。1700年,十二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整个18世纪,成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值增加了三分之一。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意味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从1789到1911年,人口增长了两倍,从150万涨到450万。适度的增长率掩盖了农业变革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再分配。到1789年,只有不到一半的苏格兰人口居住在想象的“高地线”北部,这条线东到斯通黑文(属于金卡丁郡),西到海伦堡(属于邓巴顿郡)。1911年,这个数字跌到只有六分之一。1790年,八分之一的苏格兰人生活在大城市,到1831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1911年则有五分之三。而在1911年,苏格兰是欧洲继英格兰之后最城市化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格拉斯哥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出生在高地,还有四分之一出生在爱尔兰。
疾病死亡率仍然很高,但在逐渐下降。天花在19世纪初被攻克,但直到19世纪中期,斑疹伤寒和霍乱仍是城市人口的最大杀手,对流感的控制直到1918年才有所改观。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虽比英格兰低,但仍然高得惊人,而且也没有像19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那样下降。1871年左右出生的婴儿,有四分之一活不到5岁。
19世纪苏格兰的生育制度也与众不同。妇女的结婚年龄相比欧洲标准格外大(通常是二十八九岁,五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结婚),不过,苏格兰妇女一旦结婚,生育率还是很高的。晚婚最为有效地遏制了生育率。生育率还受限于延长母乳喂养、节制性欲,或诸如体外**这样的基本避孕措施。运用机械方式选择生多少孩子、何时生孩子的现代“生育控制”,是20世纪初的发明。这种方式的引入主要由男人引导,直到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才让女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家庭规模急剧缩小。19世纪70年代缔结的婚姻,有五分之二的家庭生出六个以上的孩子,而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不到2%。苏格兰的非婚生率普遍较低,但部分地区的非婚生率是欧洲最高的:19世纪末的东北部农村,五分之四的妇女在结婚之前都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或在结婚三个月内生出第一个孩子。整个19世纪,苏格兰是一个年轻人的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是14岁或更小。
现代苏格兰大概有500万居民,其人口结构和西欧、北美大致相当,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出生率低,寿命更长,本地人口逐年下降。曾经包容人口活动的社会结构在上一代时发生了急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30岁以前结婚的妇女中有一半曾在婚前同居,而20世纪60年代只有3%。1997年,邓迪出生的孩子首次有一半以上来自单亲妈妈,或来自同居但没有结婚的父母。整个苏格兰,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中。根据1987年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末的婚姻有三分之一以离婚收场,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有7%的离婚率。其部分原因在于保守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似乎基于以下前提,即不教性健康知识就会防止年轻人发生性关系。然而,苏格兰十几岁怀孕和性疾病传播的比例却是欧洲最高的。
图8俯瞰圣安德鲁斯,展示教堂、城堡以及中世纪三街计划的东部街头。自中世纪以来,苏格兰的城镇就是教会、政府、贸易和学术的中心
生活水准
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对待贫穷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英格兰。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格兰的济贫工作是由国家组织的,国家进行地方管理并给予财政支持,并把对较富裕居民征税所获得的主要供给与非正式捐赠结合起来。苏格兰和英格兰一样也有早期立法,不过从未有效实施,其供给平衡完全颠倒。出于济贫目的(或其他目的)的征税从来就不盛行。相反,一种混合的福利经济维持着贫困人口的生活,其重点是非正式捐赠。城市有征税,但在乡村教区,教会、地主和邻里提供了绝大多数救济物,直到17世纪,苏格兰教会接手管理正式的救济工作。随着人口重新分布到城市以及苏格兰教会的分崩离析,这一体系也常常难以为继、不堪一击。
1845年的苏格兰济贫法,紧跟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和1843年的教会瓦解(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中,佩斯利112家制造商中有67家破产,四分之一的人口等待接济);这一济贫法旨在促进征税,但这些税收在高地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地方自治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范围比英格兰要大得多,现实中的济贫措施也大不一样。苏格兰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公共卫生有着更直接的态度,1845年的济贫法与1834年英格兰济贫法的不同之处,是需要为穷人提供个人医疗护理,这一规定的精神依然保留在苏格兰议会现行的老人医疗保健政策中。
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所有的孤儿都得到寄养家庭的照料;苏格兰人不希望下一代暴露在穷困潦倒的坏榜样中。人们认为,寄养在心理上和财政上都对孩子和寄养父母更有利,而且对教区而言,寄养制度也比机构化便宜(地方负责往往意味着削减开支)。实际上,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明显的差别是缺乏为穷人而设的正式机构,穷人宁愿选择家庭救济或“院外”救济,也不选择阴冷、有辱人格的英格兰济贫院。1906年,苏格兰的贫穷人口中有14%接受了机构化救济或“院内”救济,而英格兰的比例则是32%。
历史上,大多数穷人是妇女,因为她们通常寿命比男人长,又被排除在高薪职业之外,很少有机会储蓄,她们做着相同的工作收入却较少,不得不因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中断工作生涯,而且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储蓄又受到种种法律限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有所改观)。1909年通过的针对70岁以上英国老年人的抚恤金法案,某种程度上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了鼓励储蓄、工作或依赖家庭,这些抚恤金被设置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这种贫寒证书式的救济带来的也是一种社会耻辱。
尽管1750年之后英国在不断繁荣发展,1845年后的济贫工作进行了重组,但苏格兰的社会水准仍然低于英格兰。1867年,70%的“生产工人”一年收入低于30镑,而10%的上层人物吞噬了全国一半的收入。财富的两极分化在城市尤为明显,并体现在住宅上。城市贫民搬到中产阶级腾空的中心住宅,以及也是新的但往往建得很糟糕的“共同住宅”(公寓大楼),这些地方居住着像佩斯利这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镇的工业劳动力;而中产阶级则迁往乔治时代的“新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郊区。1911年,一半以上的苏格兰人住在一居或两居的房子里,格拉斯哥和邓迪则有六成以上的人口。结果便是拥挤,对近56%的格拉斯哥人来说,一个房间里要住两人以上。
几个世纪以来,饮食都取决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局限性。垃圾堆(垃圾倾倒地)表明苏格兰人在铁器时代和黑暗时代的仪式上就畅饮啤酒、寻欢作乐,而英格兰人则吃猪肉,这说明这些肉制品并非基本食物。肉食在中世纪晚期回归,但1550至1750年间,大多数苏格兰人的饮食以鱼和蔬菜为主,因为肉食太贵了。英格兰艺术家威廉·霍加斯的不朽名作《加莱之门》(The Gate of Calais, 1749)中,(烤)牛肉已成为一道标准的饮食,是英格兰的文化象征。对肉食动物来说,因与“彭斯晚宴”的联系而为人熟知的哈吉斯(剁碎的羊杂碎、燕麦片、洋葱塞进羊胃里做馅儿)并不比简陋(健康)的鲱鱼,或羊羔腿、羊头更能成为一道地道的、“标志性”的传统食物。比顿夫人(Mrs Beeton)于维多利亚时代出版的《家庭管理手册》(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中描述过羊头,但现在到处都不供应羊头,尽管位于爱丁堡达丁斯顿的最古老的苏格兰酒吧之一的“绵羊海德酒馆”过去一直都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禁止。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日常饮食也逐渐改善,工业和商业的顺利发展也允许进口食物,但直到20世纪,佝偻病仍然是城市工人阶级儿童的常见疾病。
现代苏格兰以酗酒和普遍糟糕的健康状况闻名,这体现在成年人(男性)的平均寿命非常低,并且提供油炸食品的火星酒吧最具典型意义。但很多问题与种族并没有关系,而是和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经济机会有关,这一点在整个英国和欧洲都是一样的。1945年后的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国民营养、延长寿命,而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则是现代第一项重要的环境措施。随着生活水准日益接近欧洲平均水平,过去一代人的健康意识迅速提高,吸烟明显减少、饮食更健康、锻炼更多。2014年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仅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今天,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考虑的是选择吃什么,而非考虑吃更多食物。20世纪80年代以前,下馆子吃饭还不常见,大多数食物都很无聊,而且烹饪简陋——对虾鸡尾酒的难度算最高了。现在,精致小巧的乡村旅馆到处都是,很容易就能在外面吃到美食(如果不考虑是否便宜的话)。像尼克·耐林(Nick Nairn)、哈姆什·魏肖特(Hamish Wishart)这样的苏格兰大厨都是世界级别的,就像伦敦的戈登·拉姆齐(Gordon Ramsay)一样。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精英都在热切地购买波尔多、奥波多、莱茵兰的红酒。然而奇怪的是,直到20世纪末,苏格兰的红酒消费一直很低。事实上,酒水从来没有便宜过,而且在烟草信息被强制禁止之后,酒水将是健康游说团体的下一个目标。加利福尼亚(1994)和爱尔兰(2004)充当先锋,苏格兰在2006年也引入了公共场合的吸烟禁令。
17世纪以来,威士忌一直是工人阶级的饮品,也是道德改革家的头疼之事,就像18世纪英格兰的杜松子酒一样。和大多数现代苏格兰的象征一样,威士忌目前的声望来自市场的胜利。在历史上,开化文明的精髓是白兰地,如果可能的话,走私避税优先选择的饮品是红酒或波特酒。直到18世纪,城市每年规定红酒价格,就像他们每年规定粮食价格一样。啤酒或麦芽酒(用大麦而非啤酒花制成的麦芽酒)和休闲饮料一样是一种食品,而且,在19世纪改善卫生设施减少霍乱和伤害之类的致命疾病之前,喝啤酒或麦芽酒比喝水的风险小太多。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快速地迁徙,但他们不是旅行的游客。1773年,苏格兰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和他敌视苏格兰的英格兰密友塞缪尔·约翰逊旅行到西部高地和群岛并写下那些游记时,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游客”。最早的苏格兰游记作家马丁·马丁在17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旅行了,约翰·沃克尔牧师(Rev. John Walker)在18世纪60年代也在旅行,威尔士的博物学家和古物研究者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在1769年和1772年也游历过。但约翰逊对食物的抱怨,包括对黄油上毛发的抱怨,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不断发出回响。17世纪以来,苏格兰就有了商业性的客栈,这些客栈大多数是提供给赶牲畜的人的,城市里有住宿的旅馆,但直到19世纪,乡村的好客传统的力量一直很强大,大多数想要食物和住宿的旅行者只需停留在任何一间有承诺的农舍即可:相当于现在的家庭旅馆(B&B)。土地乡绅运用他们的家庭或社会关系为彼此的住宿逗留各负其责。
“圣日”的字面意思是休息一天。为了休闲而进行比较长时间的旅行,在20世纪前都不常见,欧洲大漫游的那批贵族除外。直到1919年,苏格兰人每周工作6天,合计55小时,而带薪休假直到1938年才为人所知,此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1911年的时候,家仆占总就业人口的八分之一,工作时间无上限。20世纪30年代,两周假期变得更加普遍,那时,火车旅行发展起来,私家车拥有量首次骤增。不过20世纪50年代,周六工作仍然非常广泛。
和绝大多数战后的布立吞人一样,苏格兰人在国内海滨度假区休假,如拉格斯、洛斯西、北贝里克。对喜欢冒险的中产阶级来说,阿维莫尔有滑雪中心,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可怕的翻修和扩张(最近又翻修了一次),而对喜欢娱乐的工人阶级来说,像艾尔的巴特林这样的度假营地也是不错的选择。乘坐飞机旅行是有钱人的专属,在国外度假也不常见,大众旅游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现代苏格兰人热衷日光浴、绿色出行等,而且目前从苏格兰机场到世界各地都有直飞(而且廉价的)航班。
贵族与人民
英格兰人给苏格兰贴的最常见的社会和文化标签是“凯尔特的边缘”,这一划分通常还包括威尔士、爱尔兰、布列塔尼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然而,凯尔特的身份和起源都是很模糊的。通常的说法是,公元前1000年的某个时刻,中欧的人口迁往不列颠和爱尔兰,这些所谓的移民带来了语言、文化和物品。文化肯定发生了变革,但这是移民(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方式)的结果,还是逐渐适应已有观念和技术的结果呢?DNA分析表明,大多数现代布立吞人的祖先来自一万年前后冰期的殖民者,只有苏格兰北部的基因库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混合特征。
当然,基因模型建立的基础是现代人群,它表面上的准确性并不一定使其与历史相符。染色体并没有告诉我们共享一个基因库的区域内的移民情况,特别是公元5世纪来自爱尔兰的、可能定居在马恩岛和阿盖尔岛的盖尔人,基因也没有预言文化认同。现代“凯尔特人”对自己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与包括英语在内的日耳曼语系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证据表明凯尔特人在文艺复兴之前根据语言来定义自己。凯尔特人定居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观念源于16世纪的作家乔治·布坎南,他根据其所谓的“高卢语(Gallic)”来定义这些人,后来,威尔士学者爱德华·卢德在其《不列颠考古志》(Archaeologia Britannica, 1707)中称其为“凯尔特语”。“凯尔特”一词在古代和布坎南时期都不流行,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也没人认为他们是凯尔特人;该词是为了现代分类学方便而发明的。当代人使用的“盖尔人”和“皮克特人”更多是现代评论者的发明,但“凯尔特人”是博物学家发明出来的,博物学家为了对历史进行排列组合而创造了一个伪林奈氏的分类群体。
凯尔特人其他的历史性特征是他们的艺术,这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900年之间一种很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在整个欧洲发现的剑、胸针、镜子和其他作品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特征。以生动抽象的兽形图案为标志的“凯尔特艺术”,有时也被称为“拉诺坦”风格,该风格源于现代瑞士这一“风格的发源地”,第一批凯尔特艺术品就是在那里被发掘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后来的描述,是19世纪对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前罗马时代被认为是凯尔特人的居民创作的艺术品的称呼。这种风格的物品也在不讲凯尔特语的地方被发现,而且,讲凯尔特语的西班牙人从未运用过这种风格。语言和艺术在欧洲不同地区单独出现,影响了凯尔特之前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受它们的影响。
和平定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后来的奥克尼群岛。基因库表明,岛上的大多数男性都有挪威人的DNA标志,唯一的一个非挪威人可以追溯到该岛被苏格兰1469年吞并之后抵达奥克尼的那些人(1468年,丹麦的克里斯汀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结婚时,将北部群岛抵押给了詹姆斯二世的儿子)。由此推断,由于奴隶制是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的土著即皮克特男人,他们被驱逐、赶尽杀绝或沦为奴隶而没能繁衍生息。在整个苏格兰北部,显著的皮克特文化似乎也在10世纪消失了,但奥克尼并非因为这一原因,因为皮克特人仍然在该岛生活。
对于中世纪以前的社会,可能最好的说法是它是等级制的——为了抵御挪威人的威胁而创造了一个为国王服务的新的军事阶层。它同样也以习惯法、家族、亲戚关系网为强大的基础。“凯尔特”影响只是其中之一。1100年之后,文化制度的交融综合更加容易。盎格鲁-诺曼人引入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封土者与受封者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包括明确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盖尔人的社会在社会组织上不太严格,他们以亲缘或“宗族”为基础,其道德义务非常强烈,但权利几乎从没有具体化。
然而,氏族社会或庇护性社会与封建制度有着重要的相似性,即国王运用这些制度将地方利益等同于中央利益,将皇室利益等同于贵族利益。两种制度下缔结的关系都是人格化的,不是非人格化的,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是主与仆、贵族与附庸(依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父亲与家人的关系。在12世纪,社会的基本划分不再是自由人与奴隶,而变成了贵族与农民,而17世纪初“民兵”与骑士役同时存在,说明苏格兰的农民比大多数欧洲农民自由,封建制度的变革被已有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担当化解了。
两种社会组织都不太依赖财富,尽管财富的积累可以表现为人口、土地或牲畜的增加,而非礼物的流通。对于像武器、珠宝这些行业的产品的管控,就像立法、对穷人施惠、赞助诗歌艺术和医学这样的文化活动一样,都是贵族表达权力、提高权力的方式。中世纪盖尔人(可能在黑暗时代也一样)的社会地位是由联盟数量以及一个人的追随者的数量和身份决定的。不过,总体而言,社会地位取决于礼物、经常分配和接受牲畜和土地。这些“物资”的获得和给予是通过战争、宴请和赞助来实现的: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及其实物价值一样大。在封建社会,国王完完整整地赠送土地,但受封者服役的承诺却是不完整的、没有限制的。
封建制度对苏格兰社会的改变确实比英格兰社会大,其中一种方式便是确认将司法和税收的权力分派或委托给贵族,这是英格兰国王坚决反对的一种趋势。苏格兰贵族长期以来可能就对他们的人民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力,但在1100年以后,他们通过确保广泛的司法权力以及相关的财政特权,将与国王保持适当距离的关系制度化。这种独立性在詹姆斯六世时期逐渐被侵蚀,直到1748年被彻底清除。即便在那时,贵族仍然保留了一些法庭(权力有限),作为对他们最终丧失财产权的补偿。
在这种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声誉,包括社会的、道德的和经济的声誉,是他或她的“信誉”。被纳入一个贵族的麾下并不是失败的标志,因为贵族应该保护和提升他们的走卒:贵族越强大,附庸就越富有,反之亦然。地主独立行动的能力因贵族身份的义务而受到严格限制:有时,贵族可能是他们佃户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在亚当·斯密教会人们区分经济效用和个人情感之前,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直认为经济是极富人格化的——几乎是道德化的。只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在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逐渐发挥作用。这就形成了“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在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中为人熟知。一种源于工人生活经历(比如煤矿开采或工厂劳动)的共享群体意识,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表达自我,比如在工会、出版、教育方面,他们还寻求代表权。
19世纪和20世纪的阶级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往往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偶尔还会起冲突,代表工人劳动者的工党的成立就是例证。在此之前,社会由土地贵族主宰,苏格兰土地贵族的数量和英格兰一样多,但英格兰的居民数量是苏格兰的五倍。20世纪之前很难低估贵族的重要性:相对于社会服务而言,他们肯定是自私、贪婪、吝啬的,但出于责任感以及自利意识,在王权衰弱的时候,贵族维护了社会和政府的运行;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由有着明确原则和激进意图的人所发起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宗教改革和苏格兰革命;贵族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有钱有势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个性特征的最大印迹。焰火般绚丽的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姆,或许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伍(他站在保皇党一边,但仍然光彩炫目),他在1650年惨淡地死去,但比起他那些盟约的对手,他的生命更绚丽多彩。
“绚丽多彩”可以成为很多事情的借口,但贵族支配的社会,尤其是对乡村社会的支配,却有巨大的社会代价。大多数在土地上劳作的人都没有土地。“土地租约”,尤其是宗教改革前后教会土地的租约,有助于创造一个较小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或“庄园拥有者”(贵族)阶层,这一阶层在经济上相当于英格兰的约曼不动产保有者(虽然数量不多),在社会上接近士绅。然而,1830年的苏格兰有7500名地主,到19世纪70年代,1500名地主拥有90%的土地。土地租约通常都是短期的,佃农很容易就被赶出他们的土地,却得不到任何租金。
佃农以下,是无数比佃农还低下、生活在黑暗阴影中的乡村无产者,或者说“茅舍农”,他们构成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更不稳定。让苏格兰人如此适应国外并被其同化(因而往往在种族上毫无痕迹地淹没于白人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国内就非常适应不确定、变化和迁徙的境况。最著名的1381年英格兰农民大起义,在苏格兰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从14世纪中期开始,奴役关系就从苏格兰消失了;重赋或常规税收,因所有社会阶层都不喜欢而被免除了;而且,苏格兰贵族对农民的经济控制和社会控制比英格兰强得多。
苏格兰具有流动性和韧性的乡村社会,解释了为什么18、19世纪会轻易发生那些重大变化。到19世纪20年代,低地社会的地主、佃农、无地劳动者之间已形成两极分化,大多数佃农以下的人以及众多小佃农都从土地上被轰走。在洛锡安,劳工大多是已婚男子,报酬主要是实物。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像东北部),小农场主和单个的仆人(住在屋内或屋外的“茅舍”或“宿舍”),他们的劳动在英格兰都是由雇用的日工所做的。额外的劳动需求由妇女儿童以及来自高地的季节性流动工人(因低地需要耕种)来满足。
结构性的依附解释了苏格兰为何没有发生类似1830年英格兰南部“斯温船长暴动”的事件。19世纪无处安身的苏格兰农民可以选择受雇于城市或海外,而在乡村,地主的权力仍然很大。在一位工人阶级的自传作者、边区的鞋匠看来,地主“受到他的影响力以及赞助权利的保护,以铠甲反对一切钳制正义的虎爪:实际上,他就是那位所谓国家正义的世袭制造者”。宗教也为平静和自信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这并不是说没人反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城市居民受地主支配越少,就越能表达自己的情感,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他们的人数很少。举个例子,1615年,女王总管及其官员在本泰兰受到袭击,并被一群妇女“以(无法无天的)亚马孙强盗的方式”殴打,这群妇女的意图是阻止他们强制实施一项朝廷法令。食物骚乱让18世纪的一些城市感到震惊,任何看似不可避免的征税都可能会遇到严厉抵制。拿破仑时代和1820年的一系列重大“叛乱”中,都有真正的激进分子。
表达社会和政治观念有更巧妙的方式。不受欢迎的地主或雇主可能会因流言蜚语、挖苦讽刺或暗地暴动而迁往其他地方(有时会整个家族一起迁移),由此势力被大大削弱,甚至被摧毁。一些宗教改革遭到剧烈挑战,教派分野可以表现出阶级差异。当庄园主禁止在其土地上进行礼拜仪式时,自由教会就在停泊于苏纳河的一艘驳船上进行集体礼拜。另外还提出法律诉讼和政治游说,19世纪的工会与早期的工匠及熟练工人协会一样,它们希望在法律范围内根据公正和道德的原则行动,希望作为雇员提高它们的待遇,而非作为全体来改变整个与它们有利害关系的社会。19世纪末的自由教会与高地佃农(小农场主)合作,以保证租约的合法变更。即使是弱者,也有武器。
然而,贵族权力无处不在,景观中就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12世纪起,重要的核心村落就在东南部形成,其他地方的农业据点都比较分散,直到18世纪的农业革命才有所改观,其景象更容易让人想起斯堪的纳维亚而非英格兰。对地主们而言,重塑乡村景观在法律上很简单。构成英格兰地方立法重要内容的圈地法案在苏格兰是没有必要的,因为17世纪末的一系列法案巩固了地主的权力,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结果显而易见,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苏格兰人打造了130个与众不同的被规划的村庄。这些村庄包括柯林斯堡(法夫)、埃兹尔(安格斯)、新皮茨里戈(阿伯丁郡)以及像因弗雷里(阿盖尔郡)这样完整规模的城市——因弗雷里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夷为平地,此后又整个被重建起来。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土地所有者对新的、改善的景观规则以及他们加在这些景观之上的财富和权力的看法。18世纪“新城”项目的开发具有讨人喜欢的统一性,这也源于地主拥有把土地租赁给建筑商时将建筑视图具体化的能力(见第七章)。
一些家庭被赶出土地,但农业仍然需要它们提供劳动力。被规划的村庄解决了这些家庭的问题,这些家庭中的人口最终成为纺织之类的手工匠人。纯粹工业性的村庄是新拉纳克,它于1785年作为棉纺厂而建成,并被改革者罗伯特·欧文打造为模范社区。欧文发自内心地相信教育,在其著名的“性格培养机构”(1816)里不仅教育孩子,还教育大人。地主的政策甚至触及性和婚姻。比较一下两个毗邻的教区,一边是班夫郡的格伦戈和洛特西梅(Rothiemay),另一边是内赫布里底群岛的泰里岛,这一比较就能解释地主政策如何深刻地影响18世纪末19世纪初苏格兰农村的人口统计实践和人口水平。班夫郡的农场兼并和公用土地圈占使得夫妻建立自己家庭的过程越来越难,结婚年龄越来越大,反过来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停滞;1871年,非婚生子率达到了30%。而在泰里岛,阿盖尔公爵的政策带来了早婚和相对低比率的独身生活的状况,结果创造了许多小农场和细分的租约,从根本上促成了人口过剩和贫困。
直到19世纪,政府实际上由贵族及其掌控的人员构成。国王支持他们的精英统治,因为没有成功的贵族治理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他们帮助那些失败者走出困境,乐于将荣誉授给那些有抱负的人和成功者。1611年,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一世)为了给乌尔斯特的军队提供资助推出了准男爵继承制——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贵族,并在1625年将这一计划推广到苏格兰,将钱用于建立新苏格兰[1]殖民地。再后来,劳合·乔治首相在商业基础上做这些买卖,但《荣誉法》(1925)的滥用并没有终结,其结局得看《政党法》(2000)是否能够成功。
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土地是食物、能量、原材料的源泉,是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之本。土地仍然有极高的威信,并被两极分化的所有权进一步强化:苏格兰的农村土地是私人所有,1250人拥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四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66个家族手中)。幸运的是,几百年来,苏格兰法律允许步行者以及其他打算对土地负责的人几乎可以普遍使用土地。
然而,土地的经济力消失不见了。遗产税和不断变化的财富来源、城市化和民主化的不断加剧,这些都褫夺了20世纪贵族的财富资源和影响。1917年,乔治五世引入了新的荣誉体系,奖励公共服务和志愿部门,从而使君主制脱离了贵族制。像阿盖尔公爵(数个世纪以来,阿盖尔家族一直拥有财富、社会势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马里伯爵这样成功的现代贵族也在进行转型,对地产进行现代化管理,扩大房产和旅游产业的范围。现代苏格兰有超级富豪,但他们是商人,整个社会在根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高地
一些非苏格兰人认为高地才是苏格兰,但实际上高地只是苏格兰的一部分,其重要意义在过去和现代都与低地迥然有异。尽管如此,高地在缔造历史上的苏格兰、创造苏格兰身份认同背后潜在的紧张关系方面仍然是非常关键的。
单从地理位置上说,高地和群岛向来是分开的。罗马人最远抵达马里湾,爱德华一世也是如此,但他们以及其他人在撤退时面对的却非真正的高地人,罗马人撤退到安东尼长城后面(在福斯河和克莱德河之间),然后是哈德良长城(从泰恩河到索尔韦河)。他们的其他边界是海洋,因为罗马人没有占领北海或爱尔兰海,因此苏格兰、西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爱尔兰之间的影响和反影响长期以来此起彼伏,冲突不断。高地的交通一直很困难,直到卡洛敦战役后,为了军事目的而改善道路和桥梁,状况才有所好转。然而,迟至20世纪60年代,从威廉堡到阿德纳慕亨半岛(Ardnamurchan peninsula,英国大陆最西端)50英里的旅程,开车4小时才能走完。
地理上的差异伴随着政治社会分离的历史。中世纪苏格兰王国得以成功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君主接受了其组成部分即盖尔人和布立吞人的不同传统。但高地和国王(以及低地人)的政治联系在14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高地中部酋邦中一些整合良好的权贵被越来越少的酋长取代,后者的地位取决于战争,这种状况破坏了秩序和统治。高地社会长期以来都不同于低地,但这种差异从14世纪才开始明确化,当时的统治者反对其中一部分传统,而逐渐把那些人视为“野蛮的、残忍的高地佬”(wyld wikked hielandmen)。
高地社会表面上比低地简单,因为它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和渔业构成,那里几乎没有城市。但就社会关系和态度而言,高地就复杂多了。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主要阶层。第一阶层是地主,中世纪的酋长,他们将地产留给中间人(通常是主要家庭的幼子)管理,这些人即所谓的“小土地占有者”(tacksmen),他们反过来将土地租给次一级佃农,佃农再租给小佃农和茅舍农。一小块土地(tack[2])就像一份租约,但苏格兰的租约仅仅意味着一种占有权,而非英格兰的财产权。
18世纪,随着地主或中层地主优先权的转变,高地社会经历了各种变化。很多人实际上拒绝承认几个世纪以来有那么多贵族。因为掌管氏族的酋长是以亲缘关系、租约关系、宴请和馈赠所形成的纽带为基础的。17到19世纪,地主或小土地占有者拒绝履行的管理和照顾义务似乎并不明晰,但农民却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义务,并极为珍视它们。其核心意思是所谓可继承的共同所有权(duthchas[3]),这种权利意味着领主掌管土地是受他手下那些人的委托,他有强大而又不成文的义务。而在低地,写明条款的才有权利,没写明条款的就没有任何权利,除非领主出于自己的理由承认权利。土地租约使得社会高度流动。一些人实际上世世代代耕种着同一片土地,但几个世纪以来,高地的佃农租地周转率却像低地一样高。大多数农民租地都是随心所欲的(或心血**),因此,即便在17世纪,几乎都没有持续性的镇区或“乡镇”。
土地所有者一般会顾及农民的利益,同时也维持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庞大的“被庇护基础”。最初,他们通过重新分配劳动力供给来对应18世纪的人口增长、经济转型,以及他们自己不断变化的优先权,因为他们的权利能够让他们那样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人口拥挤、经济边缘的渔村或工业上缺乏持久力的工业企业(像从海边收割海藻充当肥料这样的企业)中采取整体驱逐或殖民行为。后来,他们尝试移民计划。
人口减少不是故事的全部。良性的地主政策和渔业的充分就业让刘易斯岛的人口在1841—1901年间从17 000增长到29 000。尽管如此,苏格兰高地作为一个整体,在18、19世纪人口逐渐减少,给低地和海外移民造成了一种长久的怨愤,高地的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低地出现,这就加剧了地区间深刻的历史差异。19世纪,高地经历了欧洲其他地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曾有过的社会剧变。
当今,90%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低地,大多数人住在核心地带的城镇和城市。苏格兰拥有不列颠三分之一的陆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高地的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只有23人(格拉斯哥是8550人)。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荒无人烟,无人居住,除了鹿,连大型动物都没有。然而,1755年,苏格兰一半人口都生活在北部和西部,显然,这里有充足的资源维持大量的人口吃喝、打斗和馈赠。自17世纪起,将牲畜从高地和群岛赶到低地以养活低地人(后来甚至还有英格兰城镇)成为一项大生意。
历史上人口缩减的程度确实令人触目惊心。1841年,天空岛养活23 000人,一个世纪后是10 000人。更极端的是泰里岛,目前除了冲浪季节,其人口只有700人,而在1831年,这里可是有5000多人。
高地与苏格兰认同
对苏格兰移民的传统理解集中在被剥夺的高地人上,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见第六章)。高地的形象在现代概念化的苏格兰历史中也扮演着一种极不相称的角色。现实还是那么复杂多变。实际上,将高地生活的物质方面(石楠和蓟花、风笛和格子裙)与苏格兰象征这二者联系起来,是18世纪浪漫主义复兴时期伦敦人的发明,19世纪一二十年代,伟大的托利党人和君主制主义者、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掀起的那场耀眼夺目的公共关系运动巩固了这一联系,而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年在位)则将其制度化。
司各特的小说早已播下了种子。当时,他意识到新国王乔治四世(1820—1830年在位)需要一番改头换面,他还规划了1822年乔治四世对爱丁堡的造访(自1651年查理二世加冕后这是头一遭)。从一个层面上讲,司各特1822年的作品是极其愚蠢的,那位胖到超重的国王被套进虚假的高地礼服,向“苏格兰的宗族和酋长”致敬,而他的祖先却曾试图削去那些人的势力;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个作品又是极其精明的,它宣扬了一个新的苏格兰形象,即它在联合中的政治从属地位是平行的,并为汉诺威人奠定了一种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司各特帮助普及了苏格兰人等同于高地人的浪漫形象。他的道具之一便是花格子,另一个道具便是短褶裙,这种裙子是18世纪20年代一个英格兰人发明的:高地人传统上穿戴一件被称为“毛呢长披肩”的花格子布,这块格子布垂在臀部以下,或者像裤子一样收拢起来。通过巧妙地营销其与名字或氏族的联系——甚至是低地的名字或氏族——花格子作为一个民族象征成为苏格兰-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并获得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这种捏造的詹姆斯主义或盖尔主义,仍然成为不列颠人的一部分。从1842年开始,维多利亚女王就特别喜欢高地,自此,她为王室塑造了一种多元的、“苏格兰化的”形象。1848年,女王买下了阿伯丁郡的巴尔莫勒尔地产,从此,它就成为温莎王室的度假胜地。为了寻求和解而非赞扬其讽刺意味,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王子乐意穿上斯图亚特的花格子,也乐意采用他们自己的发明。
司各特在把高地不能接受的那一面转化成某些值得崇拜的事情之际,还有更多需要解释的问题。罗伯特·麦格雷戈(Robert MacGregor,后来的坎贝尔)或罗布·罗伊(Rob Roy, 1671—1734)是一个(貌似可信而且讨人喜欢的)偷牲口的盗贼、骗子、勒索犯、叛徒,他借助自我宣传和一位虚构的传记作家之口,逐渐转变为苏格兰版本的罗宾汉。到了1818年,他在司各特的笔下变成了民族文化的象征:一个低级趣味的骗子。司各特制造了一种可接受的苏格兰特性,以捍卫汉诺威王朝和帝国试验,赞扬苏格兰社会的混合特征,邀请后詹姆斯党、后启蒙时代的读者拥抱一致认同中的多样性,承认政治稳定和经济变化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司各特意识形态化的发明是一种妥协;自文艺复兴以来,低地人和高地人之间的敌对从未实现这种妥协。那时候,低地人对于明显美化他们眼中的野蛮落后之地的行为感到胆战心惊。从19世纪20年代起,爱尔兰开始急切地移民,他们的态度坚定并蔓延开来。后来,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人表现为进取、勤奋、得体、有秩序(当这些特征没有被夸大时便是褒义),他们得到了比爱尔兰人好得多的宣传,而爱尔兰人反过来则被写成忘恩负义、懒惰、邪恶、半野蛮的。然而,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便是高地人身上更多的是爱尔兰人的气息。低地苏格兰人从18世纪对高地人、19世纪对高地和爱尔兰人的矛盾心理中,生发出一种种族认同感,而英格兰人缺少这种感觉。低地人认为对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经济改善的追求,在一段共有的民族史中没有族群的基础,但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种族特征。
受整个欧洲种族主义发展的刺激,19世纪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的民族寻找种族基础,他们提出“谁是苏格兰人”这样的问题。他们找不到共同的血统,相反,只有混淆的身份。最重要的是,曾被贬低的地区(苏格兰盖尔区)特征鲜明,与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区(他们的苏格兰维度包括一种主张,即民族源于皮克特人而非盖尔人)截然相反。苏格兰从未有过单独(或者甚至是单一)的族群,这一事实意味着根据欧陆模式创造民族主义的努力注定失败。低地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英格兰人共享身份认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苏格兰人热烈地支持联合、参与帝国,以及更冷静、理性、体面的君主制,而非1848年后欧洲危险的民族主义。低地人尤其认为苏格兰的盖尔传统往坏了说是一种尴尬,往好了说是一场配角的穿插表演。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众多,其中之一是苏格兰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种族认同感。(苏格兰人像谁?)
令人害怕,被误解、被诋毁或被情感主义化,苏格兰高地人保留着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也展现了“苏格兰性”和“英国性”的元素。精英们将高地置于与英国其他地区互相支持的关系中,强调它如何为帝国提供军队和粮草,从而试图弥合其与低地的鸿沟。然而,整个19世纪,高地社会本身在财富、教育、语言和景观方面仍然与低地社会存在隔阂。司各特的同时代人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 1770—1835)以及后来的查尔斯·麦凯博士(Dr Charles Mackay, 1814—1889)创作了一系列暗示文化一致的诗歌,但还是忽视了过去与现在社会和文化的分层。
如果一些高地人致力于整合,另一些人的回应则是寻求对自己不同身份的支持,比如,1893年自由长老派教会的创建。逐渐消失的盖尔语是另一个焦点(见第七章)。土著居民与外来人、独立与从属这些相互抵消的影响构成了苏格兰历史,但苏格兰本身的内在紧张、低地与高地最深刻的历史冲突也塑造了苏格兰历史。
现代高地
就高地人的身份认同而言,比语言、族群或宗教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家庭、社区和土地的情感联系和物质联系。从黑暗时代到20世纪,高地精神中流行的是通过亲近土地而纾解的相互关联的亲缘感和空间感。
最直白的表现方式在于强劲的反抗传统中——高地人认为他们以前的酋长违背了可继承共同所有权,因而他们一直抵制这种行为。强制驱逐导致19世纪中期的对抗,但后来的运动更具建设性,运用模糊但重要的可继承共同所有权观念以及数个世纪以来古老回忆的资源,把被征用的土地还给曾经耕种过它的那些人的后代。“土地劫掠运动”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代的民谣和诗歌都纪念了这一活动,法夫的现代艺术家威尔·麦克林(Will Maclean)在现代西部群岛贫瘠景观的怀古雕塑中也体现了这一点。
从1886年到20世纪20年代,高地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双重所有权”概念和“所有者使用权”概念之间一直存在政治冲突。自由党致力于通过保证小农场佃农的可靠租约来减少地主的影响;保守党希望将地主从他无利可图的佃农土地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佃农所有者占有权。改革在继续。1883年,纳皮尔委员会帮助解决了租金和租约的争论;1886年,佃农持有法减少了地主对佃农的影响。1897年的法案彻底改革了高地,但当时的情况是需要改变农业和畜牧业的态度,而这一点被佃农回避了。农场社区本身不仅在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是一分为二的,而且在佃农和茅舍农之间也是各自分开的——佃农持有小块土地,而茅舍农只能作为劳动者或被容忍可以擅自占用土地。佃农想要更低的租金、可靠的租约(所有权不是必需的),更大、更富饶的田地;茅舍农只想要田地;所有人近期都想拔掉围栏恢复放牧。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佃农而言,土地就是安全和地位的象征。
土地仍然重要,但现代高地的身份认同更多聚焦在它欠发达地区的地位以及从政府或欧盟寻求经济、社会利益的政治诉求上。这种趋势始于19世纪初,那时,英国历史上第一项重要的公共工程项目在高地进行试验,财政部把重金投到公路和桥梁上,以改善公共设施,创建就业。1965年,高地和群岛发展董事会成立,巩固了这一成就。其成功表现在人口增长,尤其是在天空岛,而当时苏格兰整体人口在下滑。
重整旗鼓的障碍仍然存在。一些人对高地怀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但高地环境糟糕,人民生活困苦。20世纪高地的移民主要是努力逃避“不被清除”(其动机说明了强制性的人口再分配)的年轻人,但家庭农场会自我剥削。1930年,圣基尔达岛应当地居民的要求被彻底清空。
现在找工作很难,住房则更难。苏格兰不同于挪威或尼德兰,它没有立法限制非当地人或非本国人对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卖掉了很多市政公房,因此租房就困难了。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像普洛克顿(罗斯-克罗马蒂)那样遥远的、风景宜人的乡村,房价几乎接近城市水平,远远超出当地收入。毫不奇怪,这让改变经济总体情况变得更难。怨愤情绪已经蔓延到“英格兰人出局”、抵制二套房的小规模运动中,因为一些人认为他们让苏格兰大农村成为繁荣的玩物,其社会代价是不可接受的。
高地地区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体现在酗酒和男性自杀率居高不下的现象上。更具建设性的是,反对天空岛过桥费(1995—2004)的艰苦而成功的运动,以及承租人从没有所有权的阿辛特地产(Assynt, 1993)、爱格岛(1997)土地中收购股份的运动,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集体记忆和强大的平权运动传统。
高地苏格兰和低地苏格兰的地区特征逐渐模糊,但对游客和新来者而言,北部和西部的人民仍然有一些自我封闭的、危险的东西,阿勒浦、勒威克、洛欣弗这样的地方仍然给人一种边界的感觉。
[1]Nova Scotia,拉丁语意为“新苏格兰”。在法语和苏格兰盖尔语中,该词都直接翻译成“新苏格兰”。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va_Scotia。
[2]Tack,是指17、18世纪苏格兰高地氏族社会的一小片土地,拥有这片土地的人被称为“佃农”(tenant)。参见http://www.petestack.com/tacksman.html。
[3]duthchas,苏格兰盖尔语,其意思很难准确地对应到英语中,大体上是指特定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这种权利根源于一个氏族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特定地区的古老世系传统。这种共同拥有土地的观念从未被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风俗,作为一种事物的自然秩序而被高地人所接受。参见http://www.clanjames.com/duthcha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