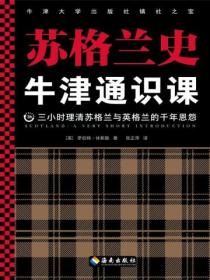第六章 苏格兰和广阔世界
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
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敌意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第一章所说,黑暗时代的不列颠在政治和社会上都是流动的。王朝联盟和“诺曼化”可能创造了中世纪更大的统一。实际上,英格兰只是在12世纪才开始将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看作野蛮人和异族;从14世纪开始,低地人才察觉到高地人和他们不同(反过来,高地人也一样), 1400年,一种固定的反英情绪才在某些苏格兰人中间明确起来。因此,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关系表层之下,冲突从未消失。
英格兰的诺曼国王们可能有时待苏格兰人不够公正,真正让两地关系恶化的恰恰是独立战争。严格地说,战争只持续到1328年,但间歇性的恶意冲突一直持续到1560年,这就带来了不信任、两面派、背信弃义、背叛的遗产,这份遗产仍然存留在当今生气蓬勃的苏格兰-英格兰的关系中。爱德华一世将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苏格兰国王的就职仪式(从1329年开始有正式的加冕礼)都在斯康宫(珀斯郡)举行。爱德华还有其他一些破坏活动,他将“加冕石”从斯康宫移走,希望盗用苏格兰国王祖先和谱系的象征。这些国王坐在“加冕石”而非站在上面,这使得它的位置十分怪异,就像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王座下的座椅式便桶。直到1996年,它才在保护托利党的苏格兰席位这一可怜的努力下被送回来。
后来的英格兰国王毫不费力地扩大了爱德华的遗产。早在1348年,一位编年史家就写道,英格兰人成群成群地死于瘟疫,苏格兰人是多么兴高采烈;而1435年一个游客评论说,“最能让苏格兰人高兴的,莫过于虐待英格兰人”。1400年,亨利四世率领军队前往爱丁堡,试图宣扬他作为苏格兰霸主的主张,但最终,他被礼貌地遣送回国。爱德华四世(1461—1483年在位)和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更具外交策略:亨利在1502年议定“永久和平”,并娶了詹姆斯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这也使得1603年两地共戴一君变为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国王逐渐认识到,苏格兰不可能被征服,英格兰才是它唯一要关心的,尽管他们从未真正承认这一事实所暗含的独立。就他们而言,中世纪苏格兰的历史把苏格兰置于欧洲和中东历史的语境中,有很长一段时间,苏格兰的政治国家似乎对他们的邻居毫不关心。
亨利八世对苏格兰的王朝从属地位有着浮夸的帝国野心和信念,相比他父亲亨利七世,他对此的推动要努力得多。亨利八世计划让他的儿子爱德华迎娶詹姆斯五世尚是婴儿的女儿——苏格兰人的女王玛丽;1542年索尔韦-莫斯战役后詹姆斯逝世,这一计划被孩子的母亲(吉斯的玛丽)以狡猾的外交策略摧毁了。亨利随后的动作毫无巧妙可言:他发起了一场“粗暴求婚之战”[1],包括对苏格兰南部毁灭性的攻击。
那时候,人民之间的联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上帝本人是英格兰人”这一主张来自1559年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该文本警告英格兰人“既不要怕法国人,也不要怕苏格兰人”。那时,英格兰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在《麦克白》(1605—1606)中把苏格兰人塑造得和英格兰人一样高贵文雅,即便有此相助,詹姆斯六世/一世还是希望苏格兰人将会忘记英格兰人的傲慢无礼,创造一个“一致消除仇恨”、忽视几个世纪历史的联盟。
制度化的歧视和偶然性的种族主义都会触动身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一些律师对于为苏格兰人要求英格兰公民权感到十分乐观,但1492年,亨利七世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没有入籍的苏格兰人从英格兰驱逐出境。边区人因几个世纪以来的侵袭对其邻居怀有复杂的心情。15世纪,在英格兰北部把某人错误地说成苏格兰人是可以对其进行控告的,而纽卡斯尔的行会则直接拒绝接受苏格兰学徒。
作为经济移民,后来的苏格兰人在18世纪的流行艺术和流行文学中屈尊俯就或被诽谤中伤,漫画恶搞苏格兰人小气、狭隘的行为和志向,这为19、20世纪媒体对苏格兰人的刻板形象奠定了基调。18世纪在伦敦找工作的苏格兰外科医生,在心怀不满的观察者眼中就像“一群贪婪的秃鹫”,而哲学家大卫·休谟及其同时代人布特伯爵这位乔治三世以前的家庭教师、18世纪60年代的政治领袖,都亲身感受到了那里的反苏格兰情绪。苏格兰议员和同侪,或者用私下取悦现代同辈的话说,被描述成“非常适合经商的一类人,爱搞阴谋诡计、狡猾、欺诈他人”。即便苏格兰人有功于英格兰社会,他们还是会有疏离感,他们仍然意识到文化模式、经济机会和政治焦点都在英格兰。
文化影响
历史上的苏格兰人和他们的现代继承人一样,只有当他们不得不思考英格兰时才会去想一想。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在做整体思考:从罗马教皇到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的贸易,再到法国的教育和外交政策。英格兰的影响是有的,但直到18世纪,它只是众多影响之一,而在像教育、法律、宗教这样的重要领域,英格兰在其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从那时起,一个世界帝国也出现了。
欧洲为苏格兰提供了战争、外交、商业和文化焦点,这些焦点经久不衰、不断变化。和法国缔结的“世交”提供了对抗英格兰的军事支持,尽管这一“世交”建立在古老得多的盎格鲁-诺曼魂灵之上:1212年,苏格兰宫廷被形容为“种族和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上都是法国的”——就像从布尔戈斯到耶路撒冷的众多宫廷一样。英格兰国王想继续索要法国领土(就像16世纪之前他们一直做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对苏格兰的侵袭多加思量。15世纪,苏格兰军人和法国人一起对抗英格兰人,并在1618—1648年**欧陆的那些战争中站在新教军队一边。
中世纪的苏格兰羊毛流向布鲁日(现代比利时),然后到勃艮第的部分地区,换来的钱用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王后(海尔德的玛丽)以及维护两个大型的攻城武器,其中一个是位于现在爱丁堡城堡仍然指向城外的“蒙斯梅格”大炮。16、17世纪,苏格兰人跨越波罗的海和北海进行贸易,但与低地国家的费勒和鹿特丹的贸易最值得关注,在那里,他们用原材料交换专业制成品,包括代夫特蓝陶和荷兰画作。欧洲的大学为苏格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罗伯特·西博尔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创建的爱丁堡植物园就是以莱顿的“药用花园”(1667)为模板的,荷兰的训练引导18世纪苏格兰的医学学校走向兴盛。
文艺复兴时期,苏格兰几乎不是主要角色,但苏格兰的国王们被认为是受过文化熏陶的。詹姆斯一世素有名声,他是位技艺高超的弓箭手、音乐家和诗人,最著名的要数他写的诗歌《国王书》(The Kingis Quair)。后来的君主因其自尊骄傲、谨慎外交、对文化和建筑的良好风格感、恰当的时尚感而在欧洲舞台上崭露头角。文艺复兴的文学很大程度上是进谏和政治文化,当詹姆斯三世创作诗歌,詹姆斯五世委托布坎南和大卫·林德赛爵士(Sir David Lindsay)创作,或詹姆斯六世撰写政府文章时,每位君主都在被文化熏陶,但每位君主也在运用他的宫廷文化实践其政治目的。出于相同的理由,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君主都赞助了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的音乐家。
从中世纪起,欧陆建筑风格的模板丰富了苏格兰的建筑环境。英格兰的垂直建筑在中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教堂中几乎是鲜为人知的,他们最强烈模仿的是法国“浮夸的”建筑风格。14至16世纪,罗马风格的建筑特征在四个重要的宗教中心都能找到。这四个中心分别是阿伯丁、邓凯尔德、圣安德鲁斯和邓弗姆林。苏格兰罗马风格的坚定复兴预示着它接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图案。林利斯戈宫,1425年始建于詹姆斯一世时期,在詹姆斯三世和詹姆斯四世时继续扩大,其模板是意大利像威尼斯宫一样的华丽宫殿,还有其他一些过于铺张的项目,包括斯特灵的布洛克宫和福克兰宫殿(两座宫殿都建于16世纪初)。荷兰影响下的鸦形山墙(vernacular architecture)成为15至17世纪苏格兰本土的建筑风格,以库罗斯到克雷尔一带法夫郡的渔村最为有名。
图10苏格兰人向来是移民民族,这里描述的是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在德意志北部为瑞典人打仗的士兵(但德国的说明文字错误地将其标成了爱尔兰人)。这幅图描述了“花格子”披肩即被绑住的那块布的穿着方式
移民
“到处都是老鼠、虱子和苏格兰人。”大约从中世纪起,这句法国谚语就流行开来。在工业化和铁路普及之前,人们在其教区教堂的见证下出生、生活、死亡(实际上法国人就是这样的),和这种通常的成见相反,苏格兰人从很早的时候移民程度就很高了。18世纪一个教区的一半人口,在一代人之内都会迁往他处,然后被新来者取代,这要多亏土地租约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有时会限制经济机会,而济贫制度让身体健全的失业者努力寻求帮助,迁徙的年轻人则成为家仆和农工(20世纪以前,大多数十几岁年轻人的工作就是这些)。不断搬家或变换工作十分常见,因此,频繁的迁移也不是什么痛苦之事。
正如以上谚语所说,从13世纪起,苏格兰移民就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到了17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包括俄国)、低地国家、伊比利亚以及法国,都能看到苏格兰人的身影。其中,一些苏格兰人是商人,另一些人是军人和水手,少量的是学生。很多临时迁移和永久迁移都是个人行为。大多数移民都是年轻人,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几个世纪以来女人初婚的年龄很大。一些是全家移民,但有组织的移民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
第一个例子便是乌尔斯特种植园(1609—1641),该种植园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承包商”实施的一项社会工程:获得土地的所有者要向人们承诺他们所获土地上的佃农应该忠于国王、信仰新教。17世纪末,苏格兰移民大多数都是勤劳的、一心想逃离迫害的长老派教徒,他们的信仰不仅使他们与爱尔兰本土的天主教冲突,而且与爱尔兰的圣公会冲突——这是杯永远苦涩的鸡尾酒。17世纪,更多的苏格兰人可能去了波罗的海,而他们在乌尔斯特所带来的长期政治遗产远远超出单纯数字的意义,因为新来者以独特的方式感受到了他们的宗教使命和社会使命。另一些人开始移民到北美(新泽西和南卡罗来纳),尤其是17世纪末以来的苏格兰移民,尽管英格兰迁移到美洲的人数远远大于苏格兰。
18世纪,苏格兰移民加快了步伐。1700至1780年间,有6万自愿的移民,但并非所有移民都有选择。17世纪,白人奴隶贸易从阿伯丁小路上拐骗9~10岁的孩子,然后将他们卖到弗吉尼亚州;1870至1920年间,有10万孩子——他们绝非都是孤儿,被船运到加拿大;迟至20世纪60年代,强制移民到澳大利亚仍是解决孤儿和赤贫孩子问题的一种方式。1776至1857年间,澳大利亚也是运输罪犯的倾泻地之一。
比儿童贸易更为人所知的不义移民是19世纪的人口清理运动,尤其是前文讨论的高地悲剧故事。但高地的强制性清场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18世纪末19世纪初,高地移民往往是农民主导的,这是地主强烈阻止的一场运动——一场“人民的清场”。如果说有一类移民是来自被高地清场运动剥夺的一无所有的人,那么,低地移民(与城市和工业极不相称)的苦涩程度与高地(农村)一样严重。这里的人口外流不是来自像挪威或葡萄牙这样落后的农业社会,而是来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尽管如此,1800至1939年间,仍然流失了200万人口。大多数人去了北美(28%去了加拿大,44%去了美国),25%的人口去了地球的另一面[2]。1781至1987年间,大约有50万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移民人口仅次于欧洲的爱尔兰,这些移民很可能是来自生机勃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自愿流亡者,而这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也吸引了大量的爱尔兰移民。移民有文化修养,有娴熟技术,还很积极进取,苏格兰向外输出的人口往往都是顶尖人才。苏格兰人在建设北美的过程中作用非常重要,其烟草商人和其他一些大商人活跃在东海岸的主要城市。1850年之前,北美(以及其他地方)几乎所有的英国医生和众多牧师要么是苏格兰人,要么在苏格兰受过训练;苏格兰的教育家在普林斯顿和费城也相当活跃。移民工业家发展经济,有助于外国经济的现代化,尤其是日本的托马斯·格洛弗(1838—1911)和美国的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60年代,移民潮再次高涨。举国恐慌的年代,诗人埃德温·缪尔(1887—1959)把20世纪30年代视为“沉默的清场”。苏格兰的移民率目前仍然是联合王国里最高的,这源于一个明显成功的现代经济。
虽然乌尔斯特的苏格兰人为联合和拥有一个新教祖国而努力奋斗,但其他地方的苏格兰移民却没有那样做,他们宁愿通过“适应”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举个例子,苏格兰人和苏格兰裔爱尔兰人(甚或苏格兰-不列颠人)都变成了美国人,天主教爱尔兰人变成了爱尔兰美国人,他们保留了一种身份,并为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贡献一份力量。海外的苏格兰人构成了一个族群范畴,他们因为历史感和与外人比较的差异感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也构成了一个族群,以社会组织和偶尔的政治组织的形式表达共同的目标,然而,尽管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苏格兰人后裔仍心系他们祖先的家乡(这种感觉在以前的“白人”殖民地最为强烈),但他们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的国家和疆域的指涉(就像爱尔兰一样)的种族共同体。苏格兰人适应外界,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世界也喜欢他们。
好吧,或许并不是全世界都喜欢他们。现在英格兰有近120万出生在苏格兰的居民,这些人和苏格兰游客有时会被随心所欲的种族主义者冠以“Jock”这样的“宠物”名,而且他们习惯性地提及哈吉斯、威士忌、苏格兰裙这些会挑起争端的话题——如果不是对抗其他少数族裔所谓的文化象征的话。通过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凯尔特祖先的特征——诸如好酒、好斗——来确认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的身份,仅仅是19世纪种族主义陈规旧习的延伸而已。
这种显然不足挂齿的傲慢突显了某些英格兰人对待苏格兰人的两种心态: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布立吞同胞接受,另一方面仍然把他们看作是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一种恼人的东西。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心态可能也一样(可见下文)。英格兰人的矛盾心态解释了托尼·布莱尔这位在爱丁堡出生并在那里受教育的前首相(1997—2007年在任)为何拒绝直接回答自己是不是苏格兰人的问题,因为如果说自己是苏格兰人,在政治上可能会受损。现在的首相戈登·布朗[3],明显更是位苏格兰人(在法夫的柯卡尔迪长大),可能有时也喜欢做同样的事。
帝国
18、19世纪的英帝国有很多苏格兰人,其中一些还帮助管理这个帝国。不过,苏格兰的首次帝国经历的结局尚可接受。有着聪明才智的罗马人把文明带到了北欧:城市、公路、文化、艺术以及公共澡堂。有一句嘲讽1066年以及全部英格兰史的口头禅(1930)便是:“罗马征服是……好事情,因为布立吞那时候只是土人。”然而,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密集,在罗马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把不列颠居民打上野蛮人标签的很久之前,不列颠就有了成熟的农业、工业、政府和交通措施。强劲的本土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解释了为什么罗马统治时期的众多文化措施——比如宗教——从未起到作用。拉丁语只在有学问的人中间经久不衰,尽管它丰富了所有的词汇。真切可感的遗产也有,比如建筑、公路、景观边界,以及非常模糊但仍很重要的整合到欧洲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网络中的经验。
殖民地人民经历了罗马人对他们(而不是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忍受了长达350年的征用、剥削和军事占领。罗马人撕裂了之前已有的政治制度,创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帝国机器,为了罗马需要而牺牲当地人的发展。公元2世纪,阿多克堡(珀斯)容纳了2万名士兵;3世纪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对抗美阿泰王国和东部低地的加利多尼亚人的战役,可能涉及5万人之多的军队交战——这个数字在此前或此后的不列颠土地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段帝国经历是在挪威人手中,接着是雄心壮志的诺森布里亚人,然后是英格兰的君主。早在10世纪,英格兰的国王就喜欢声称统治“居住在不列颠岛范围内的所有其他民族”。诺曼人也有这样的愿望,其更好的实现方式是间接影响,而非爱德华一世及其继任者们强行施加的那些强硬措施。直到16世纪,“帝国”对英格兰人而言意味着统治不列颠(以及最好还有法兰西),尽管在独立战争后,英格兰的攻击更多是惩罚或先发制人地威胁苏格兰,而不是尝试真正地征服这个国家。
从詹姆斯三世开始,苏格兰君主也明确主张扩大和巩固帝国。其中一个含义便是要面对他们的殖民问题,他们运用策略、宣传、武力来同化、平息以及“开化”讲盖尔语的氏族社会;1609年颁布的《爱奥纳法令》把这个社会污名化为“野蛮和不文明”。只有在18世纪,“不列颠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被重新定义,它强调这不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而是有共享计划或共享的公共财富,然而,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坚持不懈的高地“文明化”计划实现的。
苏格兰人自己在巴拿马建造海外帝国的计划崩溃之后,急切地参与到不列颠的世界帝国中,并陶醉于它获得的利益。18世纪中期,他们获得了格林纳达和牙买加的大片土地。18世纪末印度九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一的军官是苏格兰人。鼓舞人心的赞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由盎格鲁-苏格兰人詹姆斯·汤姆逊创作于1740年。1914年,不列颠帝国囊括了四分之一的人类,那一年,年轻的苏格兰人集结在一起反抗德国,捍卫帝国(27%的成年男人参加了战斗,10万人再也没有回来);如果没有帝国,苏格兰19世纪工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和不列颠的罗马人一样,帝国带给国外土著居民的影响有好有坏。积极的一面包括交流、行政和政府结构、正式的法典、教育以及(可以说)英语语言本身。更多消极的方面,包括饥荒、苛税、谎言、掠夺、土地劫掠、鸦片贸易,这些都不可能被忘记,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为了适应殖民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求,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扭曲的结构今天仍然能感受得到。种族屠杀、酷刑、性羞辱都是英帝国统治的工具。对牙买加奴隶起义的惩罚是“用弯曲的棍子把他们的四肢钉在地上,然后用火慢慢从脚烧到手,渐渐烧到脑袋,用这样的方式,奴隶是最痛苦的”。苏格兰人不受现代政治正确概念的束缚,他们机智多变,运用各种手段获得商业利益,包括与奥克尼的男人和加拿大哈得孙湾的土著女人“联姻”。苏格兰特有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在缓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最终鼓励退出帝国所发挥的部分作用,并不能掩盖殖民主义更黑暗的一面。
现代的评论者可能对帝国时代感到局促不安,即便那时不列颠仍然与美国致力于后帝国计划。现在几乎没人会称赞20世纪初约翰·布坎夸张的崇武精神、帝国主义的奇闻漫谈,现代读者会认为那些特征在政治上错得离谱。然而,即便深受后殖民罪恶的困扰,也很难不尊重离开苏格兰海岸线的那些人乐观、进取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多人可能盼望回家,19世纪末三分之一的移民的确回家了,但超过一半的帝国移民死于暴力冲突或死于疾病——18世纪的加勒比和印度在任何时候都特别不健康。
我们也不能忽视苏格兰人对自己在国内外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份紧张的自豪感:帝国的学校教育表明苏格兰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格拉斯哥鼓吹自己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像1883年创建于格拉斯哥的基督少年军这样的志愿团体,推动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并歌颂帝国的成就。苏格兰海外军团的自豪感既扩大了君主和崇武精神的联系,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移民与文化多元性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一直都是人口的净输出国,移民只能通过有限的内向移动来平衡,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东欧、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大量移民。19世纪以前,所有的移民都是小规模的,爱尔兰人是第一批重要的移民:1871年,苏格兰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是爱尔兰裔;1901年则有十分之一,他们主要出现在大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一些移民是乌尔斯特的新教徒,但大多数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没有融入当地,而是生活在某些特定(贫穷)的城市区域,几乎很少和当地苏格兰人通婚,他们的种族、宗教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拥护都令当地人反感。
自宗教改革以来,教派主义此起彼伏,其巅峰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在正在消退,表面上似乎局限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自1899年这支球队迁到艾布洛克斯起,其成员都是新教徒)和凯尔特足球俱乐部(历史上其成员都是天主教徒)的派系之争。在那个时代,基于恐惧和厌恶,双方都是强大凶险的势力。新教奥兰治兄弟会认为天主教是反新教、反英国的第五纵队,他们致力于歧视、消除天主教,将宗教的对抗情绪和种族主义混同起来,既反高地人,也反爱尔兰人。
17世纪以来,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裔很少为人所知,但到1921年,他们取代爱尔兰人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目前是整个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有整整五分之一住在苏格兰南部)。英格兰人在苏格兰的现代形象是反城市的“白人定居者”,他们声称抛弃了伦敦的六位数薪资、七位数房产,为的是在苏格兰高地的房子里过着宁静的生活。而现实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是来工作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最近才是管理工作。
英格兰新来者的出身有时仍然会被拿来开玩笑,他们的待遇不像其他外国人,而像英格兰人。然而,他们通常会被接纳,并逐渐理解了成为苏格兰人所蕴含的意义:历史感(包括英格兰投射过来的政治和文化阴影)、社会平等感、公民信任感和公民同情感,独立而有思想的、开放的、热诚的人民。生活在苏格兰的英格兰侨胞可能比苏格兰人还苏格兰化,他们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声嘶力竭地为这个接纳他们的国家振臂高呼。当英格兰人没有参赛时,即便是他们也会在体育赛事中认可苏格兰(或爱尔兰),这与其说是共鸣,不如说更像家长式作风。大多数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宁死也不愿双方互惠。而英格兰人无论在哪里,如果有合适的玩法的话,他们往往乐意打苏格兰牌,无论他们对苏格兰人的情感有多矛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移民群体丰富了苏格兰社会,这其中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内,为躲避贫穷和迫害而移居苏格兰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从中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长的时间形成了一个传统,即现在大多数优秀的移民都是东欧或“新”欧洲人,他们通常填补了苏格兰本地人生育率下降、变换工作选择所导致的各种体力劳动的空白。来自欧洲各地以及远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轻人,也热衷于在苏格兰生活、工作。
通过外表而非口音来辨别少数群体在苏格兰是不常见的,而且过去也一直如此。黑人除了当仆人之外,还在英国舰船和军队中工作,直到19世纪中期,新的种族主义将他们排除在外。到20世纪,生活在苏格兰的非白人有数百人,即便新的英联邦移民人数也是很少的:1950年,苏格兰有600名亚洲人,1960年则有4000人。目前,苏格兰人口中非白人的比例不到2%,“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比英格兰少得多,因为英格兰的非白人占人口总数的10%。
不宽容仍然存在,可能是因为少数群体人数太少,而且相对沉默。毫无理由的反犹主义、轻率的种族主义——比如把中餐说成“Chinky”[4],这些都消失了,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些被恐伊斯兰情绪取代了。另一些少数群体,诸如游客之类,正在被接受。但在多样性中追求平等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2000年时,和其妹安·格洛一起创建现在繁荣的Stagecoach这个交通公司的布兰恩·苏特,引领了一场充满活力也很受欢迎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成功的)反对废除禁止促进同性恋立法的运动(苏格兰在1980年才取消对同性恋的刑事定罪)。苏格兰人逐渐接受了少数群体可以追求另类的私人生活方式,但他们也保留了把某些选择视为于公众而言是道德错误的权利。
[1]苏格兰和法国的同盟历史悠久。亨利八世打算摧毁这一同盟,故发动战争,强迫苏格兰王位继承人玛丽嫁给其子爱德华,从而削弱苏格兰人,阻拦法国人。
[2]the Antipodes,指地球的对跖面,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2008年本书出版时,英国首相是戈登·布朗。
[4]Chinky,英语俚语,指中国食物,带有民族侮辱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