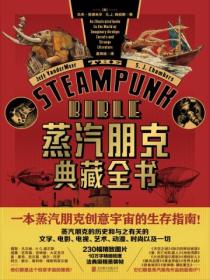蒸汽朋克艺术家,还是蒸汽朋克创客?
蒸汽朋克创作者虽然往往拥有同样的审美热情,却很难被具体定义。有些人把自己视为艺术家,并且遵循着艺术家这一群体的通用准则和术语。而另一些创作者的自我认同则是创客,这让他们和修补匠、机械师、木匠等职业一起进入了完全不同的领域。
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典型的蒸汽朋克创客致力于修复过时的设备,或者对当代技术进行改造。而蒸汽朋克艺术家则通过创造装置、雕塑和其他物件来体现蒸汽朋克美学。
然而,不管某个创作者的自我定义到底是创客还是艺术家,这两个定义之间都绝不是泾渭分明的。创客有时会制作只是看起来具有功能性的艺术作品或金属雕塑,而艺术家也可能会做出具有实用功能的装饰品。从来就无法保证一边不会对另一边产生影响或光荣的“污染”。
那么时尚算什么呢?时尚是艺术吗?是“创造”吗?还是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时尚的世界实在是过于广阔了,以至于本书必须单独拿出一章来探讨这个话题。蒸汽朋克亚文化的所有领域之间时常出现交集,这些交集往往会带来美妙的结果。
克里斯·库克西的“教会坦克”,综合材料,2008年
艾沃瑞精心编写的故事不仅呼应了蒸汽朋克这一亚文化中特有的将艺术与叙事相糅合的现象,他对“现代设计师和工程师创作的那种贫瘠无趣的东西”的抗拒也点出了蒸汽朋克艺术创作与工业革命的余韵之间的关系。
一个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克里斯·库克西的“教会坦克”。这个作品虽然拥有具备功能性的外观,在作用上却只是一尊雕像,这一点与永恒机器公园非常相似,不过“教会坦克”传达出了明确的社会政治理念,并且十分直接地融合了蒸汽朋克关注的尖端问题。库克西想要创作的是直面这个世界的作品,既不追求融入其中,也不需要通过异想天开的幽默方式对其进行改造。
“创客”和“艺术家”之间如果的确存在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与其说是亚文化的怪癖,不如说更多是基于其艺术与手工艺本源的自然发展。19世纪末出现过数次将纯美术和应用美术结合在一起的尝试,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艺术工作者行会(1884年至今)的建立。根据行会创始人瓦尔特·克莱恩的说法,这些尝试的目的在于强调工艺才是艺术真正的根源。
《约翰·罗斯金》,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爵士作,1853—1854年
许多蒸汽朋克都声称这种亚文化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毫无破绽且清洁无菌的现代技术的不满,而艺术与工艺运动或许同样是一种对工业化进程的反抗。撇开对健康和环境的恶劣影响不谈,工业时代允许制造商通过简化设计来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正是以这种简化为基础,如今廉价的产品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向消费者,但是它诞生的代价是对工人的剥削和缺乏个性的粗糙成品,而这两种现象时至今日依旧存在。
身为工业化的主要抨击者,艺术作家约翰·罗斯金(1819—1900)认为,这种趋势终将威胁到创意和智力领域的自由。在著名的论文《哥特风格的本质》(The Nature of Gothic)里,罗斯金如此写道:
你在这件事情上必然要面对一个严峻的抉择:对于工作的生物(即工人)而言,要么将他们塑造成工具,要么就把他们看成人。这二者是不可能兼得的。人类原本就无法像工具一样精准地工作,无法在所有行动中做到尽善尽美。如果你希望人们实现那种精准,希望他们的手指能够像齿轮一样测量角度,双臂像圆规一样描画曲线,那么你就必须剥离他们的人性。他们灵魂中的全部能量都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描绘完这一系列遥远却详尽的图景之后,罗斯金话锋一转,回到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敦促读者“环顾自己置身的英国房间”,控诉着房中那种死一般的完美正是奴役工人的证据。罗斯金狡猾地请求读者重新审视“古老大教堂的正门”,那些雕塑体现出的无知或许曾经无数次让我们露出嘲讽的微笑:“请重新审视那些丑陋的哥布林、形状潦草的怪物以及僵硬的人像,但是千万不要嘲笑它们,因为那是一锤一凿敲打这些岩石的工人生命与自由的象征。”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相似之处再明显不过了:蒸汽朋克试图拒绝没有灵魂也没有特色的现代科技——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一切——并拥抱维多利亚式机械在创意和技术上的起源。它同时寻求着修复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创伤。这并不能说只是一种对阶级主义、种族主义和剥削进行粉饰的冲动——虽然这一切的确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分——这种冲动实际上是进步的,它的诉求是以积极而肯定的态度对早已死去的过往进行回收再利用。与此相似的是,罗斯金的运动旨在回归他无比珍视的中世纪工坊中的那种创作自由,同时也抗拒着比维多利亚时代情形压迫更重、更加不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这两种情况下,创造力革新都是为了带来创新。
或者,正如蒸汽朋克的忠实拥趸及Boing Boing网站的创始人科里·多克托罗夫所说的那样,蒸汽朋克“抬高了机械,同时贬低了人类创造力的机械化”。因此,艾沃瑞的信条能够与眼下这一代蒸汽朋克创作者产生共鸣自然一点都不奇怪了。这其中就包括肖恩·奥兰多——蒸汽朋克树屋和射线枪哥特火箭太空船等代表性装置艺术背后的核心人物。
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单纯对用完即弃的艺术和消费品感到不满,因为它们原本就是经由纯粹的重复和生搬硬套的消费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所以,为了“解毒”,我们会对把关怀、设计以及艺术以更持久的方式运用于生活的另一个时代抱有期待,我们会被不甚常见的意识形态吸引。现代设计有时太冷酷、太精确了,它过于隐晦,以至于在美学层面难以亲近,它是光滑柔和、全无接缝的极权主义。
约翰·罗斯金的《论艺术与生活》(企鹅图书,2004年)
这一点同样与罗斯金的号召不谋而合。在罗斯金的影响下,英国涌现了一批手工艺学校,比如费列克斯·萨摩利艺术产品公司。学生们会在这样的机构里学习制作各种精美的家居用品,比如装剃须膏的小碗之类的——如同艾沃瑞的提醒:“在过去,工程师原本是艺术家。他们制作的东西美丽又巧妙,并且有很多只具备单纯装饰性的元素。”这种传承留下的遗产便是技术与创造的冲动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