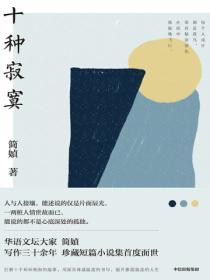她想起家乡路边常有玉兰树,
开出一阵香风,
此刻看到玉兰花竟有莫名的感动,
好像有人带讯息给她。
1
她下车,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一手扶住路边灯柱,一手压着胸口,猛然一股酸刺从胃部喷泉似的涌上喉头,五脏六腑都拉扯起来,搅得她浑身发软,止不住呕满一嘴酸水。她忍住晕眩,勉强移动正在发冷的身子,赶紧从手提袋拉出几张卫生纸捂紧嘴,跑到小巷拐角处,对准水沟,哗啦啦大吐起来。
早餐吃下的面包牛奶都化成一摊浊液泄洪似的冲下。蹲在地上,身子又冷又软,呆呆地望着沟里浊黑的水映着乱发及头上那方破碎的天空,好一会儿才擦掉眼角泪水,嘴里的腥酸却怎么也吐不掉,不死心地用力磨搓,把嘴唇都擦得干白死灰,沾着卫生纸碎屑。她勉强撑起身,走了几步又站住,拿不准要往哪儿走,眼睛来来回回兜圈,像两只迷途小鸟困在暴风雨中。
周一早晨,车辆人流特别汹涌,尤其是赶着上班的摩托车,红灯尚未转绿,连一秒钟也要抢,一群饥饿鲨鱼似的向前冲刺,尖锐声划破清晨最后的宁静,留下漫天臭烟。城市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任何一个没睡饱的人站在路边都会觉得前途渺茫、人生无望。公车站牌旁依例聚了一堆人,年轻的年老的,各等各的车。公交车驶来,停下、开门,下来几个吞进几个,关门、开走,无情无义的样子。这班开走,另一班驶来,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无须交谈。除了一两班行经医院学校市场的公交车搭乘的人较多,难免在上车时出现推挤,其余的看来还算平和,好像要去的地方都是不得已的,早到不如晚到,晚到不如不到,不到不如从来不知道。
她站在路口,也是一副不得已的样子。附近陆续响起拉铁门的声音,打呵欠的年轻小店员拿着扫把挥扫,不知在扫垃圾还是残梦。睁着像两只迷途小鸟的眼睛,她看着这些,尤其多看几眼那个年龄与她相仿、披散一头长发的扫地小妹,猜测她应是刚到这家店没多久,一面扫地还伸手巡看粉红色指甲,生怕漂亮指甲被灰尘玷污般,模样像憋一肚子闷气心不甘情不愿。要是老店员,凡事照规定,老板怎么说就怎么做,别说扫地,就是叫你刷马桶也得面带笑容认命地刷,否则遭骂:“不甘愿啊,奴才命不要给我摆大小姐脸,有才情去做少奶奶呀!”
她听过老板娘对一个挑剔工作分配不合理的女同事骂这种话,那人说要忍到拿了年终奖金才离开。她羡慕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长发小店员,看起来她的字典很小本而且没有“忍”这个字,说不定今天要是老板娘讲话稍为不客气,她翻个白眼立刻走人,邀朋友逛街看电影吃夜市,反正家里不看她的薪水袋,自由自在。而她,现在最缺的就是自由。这阵子以来,觉得头顶上有一团乌云阴魂不散地罩着,厚云越来越低,快要变成铅块,非把她压成肉饼不可。
红灯亮起。她站在路旁,不自觉地拉了拉稍嫌厚重的格子毛料外套,这是同事穿不下给她的。便宜的东西毕竟不耐洗,格子上结出拈也拈不完的小毛球,犹如每一天看起来跟昨天没什么不同、其实暗地里长出的新烦恼,加总起来就是一年份的缭乱。她拂着几个月前烫的现在已炸开的卷发,重新把发夹夹好,露出这阵子常常泡在泪水里以致微肿的瓜子脸,刚才那阵大吐把原本素净的脸逼得更苍白。她忽然把发夹拔掉,让发丝稍稍掩去半边脸,好似现在挂起帘子,外头的人看不到屋内秘密。绿灯亮了,她把外套往下拉直遮住肚子,双手插进两边口袋,驼背走路,整个人透着不应该出现在刚过完二十岁生日的人身上的瑟缩与沉重。
对面马路挂了一排争先恐后的招牌:银行、邮局、旅社、商店、理发厅、平价自助餐店及小吃摊。至于招牌最大的还是那几家私人诊所,除了一家牙科,其他都是妇产科。这里是滚滚烟尘的老商区,主街道内藏着一条长巷,走进去是宽阔的传统市场,像产道与子宫的关联。大马路上货车、摩托车忙碌进出,买菜的路过的办事的看病的人川流不息,将一条旧旧脏脏具历史风尘的老街道踩踏得更凌乱,但在这个把各种需求摊开于太阳下任君选择的地方,乱才让人有安全感。那些偌大的妇产科招牌悬在半空中,既崭新又扎眼,那么干净反倒让人无法掩藏。
她第二次到这里。有一回在自助餐厅吃饭,背后两个大嗓门妇人嚼舌根,提到某个女人惹上感情麻烦事后来去“XX街那边的妇产科处理”。她记住街名,也记得她们讲“处理”时压低声音的神秘感,好像那里是下水道内蒙面人聚集施行妖法的地方,很忌讳,不可在光天化日下提。
现在,她站在招牌最老旧的“钟妇产科诊所”前,假装在等车,其实她的回程车站牌还得再往前几步才是。诊所位于巷子口,过了巷子是一家“新星西点面包店”,这是她选择这家诊所的唯一理由,不,唯二——老旧表示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事不会拒绝人,而面包店提供很好的掩饰,毕竟从外人看来,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子去买面包的需求大于进妇产科诊所。还有,父亲面摊前面那条路叫新生路,同样有个“新”字,而面包面条都跟面粉有关,她心里觉得一脚踏在家乡路上,有个依靠。
不知何时,旁边站着一个老头,抽着烟,眯眼邪邪地打量她。她脸上露着被窥视的紧张,仿佛自己是**的,回避地转身,刚好瞥见诊所门口那道墨色自动门映着自己的身影:烫短的头发包覆着脸,双手插在口袋里,黑长裤自顾自地直下,把上半身挤得好臃肿,像被丢弃在路边的淹过水的枕头。她巡视左右,确定没人看她,安心地退到墙边斜靠,还把手提袋搁在前面,却又忍不住瞄四周一眼,好像到处都有间谍监视。她的视线落在巷子口,正巧看到面包店后门闪出一条年轻男子身影,将大包垃圾塞入桶内,背对着她抽起烟来。这么冷的天只穿一件短袖,瘦瘦的身影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可那烟味让她反感,年轻男子加上烟味的记忆像蛇盘绕脑海,她恨不得把头砍下来像切除哈密瓜发烂部分把那块记忆切掉。即使要死,也不要带着烂记忆一起死。想到这里,眼眶红起来。
门“哗”一声开了,走出一位高挑少妇,像小姐模样,正往皮包搁下一包药,走几步,又拿出药包一面走一面看,头也没抬,拐入巷子不见了。她有一点宽心感觉,注意到那小姐的洋装显出微微的半圆,大概跟自己一般年龄吧,只不过高了一些。
有一班车来,正是她前面站牌的车班,许多人上车,有人嫌挤,宁愿等下一班。她想,不会有人注意她的。忽然走来一位妇人,腆着大肚子,走路摇摇晃晃的,一位瘦高男人搀着她一起进门。这次她瞧见门里正好有个护士走过,赶紧过来搀扶那位妇人还招呼了几句,这让她觉得一下子松了口气,好像人家招呼的是她。门关的刹那,她看到里面有一个小窗口,写着两个红色大字“挂号”。
“挂号”,这两个字攫住她的脑子。她打开手提袋,摸着袋底的信封,厚厚的,早上数过一次,临出门又多放几张进去,她想,应该够的。可是又不免担心,如果不够怎么办?会不会被赶出来?想得心脏都撞得发疼,眉头锁得死紧,低低地叹气,眼眶又湿了。抽出卫生纸擤了鼻水,揉在手里不敢去丢,明明不远处就摆着一个垃圾桶。
有个妇人走到站牌旁,瞧了老半天,发现她,好大一声:“小姐,借问一下……”没等说完,她猛摇头,人就躲开,本能地进了面包店,把架上的吐司面包糕点巡过几遍差不多可以背出品项,才夹两个菠萝面包结账。也许真的饿了,咬一口竟觉得从头香到脚,好像被谁紧紧拥抱,回到光天化日的世界来。她不好再杵在诊所门口,慢慢地往前踱,走到该搭的回程公车站牌才停下。吃完一个面包还想吃第二个,又怕吃多会吐,留待晚餐吃吧。那现在呢?正当她心里七个水桶往妇产科诊所**、八个水桶往回家的路上晃时,却见回程的那班公交车驶来,怎么办?脑中一片空白,世界等着她做决定,一秒两秒……忽地一股力量推她上车,当司机关上门,她竟有解脱之感。
车开动,却后悔。大老远来买两个菠萝面包,今天又白跑了。
一小时后,回到那间四五坪小房间,她倒在**哭起来,脸蒙入被子里,咿咿呜呜一声高过一声,猛然一阵酸又涌上喉头,跑到浴室去呕,呕到胃抽搐,干咳一阵,眼泪、鼻水一起滚落。早上出门前鼓起的勇气都消失了,如今又恢复一团烂泥。她沉沉睡去之前喃喃自语: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我求求你,不要让我醒来。
2
“这房间不错吧,看得到天空。”丽香说。
十个月前,大年初六开工日前一天,她提着一口旧皮箱随丽香踏入繁华城市。丽香是远房表亲,大她四岁,介绍她到同一家成衣厂当作业员,还帮她找到这间除了漏水有霉味、嘈杂多油烟之外房租很公道的栖身处。
确实看得到一小片天空,有时铁灰像被大鸽子展翅遮着,有时水蓝好像家乡的夏日海洋。她很满足,能够脱离面摊生意到大城市赚钱,替父母分担,让她兴起成就感。母亲的厨艺不错,碍着一条瘸腿不能久站,只能在家备料做卤味,全靠身体不佳的父亲一人扛那小摊,料想弟妹们放学应会去帮忙,然而那毕竟是靠体力在风中雨里、水中火里讨生活的艰苦事,父亲总有撑不住的一天。一家担子她挑定了。城市给她一条活路,窝在小床铺上,想家的泪水多过闷热天气流的汗水,她很满足,有时也做起买一栋四室两厅两卫房子的梦,虽说那条路在哪里还不知道,但美梦不就是为了给“不可能”一巴掌叫它变成“可能”而存在的吗?
窗口吹进冷流让她醒过来,还活着,观世音菩萨不救她。躺在**瞪着天花板,那盏日光灯污黑得几乎要掉下灰尘块。天色阴沉,房间又暗,更觉得那盏灯仿佛要化作魑魅来攫她,一闭眼真的有一团黑影逼近,斥骂她是不要脸的人,干出这种事来,对得起父母吗?甩来两个巴掌,是她自己的手!惧得她不敢再闭眼。塑料衣橱上那口旧皮箱里面是空的,想到还有两个月就过年,可以回家去。她还没有回去过,从出来到现在。她曾想过给家人带些礼物,把皮箱装满,那一定是很甜蜜的沉重,说不定重到把手扭伤,她甘愿。但现在皮箱是空的,空得像一口棺材。
墙壁上挂了几件毛线衣和一条老爷裤,不是她买的,是丽香的旧衣送给她。只有那条米黄色褶裙是她买的,这辈子第一次到百货公司帮自己买衣服,感觉像地下室奴婢变成花园里的时髦小姐。那是唯一一条像样的裙子,她很喜欢穿它,只有穿那条褶裙时她才觉得自己是美丽的,可以在阳光下边走边唱歌。同事也说她皮肤白身材瘦,配上米黄色,更细致娇美。第一次穿去上班时,裁剪部的小王对她吹口哨:
“春如,水当当喔!”
丽香瞪了小王一眼,他俩是一对,大家都知道。
跟小王同组叫阿铭的,跑到她身边笑嘻嘻地说:
“小如,晚上请你吃饭!”
她们说,她打扮起来根本不像二十岁。她为此还去烫了一次头,让自己成熟些,好像运气会变好。
她现在不喜欢那条裙子,甚至想撕碎它。那是她唯一喜欢的裙子,选了很久才决心买。上班、逛街都穿它,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都穿,包括那一天。她恨恨地想撕碎它,撕碎那一天。
两个月前,阿铭邀她:“我请大家吃饭,永和的涮羊肉你一定没吃过。中秋节连假,你第一次在外头过中秋吧?”
“你们去就好,我还是回去。”她对这个时常借机在她面前晃的人保持戒心。
“有什么关系?都是外地人,出门在外互相照顾,再说,我也把你当妹妹看待,我妹妹都比你大一岁。”
“不好啦,你们去就好了。”
“小王、丽香也要去,你一个人回去啃月饼?”
“她也要去?”
“是啊,就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团圆团圆。告诉你一个秘密……”阿铭凑近她耳边,“我打算做到月底,先别跟他们说。”
“团圆”这话打动她的心,在外人像浮萍,餐桌上冒烟的四菜一汤都是梦中的事,更何况他将离职,说什么也该顾念这份情谊。
永和闹市到处亮晃晃得像白天,把她撩得很兴奋,走路像踩在云端。她穿着那条米黄色褶裙跟在丽香后面,丽香也穿得很漂亮,还化了妆,高跟鞋“叮叮”地响着。
除了涮羊肉,还有海鲜。阿铭带来一瓶洋酒,很漂亮的瓶子,她第一次看到。他们劝她喝一些,她不要。他们说不会醉,甜甜的,她还是不要。丽香说没关系啦,过节嘛意思意思。小王弄来一瓶白葡萄汽水,让她们掺着喝,说这样后劲才不会那么大。她看丽香喝,也就喝了。“干杯!”两个男人灿笑着,酒杯一举高,节庆的感觉都出来了。她放心喝,甜腻带点辛辣,喝第一口觉得甜,第二口开始有些扎喉咙,等到她喝完那杯汽水掺酒,打一个响嗝以后,全身便热烘烘起来,甚至火烧似的烫。
她说:“是不是地震?好晕哟。”他们大笑。
屋子开始旋转,她想舀汤喝,没舀到。她被搀着站起来,围着围裙的老板娘脸好大,街道弯弯曲曲的,好像一条大蟒蛇,而且是凹凸不平的大蟒蛇,每走一步就踩进一个窟窿。蒙眬中,好像回到老家,那次邻居阿嫂坐月子,她去送礼,母亲吩咐她:“阿婆若端麻油鸡给你吃,你要吃光,阿婆下次才会抱男孙……”她吃光,回到家倒在**睡到天黑。母亲的话、阿婆的笑容,丽香的声音、阿铭的话语,在她脑海交叠追逐,牵着她一下子往天边**去一下子跌落地面。她记得自己吐了,吐完说想睡觉,仿佛被塞进一个密闭箱子,掉入大窟窿不断地坠落,烟味浓浊,是火烧吗?黝黑的影子紧紧包围她,有个东西重重地压着她的头、胸口、手和脚……她迷迷糊糊地感应到火烧后的虚脱与疼痛却无力判读,只要躺平就好,沉甸甸的便什么感觉都停止了。
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宿醉像身体遭小偷,一阵晕眩搅得她头痛欲裂、浑身无力,待坐起,怎有散不去的烟味?到浴室洗澡,**不寻常的闷痛敲醒她的脑袋,她看到**沾着铁锈色血污,全身被电击般惊跳起来,这不是生理期提早来,恐怕是被……她奋力抵挡那个强烈的念头袭来却无效,跌坐地上前脑子被“强暴”这两个字狠狠地敲了一棍。
她打电话给丽香,问昨晚怎么了。
“你啊,我会被你气死,吐得跟猪一样。”
她是不能喝酒的,吃带酒的东西都会晕。
“我跟小王要去看电影,只好叫阿铭送你回去。你要谢谢阿铭,好好一顿饭没吃完就结账,白花钱。”
她缩在**,一直发抖。
连假后,阿铭没进工厂,离职了。
她问到他的租处电话,每晚到楼下打公共电话,没人接就是没人接。有一天终于通了,接电话的人说,这人已经不住这里,你别再打。她不死心,去人事室谎称欠阿铭钱要寄还他,查到他家住址。高雄县乡下,那是什么地方?就算她有胆拿刀子也杀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该拿刀子是一个半月后的事,生理期迟迟不来。顾面摊时最恨生理期,常搞得狼狈。她从没像现时那么渴望看到经血,一滴就好。恐惧袭来,她是翅膀被反折的鸟,头顶上一条绳子系一把刀,落下就是砍头。墙上挂着那条米黄褶裙,她没再穿过,褶线都爆了,皱得很厉害。她扯下褶裙,使命地撕,用尽全身力气撕,连手都颤抖,却怎么也撕不破。像一根针扎进带血带肉的脑心,她拼命地捶床,痛哭起来,猛然一个翻身,拿枕头扔墙上褶裙,连棉被也扯起来丢,半杯水也一起飞抛,水把褶裙泼湿一角,像那天的血污,抓起梳子再丢,把木板墙打得像要溃倒。一切静止,大事定了。
跑去西药房买泻药吃,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让肚子里的东西全部泻下便会没事。泻了好久,在厕所坐到脚软,一面诵念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一整天没吃东西,想站起来没半丝力气,几乎爬着上床。她抚摸腹部,似乎不再那么凸,嘴角露一线微笑,喘息着任时间在她的晕眩中流逝。
熬了一个多礼拜,每天向观世音菩萨祈求,这一带的宫庙也求了,月经依旧没来。她想起女人们进进出出的妇产科诊所,害怕到牙齿打战,她想:“人家会说我是一个无耻的贱女人!可是我没有错,我被欺负了,被欺负也是我的错吗?”
“你最近怎么搞的,老出错。”丽香板着脸把她交上去的货退回,叫她重新车线。
她虚弱得头昏眼花,低头拆线重车,什么事都不能让丽香知道,她一知道,整个亲戚圈全知道,叫妈妈的脸往哪里摆?她一想到妈妈跛着腿在厨房盘面条、炒油葱酥、卤黑白切,从早到晚走不出那间酷热小厨房,心就揪紧,把涌到喉头的话语像吞石头一样吞下去,就算吞刀子也要吞,没别的选择。
饥饿拨醒她的理智,剩下的那个菠萝面包三两口吃了,止不了饥。冬冷天气,让人特别想喝点热腾腾的汤。
此刻应是父亲最忙的时候,四张桌子一定都满座,她恨不得飞回去接手,让父亲喘口气。如果有一间自己的店面,这是父母的梦想,如果有一间自己的店,不必餐风淋雨跟人家抢地盘该有多好。
她出门觅食,一路这么想,遥远的梦想让她移开注意力,似乎也灌进来不一样的心思。进面馆点了阳春面,面端来,她一眼就知道这碗面除了烫,其他的都不及格。她遗传母亲的厨艺本能,一眼一尝就能抓到八九分,只是没有立足的半寸地。
一个穿小学制服的小女生提花篮进来兜售夜来香、玉兰花,傻笑着招徕,说出来的话像一团麻糬不清不楚,是个可怜孩子,没人理她。她想起家乡路边常有玉兰树,开出一阵香风,此刻看到玉兰花竟有莫名的感动,好像有人带讯息给她,是什么?她还不知道,大概跟未来有关吧。她不忍那女孩空手,买了一串。这种天气还在外讨生活的人要得不多,不过是想活下去而已。她带着一串玉兰花在回去的路上下定决心:“我要得也不多,活下来而已。”仿佛自言自语又像说给肚子里的某个存在听:“做人很艰苦,不要来做人。我没有能力生你,对不起!”
她打电话给主管,明后两天还要请假,同意要请,不同意也要请。要把她开除也没关系,工作再找就有,要做牛不怕没犁可拖。
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她发誓:“我也要翻过这一页。”
3
搭同样的车,还是在那一站下。同样是昨天那套衣服,好像时间暂停,只不过她去攀了一趟悬崖,等她回来,时间继续往前走。
她站在“钟妇产科”门口,九点才看诊,还有半个钟头。等车的人不多,她比较放心些。那道墨色自动门被铁卷门遮住,一动也不动,安静得像永远也不会开似的。她盯着地上那块鬃毛擦板,已经磨秃了,布满灰尘泥土,不知有多少女人的鞋印踏过。今天,她也要踩上去,用力擦鞋底,把过去擦干净。
既然需等待,她本能地往“新星面包店”逛去,怕晕车今早还没吃东西,也许还是买一个最爱的菠萝面包吧,把它当作唯一知情的好朋友,躲在胃里给她力量,陪她渡过这一关。
她推开玻璃门,门上小挂铃响起,叮咚叮叮咚,响得特别清脆。
店内没人看着,正在迟疑间,从柜台后面的烘焙间走出一个瘦高男子,穿短袖、围着围裙,第一眼看起来严肃,好像笑容是很昂贵的东西,不可以轻易拿给人看。
但第二眼,他脸上有块红胎记联结到不算远但必须翻山越岭的过往时光。他俩脸部表情同时牵动、**开,眼睛睁得大大地盯着对方,嘴角不自主地绽出昂贵的笑,同时翻山越岭。
系围裙的面包师傅笑着说:“你不是面摊那个春如吗?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我跑来这里做什么?是喔,我跑来这里做什么?”她笑着重复他的问话两遍,像个傻瓜,记起这个常常跟朋友来吃面要不就是带弟弟妹妹来、每次都点炸酱面配贡丸汤的人。
“你就是那个阿郎对不对!”春如高声指认,叫出他的名字。时间在这时乱掉了,窜成旋涡。
她打算告诉他为什么在这里,才一开口,话还没说,眼泪先流下来。
阿郎站在她面前,问:“发生什么事?”
时间旋出一朵水淋淋的红花,九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