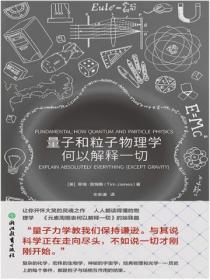第6章 盒子与猫
丹麦路径
随着观察越来越多、方程式越来越准确,两个阵营诞生了。对于如何处理这种离奇的现象,双方各执一词。
第一个阵营是想要了解量子力学本质的哲学家,比如爱因斯坦、薛定谔和德布罗意。
第二个阵营是想要不考虑它的真正含义而直接使用量子力学的数字玩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哥本哈根工作的玻尔与海森堡。
海森堡在1930年写了一本书,叫《量子论的物理原理》(The Physical Principles of the Quantum Theory),书中总结了多年来他与玻尔一直在酝酿的观点。海森堡称之为“das Copenhagen giest”,字面意思是“哥本哈根幽灵”,尽管“灵魂”或“精神”这样的词更符合他的本意。恐怕量子力学并不能完全证明幽灵的存在,尽管它确实为死而复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请往下看)。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它认为物理学的深层定律与人类经验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理解。
它主张,就像光的颜色可以混合形成白色一样,粒子的属性也可以混合形成一种“叠加态”,在这种状态中,粒子既不上旋,也不下旋,既不存在于此处,也不存在于彼处。它既是一切,也是虚空。
用海森堡自己的话来说:“粒子本身并不真实,它们构成了潜在性与可能性的世界,而非事物与事实的世界。”[1]
粒子并不在乎它们对我们是否有意义,也不会屈服于我们人类的极限,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表面理解。你要么爱上你所看到的,要么尖叫着跑开。波函数以一种半真半假的方式波动,测量改变了它们。关于这个问题再没什么好说的了。讨论结束。
总结
玻尔和海森堡相信这种观点,但令人恼火的是,他们从未阐明所有的细节。有时你可以得出特定的解,但就像量子粒子本身一样,如果它们愿意,就可以让事情变得模糊。下面简单总结了他们二人相信的观点。
不被测量时,大自然处于多种状态(或没有状态),叫作“叠加态”。而在测量时,我们像打苍蝇一样把这种叠加态拍在墙上,迫使它成为某种事物。
薛定谔方程告诉我们可能的测量结果,但在确实发生以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说叠加态“坍缩”成一种状态,就像一个泡泡被戳破那样,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普通版的粒子,有时我们称之为粒子的“本征态”。这是我们在经典物理中使用的方法,但在测量之前,我们必须使用概率波。
我们也不可能预测粒子的波函数会坍缩成哪种本征态,因为宇宙还没有决定。我们只能测量,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玻尔和海森堡夜晚睡觉的方式。
对很多人来说,哥本哈根诠释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它什么都解释不了,只是告诉你要满足于无知。批评家称之为“少废话,去计算”[2],因为它回避了直觉,不由分说地让人盲目地使用这些方程,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而且,哥本哈根诠释所引发的问题也是相当深刻的:
(1)为什么粒子可以处于多种状态或没有状态?
(2)为什么测量使粒子陷入本征态?
(3)为什么结果是随机的?
(4)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知道所有的性质?
(5)如果粒子不遵循简单的经典定律,为什么日常世界会遵循?
哥本哈根诠释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耸耸肩,说:“就是这么回事。”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尤其是爱因斯坦。
够了!
爱因斯坦和玻尔有着复杂的兄弟情谊。他们尊重对方的智慧,却在量子力学上针锋相对。他们在参加的每一场会议中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私下或公开写了很多信,指出对方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在一封写给玻恩的著名的信中,爱因斯坦说他不能接受这样一种使大自然变得随机的理论,并这样结尾:“这个理论说了很多,但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旧理论的秘密。无论如何,我相信上帝不掷骰子。”[3]这里的“旧理论”,是爱因斯坦用来代指无人格的上帝。
海森堡是他们的好朋友。根据他的说法,在听到爱因斯坦坚称上帝不掷骰子时,玻尔这样回应:“我们不应该规定上帝该如何管理世界。”[4]
月亮,美丽的
爱因斯坦之所以反对哥本哈根诠释,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物理学的目的在于弄清楚事物运作的原理。大自然通过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弄清楚。在爱因斯坦看来,当事情变得有趣时,玻尔却放弃了。
亚伯拉罕·派斯是哥本哈根诠释的支持者。在一次激烈的争论中,爱因斯坦指出了测量问题的愚蠢之处,他质问派斯,是否相信不看月亮时月亮就不存在。[5]在哥本哈根诠释中,事物要先被观察,然后才有明确的属性。所以,如果没有人观察月亮,那么严格来说月亮的波函数就是叠加态,同时处于各个地方与各种状态。
问题是,爱因斯坦的反对基于直觉,而非基于证据。仅仅因为我们乐于相信不观察的时候月亮也存在,并不能证明事实就是如此。为什么月亮不会在没人测量的时候消失呢?你能证伪这一点吗?
在玻尔看来,人类思维之所以进化,是为了在非洲平原上寻找浆果,而不是研究高等物理学。我们迟早会撞上一堵墙。一个人想要理解量子力学,就像一个家用恒温器想要理解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007:大破量子危机》(Quantum of Solace)。想想看,让恒温器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去理解《007:大破量子危机》的情节,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些争论逐渐变为了街谈巷议,爱因斯坦开始走下坡路,人们小心翼翼地为玻尔的胜利欢呼。在一些资料里,爱因斯坦被无情地描述成一位大谈着当年科学有多么好的过时的伟人,已经离开了物理学的前沿。
这可能会给人一种满足感,因为人们喜欢知道爱因斯坦也有极限,但实际上他非常了解量子力学。这就是为什么他竭力从中找毛病—他知道量子力学究竟是什么。
薛定谔那声名狼藉的僵尸猫
玻尔把爱因斯坦的上帝骰子和突变月亮视为情绪上的反对,对科学事实没有任何影响。后来,薛定谔决定要挑战哥本哈根诠释的统治地位。
我喜欢想象这样的画面:薛定谔整理领结,卷起袖子,把爱因斯坦从摔跤场上拉下来,在场边一小群啦啦队员的支持下,薛定谔对爱因斯坦说:“退后,阿尔伯特,换我拿下这一场。”
薛定谔决定走一条不同的路,他没有攻击“测量”,而是攻击“叠加”。1935年11月,薛定谔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今天众所周知的“薛定谔的猫”悖论。他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一劳永逸地打击哥本哈根诠释。
想象把一只猫关在密闭的铁盒子里,然后离开一小时。在铁盒子里,一个盖革计数器可以检测旁边的放射性物质是否发射出粒子。我们不可能预测一个小时后是否会发射出粒子,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材料,其波函数表明,该物质一小时后发射出粒子的可能性为50%。
粒子在原子内的可能性是50%,隧穿出来击中探测器的可能性也是50%。现在到了有趣的地方。盖革计数器连接着一个残忍的装置,它能让一只锤子落下来,打碎猫旁边的一瓶氢氰酸。
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可知,粒子同时采取两种选择,即处于原子核内与原子核外的叠加态。因此,锤子既落下了又没有落下,这意味着装有氢氰酸的瓶子既破碎又完好,而猫既死了又活着。如果认真思考哥本哈根诠释,你就必须接受一些荒谬的东西。叠加态一定是错的。
我不知道薛定谔为什么不用飞镖,或者其他让猫安乐死的东西,而是选择在几分钟内通过酸浴慢慢地腐蚀猫。薛定谔真是个怪人。
我也不知道薛定谔为什么选择猫。他的确养了一只叫布尔齐的狗[6],还有人说他养了一只叫弥尔顿的猫[7],但可能是杜撰的。也许有一天早晨,薛定谔正在写论文的时候,弥尔顿觉得应该在他的书桌上排便,所以薛定谔要让它永垂不朽。谁知道呢?
有时候,人们错误地把薛定谔的猫的实验描述成“你不知道猫是死是活,所以你不得不从两个方面思考”。这没有切中要害。
哥本哈根诠释说的是,粒子可以处于叠加态,这意味着任何与之相互作用的物体也可以处于叠加态。打开盒子的时候,你有50%的可能使猫的波函数坍缩成死或者活的本征态,但在打开盒子之前,这两种状态同时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做这个实验是毫无意义的。人们永远不会观察到处于叠加态的薛定谔的猫,因为这就是哥本哈根诠释的观点—叠加态随机坍缩成本征态,你测量的是本征态,而不是叠加态。打开现实世界的盒子,你看到的不是死与活的叠加态,而是要么看到一只活生生的小猫,要么看到一团乱麻并为此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