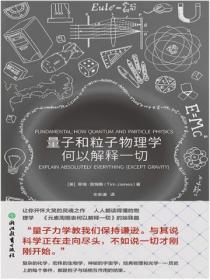第7章 世界是一场幻觉
你看得到我,你看不到我
迪士尼与皮克斯合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及其续集都是关于量子力学的。电影的主角是玩具,当主人安迪看向它们时,它们表现得像普通玩具,可一旦安迪不看它们,它们就“活”了过来。
安迪没有见过玩具的活跃状态,只看到过它们的经典行为。他似乎也从未注意到在每次游戏之间,玩具的位置发生了改变(虽然他很善良,但他并不是最善于观察的孩子)。但如果他仔细观察,可能就会发现玩具的位置每次都略有不同。
粒子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粒子身上移开,那么相比于我们观察的时候,它们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用薛定谔方程猜测它们可能的位置,但永远无法准确地预测每次我们走进房间时会发生什么。
假设安迪开始详细记录每个玩具的位置及每次的状态,他可能开始注意到,只能用概率描述自己观察到的状态。例如,胡迪(1)有90%的可能性出现在安迪上次离开的地方,但也有可能(可能性不为0)出现在房间的另一边,甚至在大楼外的某个地方。
如果安迪属于哥本哈根学派,他会用简洁的数学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他的玩具以每种可能的状态出现在所有可能的位置,直到安迪进入房间,这时玩具的叠加态坍缩成某种经典态。但有一个永恒且博大(2)的问题:当安迪出现在房间里,是什么引起玩具的波函数发生变化的?
在《玩具总动员》中,有一个场景是胡迪向一群玩具解释它们不得不打破作为玩具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究竟是什么?谁决定了这些规则?
如果在安迪的卧室安装摄像头,这些玩具会“活”过来吗?如果有人偷偷地在暗中监视玩具,它们该怎么办?当玩具被其他玩具注视时,它们还能活过来吗?为什么小狗巴斯特不算在内?如果有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怎样?黑猩猩会引起坍缩吗?那个邪恶的孩子西德看到胡迪开口说话而精神崩溃,以至于放弃学业,在《玩具总动员3》中做收集垃圾的工作,这又该怎样解释呢?(仔细看,那个人绝对是西德客串的。)
试图在《玩具总动员》的宇宙中寻找测量的哲学意义是一场噩梦,但在量子力学中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测量问题不仅仅违背直觉,还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是什么使现实成为现实?
人们经常弄混测量问题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测量问题说的是粒子在被观察时选择所处的状态;而不确定性原理说的是,即使观察也无法得到粒子的全部信息。
不确定性原理可以类比为安迪的眼睛有问题,需要特殊颜色的眼镜才能看见东西。不戴眼镜看玩具,他能分辨出玩具的颜色,但图像很模糊。也就是说,他能测准颜色,但测不准形状。如果他戴上眼镜,玩具就变得清晰,但通过有色眼镜他就看不清楚颜色了。他可以选择测量颜色或形状,但永远不能同时测量。
找一个朋友
1932年,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决定拆解双缝实验,对各个方面加以数学分析,从而确定是哪个阶段导致了波函数坍缩。测量过程的某些方面一定是特殊的。
他研究了正在生成的粒子,研究它如何离开发射器,如何接触狭缝,如何穿过狭缝,如何出现在另一侧等,并计算了相关的波函数。最后,令他大为恼火的是,他发现没有哪个阶段是特殊的。量子力学实验的每个部分在物理学上都是等价的。[1]
这极大地损害了哥本哈根诠释,因为既然不能证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波函数坍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坍缩呢?玻尔和海森堡耸耸肩,爱因斯坦挠了挠他的卷发,薛定谔关上了卧室的门。我们最好不要问里面发生了什么。
最终,匈牙利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就测量问题提出了引起最广泛讨论(最不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他扩展了薛定谔的猫实验,把科学家本人纳入其中。
我们把猫关在密闭的盒子里,它处于一种死与活的叠加态;当科学家朋友打开盒子,会发现猫坍缩成一种本征态或另一种本征态。两种可能性各占50%。现在假设实验是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进行,而维格纳等在房间外。
如果认真对待哥本哈根诠释,那么粒子既触发了探测器,又没有触发探测器,既杀死了猫,又没有杀死猫。在维格纳看来,他的科学家朋友会打开盒子,同时发现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维格纳的朋友也将处在叠加态,既看到一只活猫而感到如释重负,又看到一只死猫而感到惊恐万分,寻找刷子和抹刀。只有当维格纳打开实验室的门,弄清楚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后,他朋友的波函数才会坍缩。[2]
但这是荒谬的。维格纳的朋友不可能处于叠加态,因为从来没有人观察到这样的人类大脑。在任何时候人类都不可能同时观察和不观察。意识总是处于本征态。因此,维格纳说,意识一定是坍缩的波函数。
根据维格纳的说法,在谈论测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一个正在观察的有知觉的头脑,因为头脑不存在叠加态,所以它观察到的粒子也不存在。
需要明确的是,维格纳并不是在量子牛油果(3)领域获得网络文凭的小人物。他获得过诺贝尔奖,是众所周知的追求实际的物理学家。他并不喜欢把意识引入辩论中,但他别无选择。
小心谨慎
意识在过去是一个谜,现在仍然是。但由于实验的其他部分都可以被描述,所以波函数坍缩只可能发生在有意识的头脑中,这也是我们没能完全理解的地方。
维格纳的解释暗示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事情。首先,这意味着我们的头脑对粒子有影响,而不是粒子对头脑有影响。
其次,这意味着在数十亿年里,整个宇宙一直处于叠加态,直到有意识的生物进化到可以观察它。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早期的某个时候,由于人口稀少且分布密集,肯定存在某个时候没有人看月亮。这时月亮会突然消失吗?如果这样,为什么地球没有在太阳轨道上失去平衡而倾斜,然后也消失呢?
是不是总有什么东西盯着月亮不让它消失?有没有可能有一颗至高无上的头脑时时刻刻都有意识地观察着宇宙,防止它在没有其他人观察的时候失控?
为此,这里有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打油诗,主题是观察,据说作者是哲学家、神学家罗诺尔·纳克斯:
曾有个年轻人开言道:“上帝
一定要认为太稀奇,
假如他发觉这棵树
存在如故,
那时候却连谁也没有在中庭里。”
答:
“敬启者:您的惊讶真稀奇!
咱时时总在中庭里。
这就是为何那棵树
会存在如故,
因为注视着它的是——您的忠实的——上帝。”(4)
神奇的头脑
维格纳的意识论非常勇敢,但很自然,它被误解了,尤其是被新纪元运动(5)的某些成员误解了。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所谓的“量子灵性教义”,但我可以介绍一二。
当你在网络上检索量子力学时,会看到一些关于科学、晶体、锻炼、左翼政治、佛教、印度教、素食主义、瑜伽、自我认同和冥想方面的文章。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有趣的话题,但它们与量子力学没有任何重要的联系。
量子灵性论是“实在性哲学”介入的地方,因为许多精神导师声称,既然意识能够影响现实,那你就可以通过思考使事件发生。在这里我对他们的教义稍加改写,但由于他们的理论涉及量子力学,我想这是公平的。
在这一点上,我需要说清楚的是,灵性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都会接触到。事实上,量子力学的许多奠基人都是极具灵性的人(尤其是薛定谔与泡利)。但我们必须在是与非之间画一条线。
观察可能会引起波函数坍缩,但并不能决定我们最终处于哪种本征态。这仍然是随机的。
在薛定谔方程中,每个可能的本征态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概率幅”,它告诉我们现实的可能性。最终的状态是由可能性决定的,而不是由测量决定的。
尽管我们可以说意识使一种本征态具象化,但绝不可以说我们能影响这个过程。你是现实的观察者,但你不影响现实在量子意义上的形式。如果想让世界更美好,恐怕你还得按部就班,做一个好人。
过去,维格纳版的哥本哈根诠释一直是辩论中有趣的部分,它很好地解释了猫的悖论,因为是猫的意识使它自己的波函数坍缩。但扪心自问,这仍然是一个骗局。
它说我们不知道波函数是如何坍缩的,也不知道意识是什么,但这两种东西以某种方式把我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它又一次把宇宙的奥秘推向黑暗的洞穴,说:“答案就在这里,但不许偷看!”
大脑是神秘的,但神秘并不意味着“违背自然法则”,它只是意味着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细节。在解释量子观测时,我们没有理由援引超自然现象,却有相当多的理由忽略它。
(1)《玩具总动员》的主角,一个牛仔玩偶。—译注
(2)原文是“infinity and beyond”,出自《玩具总动员》中巴斯光年的台词“To infinity and beyond!”(飞向宇宙,浩瀚无限)。这里采取直译。—译注
(3)在水果摊挑选牛油果时,你可以通过捏一捏来判断它的成熟程度,从而选择软硬适中的牛油果。但在你捏一捏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牛油果的软硬,也就是“测量”使“状态”发生了改变。—译注
(4)本诗的译文参考了马元德的译本,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马元德译。—译注
(5)新纪元运动是20世纪60~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社会与宗教运动,主要是指把个人化的信仰与传统的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译注